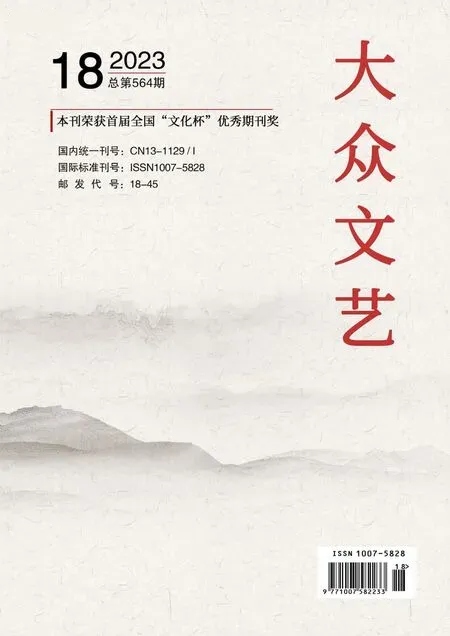培養生活的藝術家
——藝術即治療的特點和意義
薛 勁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教育與管理學院,浙江杭州 310000)
一、藝術治療
藝術治療是協助個體進行藝術創作,通過創作過程中的探索與表達,增進個體身心健康的一項專業。[1]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對藝術治療的定義雖有不同,但存在以下共同點:藝術治療是一門專門的學科;藝術治療是心理學和藝術的交叉學科;藝術品是創作者人格與心理狀態的表達;藝術行為會導致創作者的心理狀態發生變化。
藝術治療發源于20世紀初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論,經南姆伯格、烏爾曼、克萊曼和羅恩菲爾德等早期藝術治療人物的發展,在60年代的西方成為一種專門的心理療法。[1]同時英國和美國成立了相應的行業協會,以推動藝術治療的發展。中國大陸的藝術治療研究最早見于1994年龔鉥發表在《臨床神經醫學雜志》上的論文——《藝術心理治療》。在中國大陸研究藝術治療的學者中,孟沛欣的影響最為突出。2004年,孟沛欣發表了有關在精神分裂癥患者身上應用藝術治療的博士論文。其研究取樣龐大、資料翔實,有力地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在CNKI數據庫中以藝術治療為主題進行檢索并分析檢索數據可見,中國大陸的藝術治療研究在2004年之后呈現繁榮發展的勢頭,研究數量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文末圖1)。

圖1
大陸的藝術治療研究有兩個共同點,即治療工具以繪畫為主,治療對象以特殊人群為主。在CNKI數據庫中以藝術治療為主題,檢索被引量最高的前50篇文獻。其中在題目中明確為美術或繪畫治療的有21篇,占比42%。剩下的文獻雖以藝術治療為題目,但方法上仍然是繪畫治療。治療對象集中在孤獨癥或精神分裂癥患者及殘障兒童等,都屬于特殊人群。
然而,藝術不只有繪畫一種形式,藝術治療所能服務的對象也不能僅局限于特殊人群。廣義上看,藝術可按時空維度分為以下三種形式:在空間上展開的藝術(如繪畫),時間上展開的藝術(如音樂),和在時空上都展開的藝術(如電影)。[2]因此,本文中所指的藝術治療不限于繪畫治療,也包括音樂治療,戲劇治療,電影治療等其他藝術形式。伊迪絲克萊曼指出,藝術治療的最終目的是將人人都培養成“生活的藝術家”。[3]因此,藝術治療所服務的人群不應僅局限于特殊群體。
二、藝術即治療與藝術心理治療
藝術治療在發展中形成了以下兩種取向:
第一,以南姆伯格為代表的藝術心理治療(Art Psychotherapy)。這一取向強調咨詢師先通過受訪者的藝術創作完成對受訪者的洞察,再以動力學療法或認知行為療法完成治療。藝術僅作為治療師診斷與受訪者表達的手段,最終的療愈才是目的。
第二,伊迪絲克萊曼(Edith Kramer)在兒童藝術治療工作中發展出藝術治療的另一取向——藝術即治療(Art as Therapy)。[1]“藝術即治療”認為藝術創作是治療的主體,藝術本身就是療愈性的。該取向一方面源于精神分析學派的防御機制理論,即藝術創作作為一種防御機制,是潛意識中沖突的升華。另一方面源于克萊曼自身的藝術理論,即藝術是治療的主體與本質。這一療法中的藝術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療愈是受訪者進行藝術創作的伴隨狀態,但并不是最終目的;旨在培養“生活的藝術家”,而非“完全健康的人”。
伊迪絲克萊曼認為現代生活是無法剝離藝術而存在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被稱之為生活的藝術家。但缺少審美和創作經驗使得人們不能在生活中很好地運用藝術治愈自己。因此,“藝術即治療”試圖將每一個人培養成“生活的藝術家”,使他們在生活中自愈。此外,伊迪絲克萊曼認為不存在所謂的“病人”,所謂的“病人”只不過是和所處的文化環境對“正常人”的要求有所沖突而已。一些影響世界的天才正是因為他們的超越性而和當時的文化格格不入,從而被視作“病人”。因此藝術即治療不強調“完全治愈”,以保留人們超越時代的可能。
這兩類藝術治療都基于精神分析理論,但有著不同的目的和偏重。前者旨在“治愈”受訪者,強調診斷與心理分析;后者旨在培養“生活的藝術家”,強調治療師和受訪者平等地互動。克萊曼抨擊藝術心理治療(Art Psychotherapy),認為其強調對藝術作品的認知和言語處理,不過是認知療法的變形。[3]而藝術即治療(Art as Therapy)強調作者通過藝術創作對內心沖突的升華,及對自我(ego)的加強。[3]藝術心理治療中藝術不過是療愈的工具,其本質仍是心理治療。后者則強調藝術既是主體也是本質,既是方法也是目的。本質上更接近以自我實現為目標的美育。
誠然,藝術心理治療(Art Psychotherapy)看到了藝術作為治療手段的優勢,但并沒有注意到藝術本就是生活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就算不以治療為目的,普羅大眾仍然需要藝術生活。事實上,正是普羅大眾對藝術體驗的渴望促成了藝術治療這一職業的興起。[3]藝術并不僅存在于拍賣會與美術館,藝術充斥著現代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從飲料包裝到網頁上的圖片與文字,以及被賦予各種意義的自然景物,都屬于現代人日常生活中藝術創作與鑒賞的一部分。現代生活既然無法剝離藝術存在,培養每一個人成為生活的藝術家就成為可能。
Hartz等人在對青少年罪犯自尊的研究中對比了兩種治療方法。[4]他們發現兩種方法在塑造自尊的效果上沒有顯著差異,但藝術即治療能更快地促進治療團體的形成,藝術心理治療能更好地干預行為。這可能是因為藝術心理治療更貼近認知行為治療,更能促進治療對象行為的積極變化。而藝術即治療對藝術的側重能喚醒參與者對創作的渴望,更容易讓他們打開心扉以促進團體的建立。
事實上,人們更強調兩種療法的聯系而不是差別,大部分藝術治療師傾向在治療實踐中融合這兩種療法。正因如此,藝術即治療在克萊曼之后并沒有得到專門的發展。但事實上,人們更傾向于藝術心理治療而非藝術即治療,這從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行業協會有關藝術治療的定義中就能看出來。比如,美國藝術治療協會將藝術治療定義成:在藝術創作中改進并提高所有年齡段個體的生理、心理和情緒健康。英國藝術治療協會的定義是:藝術治療是在藝術治療師的幫助下,以視覺的形式將潛意識中被壓抑的思想與情感的向外呈現出來。我國臺灣藝術治療協會的定義是:藝術治療是一種結合創造性藝術表達和心理治療的助人專業。上述定義都強調藝術的表達功能,且都以“助人”或“治愈”為目的。綜上所述,這些定義更貼近藝術心理治療,而非藝術即治療。
藝術心理治療被如此重視的原因可能是其思想簡單明了,可操作性強,心理治療師只需簡單培訓就能掌握。而藝術即治療中的“藝術本質主義”和“生活的藝術家”等思想既抽象又不符合常識。不僅需要治療師有心理學和藝術理論基礎,并需要治療師掌握相當的藝術技巧。基于上述原因,藝術即治療并未得到應有的發展。
事實上,藝術即治療的理論是超越時代的,藝術即治療的理論反映了人文社會科學思想中的后現代思潮。比如,克萊曼認為藝術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中介,一切事物都經過了人的藝術處理才進入到人的認識世界中。而后現代心理學認為,文化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中介,人只能看到經過文化過濾后的世界。后現代心理學在剛提出的時候也被視為天方夜譚,但今天后現代心理學已經深入地影響了心理學研究與實踐的各個方面,這反映了藝術即治療也能在當代重新煥發活力。
三、藝術即治療的特點
“藝術即治療”理論有三個特點。首先,強調“生活的藝術家”,即服務對象是普羅大眾;其次,強調“暫時性治愈”,即治療價值觀上傾向于心理健康“精英原則”。最后,強調參與者的藝術能力。伊迪絲克萊曼認為,所有的藝術作品都來源于人與環境的沖突,所有的藝術都是具有治療性的。我們一直被日常生活中的藝術影響著,并被其中某些部分療愈著。如果我們可以成為生活的藝術家,那么已經在每時每刻地治愈自己。因此,藝術即治療不是為了改造“生病的人”以適應環境,而是以培養生活的藝術家,進而通過藝術家來改造環境。
然而,因藝術的超越性及相對獨立性,藝術家對社會的影響是間接而緩慢的。在這個過程中,藝術家勢必要超越時代進行藝術創作,進而影響社會。但過分超越了時代的藝術家勢必不能適應當下的時代。因此藝術即治療需要“暫時的療愈”,以暫時性地融入社會。
因此,藝術治療以治療為手段,以藝術為目的。不以完全融入社會為目的,而以改造社會為最終目標。克萊曼反對完全融入社會,認為這樣是對人性的破壞。這同席勒的美學思想一致。席勒認為,美育的終極目的不是讓人充分地現代化,而是要解決現代化進程對人性的破壞,喚醒被壓抑而缺失的感性,以解決時代的異化。[5]
“疾病”與“健康”作為個體與社會的“契約”,反映了人與社會關系。疾病意味著個體過分偏離了社會的要求,是這種“偏離”而不是“疫病”本身導致了個體的身心痛苦,并阻礙了個人發展。因此藝術治療應該幫助他們暫時性地融入社會,而不是謀求“治愈”。之所以是“暫時性地”,是因為他們不能“完全融入社會”。所有試圖改造社會的人都需要和社會保持恰當的距離,以看到社會的問題,從而承擔起改造社會的任務。
“暫時性治愈”符合心理健康中關于“精英原則”的價值取向。“眾數原則”與“精英原則”。前者將心理健康視作適應社會所應具備的基本品質,適用于大多數人,因此稱之為“眾數原則”。后者將心理健康視作能帶領社會進步的少數人應有的特殊品質。[6]“眾數原則”是從統計學中的正態分布為基礎,將大部分人的心理視作正常,偏離這一范圍即為異常。人本主義心理學先驅馬斯洛曾在20世紀猛烈抨擊這種心理健康觀,并提出了金字塔模型,將金字塔模型的頂端——“自我實現”視作心理健康的標準。馬斯洛提取的自我實現者的15個特征曾在心理健康界被奉為“標準中的標準”。[7]這一標準即符合“精英原則”。
“精英原則”的心理健康標準試圖培養改造世界的人,而“眾數原則”試圖培養適應世界的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應該同時擁有兩部分人,且大部分人的心理健康同時符合上述兩種原則。這就是為什么藝術即治療主張“暫時性治愈”的原因。
反觀藝術心理治療,其思路仍然站在心理學權威的高度上,試圖幫助人們“痊愈”,也即偏向“眾數原則”。而藝術即治療則試圖幫助人們成為“生活的藝術家”,即熟練地利用藝術工具隨時隨地地表現和升華自己的沖突。試圖幫助人們成為自己并改造社會,也即偏向“精英原則”。因此,為了保留藝術改造世界的能力,“藝術即治療”作為不能被忽視的一種思想,理應在當代得到發展。
此外,藝術即治療也更適用于藝術家群體的心理健康教育,因為他們較普通人本就更熟練地使用藝術技法進行自我表現以升華內在沖突。對藝術家心理健康研究的數據顯示,從事藝術活動的人的心理健康確實“堪憂”。[8]或者說,藝術活動的確讓一部分藝術家“過分超越”了社會。有研究者使用了SCL-90量表對中國藝術類大學生和藝考生被試進行研究,結論顯示藝術類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遠遠低于全國大學生常模及全國青年常模和(延鳳宇、王瑋、侯瑞賢,2010)。瑞典更有研究收集了超過30萬的樣本量,結果指出,藝術工作者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遠高于非藝術工作者。[8]因此,也需要發展特定的療法以針對性地幫助藝術家,這也是發展“藝術即治療”的另一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