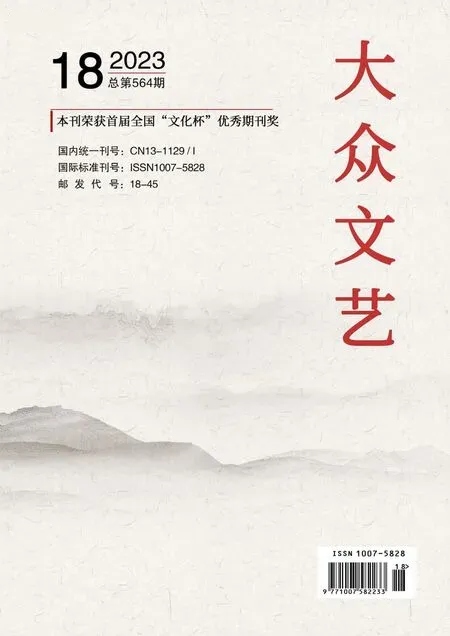“宮崎駿現象”:幻想王國與現實關懷
李 尤
(南寧市天桃實驗學校,廣西南寧 530031)
八十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來,宮崎駿的動畫作品風靡世界,受到全球觀眾的熱烈追捧,他所領銜的吉卜力工作室也崛起為足以與好萊塢的迪士尼分庭抗禮的動畫王國,傲然屹立于世界東方。就像人們常常用“村上春樹現象”“渡邊淳一”現象來形容他們作品的廣泛流行一樣,宮崎駿受關注的程度無疑也是現象級的(畢竟,《千與千尋》至今保持日本電影史上最高票房紀錄)。觀看宮崎駿的影片,我們可以徜徉在他精心打造的幻想王國里,插上想象的翅膀恣意翱翔。與此同時,宮崎駿對民族、歷史乃至全人類生存境況充滿憂患意識的觀照又把我們拉回地面,讓我們睜大雙眼直面身處的世界。本文就從幻想與現實關懷這兩個維度出發,以日本現代史為背景,探討宮崎駿作品的獨特魅力與“宮崎駿現象”的文化內涵。
一、盛世危言與烏托邦
八十年代的日本,達到了其戰后崛起的頂峰。在東京股票市場上市的企業,其總值是當時世界股票市場的40%以上,一些統計甚至表明,東京市總地產價值已經高于整個美國的房地產價[1]。這一時期,哈佛大學著名學者傅高義的著作《日本第一》在日本暢銷,銷量超過100萬冊,成為日本有史以來最暢銷的非小說類翻譯作品。總之,八十年代的日本正逢盛世,整個民族顯得生機勃勃,進取心和自我滿足幾乎膨脹到了傲慢的邊緣。
從這樣的背景出發,《風之谷》(1984)顯得相當不合時宜:影片充滿了悲觀的情緒,甚至是對人類的厭惡。甫一開場,濃濃的末世氣息就撲面而來,人類文明早已被蟲族毀滅,快速擴散的“腐海”蠶食著碩果僅存的人類家園。這種對災難的想象貫穿宮崎駿的多部作品。而《風之谷》中的腐海無疑是對飛速發展的工業文明所帶來的負面后果的一種投射。早在50年代,伴隨著日本戰后經濟的起飛,出現了一連串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水俁和新潟發生的水銀中毒,富山縣發生的鎘中毒,三重縣發生的空氣污染引發的哮喘,是當時震動全國的四大公害病。在70年代,雖然法庭對上述公害病的案例做出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決,使政府及企業擔負賠償責任,但類似的問題仍然像不時飄過頭頂的烏云,給日本平民的生活籠罩上一層陰影,甚至直至近年仍然不時出現在公眾視野中。2016年上映的原一男導演的紀錄片《日本國vs泉南石棉村》講述的就是泉南地區罹患肺病的石棉工人對政府責任的追究。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影像作品中對災難的想象或許植根于日本人的某種集體無意識,日本列島地處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火山活動、地震和海嘯頻發,地震的年爆發率最高達到1500次,從20世紀至今,就發生過三次嚴重的地震[2]。這種對自然災害的恐懼與危機感,深刻影響了日本文化的各個方面。
事實上,《風之谷》之于宮崎駿作品序列的重要意義,正在于它奠定了一系列內容表達上的母題,這些母題在之后的作品中仍然不斷出現。除了對災難的想象,另一重要母題便是對戰爭的批判反思。影片中的國家多魯美奇亞四處征伐侵略,聲稱要整合邊境各國,建立一方樂土,明顯地指涉了“二戰”中日本以實現“大東亞共榮”為名實施的侵略行徑。戰爭期間出生的宮崎駿一直對軍國主義的歷史及其殘存的幽靈持堅定的批判態度。1986年上映的《天空之城》正延續了這一母題,片中野心巨大的反派穆斯卡試圖利用天空之城的發達科技統治世界,其形象無疑是對軍國主義勢力的影射[3]。而巴茲與希達最后念出毀滅咒語“巴魯斯”,正是呼喚和平,告別戰爭的最強音。
宮崎駿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持續探討也由《風之谷》開啟。影片中腐海的擴張和王蟲的憤怒都是人類一心征服自然,破壞生態平衡的結果,而貪婪的本性又使人類不斷陷入混戰與斗爭。這種“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裹挾著一股憤怒的厭世情緒,仿佛只有人類徹底滅亡之后世界才能恢復原有的秩序。然而,宮崎駿還是讓心懷赤子之心的娜烏西卡協調著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最終在末日的邊緣拯救了世界。純粹的赤子之心向來是宮崎駿的主角們最可愛的地方,只不過他們在種種危機面前所能有的作為一直在發生變化,他們的身份地位也有其發展軌跡:《風之谷》里的娜烏西卡是有著皇室血統的基督式的救世主,到了《千與千尋》,荻野千尋只是個普普通通的鄰家女孩。
宮崎駿的自然觀就如日本的生態環境一樣,一方面透過地震、海嘯和火山這樣的災難毫不寬容地讓人類葬身其中,另一方面又溫柔地讓物產豐收,慈悲地讓人們安居樂業,于是就有了《龍貓》(1988)。這部昭和末年的作品散發著烏托邦的氛圍,田園牧歌的祥和遠離了無休止的征戰和一切災難破壞,最迫切的煩惱似乎只是生老病死而已。如果說《天空之城》里的拉普達也有著烏托邦色彩,那確乎是傳統意義上的烏托邦——不可能存在的地方。那么《龍貓》的烏托邦則是“就在身旁”的奇異世界。《龍貓》的整個故事背景是全然本土化的,跟前兩部作品都不同,主角們終于用上了日本名字,生活場景也是平日可見的日本鄉間。基于這一背景,宮崎駿提出:“早已遺忘的東西,未曾注意的東西,以為早就失去的東西,但是我相信那些東西都還在,所以提出《龍貓》這個案子[4]。”所謂“早已遺忘的東西,未曾注意的東西”,正是日本自然觀中的神靈。這種自然觀,可以看作某種萬物有靈論。日本人也許不相信組織上、教義上的宗教,但卻懷有信仰某種萬物有靈論的心。此種信仰,實踐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感應著無所不在的佛與神的力量,從動物、植物、大自然和無機物等森羅萬象當中,感應靈魂與生命的征兆。因此,我們就看到了《龍貓》里寄居在廢棄房屋里的煤球精靈,遇到了沉睡在森林身處的龍貓家族,然后和龍貓一起,見證月夜下瘋狂生長的參天樟樹。就像我們前面說到的,對自然的恐懼或敬畏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當中,眾多的神靈正是無意識的顯影,是民眾對自然的諸種敬畏和企盼的混合體。
二、贊美與憂患
隨著日本進入平成年代,長期以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宣告終止。在整個八十年代,宮崎駿都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一共推出了四部長片,進入九十年代,在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宮崎駿也進入了創作低潮,到世紀末為止只親自指導了兩部作品。1992年的《紅豬》延續了反戰立場的表達,在主角波魯克身上,宮崎駿投射了自己作為反戰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難堪境地——身為日本人,但不愿與軍國主義勢力同流合污。因此,主角波魯克就從人變成了豬,通過這樣的變形實現自我放逐,逃離所有的國家立場和民族身份,這位痛恨戰爭的孤獨者就成了一個西部片式的賞金獵人,在亞得里亞海上空與空賊周旋,賺取賞金度日。影片吸收了些許美國西部片的元素和橋段,臺詞中也直言不諱地指涉了西部片,但更有意味的是,影片還是一曲女性的贊歌。宮崎駿的多數作品都以女性為主角,在他眼里,女孩特有的純真特性使得她們更接近自然,平凡、弱小的她們承載的是勇敢與不屈的寶貴精神。《紅豬》中的那家機械制造廠里,男人們因為戰爭的原因都被征召入伍,工廠里的員工清一色是女性。18歲的菲奧是這些工作女性的出色代表,她獨立設計了波魯克的新飛艇,完工之前一直晝夜不停地趕工校準每一個細節,飛艇建造的其他所有環節也由家族的其他女性完成。[5]事實上,宮崎駿在前作《魔女宅急便》(1989)中就已開始關注相似議題,13歲的女主角琪琪來到異鄉打工,在陌生的環境下面臨重重困難,甚至于一度失去了與生俱來的法力,但她最終憑借自己的善良和勤勞完成了一項又一項成長中必經的功課。從兩位女主角的年齡上看,《紅豬》里的菲奧正是琪琪的完美延續,她在新的起點上開啟實現自我價值的新篇章。
1997年的《幽靈公主》也用一定篇幅承接這一女性贊歌的母題:達達拉城的女性是工作的主力軍,負責制造武器,同時還擔負起城防的任務。有意思的是,女性的領袖幻姬在年齡上恰好比18歲的菲奧又年長一些。九十年代的日本因為陷入經濟蕭條,又正逢生育率下跌,政府出臺了相應法案推動就業平等,鼓勵女性參加工作,以應對人力短缺的問題。1999年,《男女共同參劃社會基本法》在國會通過,承諾未來會加強立法給予男女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的平等地位。此后,重要的性別平等措施陸續出現,不少已婚婦女仍然留在工作崗位上,女性擔任管理層職位的比例也有所增加。[6]另一方面,《幽靈公主》是一部充滿了憂患意識的作品,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的“時代精神”。片中被斬首的山獸神憤怒的呼號,全身上下每個毛孔都流出黑色的濃稠液體,悲天憫人的情懷和人與自然的激烈沖突都在此刻達到頂點,男女主角充滿張力的互動也是這種沖突的絕佳載體。此外,片中諸神如山獸神、豬神、狼神、樹精比《龍貓》更進一步地刻畫萬物有靈的世界,這在下一部作品《千與千尋》中又繼續著更生動的描繪。
三、新世紀的“變形”
進入新千年后,宮崎駿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千與千尋》(2001)就創造了日本動畫的票房奇跡,拿下了290億日元,至今仍保持著日本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影片的日文片名直譯過來是“千與千尋的神隱”,所謂神隱,是日本的一個民俗概念,指孩子突然收到超自然力量的感召而從日常生活中隱匿,在異世界經過一場歷練之后再返回生活世界的現象。影片中,我們跟著主角千尋進入了一個“百鬼夜行”的世界,在這里,宮崎駿最為生動地構筑了一個萬物有靈的小宇宙:千尋的主管是以日本傳說中“大天狗”為原型的“湯婆婆”,幫助千尋坐電梯的白蘿卜客人脫胎于農神蘿卜神,追擊白龍的紙鳥則是源于日本人偶崇拜的傳統,白龍本身又是河神之子。還有《龍貓》里出現過的煤球精靈也再次登場,它們膽怯怕人,喜歡藏在古宅的墻縫中安家。然而,“百鬼夜行”所折射出的并不是關于人與自然的議題,而似乎是一個關于職場生活的寓言。影片伊始,千尋一家進入那個廢棄的游樂場,似在指涉仍未走出經濟蕭條的日本社會,此后出現的那個幽暗的異世界散發出恐怖片的氣氛,在千尋貪吃的父母變成豬之后達到頂點。此后的千尋為了拯救父母,留在這個世界當中辛苦地工作,她受盡了湯婆婆的訓斥苛責,干遍了臟活累活,還一度失去了自己原來的名字。最后,千尋終于憑借著自己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善良溫柔的心性完成了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最終拯救了父母,同時找回了自己的名字。“不要忘記自己的名字”似乎是宮崎駿送給所有初入職場的年輕人的箴言。“巨嬰”,壓榨,貪婪,面對這些成人社會的怪力亂神,似乎只有懷抱著原初的心性,才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保持最純真的自我。
就像白龍由龍變成人形,千尋忘記自己的名字也可看成是某種意義上的“異化”或“變形”,接下來的兩部作品里也延續了這一“變形”主題:《哈爾的移動城堡》(2004)里變成黑鳥的哈爾和變成老太太的蘇菲,《懸崖上的金魚姬》(2008)里變成人類的波妞。另一方面,從《千與千尋》開始,宮崎駿的主角們都很平凡,或者最終變得平凡。千尋只是一個十幾歲的鄰家女孩,沒有任何技能特長。蘇菲也只是個普通的衣帽匠學徒,沒有半點法力,但靠著自己純凈的心靈,蘇菲最終救了哈爾,破除了稻草人的魔法。波妞本來是大海里的金魚公主,法力強大,但最后為了宗介,她甘愿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類。事實上,在《千與千尋》之后,宮崎駿的作品內化了故事中的矛盾沖突,早期作品里激烈曲折的情節不再是人物行動的燃料,人物內心深處做出的選擇才是引導影片走向的指針。人物從“變形”到“還原”正是他們勇敢面對自我后實現的升華,同時也寄寓著宮崎駿在訪談中多次表達過的信念:只有純真的孩子才能讓這個糟糕的世界變得好一點,也只有心存赤子之心才能在這個糟糕的世界更好地生存下去。
結語
2013年末上映的集大成之作《起風了》是宮崎駿迄今為止現實關懷最強烈的作品:首先影片以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傳記為題材,這在宮崎駿的職業生涯中前所未有。在這種情況下,影片天然地限制了以往作品中那種幻想王國里的恣意縱橫,不能出現超越現實生活的元素。但宮崎駿在這種限制下仍然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他的長項,在掘越二郎的夢境里,他與意大利飛機設計師卡普羅尼相遇,在夢的國度里暢談理想,環游世界。另外,這部影片也最直接地面對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國族的命運:大正年間的關東大地震,“一戰”后蕭條的經濟,走上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直至最終迎來毀滅性的戰敗。這也是宮崎駿第一部具有悲劇內核的影片。主角掘越二郎是一個浮士德式的人物,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只能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為軍國主義的日本設計戰斗機。然而到了影片結尾的時候,他的愛人死去,他的國家戰敗,他心愛的作品悉數毀于戰場,正如卡普羅尼對他說的:“飛行是被詛咒的夢想。”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夢想墜入地獄。有意味的是,“飛行”也是宮崎駿本人最鐘愛的母題,他對于各種機械裝置也近乎迷戀,而侵略戰爭的歷史似乎使“飛行”的夢帶上原罪,是他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
從《風之谷》到《懸崖上的金魚姬》,心懷赤子之心的主角們總能在最可怕的危機中拯救世界,但在《起風了》的結尾,宮崎駿對此不再相信了,整個世界并沒有重新煥發生機,也并不充滿希望,只留下背對觀眾的主角在戰后的廢墟上掙扎著生存下去。不難發現,影片展開的幾大主題都最終走向悲劇的結局,只有生存這一主題面向未來敞開。此時的宮崎駿是何等悲觀,消解了創作中一以貫之的母題具有的意義,但是對于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對于我們所經歷的一切,他仍然借著掘越二郎的最后一句臺詞說了聲“謝謝,謝謝”。生存似乎才是宮崎駿最終極的關切,縱然命運風雨飄搖,這個世界仍然值得我們生存。就像影片開頭引用的瓦萊里的詩句:“起風了,唯有努力生存。”至于要如何在這個并不充滿希望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即將上映的作品《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也許會為我們呈現更進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