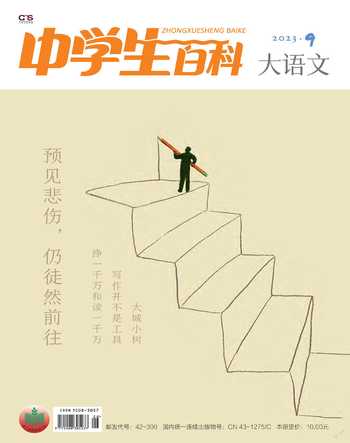掙一千萬和讀一千萬
仰宗堯
去新單位求職時,被問道:“讀過的哪本書對你影響最大?”局促茫然間,眼前浮現出了《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在黑暗幽邃的礦洞下讀《紅與黑》的場景。我想正是那些書,讓他成為理想世界的孫少平,而非現實生活中的于連。他那孤傲的倔強、落寞的勇毅不知支撐了多少在海海人生中奮力泅渡的人,如我。
二三十歲的年齡,難有與家人攜手同行,到野外讀詞念賦的閑致,也難有在風雪之夜,靠爐圍坐,悅而讀之的興味。真正的書籍應該是黑夜和沉默的產物,而非白晝和閑聊的果實。也只有在最自由的夜里,我才能有最放肆的姿勢,一遍遍沖泡母親炒出來的粗茶。讀到酣暢處,無人可談,便迫不及待地用手機拍下,發給那些可能會喜歡的朋友,不為矜夸,緣于牽掛。想念無所有,聊贈一段話。
多少次在睡意昏沉時,便隨性地枕著萬千文字間的高山大川和衣而眠,通身舒爽,因為,此刻有多疲倦,第二日便有多清醒。吹滅讀書燈,一身都是月。
福斯特說 :“人類生活有五大事實,生、吃、睡、愛、死。”愛是這個世界最復雜的事情,但既然是世界先愛我們,我們便沒辦法不愛它,這是書里說的。
記得有一次,與愛人鬧了些矛盾,下班后我便穿過整個城市,趕到她上班的地方。電話打不通,我索性對著車內的燈光,讀了大半個晚上的《顧城詩選》。長街上繁密的燈盞,好似天上的星星。書中的那些字,甚至是每一個標點,都讓人醉得忘了煩憂。此夜,頭頂浩瀚銀河,心中極度柔軟。
第二天是被陽光吵醒的,事情還無任何進展,我便徘徊到附近的書城,挑了本《知識分子論》。隨意翻來:“知識分子不必是沒有幽默感的抱怨者,他的重任之一就是破除限制人類思想的刻板印象。”可是今天啊,我不關心人類的闊大思想,我只關心某個人的苦惱惆悵。
迷茫間,電話響起,那個熟悉的聲音冷冷地問 :你在哪?我說:在路上,剛給你買奶茶去了。再見面時,周末也僅剩下一天半,想出去轉轉散心。找尋地方時,突然想到了梁衡筆下不同凡響的銀杏樹,便搜到了漢中那棵活了四千多年的古銀杏,并不多想,義無反顧就去了。窗外,草在結它的種子,風在搖它的葉子。我們坐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
某日下班后,發現鑰匙鎖在了家里,等開鎖師傅的間隙,我就著樓道里的瑩瑩弱光,翻開新買的《我與父輩》。燈光昏暗,字認得費力,我一下子想到了年輕時在磚廠熾熱的窯洞里“蒸”壞眼睛的父親。和書中那些蒼老的父輩一樣,他蹣跚著走到我面前,和我講些雞零狗碎的家常話。
彼時,我剛給學生講完李森祥的《臺階》。第三次教這篇文章了,每次都是我使盡解數,他們泛泛而答。在不大的教室里,我們相對而望,仿佛分明的涇渭之水。不知是我力有不逮,還是于他們而言,“土”成了貶義詞,“鄉”也不再是衣錦還歸的去處。當夜我含淚讀完了《我與父輩》,第二天便把它推薦給學生們。后來,我很少再聽到學生們背后開玩笑,稱我為“農村人”。
在那個青春洋溢的教室,我常常拿著名作兀自走進喧鬧中,攤開書,一言不發,就那樣等待教室一點點靜下去,靜下去。時間的縫隙里,他們一知半解地跟著作家們去“看見”廣闊的世界,或是尋找有趣的靈魂。他們將汪曾祺的句子鑲入作文里賺高分,有時還和我爭論林語堂和村上春樹誰的孤獨寫得好。
某次看到學生作文里寫道:“李白就這樣像大鵬一樣奔向了他的月亮。”我說何不加個逗號,葉圣陶講過的,這樣有韻味。不想在我的批語下,他安靜而又倔強地寫道:“長文顯氣度,短句見骨子,不長不短逞風韻。”是木心的句子,我很服氣。我沉默地看著十三四歲少年稚嫩的筆體在我面前水流花放。
有段時間,教室里多媒體背景上,推薦的是《我的阿勒泰》里的佳句。剛好班里有位女孩的父親常年在阿勒泰工作。每當看到她在教室的一角安靜地捧讀這本書時,我便覺得她很幸福——雖然和父親隔得很遠,但彼此靠得很近。
故事是講不完的,就像書是讀不盡的。一年賺一千萬的快意,自然不必去艷羨;讀一千萬,倒是可以成為經年的期盼。可惜,我知道這短暫而迅疾的人生,需要我用大把的時間去吃、去睡、去愛,最終也要像水一樣消失在水中。但我渴望,書里每一個靈魂再被我喚醒,不只是連姓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