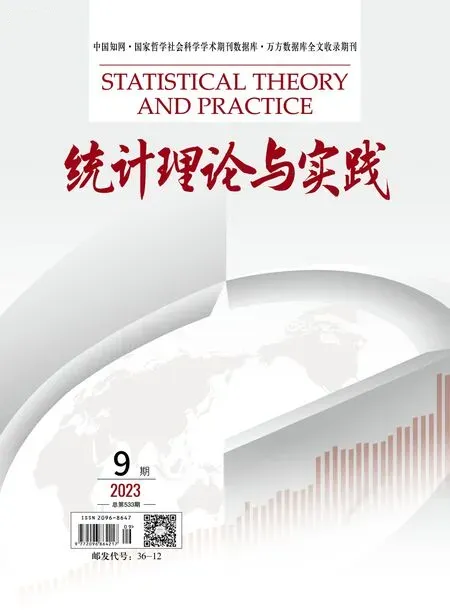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研究
焦青霞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統計與大數據學院,河南 鄭州 450016)
隨著經濟的發展,結構性問題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為第二產業疲弱、第三產業發展后勁不足、資源錯配以及科研實力不足以支持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等,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成為目前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制造業服務化向消費者提供“制造+服務”一體化解決方案,一方面可以優化企業資源配置、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減少生產中能源、資源的消耗,降低對環境的污染。不僅為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而且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對制造業服務化的產業升級效應進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目前學術界有關制造業與產業轉型升級之間關系的研究結論大致有兩類:
一類是認為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線性的。周大鵬(2013)[1]、張志醒和劉東升(2018)[2]、唐國鋒和李丹(2020)[3]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實證研究,得出服務化可以促進產業升級,服務化對制造業升級存在服務投入異質性。胡昭玲和夏秋等(2017)[4]則從科技創新視角研究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得出服務化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發揮重要作用,不同服務投入發揮的作用大小存在差異。
另一類研究認為二者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徐振鑫和莫長煒等(2016)[5]認為在服務化的起步階段,企業資源配置與服務化投資關系處理不當會導致企業步入“服務化陷阱”,從而阻礙產業升級,一旦度過這一階段,服務化開始發揮作用,企業盈利能力不斷提高,產業得到升級。但是隨著服務化程度的再次提高,過度服務化的出現將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從而不利于產業升級。夏秋和胡昭玲(2018)[6]認為,在服務化水平較低時,服務化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但經過拐點后具有促進作用,二者之間的關系呈U 形分布。王嵐(2020)[7]認為不同服務來源實現的服務化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是不同的,國內服務投入實現的服務化與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呈U 形關系,而國外服務投入實現的服務化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則呈倒U 形。
梳理已有文獻發現,研究制造業服務化與產業升級之間關系時,現有文獻更多關注的是服務化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從宏觀視角研究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影響的較少,而制造業服務化的水平和質量與制造業類型密切相關。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在定量分析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影響的基礎上,對不同類型制造業服務化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進行了分析。
二、 制造業服務化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作用機理
本部分主要從制造業服務化可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人才聚集、降低生產成本三個方面闡述制造業服務化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機理。
資源配置方面。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制造業將原來內置的服務部門獨立出來外包給專業的服務企業,不僅有利于自身將更多精力和資源投入具有競爭優勢的核心環節,優化資源配置,還有利于企業專注于核心技術,充分挖掘并實現核心技術價值,通過對專業知識、經驗的不斷積累,在資源要素投入較少的情況下生產出質量更好、品質更優、更能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提高要素的使用率。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人才聚集方面。制造業服務化不僅可以促使知識密集型產業聚集,提高地區信息化水平,還會提高服務業和制造業融合的速度,形成要素的良性循環,從而吸引高素質人才聚集。高素質人才的聚集可以促進企業改善生產流程,完善銷售與營銷,提高企業的經營水平和生產效率。同時,來自外部的高知識、高技術人才可以提高企業設計、研發和管理的軟實力,從知識層面為制造業產業升級提供智力支持,優化制造業結構,進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降低生產成本方面。對制造業來說,服務環節外包可以更好地專注于生產的核心環節,把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效率更高的部門,從而節約生產成本。另外,生產服務業專業化具有規模經濟效應,雖然在發展初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但隨著生產服務業的發展與完善,服務成本不斷下降,制造業通過服務外包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質量更優、效率更高的服務。內部生產成本和外包服務要素成本的降低,使制造業單位成本顯著下降,從而提高制造業生產效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另外,制造業類型不同對服務要素需求的種類和數量會存在差異。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勞動力投入占據主要地位,對專業和技術要求較低;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生產中除了交通運輸、批發零售這些生產經營所需的基本服務要素,更多依賴信息通信和專業科技等高端服務。不同要素的融入使對應的服務化存在差異,進而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產生不同影響。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設:制造業服務化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存在制造業行業異質性。
三、模型設定、變量選擇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為了分析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結合前文的分析,設定基準模型如下:
其中,i 表示地區,t 表示時間,變量optit表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msit表示制造業服務化水平,X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參考已有研究此處納入以下三個控制變量:政府干預程度(gov)、外商投資(fdi)和研發投入(r&d),εit為隨機誤差。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opt)。參考以往學者研究,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界定為產業發展由低形態逐漸向高形態轉變并且所占比重不斷增加。按照這一思路,參照干春暉和鄭若谷等(2011)[8]以及胡昭玲和夏秋等(2017)[4]的做法,利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來測度。
2.解釋變量
制造業服務化水平(ms)。借鑒楊玲(2019)[9]的研究思路,利用直接依賴度系數來測度制造業服務化水平。制造業j 對服務k 的直接依賴度為:
其中,aij表示制造業j 部門生產過程中對i 部門的直接消耗。
考慮到投入產出表的非連續性和投入產出結構短時間內難以發生改變,2008—2011 年服務化數據用2007 年的結果替代,2013—2016 年服務化數據用2012 年的結果替代,2018—2019 年服務化數據用2017 年的結果替代。
3.控制變量
政府干預程度(gov)。政府通過對市場的干預可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所以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必然會對地區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影響。這里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 比重表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
外商投資(fdi)。以往研究表明外商投資可以通過資金供給、人力資本、技術和產業關聯等多種途徑對地區產業結構產生影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為了使數據可比,用當年匯率將外商投資總額折算為人民幣。
研發投入(r&d)。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科技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經濟增長又會導致產業結構向高級化轉變,科技創新是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驅動力。研發經費投入的多少將直接影響地區科技創新水平,因此,用R&D 經費支出強度來測度。
4.門檻變量
服務發展水平(serl)。用服務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來衡量。
經濟發展水平(agdp)。國民收入水平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直接體現,本文用人均GDP 來衡量。為了使數據前后具有可比性,將人均GDP 利用物價指數進行消漲處理。
(三) 數據說明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2007—2019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港澳臺和西藏除外)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地區投入產出表-2012》《中國地區投入產出表-2017》《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國家統計局網站。由于本文重點考察的是制造業生產過程中生產服務要素的投入,所以具體研究之前先對生產服務業、制造業部門的范圍和界限進行說明。
為了保證投入產出表部門前后的一致性,本文將2007 年投入產出表中郵政業與交通運輸及倉儲業兩部門合并,同2012 年、2017 年投入產出表中的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相對應;將2007 年和2017 年投入產出表中的綜合技術服務業與研究和試驗發展兩部門合并,同2012 年投入產出表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相對應。參考以往學者的做法,選取與制造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批發與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作為服務化計算樣本。
為了研究不同類型制造業服務化差異,按照投入產出部門表II 級分類將投入產出表中制造業的分類進行調整。將2007 年投入產出表中的工藝品歸入造紙印刷及文教體用品制造業,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歸入通用制造業,然后借鑒已有關于制造業的分類方法,最終把制造業分為三類①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包括食品和煙草,紡織品,紡織服裝鞋帽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造紙印刷和文教用品,非金屬礦物制品,金屬制品,其他制造產品和廢品廢料,金屬制品、機械和設備修理服務;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包括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品,化學產品,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品;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包括通用設備,專用設備,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和器材,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儀器儀表。。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基于公式(1)來定量測算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考慮到如果模型中存在遺漏變量,或制造業服務化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會導致模型出現內生性,使估計結果出現系統性偏差,故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對模型進行估計,使用的工具變量為制造業服務化和研發投入一階滯后項,估計結果見表1。由表1 第2 列中LM檢驗可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模型拒絕工具變量不可識別這一原假設;F 統計量值大于19.93(10%顯著水平的臨界值),說明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相關,不存在弱識別問題;Sargan 檢驗結果表明模型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綜合以上分析,可認為工具變量的選取是合適的。

表1 制造業服務化回歸結果
回歸結果表明:控制模型內生性之后,制造業總體服務化系數為正,且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在控制政府干預程度、外商投資和研發投入變量后,制造業總體服務化水平每提升一個單位,產業結構優化程度提高0.0112 個單位,制造業總體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制造業生產中通過增加服務要素的投入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政府干預程度變量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且估計系數為正,說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確實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外商投資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為負并且在10%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可能是由于外商投資產業結構布局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資源配置不能合理造成的;研發投入估計系數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研發投入每提高一個單位,產業結構優化程度就提高0.4560個單位。
(二)異質性分析
為了考察不同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按照前文制造業的分類方法,將制造業分為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三種,研究不同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估計結果見表1。由表1 的第3 列至第5 列中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三個模型工具變量的選取是合適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系數為正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在其他變量控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程度每提高一個單位,產業結構優化程度提高0.0059 個單位;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系數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系數也為正并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對產業結構升級也存在促進作用,并且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程度每增加一個單位,產業結構優化程度分別提高0.0066個和0.0122 個單位。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促進作用最大。
不同類型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差異,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投入的服務多是科技研發等高級服務,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與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投入的服務多是專業化程度比較低的傳統服務,與科技研發高端服務相比,傳統服務的投入不能很好地改善制造業的投入結構,所以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作用有限。通過上述分析可見,制造業服務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但是不同制造業之間存在差異,存在行業異質性假設得到檢驗。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對本文結論的可靠性進行檢驗,采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法對模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利用直接消耗系數測度制造業服務化水平,并對前面基準回歸模型和門檻模型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2。

表2 模型穩健性檢驗結果
由表2 可以看出,四個模型在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時,工具變量的選取合適(工具變量與前文相同)。將表2 與表1 的結果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將核心解釋變量進行替換后,四個模型中核心解釋變量制造業服務化以及控制變量系數的符號與顯著性基本不變,說明基準回歸的結果是穩健的。
五、結論與對策
本文基于中國地區投入產出表,輔以《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利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結果發現:(1)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制造業服務化水平每變動一個單位,產業結構優化程度平均提高0.0112 個單位。(2)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影響存在行業異質性,作用最大的是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其次是資本密集制造業服務化,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作用最小。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對策:第一,順應經濟發展大趨勢,做好頂層設計,引導企業樹立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觀念,依據產業結構發展演變規律,逐漸將傳統的產品體系發展為融產品和服務于一體。積極引導科研機構和企業合作,培養高技術人才,不斷提高制造業的知識儲備和技術儲備,以便更好發揮制造業服務化在產業升級中的促進作用。第二,信息技術、專業技術這些知識科技含量比較高的產業增值能力較強,是未來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新生力量,政府應不斷加強以這些新興產業為核心的戰略調整力度,積極引導經濟向高端服務和高技術制造業方向發展,推動高端服務與高技術制造業的融合發展,以充分發揮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