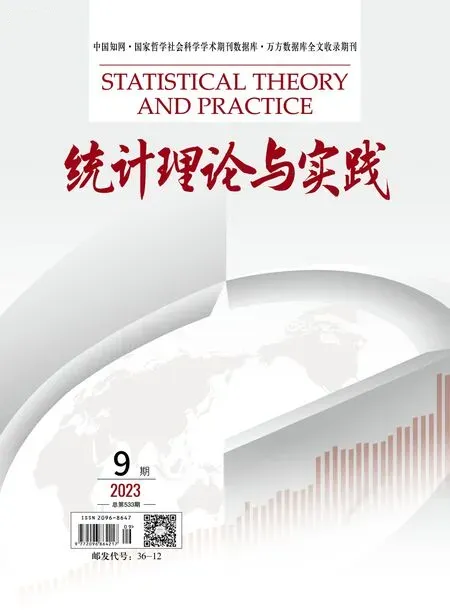中國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時空演變及影響因素分析
王玉峰
(蘭州財經大學統計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大力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加速農業強國建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農業發展上取得了顯著成果,糧食產量逐年增加,2022 年達1.37 萬億斤;棉花、油菜、果蔬等產量穩步增長,畜產品和水產品供應較為穩定。然而,農業生產不僅需要滿足人們的需求,還需要考慮生態環境,在農業經濟快速發展、糧食產量不斷提高的過程中,農業碳排放量隨之增加,糧食安全與綠色農業問題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綠色生產已經成為當前農業生產的重要發展方向。
目前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提出了“雙重約束”目標,即“雙碳”目標,并不斷尋找降低碳排放的方法。農業是除工業外的主要碳排放源,加快農業低碳排放刻不容緩。提高農業綠色生產效率以協調綠色環境和產量增長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重要內容,也是加速實現“雙碳”目標的主要路徑之一。碳匯作為環境穩定器,對環境污染的作用不可小覷。因此,在碳循環視角下,協調農業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至關重要。
時空演變是研究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視角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業生產效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變化趨勢。同時,農業生產效率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存在差異,與土地資源、氣候環境、政策支持等因素有關。除了時空因素,影響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因素還有很多,例如技術水平、資源利用效率、農業政策等都對農業生產效率產生重要的影響。同時,社會經濟因素和生態環境因素也是影響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
因此,研究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時空演變及影響因素,不僅有助于深入理解農業生產效率的變化規律和影響機制,而且可以為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
二、文獻綜述
農業綠色生產效率近年來逐漸成為學者研究的熱點,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測算方法、時空演變和影響因素分析方面。
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和隨機前沿分析法(SFA)被廣泛應用到效率測算中。全炯振(2009)、潘丹(2014)使用SFA-Malmquist 指數模型對中國農業生產效率變化指數進行測算并分析,得到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取決于技術進步,并且農業綠色發展具有不平衡性[1-2]。肖琴和周振亞等(2020)使用DDF-GML 指數對農業綠色生產效率進行測算,認為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是農業綠色生產效率提高的主要動力[3]。王麗娜(2022)使用SBM模型測算,發現省域間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差異呈現縮小態勢,但領先地區的優勢仍然較大[4]。
在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影響因素研究方面,孫一平和周向(2015)認為農業經濟的提高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5]。汪輝平和王增濤等(2017)、陳燕君和王圓圓(2022)通過實證分析得出農業FDI對農業TFP 產生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等結論[6-7]。許素瓊(2019)研究得出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會影響新型城鎮化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等結論[8]。展進濤和徐鈺嬌等(2019)、郭海紅和劉新民(2020)、劉海英和楊明等(2022)認為綠色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能有效促進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9-11]。
綜上所述,目前學者在農業生產效率上的研究已較為深入,對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測算等研究則不夠全面,并且很少考慮碳循環作用下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變化。基于此,本文將碳匯納入模型,使用SBM-GML指數對農業綠色生產效率進行測算并分解,使用三維核密度估計、基尼系數及其分解系數分析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動態演進,并運用動態面板模型對影響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因素進行分析,為各地持續推進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提供一定參考。
三、研究方法與指標說明
(一)研究方法
1.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測算方法
(1)超效率SBM模型
由于傳統的DEA 模型不能準確衡量綠色生產效率,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能很好地解決角度及方向問題,參考沈洋和周鵬飛(2022)[12]的研究,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ρ 為決策單元的效率值,其值大于等于1 則表示該決策單元是有效的。x、y、yb分別表示投入、期望產出、非期望產出,λ 為指標權重s-、s+、sb為松弛變量,分別表示投入過多、產出不足、造成的環境污染。
(2)GML 指數
通過超效率SBM模型求出各省(區、市)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后,利用GML 指數測算各決策單元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變動率,將綠色生產效率分解為技術進步與規模效應,公式如下:
其中,GML 表示綠色生產效率變動率,如果GML>1,表示綠色生產效率提高;如果GML<1,表示農業綠色生產效率下降。GTC 代表綠色技術進步,GEC代表綠色技術效率變化。
(二)指標說明
1.投入指標
勞動投入,使用各地區農業就業人數衡量。資本投入,使用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業化肥施肥量、農膜使用量、農藥使用量衡量。能源投入,使用農業柴油使用量衡量。土地投入,使用農作物播種面積衡量。
2.產出指標
(1)期望產出
農業總產出,使用農業總產值衡量,以2004 年為基期進行平減處理。
農業碳匯指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通過植被和土壤固定二氧化碳(CO2)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碳存儲,計算公式為:
F 表示農業碳匯總量,Y 表示作物的經濟產量,第i 種作物的經濟系數,為i 種農作物的碳吸收率,γ 為農作物的含水率。系數參考田云和張俊飚(2013)的研究[13]。
(2)非期望產出
農業碳排放。主要從農地利用、畜禽養殖、稻田三方面測算,農業活動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C 為農業活動二氧化碳排放總量,T 為碳源實物量,δ 為各類碳排放系數。具體系數參考田云和張俊飚(2013)的研究以及IPCC 的方法[13]。
3.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2004—2020 年中國除港澳臺和西藏外的30 個省(區、市)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EPS 數據庫、《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業統計年鑒》、各省份統計年鑒,極少數缺失數據采用插值法進行補充。
四、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時空演變分析
(一) 測算結果時空分異分析
基于2004—2020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的數據,在碳循環視角下,運用SBM-GML 模型得到總體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及分解結果(見表1、圖1)。

圖1 2004—2020 年綠色生產效率的時空分異特征

表1 2004—2020 年碳循環作用下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平均值
總體看,大多數省(區、市)處于有效生產過程,東部的效率值相對中西部地區更高。其中,上海、山東的效率值均達到1.5 以上,貴州、云南、青海、寧夏等地區的生產效率小于1,處于無效率狀態。
從時間上看,AGTFP 大小和變化趨勢與GTC 一致,說明農業綠色生產效率主要源于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是農業綠色生產的主要動力。不同地區間差異主要體現在東部地區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增長最快,中部次之,西部地區的農業綠色生產率水平趨于穩定,東部與中西部差異逐年增大。主要在于東部與中部地區地形、氣候、經濟條件較西部地區優越,有利于農業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
分地區看,2005 年廣東、寧夏等地的農業綠色生產效率較高。2020 年東部與中部地區,總體上農業綠色生產效率水平顯著提高,并出現高- 高集聚現象。廣西的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相對較低,主要由于廣西地處沿海,主要發展工業和自由貿易等,且地形地貌不利于農業生產,農業相對落后。
(二)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總體動態演進趨勢分析
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在不同地區間存在差異,構建三維核密度估計圖進一步分析總體效率及差異動態變化趨勢(見圖2)。

圖2 2 0 0 4 — 2 0 2 0 年農業綠色生產效率三維核密度圖
由圖2 可以看出,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總體在0—2之間,分布曲線呈現波動向右移動趨勢,說明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總體水平增加,存在動態發散趨勢。從分布形態看,核密度曲線圖形扁而寬,峰值逐年變低,寬度小幅度加大,意味著各地區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差異趨于變大。從分布延展性看,右尾隨著年份的增加出現輕微的拉長現象,意味著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在地區間的差異逐漸變大。
(三)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區域差異來源分析
分析發現中國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差異逐年增大,為進一步分析差異來源及變化趨勢,利用Dagum 基尼系數分析其差異大小及變動。由于2004 年為基期,研究意義不大,故對2005—2020 年數據進行分析(見表2)。

表2 2 0 0 5— 2 0 2 0 年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基尼系數及分解
從總體差異看,總體差異不斷增加,2011 年前差異增長速度較快,2011 年以后差異增長速度減緩,變化較為平緩。
區域內差異方面,東部差異最大,2009 年之前大于整體差異,2009 年之后呈波動變化趨勢。2011 年前西部地區差異處于波動增長趨勢,2011 年后呈現下降趨勢,區域內差異減小。中部差異較小,呈現上升趨勢。
從區域間差異看,東部與西部地區間的差異在研究時間段內最大,2009 年之前東中部差異大于中西部差異,2009 年之后,中西部大于中東部。2011 年之后區域內差異增長緩慢,不平衡問題得到緩解。
差異來源及貢獻度方面,超變密度逐漸變小,區域內貢獻度上升,2010 年前小于超變密度,2010 年后超過超變密度。區域內差異研究期內處于平衡狀態,貢獻度位于區域間差異與超變密度之間。主要由于“十二五”規劃提出深入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2011 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體現了我國農業在此期間取得了顯著成果。
五、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1.模型設定
為研究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影響因素,探究其是否具有動態效應,本文設定如下動態面板模型:
其中,AGTFP 為農業綠色生產效率,NAD 為自然災害,AHC 為農業人力資本,GOV 為政府干預,OPEN為對外開放水平,RD 表示科研水平。
2.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農業綠色生產效率(AGTFP)。由SBM-GML 測算得到,并以2004 年為基期,逐年進行累乘處理。
解釋變量:
(1)自然災害(NAD)。使用農作物受災面積表示,自然災害會減少農業總產量,對農業生產率產生不利影響。
(2)農業人力資本(AHC)。使用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表示,農業人口規模反映該地區農業種植規模,人口越多種植規模就越大。
(3)政府干預(GOV)。使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GDP 的比值代替,政府干預能夠反映政府對當下發展的規劃。
(4)對外開放水平(OPEN)。使用進出口總額與GDP 的比值代替,我國是農業大國,農產品大量出口國際市場,外資開放在農產品生產上起到重要作用。
(5)科研水平(RD)。使用規模以上R&D 投入占GDP 的比重表示,科研水平對地區經濟發展和綠色生產起到重要作用。
(二)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動態面板雙固定模型逐步回歸探究影響農業綠色生產效率自身因素、外在因素,結果見表3。

表3 基本回歸結果
由表3 可知,滯后一期的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對當期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有正向影響,說明前一期農業生產效率對后一期生產效率產生了顯著的影響,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存在“滾雪球”效應。自然災害的系數為負且顯著,但是影響系數較小,說明自然災害對農業綠色生產的影響不大。對外開放水平能促進綠色生產效率的提高,主要由于我國是農業大國,每年農業進出口規模較大,對外開放能帶來先進的管理與技術,提高農業出口質量與農業綠色生產技術,進一步提升農業綠色生產效率。政府干預對農業綠色生產效率起到抑制作用,并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主要由于政府財政在加快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工業化及能源的投入使用,在增加產能的同時增加碳排放,不利于農業綠色生產。農業人力資本在促進農業綠色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能夠提高勞動力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科研水平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顯著,主要由于創新大多集聚在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的創新所占比重較小,所以對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影響不顯著。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使用2004—2020 年中國30 個省(區、市)數據,基于SBM-GML 指數模型,運用三維核密度估計、基尼系數及其分解系數對我國農業綠色生產效率進行測算并進行時空演變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技術進步變化趨勢與綠色生產效率變化趨勢相同,是提高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主要動力,規模效應基本不變,作用較小。(2)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在不同地區存在差異,東部與中部的差異較小,西部生產效率相對較低。(3)由三維核密度估計圖及基尼系數分解發現,在研究期內,地區差異逐年增加,農業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各地區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差異變動趨勢較為平緩,尤其是西部地區的差異逐年減小。(4)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存在“滾雪球”效應,對外開放水平、農業人力資本能顯著促進農業綠色生產。
基于以上實證結論給出如下建議:
1.推廣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設備和技術。農業生產設備和技術的升級換代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和質量,降低對環境的影響。比如,使用現代化的農業機械可以減少人力投入,提高耕作效率;使用先進的育種技術可以培育出更適合當地環境的作物品種。加強信息化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信息化技術可以提高生產過程的透明度和可控性,減少浪費、降低損失,同時可以提高農民的收益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使用智能化的氣象監測系統,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的精準度和可持續性。
2.制定農業發展戰略,協調地區發展。不同地區由于地理位置、氣候等因素使農業綠色生產效率存在差異,政府應根據各地特點,制定適合當地農業發展的策略,從而縮小地區差距。鼓勵區域間相互合作,進而實現“經濟- 環境”長期協同機制目標。通過高效率農業綠色發展地區帶動周邊較低效率省域實現農業綠色生產效率的提升,進一步實現我國環境和經濟發展長期協同機制目標。
3.加強農業監管力度,提高管理效率。農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生產技術的投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應積極協調資源、環境、生產三者間的關系,減少農業生產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
4.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提高農業經濟的開放度。鼓勵國際間相互學習、交流合作,在保障本土糧食安全的基礎上,提高糧食進出口貿易數量與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