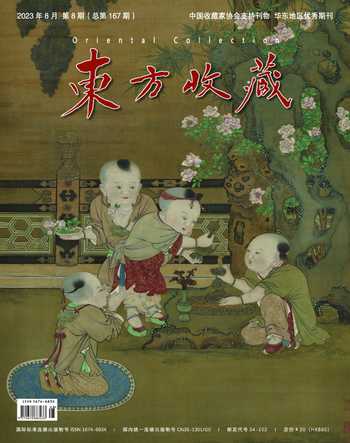米羅超現實主義時期繪畫風格的變化
摘要:胡安·米羅為西班牙畫家、雕塑家、版畫家、陶藝家,是與畢加索、達利齊名的20世紀超現實主義繪畫大師之一。在長達40年的超現實主義創作中,米羅的繪畫風格是不斷變化的,我們能從中體會到夢幻、神秘、生動,亦有怪異、悲劇、恐怖,更有童真、抒情、優美。文章從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入手,具體分析米羅在超現實主義時期繪畫風格的變化。
關鍵詞:米羅;超現實主義;風格
一、米羅早期的藝術背景
1893年4月20日,米羅出生在巴塞羅那一個從事手工藝的家庭,在傳統技能、工藝設計的熏陶下,米羅從小就對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07年,14歲的米羅進入伯納斯藝術學校學習,在這里,他遇到了烏赫爾和帕斯科兩位老師。烏赫爾寫實又富有詩意的繪畫深深影響著少年米羅,帕斯科也帶領他進一步接觸到裝飾藝術和手工藝。
20世紀20年代,由于身體原因,米羅的父親把他送到蒙特洛伊鎮附近的一個農村療養。在這里,米羅近距離地接觸著大自然,重云疊嶂的遠山、粗獷嶙峋的斷巖、錯落各異的屋舍、環繞村落的橄欖樹和葡萄園,都是米羅繪畫中喜愛表現的景色。這段農莊生活使米羅對自然和故鄉產生了深深的情感,也為米羅藝術風格的形成做了前期的準備。
二、布勒東《超現實主義宣言》對米羅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20世紀初的巴黎,那四年,歐洲成為暴力、疾病、死亡的代名詞。安德烈·布勒東作為醫療兵被派往戰場,他幸運地活下來了。看著面目全非的世界,他開始質疑起自己的社會,希望尋找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給了布勒東很大的啟發,在其影響下,布勒東于1924年出版了《超現實主義宣言》。“然而,據說米羅曾經隔著他倆工作室之間墻壁上的破洞問過馬松,他是不是應該去拜訪一下畢卡比亞或者布勒東。”[1]馬松堅定地告訴米羅,布勒東才是大勢所趨。從這之后,一位偉大的超現實主義畫家誕生了。
三、二戰前——神秘抽象的夢幻畫
(一)繁復堆疊時期
1.精美細致的造型——以《小丑的狂歡節》(見圖)為例
1924—1925年間,米羅創作了他的代表作《小丑的狂歡節》。米羅創作這幅作品時的狀態是超現實主義所推崇的“最純粹狀態下的精神不自覺”,是將大腦放空,不受任何意圖、聯想和成見控制的。當1925年巴黎皮埃爾美術館展出米羅的這幅作品時,大家都被這位大師風格的轉變所震驚,《小丑的狂歡節》也成為首次超現實主義展覽的熱點話題。
這幅作品中出現許多奇特的、說不上名的造型 ,“‘造型’原意為鑄造中制造鑄型的工藝過程,從藝術和設計的角度來看,又引申為,用一定的物質材料塑造可視的平面、立體和空間的形象。”[2]相較于立體主義時期的作品《農場》,《小丑的狂歡節》的造型更為簡練和概括,但它與“繁復堆疊”并不沖突。整幅畫面中都遍布著米羅所創造的奇怪形象、符號,雖為“無意識”,但觀察某一局部時又讓人感覺安排得十分精巧。
比如作品題名中的小丑,其中一個小丑形象的頭部被概括成了一個球體,以八字胡的球的形象出現在中央偏左一點的位置。其身體由直線和曲線構成,如同一把吉他,與空中飄浮著的音符相呼應。畫面的下方也有兩個小丑形象,其肚皮上的裂痕許是象征著米羅在這一時期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上升的梯子也可解讀為作者對現實苦難的逃避。
2.對比鮮明的色彩——以《加泰羅尼亞風景》為例
“色彩是客觀世界實實在在的東西,本身并沒有什么感情成分,但由于人的社會活動與之發生聯系,人的心理活動的參與,色彩又對人的思維、感情產生一定的影響。在這種交替的往復中,達到不斷地再認識和心理調節。”在《加泰羅尼亞風景》中,視覺沖擊力最強的是黃色和橙黃的兩塊平面,這兩塊鮮亮的背景相交于畫面中部的一條曲線。
如果說《小丑的狂歡節》是用精致的細節來豐富畫面的話,那么《加泰羅尼亞風景》則是用對比鮮明的顏色來抓住人的眼球。除去背景由大塊的橙黃構成,畫面中其他物體也以橙黃的顏色為主,那么少量的紅、綠、黑的點綴,在橙黃的基調上一下子就跳脫了出來,畫面整體也因此顯得非常生動活潑。
3.近趨平面的空間——以《耕地》為例
對比《耕地》和《農場》這兩幅描繪蒙特洛伊鄉村風景的畫作,我們能明顯感受到米羅由現實主義向超現實主義的轉變。《耕地》這幅作品中的空間和米羅這一時期大多數作品中呈現的一樣——似乎被壓扁了,可以看到這幅作品和前兩幅作品中,前景和背景幾乎無差別地融為一體,且畫面中部都有一條地平線。米羅運用地平線來表示空間,是他在伯納斯藝術學校學習時受到老師烏赫爾的影響。
畫面中不是所有的物體都真實,也不是所有物體憑空捏造。米羅曾說過他并不想追求現實以外的幻想,他要在大自然中找到出路。所以《耕地》也是以自然為題材進行創作,但它并不像《農場》中的那樣遵循現實空間中的規律,只是維持一個基本的平衡,憑借現實和幻想的交織來營造出畫面的神秘感。
(二)簡單夢幻時期
1.基本的形狀和單純的色彩
《吸煙者》和《白手套》分別是米羅在1925年和1927年時完成的,這一時期的作品背景以藍色、灰色、褐色為主,用近乎平涂的方法鋪滿整塊畫布。作品的內容十分簡潔,用線描代替油彩,以極簡的畫筆勾勒出點線面,每張作品都獨一無二。
2.媒介的超越和詩意的融合
在這一時期我們還發現米羅有一些新嘗試,《Stars in Snails' Sexes》《Photo:This is the Color of My Dreams》都是他在1925年創作的。其在畫面中加入文字或是近似文字的符號,顛覆了繪畫純粹的視覺性。
1926年,馬格利特創作了《這不是一支煙斗》,這幅作品成為他最著名的畫作之一。這幅畫之所以有價值就在于它的圖像與文字之間形成了非常強烈的沖擊。我們看到的是煙斗,但是文字卻說這并不是一支煙斗。這種獨特的文字與圖像之間的關系,恰恰是這幅畫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米羅的這些作品中,雖然圖像與文字不是對立的關系,但這樣的嘗試打破了傳統媒介的限制,讓繪畫不再是孤立的存在。以字襯畫,畫面多了一分詩意,以畫托字,文字也更具故事感。
四、二戰時——怪異扭曲的情緒畫
(一)野蠻繪畫——以《靜物和舊鞋》為例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米羅的繪畫風格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顛沛流離的生活使米羅感到厭惡,他將情緒全都宣泄在繪畫中。1937年,米羅創作了《靜物與舊鞋》,畫面中充斥著幽怖的黑,絢麗的色彩扭曲在一個捉摸不透的空間里。隨意擺放的舊鞋、燃燒到變形的酒瓶、從天而降的叉子、插著叉子的蘋果,還有像骷髏頭似的切開的面包。
這件作品反映了米羅對西班牙不幸遭受變故的痛感和厭惡,同時,米羅自己也正面臨著財務危機,食不果腹是太平常的事了。他曾說過,這張畫幾乎是他在餓到發昏的狀態下完成的。
出于生活的壓力和內心的絕望,米羅憤怒地拿起畫筆,創作大量野蠻的繪畫來宣泄自己的情緒,以野蠻的繪畫來對抗災難和死亡。
(二)絕望中的希望——以《星座》組畫為例
1.情感表現
為了躲避戰爭,米羅來到巴爾瑪生活。午飯后,陽光透過彩色玻璃,一縷一縷地喚醒著沉睡的黑暗。米羅就坐在哥特式的大教堂里,聽著風管琴的排練,想象著那些奇妙的圖案。
這時的米羅會有意識地避開現實,尋找精神上的烏托邦。他開始接觸巴赫和莫扎特的音樂,尤其是巴赫。巴赫信仰基督教,在他的音樂中,米羅能夠短暫地逃離塵世。他開始描繪天上的星星,“這些可以領悟的形象,從極高的空間與我們保持聯系,它們的光輝不久就驅除掉了折磨人的陰風和黑夜。”[3]許是星星的神秘,許是月亮的朦朧,又或是高空的莫測,都啟發著米羅在這黑暗中始終追求心靈中的那片凈土。
2.內容分析
《星座》組畫是米羅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這組作品共23幅,均為小幅的水彩畫,其曾被藝術史學家稱贊為“藝術偶爾賦予的奇跡之一”。這組畫的畫面中經常出現星星、夜晚、地球、眼睛、梯子、孩童、女人、鳥,以及一些線條。米羅把這些復雜的圖形進行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以精密又嚴格的構圖安排到畫面中。比如把女人作為中心形象安排在畫面中間,周圍被一些熱烈活潑、輕靈小巧的符號所包圍。他主動改變了各元素之間的比例,使畫面更加均衡。不難看出,米羅的創作并不是純粹的“無意識”,而是經思考過后的“無意識”。
《星座》組畫中多用薄而柔和的淺色背景,卻用純度很高的色彩來表現形象,使那些標志性的形象從畫面中跳脫出來。米羅也是在這一時期形成了自己的專屬語言符號系統,繪畫風格逐漸成熟和穩定。
五、二戰后——率真沖動的自由畫
(一)精細化——以《夜間的女人》為例
二戰結束后,米羅不必四處逃亡,因此,他又拿起了畫筆,在先前畫面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探索。他還是保持著自己的風格,但畫面傳達的內容不再與戰爭有關,他開始繪制一些天真、質樸的形象。
內心的安定使他靜下來,重新思考戰前的細密畫風。在《小丑的狂歡節》中,米羅的精細體現在對物體的處理上,他反復修改線條、不斷調整造型,將豐富的物體安排到畫面合適的位置。而在1950年《夜間的女人》這幅畫中,他的精細更多地體現在對背景的處理上,仔細觀察能看到綠色、黃色、紅色等顏色之間的過渡。《白手套》的背景也不單一,但它只是在單一的藍色中有變化。此外,《夜間的女人》的背景不僅有顏色的變化,還有技法的變化。米羅除了用畫筆涂之外,還用到了刮、擦的手法,給背景加上紋理,從而使作品看起來更加華麗。
(二)粗獷化——以《夜晚的女人和鳥》為例
受“自動繪畫”的影響,米羅晚年的創作更加聽從他的內心。從《夜晚的女人和鳥》這幅畫我們可以看到,米羅在上顏料時出現了很多黑色和白色的飛濺,滴落、流淌、四散的顏料也讓這幅畫更具感染力。這一時期的米羅是激情的、自由的、奔放的,他不再考慮其他的禁錮,純粹地體會著繪畫帶來的歡愉。
六、結語
米羅是一位偉大的超現實主義畫家。雖少年時被認為“罕見的愚笨”,但他的天賦與才華終會顯露鋒芒,他獨具一格的畫風在西班牙乃至世界藝術史上都是一顆耀眼的明珠。米羅美術館的策展人霍爾迪·克拉韋羅曾說:“米羅的畫好玩、平易近人,而且永遠有趣。他將女人、鳥和星星賦予象征意義,把它們變成充滿色彩的形狀。”米羅以他獨特的視角創造并建立出了一個奇妙的世界,與此同時,他能夠激發那些與他相仿的、懷揣著開放和自由精神且愿意共同進入該世界的人們的想象力。
米羅在超現實主義時期的繪畫風格始終如一而又變化多樣,本文以二戰為分割點,簡單分析了其神秘抽象、怪異扭曲、率真沖動這三種風格。米羅在簡與繁之間摸索著、在虛與實之間穿梭著,不斷顛覆著人們對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刻板印象。
他曾向人們表明:“真正重要的是使靈魂赤裸裸地顯現出來。”[4]靈魂能夠包羅這個世界所有的喜怒哀樂,能動地反映著人類社會。米羅做到了,不論生活如何,他都能保持初心,堅持用新的眼光、新的視角去看待這個世界。
參考文獻:
[1][英]馬修·蓋爾.達達與超現實主義[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21.
[2][瑞士]沃爾夫林.藝術風格學:美術史的基本概念[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德]瓦爾特·赫斯.歐洲現代畫派畫論選[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
[4][英]De Agostini出版公司.米羅[M].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02.
作者簡介:
周姝礽(2003—),女,漢族,江蘇無錫人。浙江外國語學院藝術學院2021級本科生,研究方向:藝術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