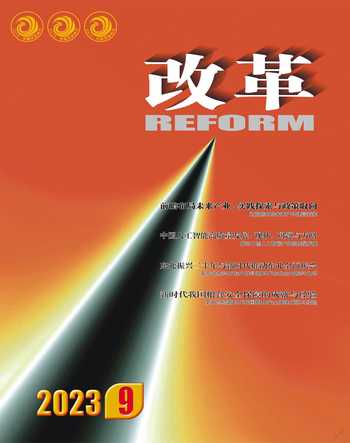新時代我國糧食安全保障的成就與經(jīng)驗
摘?? 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針對耕地數(shù)量減少和質(zhì)量下降、種業(yè)“卡脖子”、農(nóng)業(yè)科技“瓶頸”、種糧比較收益下降等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我國糧食生產(chǎn)基本面持續(xù)向好,實現(xiàn)了“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供應(yīng)保障能力不斷增強,實現(xiàn)了“產(chǎn)得出、運得走、供得上”;產(chǎn)能基礎(chǔ)更加穩(wěn)固,實現(xiàn)了“藏糧于地、藏糧于技”;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成效顯著,實現(xiàn)了“吃得飽、吃得好”;綜合生產(chǎn)能力明顯提升,實現(xiàn)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nèi)”。取得這些重大成就的基本經(jīng)驗是:發(fā)揮制度優(yōu)勢構(gòu)建糧食安全黨政同責體制機制,適應(yīng)國情把解決人民吃飯問題作為頭等大事,緊盯耕地和種子兩個要害夯實糧食安全根基,把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作為糧食安全保障的關(guān)鍵支撐,堅持系統(tǒng)觀念全方位構(gòu)筑糧食安全保障體系。未來要在守住糧食安全底線的基礎(chǔ)上不斷提高發(fā)展質(zhì)量,堅持自力更生和擴大開放更好結(jié)合,做好穩(wěn)產(chǎn)保供和節(jié)約利用雙提升,創(chuàng)新機制保障涉糧主體必要的經(jīng)濟利益和公共責任,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推動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建設(shè)。
關(guān)鍵詞:糧食安全;國家糧食安全戰(zhàn)略;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中圖分類號:F32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543(2023)09-0099-11
糧食是國家發(fā)展的基礎(chǔ)物資,糧食安全關(guān)系到國家安全、社會穩(wěn)定和經(jīng)濟發(fā)展,更是人口大國最大的民生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始終把糧食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把保障糧食安全作為穩(wěn)住國內(nèi)基本盤、應(yīng)對外部不確定性沖擊、把握經(jīng)濟發(fā)展主動權(quán)的重要抓手。面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和各種風險因素凸顯的現(xiàn)實,我國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nèi)、確保產(chǎn)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zhàn)略,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把國家糧食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高度,強調(diào)“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為構(gòu)建更高層次、更高質(zhì)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xù)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一、相關(guān)文獻綜述
20世紀70年代初,由于出現(xiàn)了世界性糧食危機,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提出了糧食安全概念。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因食物匱乏遭受饑餓和營養(yǎng)不良威脅,糧食安全保障問題研究主要集中于糧食自給、產(chǎn)量提升,主要解決“吃不飽”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糧食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人們開始關(guān)注質(zhì)量安全,力求在數(shù)量安全基礎(chǔ)上實現(xiàn)“吃得好”。黨的十八大以來,糧食結(jié)構(gòu)性過剩和有效供給不足成為主要矛盾,如何堅守數(shù)量不減、質(zhì)量提升,確保“吃得飽”與“吃得好、吃得健康”成為新課題。
基于數(shù)量保障的糧食安全問題及風險防范研究一直是學術(shù)界關(guān)注的重點。在糧食絕對短缺時期,糧食安全主要目標是讓大多數(shù)人吃飽,并為工業(yè)化積累資金。數(shù)量安全始終是人口大國糧食安全的必然條件[1],要通過產(chǎn)量、生產(chǎn)力的提高和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構(gòu)建糧食數(shù)量安全的自給體系。雖然我國完全有能力實現(xiàn)自給,但耕地減少、技術(shù)能力不強、基礎(chǔ)設(shè)施不完善對糧食單產(chǎn)提升影響較大[2],飼料和工業(yè)用糧大幅增長也使糧食安全總體水平不容樂觀,必須實施有力度的農(nóng)業(yè)政策[3],集中力量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靠中國供給解決中國需求,靠中國資源解決中國問題[4-5]。同時,要精準把控“憂患程度”,避免陷入“憂患陷阱”[6],將糧食安全放在全球農(nóng)業(yè)大開放環(huán)境中審視[7]。
隨著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的提高和經(jīng)濟社會的不斷發(fā)展,“保障數(shù)量提升質(zhì)量”的糧食安全保障機制成為重要的研究內(nèi)容。一方面,糧食安全不再單純是總量問題,而且是質(zhì)量問題[8]和結(jié)構(gòu)問題[9-10]。另一方面,要著重解決好誰來種糧、靠什么種糧、種什么糧的問題[11-12]。因此,糧食政策要圍繞“保產(chǎn)量、提質(zhì)量”作出適應(yīng)性調(diào)整,以區(qū)域分工合作和市場導向為基礎(chǔ),嚴格保護糧食生產(chǎn)資源,探索“不與人爭糧,不與糧爭地”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模式,完善糧食主產(chǎn)區(qū)利益補償機制和農(nóng)戶種糧的內(nèi)生機制[13-14],確保優(yōu)質(zhì)要素投入糧食生產(chǎn)[15],提升糧食和食物有效供給水平和質(zhì)量,與時俱進地推進糧食安全治理[16],更好地滿足人們對糧食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需求。
新發(fā)展格局下為了有效應(yīng)對各種風險沖擊,糧食安全要既保數(shù)量又保質(zhì)量,其關(guān)鍵還在供需兩側(cè)。在供給側(cè),糧田不種糧、農(nóng)戶不種田、高成本低效益、供需匹配錯位等風險需引起重視[17-18],并且氣候、疫情、地緣政治等風險因素使糧食安全問題更復(fù)雜[19],必須確保地方抓糧和農(nóng)民種糧不吃虧,穩(wěn)住糧食基本盤。在需求側(cè),飲食向多元、營養(yǎng)、健康演變,但多重因素導致糧食安全與營養(yǎng)脆弱,亟待發(fā)揮好國內(nèi)大市場優(yōu)勢,確保質(zhì)量安全,讓人們吃得放心。同時,要密切關(guān)注全球因素的影響,防范糧食供應(yīng)鏈風險[20]。糧食安全涉及生產(chǎn)、消費、分配、流通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需要堅持系統(tǒng)思維,強調(diào)風險管控[21],不斷深化對糧食安全含義、機制和政策的理解,壓實供應(yīng)鏈全過程各主體的責任,協(xié)同保障糧食安全。
已有研究為本文提供了卓有價值的借鑒,也促使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進一步完善糧食安全保障問題的研究:第一,在當前全球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zhàn)的背景下,全面總結(jié)新時代我國糧食安全保障取得的重大成就,對于深刻理解我國糧食安全戰(zhàn)略的時代價值和對世界糧食安全的貢獻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第二,立足我國人多地少、資源要素約束明顯等現(xiàn)實問題,分析我國實施的一整套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體系和形成的制度經(jīng)驗,對于更好地闡釋我國糧食安全保障的政策創(chuàng)新過程和內(nèi)在邏輯大有裨益。第三,從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的要求出發(fā),提出未來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建議,為構(gòu)建糧食安全保障長效機制提供策略思路。
二、新時代我國糧食安全面臨的問題及政策實施
我國是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發(fā)展中大國,糧食安全不僅存在人多地少的壓力,而且在種業(yè)、農(nóng)業(yè)科技、種糧收益等方面也存在許多短板、風險和隱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既保數(shù)量,又保多樣、保質(zhì)量”的政策和舉措,有效地解決了糧食安全面臨的各種問題,牢牢守住了國家糧食安全底線,依靠自己的力量很好地解決了14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
(一)針對突出的耕地問題實施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我國現(xiàn)有耕地面積為19.14億畝,僅占世界耕地總面積的7.37%。此外,我國人均耕地少、高質(zhì)量耕地少、后備資源少。2022年,我國人均耕地面積為1.36畝。全國耕地質(zhì)量較高的一等、二等、三等耕地僅占耕地總面積的27.3%,丘陵山區(qū)耕地面積占了耕地總面積的50%以上,許多還是“斗笠田”“巴掌田”。我國耕地后備資源只有8 000萬畝左右,93.2%的耕地后備資源以荒草地、鹽堿地、內(nèi)陸灘涂和裸地為主,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經(jīng)濟欠發(fā)達地區(qū),呈現(xiàn)破碎零散狀態(tài),土質(zhì)和地形條件差,受水資源制約較為明顯。總體而言,我國糧食生產(chǎn)受到資源環(huán)境的剛性約束較強,耕地保護壓力較大。
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落實和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加大力度推進高標準農(nóng)田建設(shè)”等措施,繼續(xù)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此后,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將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作為最突出的內(nèi)容加以規(guī)定。從政策制度和實施過程來看,我國一方面強調(diào)耕地數(shù)量的保護,通過實行耕地保護黨政同責,由中央和地方簽訂耕地保護目標責任書,作為剛性指標實行嚴格考核、一票否決、終身追責,確保耕地數(shù)量;另一方面,更加關(guān)注耕地質(zhì)量保護和提升,大力推進高標準農(nóng)田建設(shè),強調(diào)節(jié)約集約用地。不僅如此,還將高標準農(nóng)田建設(shè)情況納入地方各級政府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內(nèi)容,擴大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fù),推進耕地數(shù)量、質(zhì)量、生態(tài)“三位一體”保護,切實保證了耕地數(shù)量不減少、質(zhì)量有提高。
(二)面對種業(yè)“卡脖子”難題不斷深化種業(yè)體制機制改革
我國種業(yè)企業(yè)數(shù)量多、規(guī)模小、競爭力弱。2019年,我國納入統(tǒng)計、有種子生產(chǎn)經(jīng)營許可證的企業(yè)數(shù)量為6 393家,規(guī)模小于3 000萬元的企業(yè)占比超過65%。玉米是我國第一大糧食品種,但在東北、黃淮海等主產(chǎn)區(qū)大多選種的是國外種子[22]。盡管我國農(nóng)作物良種覆蓋率穩(wěn)定在96%以上,但是我國小麥單產(chǎn)比世界最高水平低37.0%、稻谷單產(chǎn)低15.7%、玉米單產(chǎn)低40.0%[23]。我國育種研發(fā)投入嚴重不足,80%以上的農(nóng)業(yè)科技投入用在了應(yīng)用技術(shù)上[24],且我國種業(yè)科研攻關(guān)組織方式比較分散,大多以“小作坊”形式存在,研究團隊之間存在親本來源單一、育種目標雷同、低水平重復(fù)等現(xiàn)象,在生物育種有關(guān)的基因編輯、轉(zhuǎn)基因、智能育種等前沿技術(shù)上仍處于“跟跑”狀態(tài)。此外,我國種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和商業(yè)化育種體系與國家種業(yè)安全的要求不相匹配,科研成果權(quán)益分配機制難以對種業(yè)研發(fā)、育種人員形成有效的激勵。
種業(yè)安全關(guān)乎糧食安全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穩(wěn)產(chǎn)保供,是農(nóng)業(yè)強國最基本、最核心的基礎(chǔ)。為了不斷深化種業(yè)體制機制改革,提高種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我國通過實施一系列種業(yè)改革政策,為國家糧食安全提供了制度保障。總體來看,這些政策發(fā)揮了三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推動種業(yè)體制改革,激發(fā)種業(yè)創(chuàng)新活力。我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guī)、中央“一號文件”、國家各部委和各省(區(qū)、市)相關(guān)政策,保障、推動、深化種業(yè)體制機制改革。尤其是深入推進種業(yè)領(lǐng)域科研成果權(quán)益分配改革,極大地激發(fā)了種業(yè)創(chuàng)新活力。第二,強化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主體地位,建立以企業(yè)為主體的育種創(chuàng)新體系。國家高度重視強化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主體地位,通過財政、金融、稅收等政策引導各種創(chuàng)新要素向企業(yè)集聚,推動開展農(nóng)業(yè)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攻關(guān)。第三,加大基礎(chǔ)科研投入,推動國家良種重大科研攻關(guān)和自主創(chuàng)新。扶持和支持種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育繁推”一體化創(chuàng)新聯(lián)盟等科技創(chuàng)新力量,推動種業(yè)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攻關(guān)和創(chuàng)新能力提升。
(三)為突破農(nóng)業(yè)科技“瓶頸”制約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zhàn)略
盡管2022年我國農(nóng)業(yè)科技貢獻率達到62.4%,但我國的農(nóng)業(yè)科技水平,尤其是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例如,我國農(nóng)機裝備低端化、同質(zhì)化問題仍較為突出,大型高端農(nóng)機、適合不同耕地規(guī)模以及丘陵山區(qū)的農(nóng)業(yè)機械研發(fā)應(yīng)用水平不高,集成配套的全程機械化技術(shù)體系還不健全。農(nóng)業(yè)機械專用傳感器、轉(zhuǎn)向橋及其懸浮系統(tǒng)、無級變速器等核心技術(shù)和關(guān)鍵零部件基本依賴進口,亟待解決“卡脖子”問題和突破“瓶頸”技術(shù)。云計算、大數(shù)據(jù)、物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等與農(nóng)機裝備制造業(yè)、農(nóng)業(yè)信息化、節(jié)水灌溉技術(shù)的結(jié)合,在我國還遠落后于發(fā)達國家。
保障糧食安全,建設(shè)農(nóng)業(yè)強國,根本出路在科技。長期以來,我國糧食生產(chǎn)面臨耕地流失、人口增加、城市化擴張、水資源短缺壓力,亟待通過提高農(nóng)業(yè)科技支撐能力化解各種問題和矛盾。為此,我國出臺了大量政策加快農(nóng)業(yè)科技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這些政策在良種、機械、灌溉、化肥農(nóng)藥、精耕細作等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一是推行良種化,包括對主要農(nóng)作物優(yōu)良品種的培育和推廣,提高良種覆蓋率。二是推進農(nóng)業(yè)機械化,加快農(nóng)機等裝備研發(fā),提高農(nóng)機等裝備水平,發(fā)展農(nóng)機等專業(yè)社會化服務(wù),促進農(nóng)業(yè)先進適用技術(shù)到田到戶,通過機械化提升糧食生產(chǎn)效率。三是加大水利建設(shè),構(gòu)建“系統(tǒng)完備、安全可靠、集約高效、綠色智能、循環(huán)通暢、調(diào)控有序”的國家水網(wǎng),實施區(qū)域規(guī)模化高效節(jié)水灌溉行動,推廣先進適用節(jié)水灌溉技術(shù)。四是扎實推進化肥農(nóng)藥減量使用,深入開展測土配方施肥、水肥一體化、生物防治、精準施藥等技術(shù)的應(yīng)用,實現(xiàn)化肥農(nóng)藥使用量負增長。五是推廣精耕細作技術(shù),包括高產(chǎn)高效栽培與耕作技術(shù)。因地制宜開展生產(chǎn)要素、農(nóng)業(yè)技術(shù)、種植模式的優(yōu)化組合,通過精耕細作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讓農(nóng)民用最好、最實用的技術(shù)種出更多、更好的糧食。
(四)因應(yīng)種糧比較收益下降趨勢多策并舉調(diào)動種糧積極性
隨著農(nóng)業(yè)投入品成本的不斷攀升,糧食價格相對于其他商品一直都比較穩(wěn)定,使得耕地的直接經(jīng)濟價值不斷減少,糧食生產(chǎn)的高成本、低效益特征較為明顯。2016—2020年,種植水稻、小麥與玉米等主要糧食作物的年平均凈利潤為-32.35元/畝,農(nóng)戶“倒貼式”參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制約了農(nóng)民的種糧積極性。許多農(nóng)民通過非農(nóng)務(wù)工或者“非糧化”增加收入,以致出現(xiàn)農(nóng)戶不種田、糧田不種糧的狀況,一些地方季節(jié)性撂荒、全年性撂荒甚至長年撂荒現(xiàn)象較為突出。糧食主產(chǎn)區(qū)貢獻了全國約75%的糧食產(chǎn)量和80%的商品糧,但糧食主產(chǎn)區(qū)的省均財政收入低于主銷區(qū)的70%,主產(chǎn)區(qū)人均財政支出約是主銷區(qū)的56.4%,且差距有拉大的趨勢[25]。這種局面不僅影響了糧食主產(chǎn)區(qū)政府抓糧的積極性,而且給國家糧食安全帶來了隱患。
為了確保農(nóng)民種糧有錢賺、地方抓糧不虧本,我國從財政補貼、金融支持、糧食價格、農(nóng)業(yè)保險、防災(zāi)減災(zāi)等方面不斷加大糧食生產(chǎn)支持力度。第一,通過增加補貼規(guī)模,向主產(chǎn)區(qū)、優(yōu)勢產(chǎn)區(qū)集中,向新型生產(chǎn)經(jīng)營主體傾斜。第二,通過“三補合一”改革,支持耕地地力保護和農(nóng)業(yè)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第三,通過完善玉米、大豆生產(chǎn)者補貼以及稻谷、農(nóng)機購置和作業(yè)、耕地輪作等補貼措施讓農(nóng)民種糧有收益。第四,通過落實好主產(chǎn)區(qū)利益補償,增加對商品糧生產(chǎn)大省和糧油豬生產(chǎn)大縣的獎勵補助,提高中央、省級財政對主要糧食作物保險的保費補貼比例,調(diào)動地方抓糧積極性。第五,通過增加農(nóng)業(yè)綜合開發(fā)財政資金投入、加大財政轉(zhuǎn)移支付力度、提高農(nóng)業(yè)綠色發(fā)展補貼和社會化服務(wù)補助等措施,建立健全調(diào)動“兩個積極性”的長效機制,確保“多種糧、種好糧”。
(五)防范“只想吃飯、不想種糧”風險蔓延,壓實各方糧食安全責任
受利益、財力、績效等因素驅(qū)動,部分糧食主產(chǎn)區(qū)、產(chǎn)銷平衡區(qū)和主銷區(qū)對糧食生產(chǎn)的重視程度越來越低,糧食發(fā)展的區(qū)域矛盾突出。近年來,我國主產(chǎn)區(qū)中糧食凈調(diào)出的省份數(shù)量在減少,2022年僅有黑龍江、河南、吉林、內(nèi)蒙古、安徽5個省區(qū)為糧食凈調(diào)出省。而且,有些產(chǎn)銷平衡區(qū)的糧食自給率已經(jīng)下降至58%,主銷區(qū)的糧食平均自給率已經(jīng)下降至24%[26]。因此,要防范“只想吃飯、不想種糧”風險,謹防糧食生產(chǎn)滑坡。保障糧食安全,既要盯緊糧食主產(chǎn)區(qū),又要盯住糧食產(chǎn)銷平衡區(qū)和主銷區(qū);不僅要提高主產(chǎn)區(qū)糧食綜合生產(chǎn)能力,而且要切實穩(wěn)定和提高主銷區(qū)糧食自給率,同時確保產(chǎn)銷平衡區(qū)糧食基本自給。
在這種復(fù)雜狀況下,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各地區(qū)、各方面要共同努力。第一,明確中央和地方的糧食安全責任與分工,地方政府要在耕地保護、用途管制、質(zhì)量提升、高標準農(nóng)田建設(shè)、糧食收儲、糧食流通等方面切實擔負起糧食安全保障重任。第二,壓實主產(chǎn)區(qū)、主銷區(qū)、產(chǎn)銷平衡區(qū)責任,明確主產(chǎn)區(qū)要建設(shè)糧食生產(chǎn)核心區(qū)、建設(shè)確保口糧安全的高標準農(nóng)田、發(fā)展糧食深加工,不斷提高糧食綜合生產(chǎn)能力。主銷區(qū)要確立糧食面積底線、保證一定的口糧自給率,要深化同主產(chǎn)區(qū)的合作,推動形成糧食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鏈體系,提升糧食安全綜合保障能力。產(chǎn)銷平衡區(qū)要承擔穩(wěn)定糧食生產(chǎn)的責任。第三,強化農(nóng)業(yè)社會化服務(wù)組織的責任,將現(xiàn)代生產(chǎn)要素導入農(nóng)業(yè)。依靠農(nóng)業(yè)社會化服務(wù)組織的引領(lǐng)帶動,提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流通的科技水平和效率。第四,突出糧食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多主體責任,構(gòu)建從農(nóng)田到餐桌的跨區(qū)域完整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確保糧食“產(chǎn)得出、運得走、供得上、買得到”。第五,實施全面節(jié)約戰(zhàn)略,抓好“產(chǎn)購儲運加銷”各個環(huán)節(jié)的減損工作,強化糧食安全教育,有效降低糧食損耗。
三、新時代我國糧食安全保障取得的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nèi)、確保產(chǎn)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zhàn)略,使我國糧食生產(chǎn)持續(xù)增產(chǎn)提質(zhì)、保供穩(wěn)價有力有效,糧食供給結(jié)構(gòu)不斷優(yōu)化,糧食流通現(xiàn)代化水平顯著提升,糧食安全“壓艙石”作用更加穩(wěn)固,為促進我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和國家長治久安作出巨大貢獻,也為世界各國解決糧食安全難題提供了中國經(jīng)驗、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一)糧食生產(chǎn)持續(xù)向好,實現(xiàn)了“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糧食總產(chǎn)量長期處于6億噸以上高位水平,保持供求基本平衡。我國糧食總產(chǎn)量自2012年躍上6億噸臺階后,一直在6億噸以上的高位水平不斷增長。2015年,我國糧食總產(chǎn)量躍上6.5億噸新臺階,此后連續(xù)8年保持在6.5億噸以上,2022年再創(chuàng)新高,超過6.8億噸。在全球糧食危機,尤其是國內(nèi)糧食消費需求剛性增長態(tài)勢延續(xù)、資源環(huán)境“硬約束”趨緊狀態(tài)下[14],我國糧食生產(chǎn)連年豐收,實現(xiàn)了“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三大糧食品種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糧食單產(chǎn)顯著增加。稻谷、小麥和玉米是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傳統(tǒng)三大品種,2022年全國稻谷、小麥和玉米產(chǎn)量分別比2012年增長了2.06%、14.22%和33.20%,其中,玉米牢牢占據(jù)我國第一大糧食作物品種位置,為筑牢我國糧食安全根基作出較大貢獻。高產(chǎn)作物玉米的擴種,使糧食單產(chǎn)顯著增加。2022年全國糧食作物單產(chǎn)386.8公斤/畝,比2012年增產(chǎn)33.8公斤/畝,增長9.58%。
人均糧食產(chǎn)量超過國際公認的糧食安全線,實現(xiàn)糧食自給。2012年我國人均糧食產(chǎn)量達到453.3公斤,比國際上公認的糧食安全線高出13.33%。2022年,我國人均糧食產(chǎn)量達到486.1公斤,比2012年增長7.24%。我國谷物自給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水稻和小麥完全自給,實現(xiàn)了中國人的飯碗不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飯碗里主要裝的是中國糧的目標。
(二)糧食供應(yīng)保障能力不斷增強,實現(xiàn)了“產(chǎn)得出、運得走、供得上”
在全面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國家糧食安全戰(zhàn)略下,糧食主產(chǎn)區(qū)、主銷區(qū)、產(chǎn)銷平衡區(qū)千方百計穩(wěn)面積穩(wěn)產(chǎn)量,不斷加強糧食生產(chǎn)功能區(qū)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保護區(qū)建設(shè),確保“產(chǎn)得出”。2022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17.75億畝,比2012年增加1.06億畝,增長6.35%,使糧食生產(chǎn)得到保障。
我國糧食流通體系不斷完善,目前基本形成節(jié)點支撐、樞紐引領(lǐng)、通道順暢的糧食物流骨干網(wǎng)絡(luò),形成公路、鐵路、水路相協(xié)調(diào)的多式聯(lián)運格局,糧食倉儲設(shè)施、運輸工具和集裝設(shè)備高效匹配與共享共用能力不斷增強,糧食物流效率和一體化組織水平穩(wěn)步提升,確保“運得走”。2020年,我國省內(nèi)糧食物流量達2.92億噸,跨省糧食物流量達2.86億噸。
糧食儲備和應(yīng)急體系逐步健全,糧食產(chǎn)銷關(guān)系順暢,確保“供得上”。我國糧食倉容規(guī)模不斷增加,2018年全國標準糧食倉房倉容已達6.7億噸,確保了政府糧食儲備數(shù)量充足、質(zhì)量良好、儲存安全。目前,我國的中央、省、市、縣四級糧食應(yīng)急預(yù)案體系已經(jīng)初步形成,應(yīng)急供應(yīng)網(wǎng)點遍布城鄉(xiāng)街道社區(qū),形成由都市區(qū)1小時、周邊城市3小時、城市群5小時構(gòu)成的“全國糧食135應(yīng)急保障圈”,確保了糧食消費需求能夠得到及時滿足。
(三)糧食產(chǎn)能基礎(chǔ)更加穩(wěn)固,實現(xiàn)了“藏糧于地、藏糧于技”
糧食生產(chǎn)的根本在耕地,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是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的物質(zhì)根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全面加強耕地用途管制,開展永久基本農(nóng)田核實整改,改革占補平衡制度,建立耕地動態(tài)監(jiān)測監(jiān)管機制,堅決遏制耕地“非農(nóng)化”、基本農(nóng)田“非糧化”。在實踐中,各地高度重視高標準農(nóng)田建設(shè)、黑土地保護性耕作、耕地可持續(xù)利用和發(fā)展。目前,累計建成高標準農(nóng)田10億畝,新增產(chǎn)能相當于新增2.75億畝耕地。
糧食生產(chǎn)的基礎(chǔ)在種子,我國糧食連年豐收,良種發(fā)揮了重要作用。2022年,我國國家級制種基地總數(shù)量達到216個,保障了70%以上用種需要。目前,我國農(nóng)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超過95%,農(nóng)作物良種覆蓋率穩(wěn)定在96%以上,水稻、小麥、大豆全部為自主選育品種,小麥、水稻、玉米三大主糧基本實現(xiàn)良種全覆蓋,良種對糧食增產(chǎn)貢獻率超過45%,夯實了大國糧倉的根基和產(chǎn)能基礎(chǔ)。
(四)糧食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成效顯著,實現(xiàn)了“吃得飽、吃得好”
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嚴格糧食安全責任制考核,確保農(nóng)業(yè)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不斷深化。從糧食數(shù)量安全來看,通過產(chǎn)量、生產(chǎn)力的提高以及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構(gòu)建糧食數(shù)量安全的自給體系。同時,當前我國糧食安全不再單純是數(shù)量問題,而且是質(zhì)量問題,圍繞“保產(chǎn)量、提質(zhì)量”作出的適應(yīng)性政策調(diào)整,滿足了人們對糧食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需求。在實踐中,隨著國家糧食安全產(chǎn)業(yè)帶建設(shè)的不斷推進、優(yōu)質(zhì)糧食工程的深入實施、綠色高質(zhì)高效行動的大力開展,優(yōu)質(zhì)、綠色、安全糧油產(chǎn)品供給能力不斷增強,做到了“多產(chǎn)糧、產(chǎn)好糧”。
隨著農(nóng)業(yè)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性改革的推進,我國糧食質(zhì)量安全整體水平不斷提高。一方面,糧食的品種結(jié)構(gòu)不斷優(yōu)化,促進供需平衡向更高水平快速提升;另一方面,糧食的品質(zhì)不斷提升,糧食產(chǎn)業(yè)發(fā)展中面臨的質(zhì)量不優(yōu)、層次不高等突出問題逐步得到解決,保障了消費端“吃得飽、吃得好”。
(五)糧食綜合生產(chǎn)能力明顯提升,實現(xiàn)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nèi)”
黨中央始終把糧食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堅持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優(yōu)先發(fā)展,連續(xù)出臺中央“一號文件”部署“三農(nóng)”重點工作,不斷完善黨的強農(nóng)惠農(nóng)富農(nóng)政策體系,持續(xù)增加物資投入,加大科技創(chuàng)新力度,使糧食生產(chǎn)提質(zhì)增量效果突出,糧食綜合生產(chǎn)能力明顯提升。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嚴格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全面落實永久基本農(nóng)田特殊保護制度,加快推進高標準農(nóng)田建設(shè),穩(wěn)步推進種植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和休耕輪作制度,確保耕地“數(shù)量不減少、質(zhì)量不降低”,土地產(chǎn)出率不斷提升。農(nóng)田水利灌溉條件不斷改善,節(jié)水灌溉技術(shù)、科學施肥、綠色防控、綠色低碳生產(chǎn)技術(shù)得到推廣。農(nóng)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shù)從2012年的0.516提高到2021年的0.568,三大糧食作物化肥、農(nóng)藥利用率分別達到40.2%和40.6%,秸稈和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分別達到87%和76%。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不斷增強,大數(shù)據(jù)、物聯(lián)網(wǎng)等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在農(nóng)業(yè)中得到應(yīng)用,農(nóng)業(yè)技術(shù)裝備水平不斷提高,農(nóng)業(yè)科技貢獻率超過61%,農(nóng)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71%。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的發(fā)展帶動了標準化生產(chǎn)和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目前,各類農(nóng)業(yè)社會化服務(wù)組織服務(wù)小農(nóng)戶7 800萬戶,全國家庭農(nóng)場超過380萬個,平均經(jīng)營規(guī)模134.3畝。
四、新時代我國保障糧食安全的基本經(jīng)驗
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實現(xiàn)國家安全、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基礎(chǔ)。黨和國家始終將糧食安全放在十分重要的戰(zhàn)略位置,堅持發(fā)揮制度優(yōu)勢構(gòu)建糧食安全黨政同責體制機制,適應(yīng)國情把解決人民吃飯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緊盯耕地和種子兩個要害,堅持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的關(guān)鍵支撐作用,以系統(tǒng)觀念全方位構(gòu)筑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一)發(fā)揮制度優(yōu)勢構(gòu)建糧食安全黨政同責體制機制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切實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nóng)”工作的全面領(lǐng)導。糧食問題不能只從經(jīng)濟上看,必須從政治上看。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nóng)村工作會議上強調(diào),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扛起糧食安全的政治責任。糧食安全要實行黨政同責,“米袋子”省長要負責,書記也要負責,為落實糧食安全戰(zhàn)略奠定了堅實的制度保障。糧食安全是最重要的經(jīng)濟安全,是統(tǒng)籌發(fā)展和安全的首要任務(wù),這是國家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和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理論基礎(chǔ)和重要依據(jù)。
實踐表明,切實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nóng)”工作的全面領(lǐng)導,實行國家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和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把黨的組織優(yōu)勢、制度優(yōu)勢轉(zhuǎn)化為糧食安全治理優(yōu)勢、治理效能,是我國糧食安全保障最重要的經(jīng)驗。2015年1月發(fā)布的《國務(wù)院關(guān)于建立健全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強化糧食安全意識和責任、鞏固和提高糧食生產(chǎn)能力、切實保護種糧積極性、管好地方糧食儲備等工作,是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主要內(nèi)容。在全面總結(jié)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2021年《糧食流通管理條例》落實黨中央“糧食安全要實行黨政同責”的最新要求,首次在行政法規(guī)中明確規(guī)定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應(yīng)當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切實壓實地方黨委和政府的責任,這是黨中央總攬全局保障糧食安全的又一制度創(chuàng)新。
(二)適應(yīng)國情把解決人民吃飯問題作為頭等大事
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必須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解決好人民的吃飯問題。我國之所以能夠?qū)崿F(xiàn)社會穩(wěn)定、人心安定,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為了解決好人民吃飯問題,讓人民群眾吃得飽、吃得好、吃得放心,黨和國家將解決人民吃飯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作為發(fā)展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始終強調(diào)“要扛穩(wěn)糧食安全這個重任,確保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特別是糧食供給”,通過制定一系列符合世情、國情、農(nóng)情的糧食安全保障政策,使得我國糧食產(chǎn)量連續(xù)8年超過6.5億噸,穩(wěn)穩(wěn)地端牢了中國人的飯碗。
(三)緊盯耕地和種子兩個要害夯實糧食安全根基
我國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落實好耕地保護制度。一方面,在數(shù)量上確保基本農(nóng)田數(shù)量穩(wěn)定,堅決遏制耕地“非農(nóng)化”、防止“非糧化”。我國耕地面積占世界耕地面積的7.39%,卻要養(yǎng)活世界近22%的人口。因此,農(nóng)民可以“非農(nóng)化”,但耕地不能“非農(nóng)化”。另一方面,在耕地質(zhì)量的保護和提升上下功夫,確保“農(nóng)田就是農(nóng)田,而且必須是良田”,通過推進高標準農(nóng)田建設(shè),嚴格保護黑土地資源,提高耕地質(zhì)量,建成一大批旱澇保收、高產(chǎn)穩(wěn)產(chǎn)的優(yōu)質(zhì)良田。
種子是保障糧食安全的關(guān)鍵,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關(guān)鍵是實現(xiàn)中國糧用中國種。種業(yè)是國家戰(zhàn)略性、基礎(chǔ)性核心產(chǎn)業(yè),只有加快解決制約種業(yè)發(fā)展的關(guān)鍵問題,把種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源頭上筑牢國家糧食安全屏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種業(yè)發(fā)展,強調(diào)“必須把民族種業(yè)搞上去,集中力量破難題、補短板、強優(yōu)勢、控風險”,打贏種業(yè)翻身仗。在黨中央的堅強領(lǐng)導下,我國農(nóng)業(yè)用種安全總體有保障、風險可管控,為糧食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穩(wěn)產(chǎn)保供、增產(chǎn)提質(zhì)、高產(chǎn)高效作出重要貢獻。
(四)把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作為糧食安全保障的關(guān)鍵支撐
“解決吃飯問題,根本出路在科技”,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提高單產(chǎn)、挖掘潛力、防災(zāi)減損,全面提升土地產(chǎn)出率、勞動生產(chǎn)率和資源利用率。進入新時代,我國農(nóng)業(yè)科技不斷發(fā)展,聚焦確保糧食安全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有效供給,著力解決“夠不夠”“好不好”“強不強”問題。黨中央堅持農(nóng)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發(fā)展,為“種什么糧”“怎樣種糧”“產(chǎn)什么糧”插上了科技翅膀,為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加快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保障糧食安全提供了更加堅實的科技支撐。
當前,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搶占以信息技術(shù)、生物技術(shù)為特點的新一輪農(nóng)業(yè)科技革命的制高點,“作為一個農(nóng)業(yè)大國,我們絕不能落后”。面對人口多、耕地少、水資源匱乏的基本國情,我國始終重視推進種業(yè)科技創(chuàng)新,提高農(nóng)業(yè)物資技術(shù)裝備水平,加強農(nóng)業(yè)和科技的融合。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nóng)業(yè)科技呈現(xiàn)強勁發(fā)展勢頭,為實現(xiàn)農(nóng)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和保障糧食安全發(fā)揮了關(guān)鍵支撐作用。
(五)堅持系統(tǒng)觀念全方位構(gòu)筑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發(fā)展的“壓艙石”“穩(wěn)定器”,糧食安全問題既重要又復(fù)雜。然而,我國糧食安全基礎(chǔ)仍不穩(wěn)固,糧食安全形勢依然嚴峻,既要實現(xiàn)眼前的糧食產(chǎn)量穩(wěn)定,又要形成新的競爭力,注重可持續(xù)性;既要發(fā)揮市場機制作用,又要加強政府支持保護。為此,必須系統(tǒng)考慮國內(nèi)資源環(huán)境、供求格局和國際市場貿(mào)易條件,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nèi)、確保產(chǎn)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zhàn)略。
為了確保糧食安全,黨中央堅持系統(tǒng)觀念,全方位構(gòu)筑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第一,通過實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戰(zhàn)略,確保耕地數(shù)量不減、質(zhì)量提升,確保糧食穩(wěn)產(chǎn)增產(chǎn)、提質(zhì)增效、有效供給。第二,通過培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推進糧食生產(chǎn)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和綠色農(nóng)業(yè)發(fā)展。鼓勵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主體發(fā)揮聯(lián)農(nóng)帶農(nóng)作用,擴大規(guī)模、延長產(chǎn)業(yè)鏈、采用先進農(nóng)業(yè)技術(shù)和裝備,有效解決“誰來種地”“怎樣種地”問題。第三,通過完善農(nóng)業(yè)補貼和糧食價格機制,保障農(nóng)民種糧有錢賺。不斷增強政策的精準性、穩(wěn)定性、實效性,鼓勵農(nóng)民多產(chǎn)糧、產(chǎn)好糧。堅持并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注重發(fā)揮市場形成價格作用,做到“政策保本、經(jīng)營增效”。第四,通過完善糧食主產(chǎn)區(qū)利益補償機制和支持政策,保障主產(chǎn)區(qū)抓糧不吃虧。強化產(chǎn)糧大縣獎勵政策,加大轉(zhuǎn)移支付力度,保障主產(chǎn)區(qū)抓糧得實惠、有發(fā)展。第五,通過深化糧食收儲供應(yīng)安全保障制度改革,強化糧食收儲供應(yīng)安全保障體系建設(shè),確保儲備數(shù)量實、質(zhì)量好、調(diào)得動、用得上。第六,通過完善節(jié)糧減損機制,推進糧食生產(chǎn)、加工、儲運減損,營造全社會節(jié)糧減損的良好氛圍。
五、保障糧食安全、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的政策建議
展望未來,我國糧食安全保障要在統(tǒng)籌發(fā)展與安全視域下,基于我國國情多策并舉,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第一,在守住糧食安全底線的基礎(chǔ)上不斷提高發(fā)展質(zhì)量。一是守住糧食安全底線,防范大豆、油料等初級產(chǎn)品對外依存度過高可能帶來的風險。二是以科技創(chuàng)新促發(fā)展。盡快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攻關(guān)新機制,推進農(nóng)業(yè)種源、耕地質(zhì)量、農(nóng)業(yè)機械設(shè)備、農(nóng)業(yè)綠色投入品等關(guān)鍵領(lǐng)域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三是建立“多產(chǎn)糧多賺錢”的價格機制,激發(fā)農(nóng)民種糧積極性。可嘗試建立糧食收購價格梯度定價機制,將年度內(nèi)農(nóng)戶生產(chǎn)糧食的數(shù)量與價格梯度進行關(guān)聯(lián),根據(jù)不同區(qū)域?qū)嶋H情況設(shè)計方案,實現(xiàn)“誰種糧誰受益”,引導“小田變大田”,減輕季節(jié)性撂荒、耕地“非糧化”帶來的風險。四是開展農(nóng)業(yè)種質(zhì)資源普查工作,摸清底數(shù),建立種質(zhì)資源數(shù)據(jù)庫,推動實現(xiàn)種源自主可控。五是發(fā)展綠色生態(tài)農(nóng)業(yè),增強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和化解各種不確定性的能力,實現(xiàn)高質(zhì)量的糧食安全,滿足消費升級的需求。
第二,堅持自力更生增強風險應(yīng)對能力,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增強糧食供應(yīng)鏈韌性。一方面,要采取“長牙齒”的硬措施,堅持數(shù)量、質(zhì)量、生態(tài)并重,強化現(xiàn)有耕地的用途管制,切實做到“保數(shù)量、提質(zhì)量、挖潛力”。另一方面,要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以持續(xù)提升供給保障能力為目標,科學制定主銷區(qū)、產(chǎn)銷平衡區(qū)糧食種植規(guī)模底線,通過“飯碗一起端、責任一起扛”,增強自主供給和風險應(yīng)對能力。同時,要積極參與全球國際合作與貿(mào)易治理,提升我國的話語權(quán)和影響力,通過利用好國際市場,增強我國糧食及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韌性。當前尤其要促進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農(nóng)產(chǎn)品貿(mào)易合作,提升糧食供應(yīng)鏈關(guān)鍵節(jié)點的掌控能力。此外,要適應(yīng)城鄉(xiāng)居民對食物的多樣化、差異化需求,優(yōu)化糧食等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及進口布局。
第三,提高糧食綜合生產(chǎn)能力,推進全面節(jié)約戰(zhàn)略,做好穩(wěn)產(chǎn)保供和節(jié)約利用雙提升。一是通過建設(shè)國家糧食安全產(chǎn)業(yè)帶、推進高標準農(nóng)田建設(shè)、深入實施種業(yè)振興行動等措施,提高糧食綜合生產(chǎn)能力,使糧食安全成為我國經(jīng)濟社會行穩(wěn)致遠的基本保障。二是不斷創(chuàng)新支持政策,構(gòu)建穩(wěn)步提升“兩個積極性”的政策集合。對于農(nóng)戶,要重點做好糧食生產(chǎn)補貼、最低收購價制度、完全成本保險與收入保險的相互配合。對于糧食主產(chǎn)區(qū),要使財政獎補政策與促進糧食加工業(yè)發(fā)展的產(chǎn)業(yè)政策相互配合。三是增強節(jié)約意識,實施全面節(jié)約戰(zhàn)略。一方面,完善節(jié)糧減損激勵機制,提升節(jié)糧減損的邊際收益,促進糧食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各環(huán)節(jié)降低損失、損耗;另一方面,培育勤儉節(jié)約觀念,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四是堅持生態(tài)優(yōu)先、綠色發(fā)展,發(fā)展節(jié)水農(nóng)業(yè),推廣綠色生產(chǎn)技術(shù),促進農(nóng)業(yè)先進技術(shù)的引進、開發(fā)與應(yīng)用,提升糧食綜合生產(chǎn)能力和供給保障能力。
第四,保障糧食供應(yīng)鏈主體獲得必要的經(jīng)濟利益,賦予其必要的公共責任。首先,讓種糧農(nóng)民有收益,地方抓糧不吃虧。要堅持通過各種補貼、價格、保險等政策措施,確保種糧不吃虧、得實惠、有發(fā)展。其次,著重解決涉糧獲益低的問題,保障“產(chǎn)購儲運加銷”各環(huán)節(jié)的合理收益。激勵糧食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協(xié)同化、系統(tǒng)化、科技化、專業(yè)化發(fā)展,確保產(chǎn)得出、供得上、賣得好。再次,壓實地方黨委和政府的責任,提高政治站位,確保各地糧食播種面積和產(chǎn)量保持穩(wěn)定、穩(wěn)中有升。嘗試建立糧食主銷區(qū)對糧食主產(chǎn)區(qū)的責任補償基金,考慮糧食自給率或糧食消費量與生產(chǎn)量差額,按照合理適度的方式由主銷區(qū)對主產(chǎn)區(qū)進行責任補償,一方面緩解國家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將“飯碗一起端、責任一起扛”落到實處。最后,加強糧食安全責任宣傳,賦予“產(chǎn)購儲運加銷”各環(huán)節(jié)主體必要的公共責任,激勵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實施企業(yè)責任儲備,增強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韌性,確保關(guān)鍵時刻不“掉鏈子”,實現(xiàn)穩(wěn)產(chǎn)保供。
第五,發(fā)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加快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建設(shè)。一方面,要充分體現(xiàn)糧食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商品性,推動市場化改革,按市場需求、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需求調(diào)整糧食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和經(jīng)營體系,讓價格機制在解決糧田“非糧化”、耕地“非農(nóng)化”等問題中發(fā)揮作用,形成“愿意種、種得好、賣得好”的局面。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從如下方面著手:一是通過穩(wěn)定和提高農(nóng)民種糧收益預(yù)期,激發(fā)農(nóng)戶主動調(diào)整生產(chǎn)、優(yōu)化結(jié)構(gòu)、改進技術(shù)的積極性。二是通過提升農(nóng)業(yè)社會化服務(wù)水平,促進小農(nóng)戶與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有機銜接,降低農(nóng)業(yè)物化成本,提高糧食數(shù)量和質(zhì)量,提升種糧生產(chǎn)效率和效益。三是通過促進產(chǎn)銷協(xié)調(diào),發(fā)揮訂單農(nóng)業(yè)、就地加工、股份合作等利益聯(lián)結(jié)方式的作用,促進糧食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與價值鏈融合,實現(xiàn)優(yōu)糧優(yōu)價和糧食產(chǎn)業(yè)就地增值。另一方面,要深刻認識糧食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基礎(chǔ)性、戰(zhàn)略性和安全性,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聚焦提高糧食和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能力、加強儲備應(yīng)急管理、強化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韌性,切實發(fā)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激勵糧食安全利益鏈、供應(yīng)鏈、責任鏈融合,使社會各方在糧食安全問題上“有組織地負起責任”,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自主可控。
參考文獻
[1]李雪,呂新業(yè).現(xiàn)階段中國糧食安全形勢的判斷:數(shù)量和質(zhì)量并重[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21(11):31-44.
[2]姜長云.我國糧食供求平衡問題的現(xiàn)狀與展望[J].經(jīng)濟研究參考,2004(41):21-36.
[3]朱晶,李天祥,臧星月.高水平開放下我國糧食安全的非傳統(tǒng)挑戰(zhàn)及政策轉(zhuǎn)型[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21(1):27-40.
[4]韓長賦.全面實施新形勢下國家糧食安全戰(zhàn)略[J].求是,2014(19):27-30.
[5]張紅宇.牢牢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quán)[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21(1):14-18.
[6]倪國華,王賽男,JIN Yanhong.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糧食安全政策選擇[J].經(jīng)濟研究,2021(11):173-191.
[7]王曉君,何亞萍,蔣和平.“十四五”時期的我國糧食安全:形勢、問題與對策[J].改革,2020(9):27-39.
[8]黃季焜.對近期與中長期中國糧食安全的再認識[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21(1):19-26.
[9]鐘甫寧,向晶.人口結(jié)構(gòu)、職業(yè)結(jié)構(gòu)與糧食消費[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12(9):12-16.
[10]王濟民,張靈靜,歐陽儒彬.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糧食安全:成就、問題及建議[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18(12):14-18.
[11]何秀榮.國家糧食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20(6):12-15.
[12]高鳴,張哲晰.新時代走出“誰來種糧”困局的思路和對策[J].中州學刊,2022(4):36-42.
[13]羅必良,張露,仇童偉.小農(nóng)的種糧邏輯——40年來中國農(nóng)業(yè)種植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與未來策略[J].南方經(jīng)濟,2018(8):1-28.
[14]朱晶,臧星月,李天祥.新發(fā)展格局下中國糧食安全風險及其防范[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21(9):2-21.
[15]杜志雄.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J].紅旗文稿,2023(2):29-32.
[16]羅萬純.中國糧食安全治理:發(fā)展趨勢、挑戰(zhàn)及改進[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20(12):56-66.
[17]仇煥廣,李登旺,宋洪遠.新形勢下我國農(nóng)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的轉(zhuǎn)變——重新審視我國傳統(tǒng)的“糧食安全觀”[J].經(jīng)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4):11-19.
[18]杜志雄,韓磊.供給側(cè)生產(chǎn)端變化對中國糧食安全的影響研究[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20(4):2-14.
[19]青平.構(gòu)建新型農(nóng)食系統(tǒng) 保障糧食與營養(yǎng)安全[J].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6):1-4.
[20]程國強,朱滿德.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糧食安全:趨勢、影響與應(yīng)對[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20(5):13-20.
[21]陳秧分,王介勇,張鳳榮,等.全球化與糧食安全新格局[J].自然資源學報,2021(6):1362-1380.
[22]李國英.國家糧食安全視角下中國種業(yè)安全隱憂及商業(yè)化發(fā)展路徑研究[J].改革與戰(zhàn)略,2022(2):1-10.
[23]韓磊.大食物觀下我國重要農(nóng)產(chǎn)品穩(wěn)產(chǎn)保供的現(xiàn)實困境與政策思路[J].當代經(jīng)濟管理,2023(4):1-10.
[24]張亨明,尹小貝.我國種業(yè)發(fā)展的現(xiàn)實困境及其破解之道[J].改革,2022(12):78-88.
[25]王一杰,邸菲,辛嶺.我國糧食主產(chǎn)區(qū)糧食生產(chǎn)現(xiàn)狀、存在問題及政策建議[J].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研究,2018(1):37-47.
[26]杜鷹.中國的糧食安全戰(zhàn)略(下)[J].農(nóng)村工作通訊,2020(22):17-21.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WANG Ke-sha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taken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the reduction of farmland, problems tha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ed industry, the "bottleneck"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decrease in comparative income from grain production. With the help of that, fundamentals of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goal of "no panic with grain in hand" has been realized; our capability for supply guarantee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hanced, and the goal of sufficient grain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supply has been realized; the foundation of grain capacity has been stabled, and the goal of "storing grain in the ground and storing grain in technology" has been realized;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as been made, and the goal of "having enough food and eating well" has been realized; and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goal of "food security based on domestic supply" has been realized.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achieving thes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s to leverag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to build a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food security, to adapt to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make solving the problem of people's food supply a top priority, to closely focus on the two key issues of farmland and seed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food security, to mak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a key support for food security, and to adhere to a systematic concept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system. In the future, while maintaining the bottom line of food security,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adhere to a better combination of self-reliance and expanding openness, do a good job of improving both stable production & supply and conservation & utilization, innovate mechanisms to ensure the necessar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of grain related entit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food security system through effective markets and meaningful governments.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food security system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糧食數(shù)量質(zhì)量雙安全的風險測度與協(xié)同共治機制研究”(22AGL026)。
作者簡介:王可山,北京物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