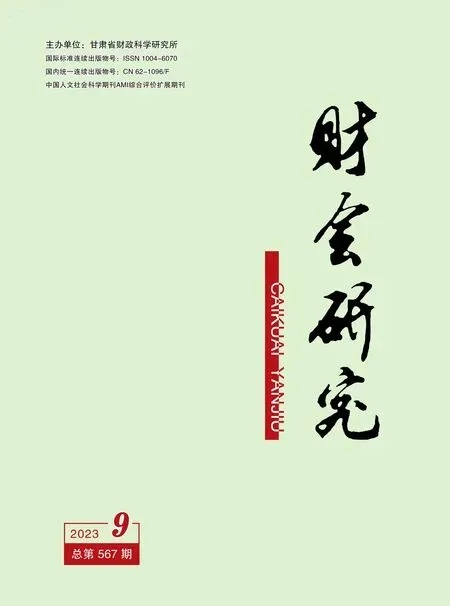項目治國視角下完善轉移支付政策體系研究
■/ 張凱強
一、項目制與項目治國
近年來,“項目制”和“項目治國”作為核心詞匯和研究主題的文章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內文獻中(于君博、童輝,2016;姬生翔,2016;周飛舟,2019),在建設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項目制治理模式成為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的延伸。項目制治理模式有效地拓展了科層制和市場機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項目治國”現象也成為研究的熱點和討論的焦點(曹龍虎,2016;陳家建,2017)。在2012年后,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網絡化不斷發展,國與國之間的依賴性和不確定性大幅增加,國內也面臨經濟改革有待深化、生態環境惡化、社會貧富分化等問題,面對國內外環境形勢,中央政府提出以國家治理現代化和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為目標。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到2035年,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包括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優化制度體系頂層設計,樹立統籌規劃和整體推進的改革思維,大力發揮項目制治理模式的優勢,系統性解決社會治理難題。
那么應該如何理解項目制的運作機理,如何理解項目制引起的社會治理的熱點呢?總體來說,可以分為兩條線索,一是項目制的運行范圍線索,即項目制運行所需要的制度環境,從企業到政府,從政府到社會,項目制的運用越來越廣泛;二是項目制的目標對象線索,即項目制運行的實施主體與目標的對象,從專項轉移支付制度到政府層級間的項目制,從政府層級間項目制到政府引導的社會合作的項目制,再到市場主體引導的項目制。項目制的運用范圍和目標線索越來越廣,文獻關注熱點也越來越廣泛。
在項目制治理模式的運行線索方面,首先,在企業視角下的項目制模式,國際項目管理協會對項目的定義為,項目是為創造獨特的產品、服務或成果而進行的臨時性工作。朱方偉等(2013)、杜亞靈等(2015)分別對戰略項目管理、工程項目管理的運用進行闡述,遲仁勇(2009)也指出,項目是臨時性、一次性、有限的任務,這是項目區別于其他常規活動和任務的基本標志。史普原(2015)將項目制的三個特點總結為臨時性、目標導向、新機構或新規劃。遲仁勇(2009)、朱方偉等(2013)、杜亞靈等(2015)文獻強調項目制的運行范圍主要為市場主體企業,即為企業視角下的項目管理機制,而史普原(2015)則將項目制運用到政府管理活動和目標中,即為政府治理下的項目制模式。其次,在政府視角下的項目制治理模式,使得“項目治國”現象展開廣泛討論,也使得一系列項目制文獻不斷拓展。折曉葉、陳嬰嬰(2011)基于“項目進村”案例來解釋項目制在不同政府級別間的運作機制和邏輯;渠敬東(2012)則分析項目制與單位制異同點,提出項目制是行政體制內的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周黎安(2014)、周雪光(2015)分別從行政發包制、“控制權”的理論視角解讀政府層級之間的運作和治理模式;焦長權(2019),苗大雷、王修曉(2022)則分別從科層制與項目制的組織行為關系、分稅制與項目制的制度演進、單位制與項目制的國家治理體制等視角來擴展和描述政府視角下的項目制運作機制。第三,以在政府視角下的項目制的運行為基礎,社會視角的項目制管理模式也逐步展開。王向民(2014)、沈費偉和張丙宣(2019)、吳月(2019)對社會組織的項目制治理模式進行描述和闡述,其中,社會組織的治理項目主要側重于與公共服務相關的項目,與之相隨的研究重點和核心是政府在該項目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此外,很多文獻則聚焦于社會組織對項目制治理模式在具體事項的運行機制,如管兵、夏瑛(2016)對政府購買服務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闡釋和說明。
隨著項目制治理模式在政府治理視角的不斷拓展,項目制的運用范圍和目標線索也越來越廣泛。在政府治理視角下,項目制的運行開端是專項轉移支付制度運行,隨后不斷擴展到層級政府和政府部門間的項目運作和執行。項目制具有高效性、目標性和協同性,使得其在政府和社會治理視角下發揮廣泛的積極作用,因此在政府層級之間、政府部門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得到推廣和使用。項目制治理模式一方面提高整個社會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一方面有利于彌補科層制、單位制、市場制等治理模式之間的交易成本和政策失靈。然而,項目制也有不足之處。項目通常是臨時性、一次性、有限的任務,而項目制治理模式依賴于科層制、單位制和市場制等治理模式來發揮作用。
總之,項目制運作是介于科層化與市場化之間的一種新型國家治理方式。這種治理方式與我國當前的行政體制結構特征相聯系,是調節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時也是統籌政府、市場主體、社會組織之間有序合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在項目制運作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并非僅源于項目制本身,而與項目制的類別及所處的行政體制環境有關。因此,通過強化項目設置的制度化、市場化與科層化運作,規范項目制的運行機制,項目制能夠在調動政府層級之間的積極性、發揮市場主體的能動性、提高國家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推動地方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二、不斷下降的專項轉移支付規模
轉移支付制度作為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重要內容,始于2015年,以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的政策設計不斷推出,從調整轉移支付結構到完善轉移支付與財政支出、財政收入關系,進一步規范和調整政府間的財政關系,發揮市場的競爭性作用和服務于中國高質量增長轉型。在2015和2016年,中央政府均提出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規范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的績效目標管理,以及優化和提高中央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辦法。在2018年2月,中央政府設立共同財政事權分類分檔轉移支付,推進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內劃分、整合、調控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范圍。在2018-2020年,中央政府依次穩步推進在醫療、教育、科技、交通運輸、生態環境、公共文化、自然資源和應急救援等各領域中的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在2021年和2022年,中央政府推出規范中央對農村綜合改革和繼續完善均衡性轉移支付的辦法條例,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在“十四五”時期和新發展格局下繼續優化轉移支付結構和發揮其經濟效應。
基于上述相關政策的推進,轉移支付的結構和規模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首先,轉移支付的規模不斷擴大,繼續促進和保證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在2002年、2017年和2021年,轉移支付總額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為28.4%、32.9%、33.5%,如圖1所示。其次,為優化轉移支付的結構,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占比大幅提高,專項轉移支付得到進一步清理整合。一是在2018年,中央政府設立共同財政事權分類分檔轉移支付,并將其歸為一般性轉移支付的統計指標,進一步將稅收返還數據指標與一般性轉移支付數據指標合并,該一般性轉移支付的資金規模占轉移支付總額的84.3%。二是專項轉移支付的資金項目已經從2013年的220項壓減到2018年的66項,2019年的預算分類指標中又進一步壓縮至22個,這強化了專項轉移支付的針對性、有效性。在2017年,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稅收返還占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總額的比重依次為54.0%、33.6%、12.4%,而2018年,該比重大幅調整為74.2%、8.9%、16.9%,如圖2所示。轉移支付的結構調整有利于進一步統籌資金管理,以區域發展事實為基礎,進一步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的占比,發揮地方政府的信息優勢,實現財政資金的合理配置,促進社會公平發展。三是在優化轉移支付政策的制度設計的基礎上,一系列規范轉移支付制度的執行和監督文件相繼實施。伴隨著2014年《預算法》的修訂,以及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條例》和2021年《進一步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相繼實施,轉移支付資金的預算執行、管理、績效評估和監督機制方面也穩步推進和逐步優化。

圖1 1994-2021年轉移支付構成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

圖2 1994-2021年轉移支付類別占轉移支付總和的比重
根據轉移支付政策推進和結構調整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和占比不斷下降,而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占比則不斷提高。這種趨勢主要是由專項轉移支付項目過于繁多,資金管理不規范,項目審核機制存在缺陷,且缺乏項目退出機制等問題所引起的。張凱強、范秋萍(2020)還深入闡明了專項轉移支付政策轉向的機制邏輯,并指出政治分權、信息不對稱以及行政管理體制方面是導致專項轉移支付資金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因此,為了減少轉移支付資金導致的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跑部錢進”和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等現象,中央政府從財政管理和資金規模上進一步突出一般性轉移支付,弱化專項轉移支付。
三、擴展的項目治國與不斷下降的專項轉移支付之間的“矛盾悖論”
項目治國的政策體系不斷擴展,項目制的運用范圍和目標線索也越來越廣。然而,在政府治理視角下,以項目制為運行基礎的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和比重則不斷減小。這就存在了一個明顯的“矛盾悖論”,擴展的項目治國與不斷下降的專項轉移支付規模之間的“矛盾悖論”,其闡釋需要關注以下兩點。
首先,雖然專項轉移支付采用項目制的運行機制,但是,項目制的運行機制也被廣泛地運用到其他政策機制中,例如一般性轉移支付、政府債務管理以及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等。雖然專項轉移支付是政府治理視角下項目制運行的始點,但在政策初期,項目制的高效性、目標性和協同性在專項轉移支付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促進了區域均衡發展、引導了政府政策運行以及解決了區域間的重要難題等。因此,項目制的治理模式也逐漸推廣到其他政策項目中。例如,一般性轉移支付的稅費改革轉移支付、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生豬和牛羊調出大縣獎勵資金以及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中的大部分補助資金多采用項目制治理模式運作。這些轉移支付可以歸類為“準專項”性質的轉移支付,旨在保障和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史普原,2019)。此外,政府債務管理的專項債務、政府和社會資本項目也采用項目制治理模式來保障政策的有效執行,充分發揮項目制的高效性、目標性和協同性。
其次,專項轉移支付是一項政策,而項目制是一類政策工具。專項轉移支付作為一項政策,可以采用不同的政策工具進行實施,其中包括項目制等多種形式。同樣地,項目制是一類政策工具,可以被廣泛應用于不同的政策領域中。因此,專項轉移支付和項目制雖然存在交集,但是彼此之間有獨立的內涵和應用范疇。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和比重的下降,以及項目制治理模式的不斷擴展,本質上是施政政策與政策工具之間的差異。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和比重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專項轉移支付在實踐中存在資金效率低下等問題(Zhou,2012;尹利民,2015),而項目制治理模式具有高效性和目標性,在其他政策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中央政府因此不得不調整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和比重,但在其他政策領域中繼續推進項目制治理模式。
因此,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的下降與項目制治理模式的不斷擴展之間的“矛盾悖論”,本質上是不同概念內涵的沖突,存在不同內涵和應用范疇。將二者的概念內涵等同化或模糊化,會導致認知問題,并不能有效地解釋現象和解決問題。進一步,專項轉移支付和項目治國并不是矛盾的關系,反而有著內在的聯系和互補性。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和比重,逐步推行項目治國的治理模式,以更好地實現政策目標和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四、項目制視角下轉移支付政策改革的方向
基于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的下降與項目制治理模式的不斷擴展之間的“矛盾悖論”,一方面,專項轉移支付政策存在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的問題,導致中央政府不得不減少其資金規模。另一方面,由于項目制治理模式具有高效性、目標性和協同性等特點,各層級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不斷推廣其在各項政策或各項任務目標上的應用。然而,項目制本身不能解決專項轉移支付政策現階段存在的效率低下問題。因此,從項目制的角度來看,轉移支付政策改革的方向應關注以下方面。
第一,專項轉移支付政策應繼續發揮其機動性和目標性,但同時需要解決存在的執行漏洞問題。為此,政府應完善審核、退出、監督和績效考核機制,特別是加強對資金流向、政府層級間的資金分配和信息公開的監控。因而,中央政府在專項轉移支付政策調整和設計時應高屋建瓴、有的放矢。如財政分權下政府層級間的支出責任不清晰,應明晰政府層級間的資金分配和事權分配,明晰專項轉移支付的申請部門和退出時間等;信息不對稱容易導致專項轉移支付的執行效率和資金流向出現偏差,因而應該細化各項資金的信息公開制度和監控資金流向。在2015年,財政部相繼出臺《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績效目標管理暫行辦法》《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管理辦法》《專員辦開展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監管暫行辦法》等政策文件,進一步加強對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管理,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規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說,專項轉移支付政策的實施與執行應綜合評估,應有效權衡和統籌發揮專項轉移支付的機動性、目標性與解決專項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的問題。
第二,繼續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重,充分發揮項目制在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分配的高效性和協同性,實現地方政府的能動性和中央政府激勵性在一般性轉移支付政策的統一。一般性轉移支付涵蓋廣泛的“準專項”性質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準專項”性質的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有效運行有利于發揮項目制的特點與優勢。在此類轉移支付中,項目制治理模式與地方激勵性、地方資源稟賦和社會參與性密切相關,直接關系到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從2015開始,中央政府不斷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優化中央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辦法,既要提高均衡性轉移支付規模,保障地方政府的財力和能動性;也要發揮“準專項”性質的一般性轉移支付的目標性和協同性,進而發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兩個積極性。因此,在未來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應該注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協同配合,達到更好的使用效果。
第三,因地制宜地推進和優化項目制治理模式,加大轉移支付的直達力度,充分發揮特殊轉移支付機制的高效性和目標性。首先,在2020年6月和2021年2月,財政部依次出臺《中央財政實行特殊轉移支付機制資金監督管理辦法》《關于做好2021年財政資金直達機制有關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并指出“加強中央財政實行特殊轉移支付機制資金監管,確保有關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按照預算管理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為推動建立常態化財政資金直達機制,進一步加強直達資金管理和監督,提高資金使用效益”。這些措施充分體現了特殊轉移支付機制的重要性,既能保障轉移支付的補助機制,又能發揮項目制的高效性、目標性和協同性。在一般性和專項轉移支付資金運用中,中央政府也應在政府層級間的資金管理、資金監管機制、受益對象實名機制、信息公開機制、報告和反饋機制等方面不斷進行規范和優化。
第四,借鑒對口支援的經驗,健全橫向轉移支付制度,推進對口協作項目的建設和促進鄉村振興。對口支援是我國具有悠久歷史的合作制度,起初用于工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城鄉協作,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不斷變革,對口支援機制也在不斷創新與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對口支援的創新推進,主要表現為對口支援逐步精細、運用場域持續擴大、運行過程日益規范(王禹澔,2022)。對口支援項目不僅包括橫向轉移支付的資金規模要求,更需要人力資本、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地方政府可以借鑒對口支援的成功經驗,推動橫向轉移支付的變革和推進,建設更多的對口協作項目,并加大對鄉村振興的支持。同時,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強各地政府之間的援助、合作和共贏,通過橫向轉移支付制度的健全與完善,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更加均衡的區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