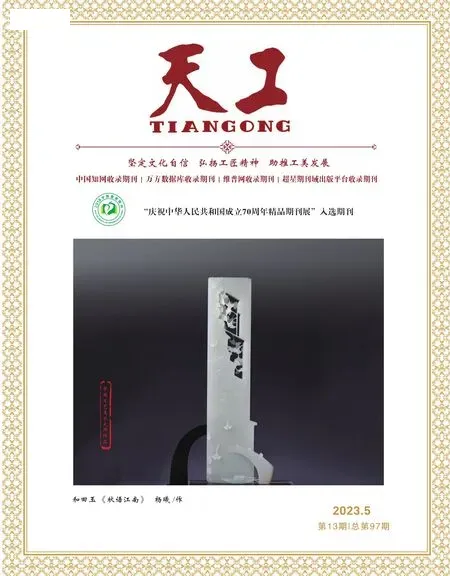雕塑語言在城市空間中的創作路徑探究
趙 希
四川雕塑藝術院有限責任公司
雕塑是時空藝術,是藝術家創作靈感的瞬間凝固,它不僅展現著藝術家對作品內涵的深刻理解,也鐫刻著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的探索與哲思。我國現代雕塑體系傳承脈絡清晰。早期深受西方現代雕塑理念和技法影響的雕塑體系,在當代呈現出守望本土、根植歷史的發展特征。這就要求創作者在掌握扎實的創作技法的同時,要將個人的藝術風格、審美品質與城市的精神空間緊密結合。
一、城市雕塑創作的語言系統
(一)雕塑材料的體驗
在雕塑作品中,材料既彰顯了物性表面的獨特性,即通過肌理、質感、空間和知覺等多維度呈現,也是理念表達與物之本性的連接載體。不同的材質使雕塑作品產生了不同的質感、肌理、觸感,如主題性雕塑的材質凸顯出了力量與激情;景觀雕塑的材質多變,活躍了空間氛圍,促進了與觀者的互動;小品雕塑的材質更為獨到與考究。總之,不同材質的特性在空間交織、光影疊映、體量重力等方面產生著積極的影響。特別是具象雕塑向抽象雕塑的過渡,材質本身凸顯著塑與造的不同體驗,塑造和雙手的價值經過材質特性的折射被進一步放大。
(二)雕塑形體的塑造
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雕塑具象表達、主題塑造和人物群像刻畫等命題是藝術家關注的焦點。伴隨著現代主義雕塑的興起,追隨自然、忠于對象的寫實刻畫、把握形體解剖結構的創作思想,受到以羅丹為代表的藝術家群體的挑戰,并影響至今。20 世紀20年代,留歐歸來的雕塑家開始探索雕塑的本土化語言轉變,《羅丹藝術論》甚至成為部分美院雕塑系的必讀讀物,其成就被廣泛認為是一種對傳統雕塑體系和思維的挑戰。雕塑形體作為一種力量,對丑陋或容貌損毀的接納,通過形體塑造的結果,將人體的能量疏導于物質對象當中,進而使作品每一個形體的表達都充滿著動力與激情。米開朗基羅曾言:“真正的雕塑是從山上滾下來的剩下的部分。”①威廉·塔克:《雕塑的語言》,徐升譯,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7,第XIII 頁。只有這樣的動勢,才能保留雕琢與塑造對象中力量的飽滿與視覺的張力。
(三)雕塑體量的表達
雕塑的體量給予觀者不同的情感體驗,也在空間中產生著不同的作用。體量宏大的作品,并不一定會給觀者以“崇高”的感受;體量精致的作品,并不一定不會給觀者以“震撼”的感知。雕塑的“重力感”與質量本身的關系并不大,它能調解觀者對藝術作品的視覺感知,也是雕塑“真實”形式的“概念性知識”必不可少的要素。雕塑作品偶爾會出現“失重”的假象,或視錯覺方法中的“偏差”,這正是雕塑體量的魅力所在,它會改變觀者對客觀對象的固有認知,進而從側面思考雕塑作品可能帶來的“隱性”內涵。雕塑的生命狀態正是在這種固有思維與感知層認知偏差中彰顯出來的。
經歷了時間見證的雕塑作品,往往作為記憶中的時代象征和標志,在特殊的時間節點和歷史語境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物’所彰顯的技藝與尺度構成了物與物、人與物之間的和諧空間,它也不斷地規范和調整著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卻又因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伴而略顯平凡。”①柳宗悅:《日本手工藝》,張魯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第2 頁。雕塑與人之間的適宜尺度,即是在城市性空間、物質性的社會生活基礎之上,逐漸積累、構筑起來的。雕塑作品作為物的實體,連接著情感的記憶與牽絆,在生活與城市的發展中,產生了“緩沖”的價值。
二、城市空間雕塑符號的轉譯
雕塑作品作為特殊的符號語言,承載著美的功能,并在藝術家的塑造中逐漸產生新的形式,進而負載著屬于自己的意蘊。同時,賦予作品新的含義,探求著新的內容,然后超脫出固有的語言模型,賦予內容新穎的形式與聯想。城市空間中的雕塑作品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它應當被賦予特殊的情感寄托,或在特別的位置中發揮價值。“它的確定性、穩定性和崇高之處并非來自它的重要性,而是來自它與周圍環境的和諧相處。”②萊內·馬里亞·里爾克:《羅丹》,梁宗岱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第9 頁。公共空間的作品應當由藝術之作上升為藝術之物,它在無聲的空間與環境中,發揮出精神傳遞與文脈寄托的價值。
(一)材料與塑造的轉換:作品中的知覺體現
雕塑作品的塑造方式與藝術家選用的材質息息相關。幾個世紀以來,藝術家用黏土制作一些小的草圖模型,將其作為塑造靈感的萌發,將人像作為傳播的媒介,通過材料的特殊性質,逐漸打破藝術形式與具象對象之間的明顯聯系。在創作過程中,藝術家發揮了黏土材質柔軟、無結構、易于操作的特點,充分彰顯了材料的特質,使其成為訓練與思維流動的重要材料之一。藝術家通過材料塑造體量,這也成為雕塑作品內在力量彰顯的重要表征。透過塑造的體量輪廓,觀察雕塑每一個角度的變化,其對身體的感知、觀者的觸覺與重力的內在感知,以及雕塑與空間、地面的關系,是知覺中不可或缺的內容,超然于傳統的感知經驗。
(二)觀看與觸摸的暗示:雕塑中的空間屬性
雕塑作品作為視覺藝術的重要載體,是在靜態時空中,通過視覺物體體量間的組織部分形成關系,對于觀者而言,其存有共識性,因為他們是在同一時空中被感知的。雕塑的空間性在現代藝術的發展演進中,由立體派的線條與塊面結構生發而成,進一步強化了它的特殊屬性。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更加注重將雕塑影響和暗示出的空間,與雕塑的實際占有空間相關聯,豐富其在雕塑結構和樣式方面的探索。城市空間中的觀者在與雕塑互動的過程中,為了觸及與把握新的語言,空間成為一種對傳統視覺經驗提出質疑的載體,詮釋出物質形態存在的多重可能。
作品含義的生成,是觀者在體驗作品時對自身所處時間、空間的意識。由靜止之物制作而成的公共空間中的雕塑作品,是時間與空間的“雙向延伸”。藝術家通過體量的改變,或通過光影消解質量、豐富空間層次的方法,增強了靜態空間中雕塑作品的動勢。而雕塑作品因本身特有的“紀念碑性”,或喚醒了歷史記憶,或展望了未來的影像,其創作持續不止,既是萬物瞬間的捕捉,也在考量瞬間之中各種關系的變化,藝術家凝聚于瞬間表象和關系的組合,既可將其作為前一個瞬間的產物,又可將其作為下一個瞬間的起因,通過作品豐富空間的內容、深化時間的體量,形成空間環境的中心。
(三)靜態與動態的交織:雕塑中的語言內涵
城市雕塑符號的象征性特質,給予空間場景不同的文化內核,這與雕塑作品內涵的表達方式有著密切的關聯。雕塑作品含義的生成,“在于其自身形式中所包含的對立面的潛在經驗:共時性中隱含著序列性的經驗”③羅莎琳·克勞斯:《現代雕塑的變遷》,柯喬、吳彥譯,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7,第4 頁。。雕塑作品作為靜態與動態交合點的特殊媒介,其體量、組織、結構間的張力皆在于此的瞬間捕捉。觀者對作品的理解,也是伴隨著創作中現代感受力的多元表現而逐漸萌發的。萊辛提出:“只能運用動作中的某個瞬間,因此必須選擇最富孕育性的那個瞬間,最能表現前因后果的那個瞬間。”④萊辛:《拉奧孔》,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第157 頁。由此,雕塑創作兼具對敘事情節、空間組織、體量輪廓和光影形態的多重把握,通過不同角度的特定構圖,串聯具有前因后果的軸線。
雕塑的主題表達通過“敘事性”的脈絡,深化創作者的表述含義。作品的形式語言應當在一個更為全面、綜合的形式中得到統一,作為平面空間和三維空間的延展,呈現出形式的豐富性。雕塑作品的豐富性在于表現對象的內部力量與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如雕塑作品的內部力量涵蓋其自身結構與組織,而外部力量則來自藝術家的操作技巧與制作過程。透過作品的語言與固有經驗共時、共情,進而豐富情感體驗,感知新的事物,使雕塑語言更合乎邏輯、易于理解。
三、城市雕塑語言的實境與意境
(一)雕塑作品外部形式的拓展
正如在“新藝術”運動中,公共空間中雕塑的量感超越其內部結構的影響,在形式與美感間的探索一般,這些質感從外部進一步塑造與刻畫物質實體,它與材料的內在結構毫無關聯,而又成為部分雕塑作品的藝術特質,甚至模糊了作品結構與功能的區分,表現出均勻布在表面的張力而更顯神韻。藝術家在形式語言的探索中,超越流動的表面,試圖雕刻出更具有結構感和多側面的體量空間,將外部形態與作品內核相對應,回歸于美感層面進行持續探索,進而具有了構成主義的特質。
對于創作者與觀者而言,“觸感”發揮著積極的連接作用,特別是公共空間中的雕塑作品,觀者可以通過觸感進一步理解雕塑整體,以及包羅萬象的深度觀念。一名成功的藝術家,應當“深諳實體形狀,胸有成竹……從各種角度想象一個復雜的形式;將自己作為形狀的引力、體塊、重量的中心;經過藝術家的手形成的形狀體量就好像在空氣中置換了形狀所在的空間”①赫伯特·里德:《現代雕塑簡史》,曾四凱、王仙錦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5,第74 頁。。通過觸感感知作品所形成的“體量知覺”,作為滿足感的延伸,豐富了作品感知、解讀和體驗的層次。
(二)雕塑語言象征意義的建構
公共空間中雕塑作品生成的形象,超越了其具象本身,成為抽象化的符號,傳遞著藝術家的意圖與信息。傳統的繪畫與攝影技術,在作品與觀者間建立了一種關系,它依托于固有的經驗傳遞信息;抽象化的雕塑作品語言則獨立于觀者的存在,沒有固定的表達對象,符號和象征的語言系統,通過指令的形式表達空間中的意涵。不同時空、角度、經歷與認知,優化了接受指令的路徑和過程,豐富了作品與觀者的互動效果。特別是不確定的對象與空間呼應的形式探索,觀者與雕塑實體的交流方式發生新的轉換,進而觸發互動交流系統。
雕塑作品的敘事性與情節性是語意傳遞的重要路徑,其形式與體量的塑造,豐富了信息接收的感知體驗。現代技術的革新,特別是光影效果的展示,將“劇場性”置于雕塑作品的創作中,深化了雕塑作品的“舞臺效果”和“時間特質”。這些雕塑作品將展示空間戲劇化,通過光線變換、音影交織,將雕塑作品轉化為劇場或戲劇背景,強化其劇場感。雕塑的邊界與展陳有了更多方式,“燈光藝術”強化了語言中的象征意味,這是傳統雕塑所未關注的。燈光的強弱與陰影的互動,強化了雕塑作品的時間性和戲劇性,它成為一種能量,光也成為時間性的媒介,豐富了雕塑的表現形式。
(三)雕塑作品場所精神的營造
公共空間中的雕塑作品有著物質環境與精神環境的雙重屬性,只有觀者的精神活動滲入其中,雕塑作品才具有了從物質性轉換為精神性的可能。不同主題的雕塑作品豐富著觀者理解其所蘊含的深層內容的情感體驗。藝術家通過藝術創作預見著雕塑精神環境與物質環境轉化的方式和途徑。“雕塑與觀眾的相互關系,雙方既是互相征服的一方,也是雙方的精神環境,其在精神上的作用,不完全取決于雕塑自身物質環境的差異。”②王朝聞:《雕塑美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417 頁。在物質性與精神性的張力中,觀者基于審美的個性差異,對雕塑形成不同的情感體驗。
觀賞主體與雕塑精神空間有著密切的聯系,雕塑作品應當符合人的情感需求。區別于架上雕塑的城市空間雕塑,在語言形式中傳遞著設計者、創作者的創作意圖,在技術、形式、符號等多種語言系統中,豐富了美感感知的情感體驗。在雕塑場景空間營造中,氣候變化、自然條件和物質環境的變遷帶來的不確定性,為雕塑賞析提供了更多可能。
四、結束語
在藝術形象的建構中,雕塑作品的內容、形式,物質環境的廣狹,對觀者的視界乃至精神境界也有影響,它既在適應物質環境,也在創造精神環境。城市空間中的雕塑作品的環境更為多變和復雜,不同的物質環境會對觀者的欣賞過程產生不同的影響,并在其精神空間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雕塑作品的出現,影響了實際環境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雕塑的精神空間也達到了預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