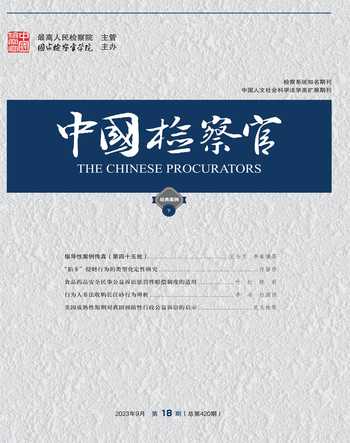最高檢首批刑事抗訴指導性案例評析
熊秋紅
摘 要: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對于刑事抗訴的條件和標準作了規定,為檢察機關依法履行刑事抗訴職責提供了基本指引。最高檢發布的首批以刑事抗訴為主題的指導性案例集中體現了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把握刑事抗訴的條件和標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指導性案例中的“精準抗訴”突出地體現在對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準確適用、對此罪與彼罪的準確界定、對適用死刑與適用死緩條件的準確理解以及對遺漏犯罪事實、遺漏同案犯的妥當處理等方面。指導性案例還展示了檢察機關對案件進行實質性審查、自行補充偵查、全面論證抗訴意見、深挖關聯案件、確立新的法律適用規則等成功經驗以及通過能動履職延伸審判監督職能與效果的具體做法。
關鍵詞:刑事抗訴 指導性案例 抗訴條件與標準 能動履職
2021年6月印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要“綜合運用抗訴、糾正意見、檢察建議等監督手段,及時糾正定罪量刑明顯不當、審判程序嚴重違法等問題”“完善審判監督工作機制” 。2023年6月25日,最高檢發布了第四十五批指導性案例,共計5個案例,這是最高檢發布的首批以刑事抗訴為主題的指導性案例。這些案例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既有危險駕駛等輕罪案例,也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重罪案例;既有二審抗訴案例,也有再審抗訴案例;既有輕罪抗重罪案例,也有無罪抗有罪案例;既有單人犯罪案例,也有共同犯罪案例;既有證據采信、事實認定爭議案例,也有法律適用爭議案例。透過這5個指導性案例,可以看到刑事抗訴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重要價值以及檢察機關準確把握刑事抗訴條件和標準對于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
一、刑事二審抗訴與再審抗訴的條件與標準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于刑事二審抗訴與再審抗訴的條件作了規定,最高檢發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明確了刑事二審抗訴與再審抗訴的標準,為檢察機關依法履行刑事抗訴職責提供了基本指引。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的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這里的“確有錯誤”包括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或者量刑不當,也包括原判決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以及嚴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如違反公開審判原則、違反回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等。《刑事訴訟規則》第78條補充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第一審人民法院有關證據收集合法性的審查、調查結論導致第一審判決、裁定錯誤的,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刑事訴訟規則》第584條細化了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同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裁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提出抗訴:(一)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或者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的;(二)有確實、充分證據證明有罪判無罪,或者無罪判有罪的;(三)重罪輕判,輕罪重判,適用刑罰明顯不當的;(四)認定罪名不正確,一罪判數罪、數罪判一罪,影響量刑或者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的;(五)免除刑事處罰或者適用緩刑、禁止令、限制減刑等錯誤的;(六)人民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嚴重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54條的規定,最高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刑事訴訟規則》第591條進一步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一)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二)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的;(三)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依法應當予以排除的;(四)據以定罪量刑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五)原判決、裁定的主要事實依據被依法變更或者撤銷的;(六)認定罪名錯誤且明顯影響量刑的;(七)違反法律關于追訴時效期限的規定的;(八)量刑明顯不當的;(九)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十)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的時候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二審抗訴與再審抗訴在適用條件上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檢察機關“認為”一審裁判確有錯誤,后者是檢察機關“發現”生效裁判確有錯誤。一個是“認為”,一個是“發現”,從用詞上可以看出,再審抗訴在對“確有錯誤”這一條件的把握上應當比二審抗訴更為嚴格,這主要是因為再審抗訴涉及到如何處理糾正錯判與維護生效裁判的穩定性之間的關系。在最高檢發布的5個指導性案例中,有3個屬于二審抗訴案,1個屬于再審抗訴案,還有1個同時涉及二審抗訴和再審抗訴。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包括法院判決未能正確把握證明標準、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認定罪名錯誤、量刑不當、遺漏犯罪事實與同案犯等多種情形,彰顯出檢察機關全面、充分地行使抗訴權的必要性。5個指導性案例為檢察機關如何運用好刑事抗訴職責、確保法律統一正確實施,提供了具體指導。
二、指導性案例對刑事抗訴條件和標準的正確把握
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對于刑事抗訴的條件和標準作了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正確把握刑事抗訴的條件和標準仍然有相當的難度,這也是造成刑事抗訴案件數量少、質量低的重要原因。最高檢發布的5個指導性案例在抗訴的準確性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一)關于刑事證明標準
刑事證明標準是刑事訴訟中證明主體運用證據證明案件待證事實所需達到的程度要求。在刑事訴訟中,證明標準是貫穿整個刑事證明過程始終的一根金線。刑事訴訟主體收集證據、審查判斷證據、進行實體處理的活動均需圍繞著證明標準而展開。在傳統上,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有罪證明標準,2012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做法,增加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表述,從而形成了主客觀相結合的刑事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標準的引入,可以發揮與“疑罪從無”類似的功能。“疑罪從無”被視為無罪推定原則的必然要求,是司法機關處理疑罪案件的基本準則。 在某種意義上,“排除合理懷疑”的引入,意味著裁判者在綜合審查全案證據之后,如果仍然存在合理懷疑,那么,他就只能遵循“疑罪從無”的理念,按照“疑問時做有利于被告人解釋”的原則,作出被告人沒有實施犯罪行為的認定。疑罪從無,應當是公安司法機關窮其努力,仍然無法查清案件事實時的一種處理。
在劉某某販賣毒品二審抗訴案中,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是第一審判決未能正確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規則,錯誤地將有罪判為無罪。劉某某辯稱其車內毒品為其朋友周某(舉報人)所留,一審法院基于劉某某車內毒品可能為周某所留的“合理懷疑”,作出了劉某某無罪的判決。檢察機關通過核查劉某某與周某之間的關系及其經濟往來情況,梳理劉某某的社會關系和5起毒品犯罪關聯案件,排除了劉某某車內毒品為周某所留的合理懷疑,并進一步夯實了劉某某具有販賣毒品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的證據基礎。二審法院依法改判被告人有罪,以販賣毒品罪判處劉某某無期徒刑。司法機關正確把握刑事證明標準,直接關系到有罪與無罪的準確認定。在該案中,被告人從一審被判無罪到二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兩次判決可謂天壤之別,檢察機關通過補充證據,排除了犯罪為其他人所為的合理懷疑,保障了刑事裁判的正確性,防止了有罪的被告人逃脫法網。
在宋某某危險駕駛二審、再審抗訴案中,同樣涉及司法機關對刑事證明標準的正確把握問題。在該案中,被告人宋某某停車走到人行道上睡覺時被發現,進而檢測出其血樣酒精含量超標;宋某某的小轎車涉及一起交通肇事案,造成被害人張某輕微傷。一審法院以宋某某危險駕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排除其間有其他人駕駛車輛的可能性為由,判處宋某某無罪。在該案中,宋某某辯稱其小轎車由“魏某”駕駛,而“魏某”身份信息無法核實,屬于典型的“幽靈抗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刑事司法實踐中,類似這樣的“幽靈抗辯”并不罕見,給檢察機關承擔舉證責任提出了難題。在該案中,檢察機關通過仔細審查鑒定意見、自行偵查補強證據,力圖澄清其間有其他人駕駛車輛的合理懷疑。不同的司法鑒定機構對于視頻監控圖像與被告人宋某某的同一性鑒定,作出了不同的鑒定意見,基于此,法院一審、二審判決均作出了被告人無罪的裁判。在再審抗訴中,檢察官發現了新證據——案發路面監控抓拍的影像資料,并委托司法鑒定機構進行影像中出現的小轎車駕駛員與被告人宋某某的同一性鑒定,得出了肯定性的鑒定意見,從而使全案證據更加確實、充分,排除了其間有其他人駕駛車輛的可能性。再審法院據此裁定撤銷原判,改判原審被告人宋某某犯危險駕駛罪,判處拘役6個月,并處罰金2萬元。該案例表明,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刑事證明標準的把握,法檢之間可能會產生分歧,在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新證據的發現往往是破解僵局的關鍵之所在。檢察機關積極充分履職,可以有效避免不經仔細查證而作出“疑罪從無”判決,錯放真正的罪犯。
(二)關于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
正確認定事實是正確適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礎。在李某搶劫、強奸、強制猥褻二審抗訴案中,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是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錯誤地將搶劫罪認定為盜竊罪,從而導致量刑畸輕。盜竊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取他人占有的數額較大的財物,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行為;而搶劫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強制性方法,強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搶劫罪不僅侵犯了他人財產,而且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這是搶劫罪區別于盜竊罪的重要標志,又使搶劫罪成為財產罪中最嚴重的犯罪。在李某搶劫、強奸、強制猥褻二審抗訴案中,李某約見被害人榮某,并將其帶至酒店,趁榮某昏睡之際,指紋解鎖其手機,盜取支付寶賬戶內4000元。對于李某的行為,公安機關認為構成盜竊罪,檢察機關認為構成搶劫罪,一審法院認定構成盜竊罪,判處李某有期徒刑1年11個月,并處罰金4000元。檢察機關通過破解被告人李某的電腦硬盤加密分區,發現了李某其他搶劫、強奸、強制猥褻線索,并查找了李某獲取精神類藥物的途徑和方式,此外,還調取了飯店監控錄像等,從而得出了現有間接證據能夠證明榮某被投放藥物后處于“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狀態的結論,據此認定李某的行為屬于以強制方法強取公私財物,構成搶劫罪。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改判被告人李某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并處罰金20萬元。該案例表明,正確認定此罪與彼罪,直接影響到對被告人的量刑。區分盜竊罪與搶劫罪的關鍵在于是否使用了強制方法,在該案中,盡管缺乏被告人使用了強制方法的直接證據,但檢察機關通過間接證據所形成的證據鏈,對“被告人使用了強制方法”這一犯罪構成要件進行證明,從而使該案的性質從盜竊罪改判為搶劫罪,并且帶來量刑上的巨大差異。
(三)關于判決適用刑罰明顯不當
重罪輕判,輕罪重判,均屬于適用刑罰明顯不當的情形。根據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在適用死刑時,必須綜合評價所有情節,判斷罪行是否極其嚴重;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2年執行。刑法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有明文規定,但對哪些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情形沒有明文規定。根據刑事審判經驗,應當判處死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認定為“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犯罪后自首、立功、坦白或者有其他法定從輕情節的;在共同犯罪中罪行不是最嚴重的,或者其他在同一或同類案件中罪行不是最嚴重的;被害人的過錯導致被告人激憤犯罪或者有其他表明容易改造的情節的;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糾紛激化引發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對被告人表示諒解的;對被害人積極進行賠償,并認罪、悔罪的;有令人憐憫的情節的;雖然極其嚴重罪行的證據確實、充分但具有其他應當留有余地情況的。
在嚴重犯罪適用死刑還是死緩的判斷中,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的賠償諒解情節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在王某等人故意傷害等犯罪二審抗訴案中,一審法院基于賠償諒解情節對王某作出了適用死緩的判決。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是第一審判決“量刑不當”,其中的重要爭議點是“賠償諒解情節是否足以影響量刑”以及“王某是否可以判處死緩”。檢察機關經過深入調查,一方面補充了被告人罪行極其嚴重的證據,包括犯罪的性質屬于惡勢力犯罪、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嚴重侵害等,另一方面補充了賠償附加條件、被告人并非真誠悔罪的證據,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應當適用死刑的抗訴意見。二審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改判王某死刑。該案例表明,賠償諒解等酌定量刑情節對于適用死刑與適用死緩的影響不是絕對的,需要結合案件的性質、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主觀惡性等作出綜合評判,司法機關不能因存在賠償諒解情節徑直對被告人作出死緩判決。
(四)關于對遺漏犯罪事實、遺漏同案犯的處理
認定罪名不正確,遺漏犯罪事實、遺漏同案犯,均會影響量刑或者造成嚴重的社會不良影響。在孟某某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尋釁滋事等犯罪再審抗訴案中,一審法院對孟某某等12人以非法采礦罪、妨害公務罪、故意傷害罪判處10個月至4年10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檢察機關以原審判決事實認定、法律適用錯誤,量刑畸輕,且存在遺漏犯罪事實、遺漏同案犯的重大線索為由提出再審抗訴。檢察機關通過走訪證人、調取證據,發現該案是涉及自然資源領域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進行了補充、追加起訴,再審法院對被告人孟某某以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搶劫罪、非法采礦罪、強迫交易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妨害公務罪、非法捕撈水產品罪、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9年,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12年6個月至2年3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該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保護傘”李某等5人,以受賄罪、徇私枉法罪被判處5年6個月至1年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另有11名公職人員被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于多人實施的共同犯罪案件,是否涉黑涉惡,對于定罪量刑至關重要;在黑惡勢力犯罪案件中,涉及一人犯數罪、多人犯一罪、多人犯數罪等復雜情形,只有進行徹查,才能為準確定罪量刑奠定基礎。在該案一審程序中,檢察機關以非法采礦罪、妨害公務罪、尋釁滋事罪提出指控;后以原判決部分情節、部分事實、個別罪名認定不當提出再審抗訴;后又通過自行偵查,補充、追加起訴,還原了案件的全貌,從而實現了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全面精準打擊。
三、刑事抗訴指導性案例所帶來的經驗和啟示
最高檢發布的5個刑事抗訴指導性案例最終均達到了通過抗訴使錯誤的刑事裁判得以糾正的效果,其成功經驗主要體現在:第一,檢察機關對于一審裁判和生效裁判中的證據采信、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進行實質性審查,從中發現存在的問題。如在王某等人故意傷害等犯罪二審抗訴案中,檢察機關通過對賠償諒解協議進行實質性審查,發現了賠償附條件、被告人并非真誠悔罪等情況,進而認為賠償諒解協議不應當成為對被告人適用死緩的充分理由。第二,檢察機關圍繞案件中的爭議焦點,進行自行偵查,補充完善相關證據。如在劉某某販賣毒品二審抗訴案中,檢察機關補充收集了關于被告人與舉報人關系的證據以及劉某某社會關系的證據;在李某搶劫、強奸、強制猥褻二審抗訴案中,檢察機關補充收集了李某大量的類似行為證據以及從未患過精神類疾病卻多次以失眠抑郁、癲癇疾病為由開具精神類藥物的證據。檢察機關通過補充收集證據,澄清了案件中的疑點,促使法院對原判決進行改判。第三,檢察機關注重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證抗訴意見。如在劉某某販賣毒品二審抗訴案中,檢察機關一方面排除了劉某某車內毒品為周某所留的合理懷疑,另一方面通過舉證證明了劉某某具有販賣毒品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主客觀相結合、正反兩方面相結合準確把握有罪認定的證明標準。第四,檢察機關深挖關聯案件,防止遺漏犯罪事實與同案犯,保障案件辦理的全面性。如在劉某某販賣毒品二審抗訴案中,檢察機關發現劉某某販賣毒品案的上家為陳某,經報告最高檢協調公安部,成功抓獲了陳某,陳某后被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孟某某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尋釁滋事等犯罪再審抗訴案中,檢察機關不僅挖出了首犯孟某某的多項漏罪,而且追加了16名被告人,還開展了“破網打傘”行動。第五,檢察機關對于查清事實后足以定罪量刑的抗訴案件,如未超出起訴指控范圍的,建議法院依法直接改判。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36條的規定,對于原判決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的,第二審法院在查清事實后可以依法改判或者發回重審。檢察機關對于案件事實已查清的案件,建議法院直接改判,減少了程序回流,有利于兼顧訴訟經濟與人權保障。
在5個刑事抗訴指導性案例中,檢察機關行使刑事抗訴權,除了嚴格依法履職之外,也涉及能動履職問題,如正確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如王某等人故意傷害等犯罪二審抗訴案涉及惡勢力犯罪,孟某某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尋釁滋事等犯罪再審抗訴案涉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國家曾開展“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有組織犯罪法》,對于此類犯罪應當依法從重打擊。在有組織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有時將魔爪伸向了未成年人,未成年人被迫成為有組織犯罪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對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殘忍、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的,出于優先保護未成年人的特殊考慮,對于犯罪分子應當從嚴懲處;對于涉案的未成年人,還需要做好司法救助、安置幫教等工作,以幫助他們回歸社會。對于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的社會治安管理漏洞,檢察機關有必要向有關部門制發檢察建議,促進犯罪的源頭預防與治理。如在案例中,檢察機關針對城市房屋租賃監管、重點人員管理、街面治安巡查等問題和騙購精神類藥物等管理漏洞,向有關部門制發了檢察建議,延伸了審判監督職能和效果。
最高檢發布的5個刑事抗訴指導性案例對于檢察機關如何履行好刑事抗訴職責、提升審判監督質效,作出了鮮活的闡釋,對于破解檢察人員不愿抗、不敢抗、抗不準現象,改變抗訴案件數量少、抗準率低的局面以及重個案輕類案、重二審輕再審等傾向,能夠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教授[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