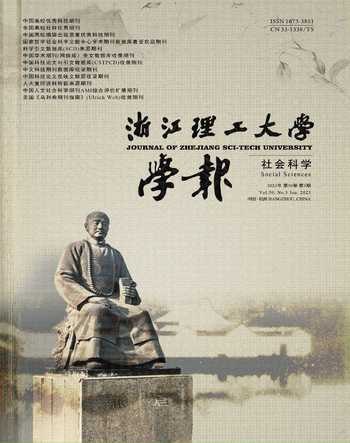清末小說翻譯中的偽譯現象研究
郭榮榮 成思
摘 要: 為探究清末小說家的偽譯方式及其成因,根據波波維奇和圖里等對偽譯的定義及羅丹對偽譯的分類,結合勒費弗爾的操縱理論,對當時翻譯中的偽譯現象進行了系統性分析。研究發現:清末小說家通過對文本外及文本內因素的操縱實現偽譯,具體方式包括虛構原本、原作者及譯者信息,借助外國知名作家的名氣,描寫異國文化及使用異國語言表達方式等;清末大規模的偽譯現象受到了當時詩學變化、意識形態及經濟因素等方面的影響。該研究通過探討清末小說翻譯中的偽譯現象,深化了對偽譯這一特殊翻譯現象的認識,為解讀清末小說翻譯史注入新活力。
關鍵詞: 翻譯研究;翻譯史;清末小說翻譯;偽譯;操縱
中圖分類號: H315.9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673-3851 (2023) 06-0285-07
A study on pseudotranslation in novel transl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O? Rongrong, CHENG? S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the pseudo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novel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ir reason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pseudo-translated novels during that period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Popovicˇ′s and Toury′s definitions of pseudotranslation, Luo Dan′s categories, and Lefevere′s manipulation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novel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chieved pseudotranslation by manipulating the texts′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fabricat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urce text, the author or the translator, taking advantage of famous foreign writers′ fame, writing the foreign cultures, and using the foreign expressions. The large-scale pseudo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influenced by the poetics, the ideology, and the economic factors then. This research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pseudotransl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thinking novel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history; novel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seudotranslation; manipulation
偽譯(pseudotranslation)是指無原文本而借翻譯之名、行創作之實的行為,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1]47。盡管中外翻譯史上存在大量偽譯作品,然而長期以來偽譯研究卻沒有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隨著翻譯多元文化研究的發展,尤其是描寫翻譯學的興起,不少學者指出,偽譯雖在文學及翻譯學研究中處于邊緣地位,但在翻譯史上并不罕見,應當給予一定的重視。國外學者吉迪恩·圖里[1]、波波維奇[2]、喬治·拉多[3]、蘇珊·巴斯奈特[4]、安德烈·勒費弗爾[4-5]等對偽譯的定義、方式及成因等展開了一系列討論,推動了偽譯研究的發展。近年來,國內也有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偽譯研究,對中國翻譯史中的偽譯現象展開討論,其中有關清末大規模的小說偽譯現象研究已成為研究的焦點。胡翠娥[6]、孟松[7]、齊金鑫等[8-10]、羅文靜[11]等對清末偽譯小說的類型、成因及當時小說家的偽譯策略等展開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豐富了學界對清末偽譯小說的認識。但總體來看,國內現有相關研究仍比較少,且多以個案分析為主,側重解讀特定偽譯者的偽譯方式或個別因素對偽譯者的影響,對清末小說家的偽譯方式及背后成因做出系統性歸納的較少。鑒于此,本文根據波波維奇和圖里對偽譯的定義及羅丹對偽譯的分類,在勒費弗爾操縱理論的指導下,探討清末小說家的偽譯方式,并從詩學規范、意識形態及經濟因素三方面來系統分析當時大規模偽譯現象的成因。通過討論清末小說家的偽譯方式,并揭示背后的文化、政治及經濟等驅動因素,本文期望更加深刻地認識偽譯這一特殊翻譯現象,為解讀清末小說翻譯史提供新思路。
一、偽譯研究概述
西方學者對偽譯現象的研究較早。1976年,波波維奇[2]提出了“虛假翻譯”(factitious translation/make-believe translation)這一概念,并將其定義為作者借助翻譯的名義出版原作,以獲取讀者支持的行為。之后,喬治·拉多提出了“偽譯”(pseudotranslation)概念,認為“偽譯”是指“那些過分偏離原文的目標語文本”[3]。1985年,吉迪恩·圖里在其著作《描述翻譯學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中也使用了“pseudotranslation”一詞,將其定義為無實際翻譯操作過程,借翻譯之名行創作之實的翻譯[1]47-48。按照圖里的定義,偽譯作品實際并不存在與之對應的原文本,其產生過程并不是語言轉換過程,而是原創文本生成過程。
從上述三位學者對偽譯的定義來看,圖里所講的“偽譯”與波波維奇的“虛假翻譯”概念所討論的問題實際是一致的,這兩位學者都認為偽譯是指杜撰式翻譯,即偽譯者稱自己從事的是翻譯工作,產出的文本是譯本,但實際是在進行原創工作;而拉多對偽譯的定義比較寬泛,他將任何基于原文本的改寫都納入偽譯范疇。雖然波波維奇、圖里和拉多對偽譯有著不同的定義,但三人均將偽譯看作一種翻譯現象或創作手段進行研究,偽譯概念在學理上并不完全是貶義的[12]。本文對清末小說翻譯中偽譯現象的討論是基于波波維奇與圖里的定義進行,即所謂的“翻譯”并不存在原文本,只是具有偽造性質的文學創作手段。
蘇珊·巴斯奈特[4]29-38根據圖里的偽譯研究總結了五種生成偽譯的方式:a)偽造原文(the inauthentic source),作者通過諸多內、外副文本的方式使讀者相信原文本的存在;b)自譯(self-translation),作者本人提供兩種語言文本,證明自己的翻譯行為;c)創作譯文(inventing a translation),作者將自己的文本冠以翻譯之名發表;d)游客變譯者(travelers as translators),游記作家將自己定位為譯者,來減少文化沖擊,這種偽譯方式經常出現在游記中;e)虛假翻譯(fictitious translation),作者在其創作中刻意模仿另一種文化中的話語,以增加其文本作為“翻譯”而存在的真實性。巴斯奈特對偽譯方式的分類存在重疊,羅丹[13]對此作了討論,她在巴斯奈特觀點的基礎上將偽譯分為三類:一是無原本可參照的偽譯,即通過虛構原本信息、原作者及譯者信息或借助國外知名作者作品之名實現;二是有異國情調的偽譯,即通過描寫異國文化或使用異國語言形式實現;三是享特殊自由的偽譯,主要指自譯。羅丹的分類考慮了偽譯文本的內外因素,第一類偽譯強調偽譯者如何通過副文本或其他文外因素使讀者相信其文本為翻譯;第二類偽譯強調偽譯者如何通過文本內因素達到其目的,包括文本內容及語言形式兩個方面;而第三類則指除第一、二類經典典型情況外的其他特殊偽譯方式。羅丹的分類較為清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本文對清末小說偽譯方式的討論將以此分類為指導。
偽譯的產生有著復雜且深刻的個人及社會文化原因。操縱學派代表人安德烈·勒費弗爾認為偽譯反映了特定社會中的權力關系,作者可能借助偽譯來“顛覆某種世界觀”或“創造新觀點”[5]。偽譯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反映了偽譯者對文化規范的有意識操縱。偽譯者利用當時翻譯的相關規范來操縱目標讀者,為介紹有爭議的詩學觀點或意識形態創造相對寬容的接受環境。同時,勒費弗爾[5]也指出,偽譯并不總是與詩學、意識形態相關,有些作者進行偽譯的動機可能比較簡單,他們僅僅是為了名利而作出這種選擇;經濟因素對偽譯者的驅動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5]。盧宏志等[14]、林躍武等[15]認為偽譯中存在“雙向操縱”,譯者并非受到意識形態、詩學與經濟因素的單向操縱,還會對文化規范進行主動操縱,以實現偽裝自己和影響讀者的目的。
總之,波波維奇、圖里及羅丹對偽譯的定義和分類為鑒定翻譯史中的偽譯作品及探討偽譯者的具體策略提供了一定參考,而勒費弗爾的操縱理論則為解讀偽譯者的背后動因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將使用波波維奇、圖里及羅丹對偽譯的定義和分類,結合操縱理論,對清末小說家的偽譯方式及背后原因進行研究。
二、清末小說家的偽譯方式
清末小說翻譯事業繁榮,翻譯小說在數量上甚至超過了本國創作小說。據阿英[16]210統計,清末翻譯小說的數量占當時小說總量的三分之二。在大規模的小說譯介過程中,偽譯現象泛濫,出現了許多偽譯作品。有些偽譯作品甚至廣為流傳,被視為當時極為優秀的小說譯本。例如,1873年出版的《昕夕閑談》被視為中國近代文學翻譯史上“第一部翻譯長篇小說”,開創了中國介紹西洋文學的先河,然而該小說原作信息、署名為蠡勺居士的初譯者信息以及署名為藜床臥讀生的改譯者信息皆不詳[17]。有學者認為該小說存在譯作人根據所讀外國譯本進行偽譯的可能[17]。《昕夕閑談》并不是個例,清末小說翻譯中有大量已確定或疑似是偽譯的作品。據孟松[7]10-12粗略統計,1901—1911年,已較為明確的清末偽譯小說作品有60部,其中偽托者及實際作者已確定的有22部,魯迅、李伯元、吳趼人、徐念慈、張肇桐等多位知名作家均進行過偽譯;偽譯的出版機構中不乏當時有名的書局和報刊,如《新小說》、《時報》、上海書局等。清末大批小說家費盡心思將其原創作品偽裝為翻譯,他們的偽譯方式值得翻譯研究者的關注。
本文對清末大量偽譯小說進行了分析,發現當時的偽譯作品大體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無原本可參照的偽譯,主要通過對文外因素進行操縱實現;二是有異國情調的偽譯,主要通過對文內因素進行操縱實現。小說家們的具體偽譯方式可分為以下四種:一是虛構原本、原作者及譯者信息;二是借助外國知名作家的名氣;三是描寫異國文化;四是使用異國語言表達方式。
(一)虛構原本、原作者及譯者信息
清末偽譯小說的一大特色是原本、原作者及譯者信息不清晰,偽譯者極力使這些副文本體現“翻譯”元素,以使讀者相信其小說是翻譯文本,而非創作文本。
首先,有些小說雖以翻譯之名出版,但僅有譯者署名,未標明原作者及作品信息,有些甚至連譯者信息也沒有,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偽譯的。例如,光緒十四年(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申報》刊登了小說《今古奇聞》的廣告,廣告中僅介紹了小說的譯者為東壁山房主人,未注明原作者及原作品信息[18]。東壁山房主人是指王寅,他在該書序言稱:“寅昔年借書畫糊口,浮海游日本國,搜羅古書中,偶得《今古奇聞新編》若干卷”[18],似乎這本書是他根據日本原本翻譯來的。但是,王寅之后又稱“是書乃東壁山房主人所輯”[18],承認該書是其原創作品。
其次,部分小說在出版時,雖注明了譯者信息及原作者信息,但這些信息是作者杜撰的。有些作者為了讓讀者相信其作品為譯作,刻意偽造原作品及作者信息,托外國作者名發表作品。1903年自由社刊行小說《自由結婚》就是采取這種偽譯方式的典型代表。該小說的譯者署名為震旦女士自由花,注明原作者為猶太遺民萬古恨。小說弁言寫道,此書原名為“Free Marriage”,作者是猶太作家“Vancouver”,“譯者”為震旦女士自由花,所謂的“譯者”還虛構了自己與“Vancouver”先生的交往經歷:“余往歲初識先生于瑞西……而先生又有此書之作,稿未脫,即以相示。余且讀且譯,半閱月,第一編成。”[19]109 此外,“譯者”還給予了原書高度評價:“余去國以來,讀歐美小說無慮數十百種,求其結構之奇幻,言詞之沉痛,足與此猶太老人之書媲美者,誠不易得也。”[19]109 作者極力營造該小說是譯本的假象,讓讀者相信原作及原作者是真實存在的。但阿英[16]102-109指出,該書似為譯作,實則非也,書中所寫的奴于異族者之苦的國家不是別國,而是中國,他推測該小說的作者為中國人。后來于必昌證實,阿英的推測是正確的;所謂的原作者“Vancouver”的確不存在,該小說也并非譯作,而是東京青年會的發起人之一張肇桐在日本留學期間創作的作品[20]。《自由結婚》并非個例,周瘦鵑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不少是借助這種方式實現偽譯的。例如,其在發表于《小說時報》的《鴛鴦血》中注明原作者為英國達維遜,《孝子碧血記》中注明原作者為俄國豪某,《鐵血女兒》的原作者為法國毛柏霜氏等,但不久后周瘦鵑又承認上述作品皆為其原創作品,而非翻譯作品[21]。
在虛構作者信息時,清末小說家還多有署外國名尤其是日本名的傾向,期望用這種方式來迷惑讀者,使他們相信作品是外來的,而非本土的。如李伯元署名南亭亭長,出版偽譯小說《官場現行記》;徐念慈取名東海覺我,出版偽譯小說《新法螺先生譚》;吳趼人署名偈,出版偽譯小說《預備立憲》。當時出版的偽譯小說,作者多使用日本名作筆名來增強文本的可信度,類似的名字還有猶亞子、雨塵子、角勝子、臥龍仲子、南野浣白子、獨立蒼茫子、春申浦、孤山小隱、蟲天逸史等[7]10-12。
(二)借助外國知名作家的名氣
偽譯者也常常借助外國知名作家的名氣來增加公眾對作品的興趣,從而宣傳其文學或政治主張[22]。清末,有不少小說家通過這種方式來推廣自己的作品。這些小說家通常借助國外已有名氣的作品,使用原作品名創作新故事,然后謊稱自己是在翻譯外國作品,以此滿足讀者閱讀外國作品的期待。當時很多福爾摩斯系列偵探小說就屬于此類偽譯作品。
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的作品《福爾摩斯偵探案》是近代第一本譯入中國的外國偵探小說,頗受清末讀者的歡迎。1896年,上海《時務報》最先刊登了張坤德翻譯的《英國包探訪喀迭醫生奇案》,但從語言風格、體裁特征、敘述手法看,該小說很可能是張坤德借助柯南·道爾的名氣創作的偵探小說[8]。《時務報》又率先刊登《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該作品中收錄了四篇由張坤德真翻譯的福爾摩斯偵探小說,作品出版后大受歡迎。隨后,中國偵探小說翻譯界興起了福爾摩斯偵探作品熱,越來越多的譯者開始譯介福爾摩斯系列作品。從1899年到1914年,多部收錄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的譯作出版,包括《新譯包探案》《泰西說部從書之一》《續譯華生包探案》《補譯華生包探案》《福爾摩斯再生案》《歇洛克奇案開場》等[23]。福爾摩斯系列作品在清末譯介不斷,當時國內很多有影響力的刊物都曾刊印過相關譯本。
在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真翻譯”行為的刺激下,不少作家借該系列作品的名氣,謊稱自己是在翻譯柯南·道爾的作品,以此來增加原創文本出版的可能性并提高其市場接受度。例如,1905年在上海《時報》上刊載的翻譯小說《歇洛克來游上海第一案》就是借外國作品名氣而產生的偽譯作品。該小說以譯本名義發表,但在發表時并未標明原作者信息,只有譯者署名“冷血”。后來有學者發現,這部小說其實并非翻譯作品,而是一部基于福爾摩斯系列探案故事創作的中國本土原創偵探小說,其真實作者為清末民初著名作家、翻譯家、新聞工作者陳景韓[7]17。
(三)描寫異國文化
描寫異國文化是清末小說家實現偽譯的另一重要策略。為了讓讀者相信作品從外國翻譯進來的,當時很多中國作家在創作時,努力使其作品中的人物、地點及故事情節等具有外國元素,然后將作品以譯文的名義公開,這樣一來,讀者自然接受了這些文本是翻譯作品。此類偽譯作品中,比較典型是魯迅創作的《斯巴達之魂》及周瘦鵑創作的《鴛鴦血》。
1903年,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創作了小說《斯巴達之魂》,并于《浙江潮》月刊上發表[24]13。盡管魯迅在該小說中署名“自樹”,以譯者自居,不承認該小說為自己所作,但在1987年,李昌玉[25]發表了《魯迅創作的第一篇小說應是〈斯巴達之魂〉》一文后,很多學者開始對《斯巴達之魂》究竟是翻譯還是創作展開討論。蔣荷貞[26]、高旭東[27]等學者也認同《斯巴達之魂》是魯迅的第一部原創小說而非其翻譯作品。在這個小說中,魯迅描寫了斯巴達人抵御波斯大軍,浴血奮戰,英勇殉國的故事。從斯巴達、波斯、愛爾俾尼、依格那海、西蒲斯、奢剎利、胚羅蓬等地點,到澤耳士、黎河尼佗、亞波羅、不動明王、格爾歌王后、蝶爾飛神等人物,再到斯巴達人的尚武精神,整部小說都充斥著異國元素。原作者魯迅自愿退到了譯者身份,讀者不做深入研究的話很難發現這是一部偽譯作品。
《鴛鴦血》是周瘦鵑的第一部偽譯作品,刊于《小說時報》,作者在發表時也以譯者自居。這部小說以俄國莫斯科為背景,講述了虛無黨人莫羅司克為了國家利益殘忍將其愛人波麗芬刺殺的故事。周瘦鵑順應了清末大量翻譯俄國虛無黨小說的潮流,在故事背景、人物以及情節上進行模仿,以增加其文本內真實性,吸引讀者。但在該小說發表不久后,周瘦鵑就承認,這是一部杜撰作品,稱其“有述西事而非譯自西文”[28]。盡管周瘦鵑在偽譯該作品時在體裁和語言上露出不少“馬腳”,似有“強行拼湊之嫌”[9],但其對外國故事的描寫可能會使當時的部分讀者將該小說當成翻譯作品。
(四)使用異國語言表達方式
偽譯者除了通過書寫外國故事增加文本的文內真實性,還會使用異國語言表達方式,使讀者將偽譯作品接受為翻譯作品。
清末,由于小說翻譯之風盛行,中國作家開始刻意模仿外國作家的寫作技巧,這進一步促進了偽譯小說的發展。梁啟超曾說道:“吾近好以日本語句入文,見者已詫贊其新異。”[29]在寫文章時,梁啟超“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30]85-86。當時在梁啟超等人的影響下,中國作家多樂于模仿外國的寫作方法,使讀者覺得其作品“別有一種魔力”[30]86。梁啟超所倡導的“新文體”,不同于中國傳統小說,其采用非章回體結構,第一人稱敘事,多使用外國語言形式及句法結構。偽譯者將上述特點應用到自己的寫作中,刻意模仿當時的外國小說及“真翻譯”譯本特色,使讀者將其作品當成翻譯作品接受。如在偽譯小說《預備立憲》中,作者吳趼人刻意模仿當時日譯中的翻譯作品風格,采用日式小說的敘事及語言風格,以達到迷惑讀者、使其相信這是“真”譯本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小說家往往會結合了多種方式進行偽譯,盡力使文本內外因素具備“真翻譯”的特征,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上述所列小說僅為各種偽譯類型中較為經典的案例。
三、清末小說翻譯中偽譯現象的成因
偽譯同“真翻譯”一樣,是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下的產物。清朝末年,中國社會內部出現大調整,小說家往往兼有改革家、革命家、新聞工作者等身份,小說翻譯中的偽譯現象錯綜復雜。在勒費弗爾操縱理論的指導下,本文認為清末偽譯小說主要可歸納為詩學變化影響、意識形態作用及經濟因素驅動這三方面的原因。
(一)詩學變化的影響
詩學是指“文學觀念”,包含文學要素及文學的社會文化功能兩方面內容。在一種文化中,文學翻譯必然受到其主流詩學的影響,但同時,翻譯也“能為那些(反主流詩學的)作家提供一定的保護,因而對主流詩學的攻擊通常都偽裝成譯本”[31]。
清末大量外國小說進入中國,不斷沖擊著傳統詩學,使中國的詩學形式發生了轉變。在當時,從外國引入的小說成為社會上流行的文學形式,且被賦予重要的社會、政治及文化功能。在接受外國小說的過程中,中國文學創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正如陳平原[32]對清末民初外國小說在華影響力的總結,當時中國小說家對待外國小說的態度經歷了從“漠然到消極接受,到積極接受,到自覺模仿,到力圖擺脫模仿走向獨立創造”的過程。1902年,梁啟超[33]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一文,文中寫道:“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明確指出小說及小說翻譯具有政治功能,引發了巨大的社會轟動。當小說與國家、民族命運捆綁在一起時,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借小說翻譯及小說創作來實現救國新民的目的。相比原創政治小說,從西方譯介的小說在當時的接受度更高,這就導致部分中國作家想借助偽翻譯來傳播其政治主張。
魯迅借偽譯小說《斯巴達之魂》中所反映的斯巴達尚武精神來改造國民精神。他說道:“斯巴達將士殊死戰,全軍殲焉。兵氣蕭森,鬼雄晝嘯,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復,迄今讀史,猶懔懔有生氣也。我今掇其逸事,貽我青年。”[24]6 魯迅希望中國人民像斯巴達人一樣英勇御敵,不畏犧牲。張肇桐的偽譯作品《自由結婚》旨在借助小說開啟民智,為資產階級革命積蓄力量。在該小說序言中,他借虛構原作者“Vancouver”之口說出寫作目的,稱“倘一得之愚,賴君以傳,使天下后世,知亡國之民,猶有救世之志,則老夫雖死亦無憾矣。”[19]109 張肇桐也借虛構譯者之口感慨道:“嗚呼!不知山徑之崎嶇者,不知坦途之易;不知大海之洪波者,不知池沼之安;不知奴隸之苦者,亦不能知自由之樂。”[19]109 他希望讀者能從該小說中汲取精神力量,投身國家建設。可以看出,當時的知識分子迎合了主流詩學,順應了當時大量外國小說譯介到中國的潮流,借助翻譯之名傳播先進思想。
(二)意識形態的作用
勒費弗爾認為,意識形態是由觀念與態度構成的概念網絡,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特定社會所接受[4]48。譯者的翻譯行為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當原作反映的意識形態及譯者的個人意識形態與占主導地位的譯入語意識形態相沖突時,譯入語意識形態將對譯者的翻譯行為發揮強制規范作用。意識形態能操縱真譯本,同時也能刺激偽譯本的產生。
清末,我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可以歸納為開民智求變革。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積極向西方學習,企圖變革中國社會,如梁啟超倡導新民以實現政治革新,嚴復倡導變法等。當時,國家權力仍然掌握在清政府手中,這些知識分子與清政府處于對立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要發表抨擊清政府、主張變新的言論時,需要格外小心。一些作者將偽譯視為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的傳播方式,為自己的作品帶上翻譯的面具,使其順利通過審查,在社會上傳播。在清末,政府對翻譯作品的審查要比對原創作品的審查寬松得多,這也正印證了圖里所講的,人們對翻譯的容忍度較高[1]47。
1903年上海獨社出版的政治小說《瓜分慘禍預言記》就是當時意識形態作用下產生的偽譯作品。該小說雖然標明其原作者為日本女士中江篤濟,譯者為中國人軒轅正裔,但其實際為福建革命派鄭權的原創政治小說。《瓜分慘禍預言記》假托某日本隱士的預言,稱1904年中國將面臨列強瓜分之禍,中國人民將遭遇滅種之劫。鄭權在該小說中抨擊了滿人政權的昏聵無能,主張建立漢族自治政權,建立三權分立的現代國家。該小說的矛頭直指“顢頇保守、拒絕變革的清朝統治者”[34],嚴重威脅清政府的利益。參考戊戌六公子慘遭清庭殺害的結局便可推測出,如果當時鄭權選擇公開自己的作者身份,那他勢必同樣會被清政府追究責任,甚至會引來殺身之禍。在這種情況下,鄭權為其作品打上翻譯的烙印,使用軒轅正裔譯名來掩蓋自己的作家身份,并通過杜撰原作品及原作者信息來增強文本作為譯本的可信性,使其順利通過審查,避免了實名發表作品帶來的風險。由此可見,清末復雜的意識形態是造成當時小說翻譯界偽譯現象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經濟因素的驅動
翻譯活動應當被放到社會文化語境中考察,其不僅受到詩學、意識形態的影響,還是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偽譯作為一種特殊的翻譯現象,自然也離不開經濟因素影響。
清朝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革時期,資本主義商業化理念貫穿文學社會運行機制的各個環節[35]。文學運行機制的商業化使得作者可以獲得一定報酬,職業作家數量增多。此外,大量商業化報刊問世,以吸引讀者、追求商業利潤為主要目的。清末小說翻譯的繁榮是資本主義文學運行機制對文學沖擊的典型表現[35]。當時,很多小說譯本在報刊上刊登,這些譯本受到市場的歡迎,為譯者及出版商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隨著外國小說翻譯事業的崛起,一些作者及出版商認為該事業有利可圖,便制造了大量偽譯作品,借翻譯的名義發表作品來獲得高額的翻譯報酬,或提高其作品的市場接受度,以此來獲取經濟利益。1907年出版的《滑稽旅行》《雌蝶影》、1909年出版的《機器妻》及1912年出版的《鴛鴦血》等偽譯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及出版商迎合市場需求、追求經濟利益的動機。
鴛鴦蝴蝶學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周瘦鵑從事寫作及翻譯事業就受到了經濟因素的驅動。他出版偽譯作品《鴛鴦血》時,“不能否認其經濟考量”[9]。周瘦鵑出生于上海普通職工家庭,有三個兄弟姐妹,在他六歲時,父親因病逝世,家中一貧如洗,甚至連一口棺木都是親戚們湊錢買的,從小母親就教育他“要爭氣,要立志向上”[36]。十六歲時,周瘦鵑受《浙江潮》中的一則故事啟發,開始嘗試寫作,并向商務印書館創辦的刊物《小說月報》投稿了其作品《愛之花》。當該小說被采用后,周瘦鵑收到了銀洋十六元報酬,他稱“這一下子,真使我喜心翻倒,好像買彩票中了頭獎一樣”[36],因為在那個時候這筆錢夠他們家買很多糧食。自此,周瘦鵑正式開啟了其筆墨生涯。1914年之前,周瘦鵑得到包天笑和陳景韓的支持,當時包天笑得知周瘦鵑大病,又家境清寒,便預支其稿費,稱“以后只要他的稿件一到,不論發表與否,即優先付酬”[37]。這也是在1912年到1913年期間,周瘦鵑將大部分作品發表于包天笑及陳景韓主編的《婦女時報》和《小說時報》的原因之一,而這一階段,也正是周瘦鵑進行偽譯的重要時期[37]。《鴛鴦血》是周瘦鵑在1912年發表于《小說時報》的偽譯作品,結合當時他的家庭狀況及小說翻譯的經濟價值,可以推測該偽譯小說的誕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經濟因素的影響。清末還有很多作家同周瘦鵑一樣,因為生活壓力而進行偽譯,經濟利益促進了清末大規模偽譯現象的產生。
四、結 語
清末是我國小說翻譯的高潮,也是偽譯十分活躍的時期。本文研究發現,清末偽譯作品大體可分為無原本可參照的偽譯及有異國情調的偽譯兩種情況。清末偽譯小說家通過虛構原本、原作者及譯者信息,借助外國知名作家的名氣,描寫異國文化及使用異國語言表達方式等具體策略來“欺騙”讀者,使自己的作品帶著翻譯的面紗被大眾接受。無論偽譯者采取何種方式,他們都在努力使其偽譯作品擁有當時“真翻譯”所具有的文本內外因素。同“真翻譯”一樣,偽翻譯也是特定時期、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下的產物。清末的偽譯現象與當時的詩學、意識形態及經濟因素息息相關。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讀者更加深入地理解清末小說翻譯中的偽譯現象,從新的視角解讀清末小說翻譯史。除清末小說翻譯外,中國其他時期的翻譯史上還有眾多偽譯作品尚未被關注,期待未來能有更多國內學者對偽譯這一特殊翻譯現象進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Rev. e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 Co., 2012.
[2]Popovicˇ A. A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M]. Edmonton: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Alberta, 1976: 20.
[3]Rad G. Outline of a systematic translatology[J]. Babel, 1979, 25(4): 187-196.
[4]Bassnett S,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5]Lefevere A. Pseudotranslations[M]∥Classe O. (Ed.).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2 vols. London: Fitzroy Dearborn, 2000: 1123.
[6]胡翠娥. 不是邊緣的邊緣: 論晚清小說和小說翻譯中的偽譯和偽著[J]. 中國比較文學, 2003(3): 69-85.
[7]孟松. 清末偽譯小說研究[D]. 重慶: 西南大學, 2013.
[8]齊金鑫, 李德超. 假作真時真亦假: 清末民初第一部偽譯偵探小說揭示的文化和文學現象[J]. 中國翻譯, 2019, 40(6): 42-51, 190.
[9]齊金鑫, 李德超. 周瘦鵑偽翻譯《鴛鴦血》語言特點管窺[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20, 43(6): 141-147.
[10]齊金鑫, 李德超. 魯迅小說《斯巴達之魂》的偽譯解讀[J]. 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 2021(3): 70-77.
[11]羅文靜. 文本內真實: 清末以來偽譯現象透析[J]. 樂山師范學院學報, 2021, 36(6): 44-49.
[12]封一函. 再創作的偽翻譯屬性[J]. 中國翻譯, 2005, 26(4): 27-30.
[13]羅丹. 閾際空間的偽譯研究[J]. 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08, 16(3): 45-48, 66.
[14]盧志宏, 張雯. 偽譯現象對于翻譯的啟示[J].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1, 35(6): 93-98.
[15]林躍武, 陳譜順. 從翻譯中偽譯現象看“雙向操縱”[J]. 江西社會科學, 2014, 34(3): 240-243.
[16]阿英. 晚清小說史[M]. 北京: 東方出版社, 1996.
[17]趙紀萍. 創造性叛逆視野下的清末民初文學翻譯研究[D]. 濟南: 山東大學, 2015: 17.
[18]潘建國. 晚清上海書坊東壁山房與《今古奇聞》小說[J]. 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0(3): 125-127.
[19]陳平原,夏曉虹.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 第一卷 1897-1916[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20]《文學評論》編輯部. 文學評論叢刊-第十六輯-古典文學專號[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2: 362-364.
[21]黃艷群. 掩飾與暴露: 副文本對偽翻譯研究的意義[J].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 13(1): 70-74.
[22]曾記. “偽翻譯”的重新解讀[J]. 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 6(10): 77-80.
[23]沙仲輝.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在中國的譯介出版分析[J]. 出版廣角, 2020(20): 92-94.
[24]魯迅. 斯巴達之魂[M]∥劉偉編. 集外集.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2: 6-17.
[25]李昌玉. 魯迅創作的第一篇小說應是《斯巴達之魂》[J]. 東岳論叢, 1987, 8(6): 49-50.
[26]蔣荷貞. 《斯巴達之魂》是魯迅創作的第一篇小說[J]. 魯迅研究月刊, 1992(9): 12-18.
[27]高旭東. 魯迅: 從《斯巴達之魂》到民族魂: 《斯巴達之魂》的命意、文體及注釋研究[J]. 文學評論, 2015(5): 5-14.
[28]周瘦鵑. 斷頭臺上[J]. 游戲雜志, 1914(5): 87-101.
[29]梁啟超. 夏威夷游記[M]∥張品興編. 梁啟超全集: 第四卷.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219.
[30]梁啟超. 清代學術概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31]黃碧蓉. “偽翻譯”: “翻譯”之邊界行走者[J]. 外語學刊, 2014(6): 92-94, 98.
[32]陳平原.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 23.
[33]梁啟超. 飲冰室合集[M]. 影印本. 北京: 中華書局, 1989: 10.
[34]耿傳明, 于冰輪. 近代“文明論”的興起與清末小說中關于“文明”的歧見: 以《瓜分慘禍預言記》和《新石頭記》為例[J]. 社會科學研究, 2017(4): 168-177.
[35]袁進. 中國近代文學社會運行機制的轉變及作用[J]. 學術月刊, 2000, 32(8): 83-89.
[36]周瘦鵑. 姑蘇書簡[M]. 北京: 新華出版社, 1995: 53.
[37]范伯群. 周瘦鵑論[J]. 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50(4): 36-52.
(責任編輯:柯 丹)
收稿日期:2022-10-22? 網絡出版日期:2023-04-04網絡出版日期
基金項目: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9YYC007)
作者簡介:郭榮榮(1999— ),女,山西臨汾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翻譯理論與實踐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成 思,E-mail:chengsi@se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