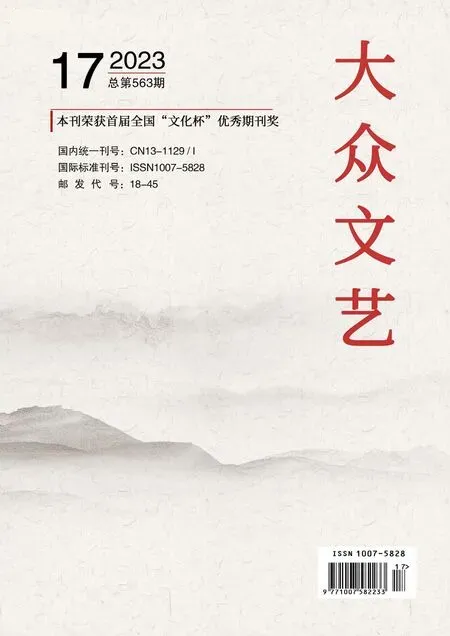隱喻理論視角下《肖申克的救贖》敘事分析
岳亞芳 羅建輝
(喀什大學 中國語言學院,新疆烏蘇 844000)
比較早的是意大利著名的法學家、修辭學家、哲學家吉安貝斯塔?維柯是對隱喻進行認知研究的,吉安貝斯塔?維柯覺得隱喻是因為人類對事物的想象而產生的,人類會通過自己的生存體驗隱喻去對世界進行認知。不久之后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一起出版了著名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人們開始從認知的角度研究隱喻,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概念隱喻理論”,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認為隱喻產生于身體和人類的經驗,人們通過對世界的認知而形成概念,概念隱喻的認知基礎是人們的身體經驗對于外界事物的概念化。
美國語言學者吉爾斯?弗科尼亞和馬克?特納又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論”,“概念整合理論”是人們在進行思維和活動時的一種認知過程,并且還運用了心理學和語言學的大量重要知識,把話語意義構建過程看作是兩個或者多個語義整合形成新概念的一個過程。[1]
概念隱喻理論和概念整合理論的研究重點都是人類對世界的認知活動,而隱喻是人類的對世界的認知和理解途徑。[2]
弗蘭克?德拉邦特導演執導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是一部深刻解剖人性,講述救贖與希望的經典電影。此電影以極富新意的敘事手段陳說了年輕有為的銀行家安迪因被誤判為槍殺妻子及其情人的罪名入獄后,他不動生聲色、步步為營地謀劃經營自我拯救并且成功越獄,重獲自由的故事,[2]此電影也成了世界電影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它不僅在世界電影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也為后世的電影創作提供了寶貴的啟示經驗。主人公安迪因被誤判為槍殺妻子及其情人事件而入獄,并且在監獄中遭受各種欺凌,經歷各種磨難。安迪從一開始就拒絕去屈服于監獄的體制體系化生活,并且運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去改變現在的困境,在監獄里,安迪結識了很多朋友,并設法在黑暗的監獄中找到了自己的希望與救贖。電影所講述的故事雖然簡單,但是其帶來的思考意味深長。影片中有多處隱喻現象,如導演對視聽修辭的符號隱喻、人物形象的隱喻以及對價值觀的隱喻等,促進了故事情節的發展、給觀眾帶來沖擊和思考。
一、視聽修辭的符號隱喻
文字學中因為二種事物在某一性質上有相似之處,而用以描述其中一種事物的詞來表示另一種事物的演變形式稱之為隱喻。事物都是以“相像”和“聯想”為依據的,即二種東西的特性都有相似之處,在這時,一種事物也通常用于比喻為其他一種東西。理查德在1936年出版的《修辭的哲學》書中寫道:所有事物的構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主體,即我們所表述的主體;二是喻體,亦即作品中用來表達的一部分。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贖》中運用了許多視聽修辭的符號進行隱喻,敘述整個電影。[3]
(一)“監獄”
電影第一幕,主人公安迪便被宣判監禁終生,緊接著就來到肖申克監獄。監獄作為主人公生活和逃離的地方,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常常有人把生活比作監獄,該片中就用監獄隱喻生活,隱喻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里,體制化是一種不可或缺的規則,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體制化的影響,其中影響最為嚴重的莫過于圖書管理員老布魯克斯,他生活在這座監獄里已有50年之久,以至于深深依賴起了這種監獄內的體制,逐漸變成了這個體制的一部分,甚至直到被告知可以假釋,并且離開監獄的那一天,他才真正地意識到,自己已經離不開這種制度化的體系體例了。最明顯的是監獄長也被體制化深深的影響,是電影中典型的惡人壞人形象,最終寧愿吞槍自殺也不愿意被逮捕。就像電影中瑞德所說的,“監獄里的高墻實在是有意思。剛進來的時候,你想盡辦法要逃出高墻;不久之后,你慢慢適應了這里;最后你會明白自己已經離不開這高墻。這就是體制化。”[4]故事中的監獄就像是一個體制化的牢籠,是一個微型的社會,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桃花源”。里面充滿著各色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各種生活與交易,而這些東西會慢慢侵蝕“居住”在這里的人們,這些人便會慢慢離不開這個社會環境。
(二)“小鳥”
電影中多處出現“小鳥”這個隱喻符號。第一次出現是老布將飯菜里的蟲子喂給懷里的“小鳥”;后來“小鳥”長大了,在老布出獄前被放生,頭也不回地飛出監獄了;再次提到“小鳥”是安迪打開廣播,“她們唱出難以言傳的美,美得令你心碎”。歌聲直竄云端,超越失意囚徒的夢想。仿佛“小鳥”飛入牢房,使石墻消失無蹤。仿佛就在那一剎那間,肖申克里的眾多囚犯似乎重新獲得了自由。”;然后是安迪從監獄逃出去后,在雨中,伸開胳膊的樣子,就像一只“小鳥”,也是電影的海報形象;最后一次提到“鳥”,是安迪逃出去以后,監獄老友們的議論:影片中關于“小鳥”的隱喻不言而喻,從影片開始掉到監獄里被囚犯們照顧,到后來羽翼豐滿扇振翅膀頭也不回地飛出了監獄,恰恰是隱喻了主人公安迪,他就像掉落在監獄的“小鳥”一樣,是自由的,不屬于這里的,囚籠是關不住他的,以至于逃出監獄后的“小鳥”形象和獄友口中的“小鳥”比喻,正是表達了安迪對自由的向往,也暗示了安迪最終逃出監獄,奔向自由的美好結局。[5]
(三)“圣經”
看過電影的觀眾都知道,“圣經”在該電影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電影中也多次出現了“圣經”相關的符號。第一次出現,主人公安迪剛入獄時,典獄長讓大家讀圣經。第二次出現,典獄長諾頓來查房,在安迪房間沒有查出任何異常,便與安迪討論“圣經”,離開之時,諾頓把“圣經”還給安迪,并對安迪說道:“得救之道,就在其中”。后來諾頓將安迪交到辦公室,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一幅編制畫,上面寫著“主的審判迅速降臨”。最后一次出現“圣經”,是當諾頓翻開之前藏著安迪小石錘的《圣經》時,打開的那頁正是《出埃及記》,這一章節詳細地描述了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引領下離開埃及的故事,這段路程是由以色列人的先知摩西帶領,通過荒野,前往應許之地。“圣經”這個意象符號作為影片中關鍵的工具,也具有預示作用,而“圣經”這個隱喻符號更是很大程度上和典獄長諾頓有著密切的聯系,從電影前期中典獄長要求肖申克的囚犯們讀圣經開始,就暗示了他表里不一、人面獸心、與圣經不符的形象,形成極大的反差,也暗示了典獄長最終的結局:諾頓被審判;而安迪最終被救贖,離開暗無天日的監獄。
(四)“石頭”
符號“石頭”在電影中反復出現,并且在監獄這種資源有限的地方,煙,工具,書,撲克,漂亮的圖片等都很稀缺,那么“石頭”隱喻的就是資源,石頭也就是知識,安迪是通過“石頭”以及所學的地理學知識,判斷出監獄的地形,從而挖墻逃出監獄。石頭也是他的一項愛好,他用石頭雕刻棋子,他利用石頭的特性制定了嚴密的逃獄計劃。“石頭”也是主人公安迪逃獄的掩飾,利用這項愛好掩蓋他為逃獄挖隧道的既定事實。“石頭”更是主人公安迪對命運不公的反抗,最后典獄長用石頭打開安迪出逃的路線,也給電影帶來高潮的體驗,讓觀眾拍案叫絕。
二、三大主角的人物形象隱喻
人物形象歷來都是電影中最容易被討論的點,因為電影講的是大眾生活中的某種縮影,其中的人物形象經過藝術創作基本具備典型性,集中了許多人的特定,具有共性。筆者將《肖申克的救贖》中的主角定為三種:
第一種是深受監獄體制化而影響的人物形象,最典型的代表是老布魯克斯,在影片之中,老布魯克斯是肖申克監獄內的一名圖書管理員,在監獄生活五十年,也是最久的一個,鋃鐺入獄之初,布魯克斯或許也有著如主人公安迪一樣渴望自由的心,或許也不甘于現狀,心有希望。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老布魯克斯漸漸的被迫適應了監獄之中的生活,也漸漸地適應了監獄這種體制,開始像周圍的人一樣在這個巨大的黑暗的牢籠之中,變得如魚得水起來。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更是在不知不覺中開始依賴起了這種監獄內的可怕體制,逐漸變成了這個體制中的一部分,甚至直到被告知可以假釋,離開監獄的那一天,布魯克斯才真正地意識到,自己已經離不開這種體制了。在“漫長”的假釋之中,所謂的“自由”讓年邁體衰、跟不上時代的老布魯克斯滿心驚恐害怕,最后在精神不斷受到摧殘的情況下,逐漸崩潰,選擇不再停留,笑著離開了這個世界。影片中有這樣一幕,70多歲的老布魯斯在出獄前將自己養了多年的烏鴉放掉,這也暗示著他即將獲得自由,在走出監獄時,老布魯斯身后是監獄欄桿,也是暗喻他終將走不出制度化,結果老布魯斯果然不能適應外面未知的生活,最終選擇上吊自殺。其中還有許多深受體制化影響的人,如湯米,雖然他入獄的時間不長,但是本性善良正直的他卻因為與監獄的體制沖突,告訴了安迪真相,被監獄長叫去談話,典獄長選擇的談話的地方在一個可以逃出監獄的出口,因此湯米被監獄長叫人打死,并且誣陷湯米逃獄反抗被打死。除此之外,依然還有一些監獄內“潛規則”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他們都深受監獄體制化的毒害。
第二種是屈服于體制化的人物形象,如瑞德,他一開始也和主人公安迪一樣,非常希望逃離監獄這個牢籠,在電影中,描述了瑞德三次假釋的場景,三次面對假釋官,瑞德都有不同的表現,然而前兩次都沒有得到假釋批準,所以在第三次假釋審問中,他說了句“老子已經不在乎了”,但卻意外得到批準,他經歷了老布魯克斯的遭遇后,顯示出了自己已經被體制化的跡象之后,才假釋成功。雖然成功出獄,但是他同樣發現自己其實已經被體制化深深侵蝕了。影片開始時,都認為瑞德是個足夠冷靜的人,他勸說安迪不要對生活抱有太大的希望,但卻在假釋被駁回時看到了失望,安迪送給他了一個口琴,并沒有立刻吹,而是在夜晚一人時讓口琴響起,只是短暫的一瞬,才感受到瑞德也被體制化了。“40年來每次上廁所都要請示,不請示連一滴尿都尿不出來。”他無法想象監獄外的生活,好像只有生活在監獄里的制度里,他才可以安心。[6]瑞德入獄初期還可以對其他犯人說“你還有期望,不要放下”。但慢慢地,時間消磨了他所有的期望,在被審問中,他無所謂說“這會,你們填什么都行,我不在乎”,直到最后,他可以出去了,可所有人都明白,他已經屈服于體制化了。但是慶幸的是,他所見到的正是由安迪,自安迪在離開肖申克之前,就向瑞德交代了自己將要逃去的目的地,還告知瑞德要是有一日可以假釋適用,就必須要去那里重新尋找自己,也就只有當瑞德再看到在監獄外的由安迪時,才再次找回對自由的向往,對自己的向往。
第三種則是對抗體制化的人物形象。毫無疑問,安迪從始至終都在對抗監獄的體制化,在漫長的牢獄生涯之中,雖然向生活做出了妥協,但卻從來沒有在內心之中屈服過。入獄之時,安迪堅持自己無罪,但迫于證據確鑿,無奈入獄。在獄中的這二十年,安迪經歷過很多事情,被暴力對待、被眾人排擠,甚至連唯一的精神寄托——自己的學生,都因為想為自己翻案,而被典獄長設計槍殺。安迪即使失去了妻子,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嚴,但是他依舊沒有向生活屈服,反而始終保持著希望,希望是美好的,也是人間至善,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新建圖書館之際,安迪大膽打開留聲機,對著整個監獄廣播了一首象征著自由的歌曲,因此被關進了禁閉室,瑞德等人在欣喜聽到”最美妙的歌曲“之余,也不禁為安迪的心理狀態擔憂。在本就枯燥乏味的監獄之中,身邊有人是確定自己還活著的重要標志之一,被關進禁閉室里,不見天日,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精神折磨。但當安迪出來的時候,卻面帶笑容,只因那首歌讓他感受到了外界,讓他的內心里充滿了希望。他是一個充滿希望但是又付諸行動的人,他不僅說到還會做到,是一個真正的對抗體制化的勇者。
三、信仰與正義的價值觀隱喻
這部電影之所以是世界電影史上的巔峰之作,除了情節、藝術手法之外,其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也是不容忽視的。其本片中主要體現出的信仰與正義,也深深影響著許多觀眾。一開始觀眾被影片中的法官以“證據確鑿”為由判處安迪終身監禁,許多人或許真的相信安迪就是“戴罪之身”,而且從他起了要越獄的念頭開始時,觀眾也只是把他當做犯罪分子越獄的滑稽戲碼,然而湯米的出現卻打破了這一猜想。安迪從始至終都沒有殺害妻子及其情人,他是一個清清白白的人,卻平白無故遭受到了20多年的監獄生活,為其申冤的學生兼朋友湯米也被道貌岸然的卑鄙典獄長暗中殺害。監獄長本想借其淫威逼迫安迪為自己服務,所以為了心中的信仰和公平正義,安迪只能暫時屈服于典獄長的淫威之下。當然他并不只是屈服于淫威之下,他反而利用這層關系做了許多有意義的事情。最后他也不是單純地為了逃獄,因為心中有信仰,他才有了越獄的決心,并且勇往直前;因為心中有正義,他才收集典獄長犯罪的證據,力求一舉擊倒;因為心中有情義,他才會和瑞德成為朋友,并給予對方生的希望。
正如一句話說得好,“記住,‘希望’是永遠存在的。”在以安迪、典獄長、獄警和囚犯們構成的這個制度世界里,本身就是錯謬、混亂的,安迪是一個沒有犯罪的好人,卻被關進監獄被迫接受改造,面對欺凌。但是值得慶幸的是,安迪作為電影中的第一主人公,具備了許多優良的品質,他聰明、善良、隱忍、堅強等等,是電影中正義的化身,他始終心懷信仰,始終懷抱希望,選擇自由,對抗黑暗,他沖破的不僅是監獄的“牢籠”,更是黑暗的制度的“牢籠”,他不僅救了自己,也救了瑞德,甚至是救了整個監獄里的囚犯們。在這樣一個錯謬、混亂、顛倒黑白的世界,大部分人通常會自甘墮落或者精神崩潰,而我們的主人公安迪卻像一只浴火重生的火鳳凰,帶著正義與信仰健康自信地飛出了煉獄的火坑。
結語
作為一部偉大的歷史影片,導演在《肖申克的救贖》中所運用的多重敘述者敘事、將天然生物性空間和藝術表意空間融合的敘述方式,引導觀眾思索影片中“救贖”的深刻含義。影片中通過視聽修辭的符號隱喻、三個主角的人物形象隱喻以及信仰與正義的價值觀隱喻方式的運用,幫助觀眾在觀影的過程中重新構建情節,從而更能清晰明了地掌握影片敘事內容和內涵,而肖申克監獄空間中的制度和人性的真美善都被演員演繹得淋漓盡致,具有很大的藝術觀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