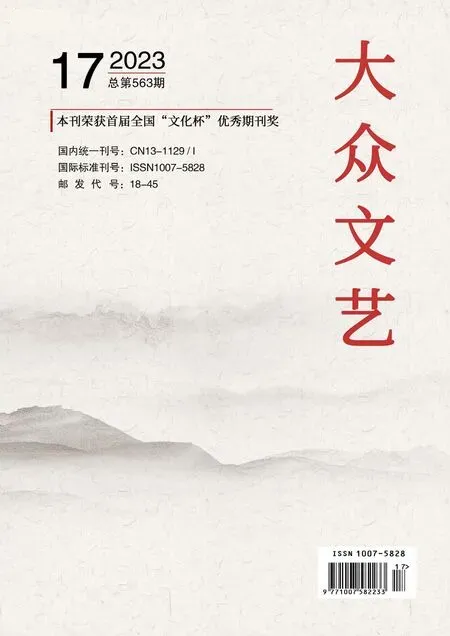數字技術下光暈再造的實現路徑
孔雅琪
(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哈爾濱 150000)
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本雅明把藝術作品的生產時代劃分為“手工復制時代”與“機械復制時代”。隨著機械復制技術的發展,大批量的復制藝術品出現在人們視野中,大大增加了藝術品的展示機會,導致了藝術品的獨一無二性、原真性與光暈都隨之消失。然而,我們所處的時代與本雅明的時代相比又有所不同,隨著信息技術不斷發展,我們迎來了數字技術時代,互聯網、人工智能、AI等技術紛紛與藝術作品相融合,不僅拓寬了藝術作品的傳播渠道,也推動了藝術作品光暈的再造。
一、光暈的原初概念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從光暈消失的角度批判了復制藝術品。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時代的那些復制藝術品,那些大批量走技術化路線生產出的美學作品,一些直接借鑒甚至復制藝術作品、藝術風格的東西,從外觀上看的確是美的也很和諧,但都缺少了光暈。光暈是本雅明獨創的理論概念,數次出現在本雅明的文章當中。因此,要理解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思想、分析光暈消失的原因以及找尋光暈再造的實現路徑,明確理解光暈原初概念至關重要。
光暈一詞最早出自德語Aura,被譯為(一個人特殊的)光芒、氣息、影響作用,同時也是指教堂中圣像畫上圍繞著圣人頭上的一抹光。例如:圣母、耶穌頭頂都有一抹光暈,這便是光暈的出處。光暈在德語、英語、拉丁語中的解釋都是大同小異的,無一例外地與“光”相聯系,這些都在彰顯著光暈中摻雜著神學的韻味。因此,在這個層面上便不難理解本雅明所說的藝術作品的膜拜價值也正是來源于此[1]。
本雅明認為,光暈這一概念是傳統藝術與機械復制藝術的根本性區別,也是傳統藝術的魂之所在。本雅明初次提及光暈是在他的《攝影小史》中“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在眼前。靜歇在夏日正午,沿著地平線那方山的弧線,或順著投影在觀者身上的一截樹枝,知道“此時此刻”成為顯現的一部分——這就是呼吸那遠山,那樹枝的光暈。”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本雅明將光暈表述為“在一定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切之物的獨一無二的顯現。”[2]本雅明指出,藝術作品的“獨一無二”的價值根植于神學,同時獨一無二性也成了光暈的本質特征。基于此,我們清楚地了解了光暈的原初概念以及光暈的本質特征“獨一無二性”。20世紀開始,機械復制技術達到了空前的水平,發達資本主義時期機械可以將人的手解放出來,用機器替代對藝術品進行大規模標準化復制生產,復制藝術品喪失了作為藝術品的獨一無二性,最終造成了藝術作品的危機—光暈的消失。
二、光暈的消失
本雅明對于光暈消失的態度是矛盾且復雜的,在他為藝術品逝去的光暈感到惋惜的同時,也驚喜于機械復制技術帶給社會的巨大變化,不僅在規模上制造了數量頗豐的藝術品,更是對人的感知方式產生了深刻變革。通過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關于原真性、膜拜價值與展示價值的論述,可以分析出光暈消失的原因來自以下兩方面:
(一)原真性的喪失
原真性是指即時即地性,即它在問世地點的獨一無二性,藝術作品只有借助的獨一無二性才能夠構成歷史,這也是機械復制的藝術品不能實現的,復制藝術品無法再判斷藝術品實際存在時間與長短,這導致了復制藝術品的歷史證據難以確定,消解了藝術品內在的歷史感,在此基礎上,該藝術品的權威性也難以確定。本雅明認為,即便是最完美的藝術品,也無法具備藝術品的即時即地性、獨一無二性,這是藝術品原真性的根本屬性,也是光暈的本質特征,而那些機械復制技術的東西根本無法分清它的即時即地性,它隨處可見,因此消解了原作的原真性。好比說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世界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這些藝術品它們都有很多的復制品,可以出現在公眾建筑、走廊、書本、廣告中,但是哪怕是最精細的仿制品也無法將原作的原真性復制出來,只有我們到了米蘭圣瑪利亞感恩教堂、盧浮宮,即時即地看到原作時,才能感受到藝術品的原真性。因此,機械復制時代的復制藝術品,他們喪失掉了即時即地性、獨一無二性,也失去了獨一無二性中蘊含的歷史感與權威性,消解掉了藝術品的原真性,最終導致了光暈的消失[4]。
(二)膜拜價值轉向展示價值
本雅明指出“一件藝術品的獨一無二性是與它置身于其中的傳統關聯相一致的。”“最早的藝術品起源于某種禮儀——起初是巫術禮儀,再后來是宗教禮儀。”[2]而藝術品的獨一無二性也就是光暈的價值是通過膜拜價值展現出來的,因此很容易理解膜拜價值是與神學、禮儀、傳統相關的。例如中世紀大教堂的圣母像,正是為了受教徒頂禮膜拜所產生的。隨著機械復制技術的發展,對藝術品的觀賞不再局限于該藝術品所在地,人們可以在不同地點以不同方式去參觀這些復制藝術品,隨著單個藝術活動從膜拜解放出來,其產品便增加了展示機會,大大地提高了藝術品的可展示性,同時藝術品喪失了即時即地性,它的膜拜價值也被推向了展示價值的一端。膜拜價值作為光暈價值的展現,在膜拜價值滑向展示價值的過程中,光暈也隨之消失了。[5]但是本雅明并不認為藝術品在禮儀中被解放是一件壞事,他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一件藝術品的可機械復制性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把藝術品從它的禮儀的寄生中解放了出來。”[2]
藝術品之所以具有膜拜價值,是因為藝術品及其技術只能與當時的社會、禮儀相融合才能使藝術品存活下來,與傳統相關聯才能展示其光暈。隨著機械復制技術的進步,藝術品技術與社會結構、傳統逐漸對立起來,藝術品從膜拜價值轉變為了展示價值,光暈也隨之消失。因此,如何引導藝術品及其技術的發展,如何實現藝術品光暈的再造以及膜拜價值的回歸,這都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課題。
三、數字技術下光暈再造的實現路徑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嘗試通過將藝術品及其技術與數字技術相融合,找到光暈在數字時代的再造的實現路徑。
(一)虛擬空間的塑造
數字技術所塑造的虛擬空間,可以使觀眾穿梭在“過去與未來、感性與理性”不同邏輯的時空維度里。過去的無論是藝術品原作還是復制藝術,采取的參觀方式都是直接參觀的方式,但這種參觀方式具有很大的時空局限性。塑造虛擬空間,應將數字技術融入藝術品中,突破藝術品原有的時空界限、拓寬藝術品參觀渠道,為沉浸式交互體驗奠定環境基礎。例如“發現?養心殿”體驗展,將高精度掃描技術應用于97件藝術品上,實現了數字復制。同時借助VR眼鏡等虛擬現實設備,在虛擬空間中,觀眾不僅可以身臨其境的觀賞、挑選心儀的作品,還可以全面體驗藝術品的制作過程,感受來自古代藝術作品的光暈與魅力,極大地豐富了觀眾的體驗感,增強了傳播效益。除此之外,還可以將LED、全息投影技術運用于畫展,打造出全方位立體環繞的藝術效果,能夠使觀眾好似處于藝術家創作藝術品的時代或是無盡貼近藝術品、藝術場所,見證偉大藝術作品的誕生,感受來自藝術品的光暈。在這種由數字技術打造的虛擬空間中,觀眾仿佛置身于數字技術為藝術品帶來的神秘光暈中。因此,藝術品可以在虛擬空間的塑造的過程中實現光暈再造。
(二)沉浸式交互體驗的營造
1.感官交互體驗
人類感知與認識外界事物的橋梁是感覺器官,人們可以通過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形成對事物的初步認知。以“發現?養心殿”體驗展為例,該展將博物館與數字技術相結合,突破以往展覽以視覺為核心的展示方式[3]。目前,博物館的數字文化展覽,更多采用了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相結合的多感官交互體驗模式。
首先,在藝術作品數字化的視覺體驗方面,設計師們更多將視野放在造型與色彩上。展示空間造型的復雜多變可以為觀眾帶來視覺上的新奇感與美感,此外,色彩是視覺交互設計的靈魂,會影響觀眾的內心感受與參觀行為。例如,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的展廳以紅色作為展內的主色調,大面積的紅色給觀者強烈的視覺沖擊的同時,也會營造出濃厚的革命文化氛圍,使觀眾們會不自覺地將自身代入其中被革命精神所震撼。
第二,在藝術作品數字化的聽覺體驗方面,設計師往往會用聽覺去彌補視覺藝術無法到達之境,視覺與聽覺的結合為觀眾帶來更為震撼的視聽交互體驗。設計師不僅可以通過對藝術品的解說增強觀眾對于藝術品的理解與印象,還可以運用合乎主題的背景音樂渲染氣氛。例如裸眼VR《清明上河圖》的設計就很好地運用了背景音樂及聲音,通過聲音來傳達專屬于北宋的時代特點與人文風格,使人身臨其境。
第三,在藝術作品數字化的嗅覺體驗方面,無論是回憶或是藝術作品對于觀眾來說都是有特定味道的。例如,當觀眾們聞到檀香的味道會想起故宮或是博物館,聞到向日葵的味道會想到凡?高的《向日葵》作品等。因此,近年來設計師將嗅覺體驗加入交互體驗中,使觀眾不僅可以通過視聽交互體驗了解感知藝術品,更可以通過嗅覺進而喚醒埋藏在觀眾心底的記憶。
第四,在藝術作品數字化的觸覺體驗方面,這是一種作為直接的交互體驗模式,能夠直接影響人的感受與心理活動。在以往以參觀為核心的藝術品展覽中,往往放置著請勿觸摸的牌子,使觀眾們只可遠觀,但觸覺體驗的加入大大彌補了這一處的空白。例如,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使觀眾在虛擬空間中任意觸摸、拿取,實現觀眾與藝術品之間的“0距離”,打破了觀眾與藝術品現實的隔閡。同時,將觸屏設備應用于藝術作品或博物館,運用信息技術的儲藏功能,觀眾可以通過滑動觸摸屏更為直觀且快速地了解他所欣賞藝術品的相關信息。
2.行為交互體驗
行為交互體驗更加注重通過身體的互動來實現信息的交流與傳播,這種交互設計在增強展示空間趣味性和娛樂性的同時還能保證信息傳播的有效性。在趣味性強的行為交互設計中,可以獲得全方位的身心體驗,例如VR皮影戲《田忌賽馬》通過趣味性行為交互設計與藝術作品相結合使觀眾們實現更為深層次的體驗,進一步提升觀眾的沉浸感,更好地滿足了觀眾對于藝術品的生理以及心理需求。
(三)膜拜價值的回歸
1.膜拜價值轉向展示價值
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到過,機械復制時代之前是藝術作品是以膜拜價值為主的,膜拜價值起源于巫術禮儀、宗教禮儀并伴隨著機械復制技術的發展,到了機械復制時代的復制藝術品從禮儀中解放出來且不斷增加展示機會,最終導致了膜拜價值轉向了展示價值[2]。例如,《蒙娜麗莎的微笑》《最后的晚餐》等藝術作品,在機械復制時代出現了太多的仿制品了,人們去參觀或是擁有這些復制藝術品其目的也不是單單的膜拜了,復制藝術品更多起到展覽、裝飾的作用。隨著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我們似乎可以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推動膜拜價值的再次回歸,由此實現光暈再造的可能。
2.膜拜價值的回歸
首先,數字技術的巨大進步,例如全息投影、VR的應用,不僅為觀眾營造了感官與行為的交互體驗增強其沉浸感,也會使觀眾嘆服于數字技術的強大魅力。其次,藝術作品與數字技術的融合,有助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與發展。例如,“發現?養心殿”體驗展更能提供給觀眾家國情懷等情緒價值,促進中華文化的推陳出新,增強觀眾的文化崇拜與文化認同。借助數字技術可以使觀眾肆意穿梭在過去與未來[3]。通過在虛擬空間的交互體驗,不僅使觀眾們嘆服日新月異的數字技術,更可以增強觀眾對藝術品的崇拜,這些都可以推動膜拜價值的回歸并賦予膜拜價值新的時代內涵。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使觀眾超越時空的界限,也推動了藝術品收獲了教育價值、社會價值等附加價值,實現多元價值共振,加速了藝術作品與數字技術與時代相融合,兼收并蓄,推陳出新,助力藝術作品光暈的再造。
結語
本雅明認為,每一個藝術品都有其獨一無二性,都有其光暈,不過是隨著機械復制技術的發展以及膜拜價值轉向展示價值的過程中,藝術品的光暈消失了。在數字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依舊希望藝術品再次散發其光彩,實現光暈再造。在數字技術的背景下,將技術與藝術作品融合,通過塑造虛擬空間、營造交互體驗與推動膜拜價值回歸都會讓本身被展示價值所掩蓋的藝術作品的光暈再現。與此同時,重建藝術作品的光暈是時代賦予我們每一個人的重要任務,事關著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我們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