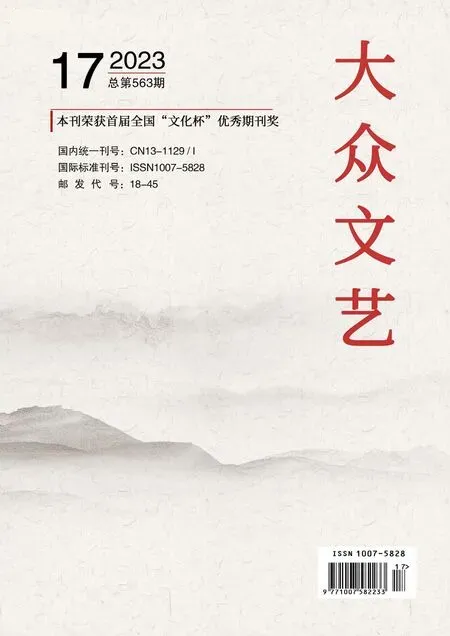論日本近現代美學論題中文藝與道德的復雜關系
——以物哀和陰翳為例
吳蘇桐
(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蕪湖 241000)
“物哀”是日本美學的核心論題之一。該論題深受中國古代“物感說”影響,自18世紀日本江戶時代的學者本居宣長始,“物哀”成了獨立的美學論題,與中國古代的“物感說”分庭抗禮。在本居宣長對“物哀”美學論題的構建過程中,文藝與道德的關系問題這一文藝學的經典議題,因與意識形態糾纏在一起,從而呈現出復雜性。
“陰翳”是日本美學的另一重要論題。這一論題與“物哀”緊密聯系,由作家谷崎潤一郎在文藝隨筆《陰翳禮贊》中總結提出。谷崎潤一郎在隨筆中概括了日本陰翳之美的方方面面,包括建筑、器物、藝術、藝妓、文學等,在隨筆的最后,他痛心地指出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日本傳統陰翳之美正在流逝的現狀,并試圖喚醒沉睡中的陰翳之美。在“陰翳”美學論題中,文藝與道德的關系同樣呈現著復雜性。
一、道德宗旨的退場與復歸:去漢化語境下的“物哀”美學
日本文化深受中國古代文化影響,“物哀”也與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物感說”緊密相關。在中國古代文論中,最早提出藝術源于主客之間審美交感的文獻是《禮記?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動,故形于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①[1]《樂記》以音樂創作為例,提出了審美體驗之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的觀點,它首次明確了“樂”產生于人內心的情感,而人內心的情感的產生原因則是受到了外物的影響。由此,“物—心—樂”的審美邏輯鏈首次被闡發了出來。②[1]《禮記》作為一部總結先秦思想的書籍,其資料大多來源于先秦諸子,但其成書于西漢,難免成為漢儒闡發儒家義理的工具,“物感說”也是漢儒禮教詩學的產物。“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物”在此時也被局限于儒家禮教的狹小天地內,其作為審美自然物的一面以及其他更深廣的可能性空間則被隱藏于儒教之下。由此可見,來源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物感說”內蘊著道德倫理的規訓。朱光潛先生在《文藝心理學》中指出:“在中國方面,從周秦一直到現代西方文藝思潮的輸入,文藝都被認為是道德的附庸。這種思想是國民性的表現。”③[2]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的日本文化也接收了儒家道德倫理的影響,本居宣長之前的日本文論中也存在類似的概念,如9世紀初,空海在《文鏡秘府論》中,有“政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南卷?集論》)之句,明顯能看出中國古代《毛詩序》的影子;在對日本文學經典如《源氏物語》的闡釋中,“懲惡揚善”的道德規訓論調也十分常見。
18世紀,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在去道德化與對抗漢意的文化語境下完成了對“物哀”美學論題的建構,而這一建構正是通過對《源氏物語》的重新闡釋來實現的。在1763年對和歌的研究著作《石上私淑言》中,他對“物哀”這一論題進行了辭源學上的探究④[3],他指出,在古代日本,“哀”(れです)是一個嘆詞,可用于表達多種情感,如悲傷、哀愁、高興、氣惱、訝異等,由此可見,不可用中國語言中“哀”的含義來對釋該詞,中文中的“哀”偏向消極情感,而日語中“哀”的情感指向更為復雜,同時包羅積極與消極的情感。在對“物哀”進行辭源學追溯的基礎之上,在研究《源氏物語》的專著,與《石上私淑言》同年發表的著作《紫文要領》中,本居宣長嘗試顛覆長期以來人們對《源氏物語》的道德主義理解,他認為,這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儒學道德主義立場所致的謬誤,實際上,《源氏物語》等中古日本物語文學背后的寫作目的是“物哀”或“知物哀”。在本居宣長的理論中,“物哀”是剝離了道德色彩的。他將“物哀”分為兩部分,一是“感物之心”,一是“感事之心”。“感物之心”就是指人心能對客觀自然風物有所感受,如看見櫻花飄落的美麗而心生感動,就是能知物哀之人,而看見美麗的櫻花雨而無動于衷,就是不知物哀的表現。“感事之心”就是能夠通達事理人情,有強大的共情能力,對人世間的情感有敏銳的體察,如看見他人悲傷,我心也跟著傷悲,即是知物哀的表現。在世間人情中,本居宣長認為最令人動容的莫過于男女之情,而男女之情中,最能使人知物哀的即是“不倫之戀”。在《源氏物語》的文本中,主人公光源氏周旋于一眾女性之中,常與她們發生違背道德倫理的不倫之戀,這些引起了本居宣長的關注,由此引起的興奮、思念、自責、焦慮、痛苦等情感,都是人情中最珍稀可貴,這些消極悲傷的情感比積極喜悅的情感更有深度,不論道德與否,只要出自心中的真情,都無可厚非,都是能知物哀的好人。《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就是將主人公光源氏當作“好人”來寫的,翻開小說,多處相關描寫似乎都可佐證本居宣長的論點,例如,《須磨》卷中,光源氏遭遇貶謫,世人多有嘆息,對朝廷這一做法不滿。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本居宣長借助對《源氏物語》的重新闡釋完成了對“物哀”美學論題的建構。“物哀”即是外在之物觸發人心引起的諸種自然情感,是對人情的廣泛理解與包容,其中并無道德訓誡因素,也無現實功利性。但如果就此指認他對背德之事大加推崇,就有失公允了。本居宣長認為,《源氏物語》看似對違背道德倫理的不倫戀情津津樂道,但這并非對不道德之事的推崇,而是為了表現“物哀”。他認為,不道德之內容仿佛是污泥濁水,而對“物哀”的最終感悟則是美麗的蓮花,蓄積污泥不是為了欣賞污泥本身,而是為了培育出美麗的“物哀之花”。《源氏物語》及之后的日本經典文學的創作宗旨就是“知物哀”,作者要將自己的感受生動如實地呈現,以尋求讀者的共情共感,讀者的閱讀宗旨也是“知物哀”,雙方都單純只有審美目的,而無任何功利。“知物哀”就是從本真的自然人性與人情出發,不受道德倫理的束縛,從而達到對萬事萬物的理解,尤其是能夠對悲傷、痛苦、哀怨等情緒有深刻的感悟。“藝術的功用,像托爾斯泰所說的,在傳染情感,打破人與人的界限。”⑤[2]在《文藝心理學》中,朱光潛先生論及文藝與道德的關系時,談及了藝術的這一功用。情感比常人更豐富細膩的藝術家借他們的眼睛給讀者看,使讀者從個人畫地為牢的狹小天地中解放出來,進入更廣闊的世界,獲得不尋常的啟發。這種啟發正是一切道德的基礎,它使人類的想象力增加,同理心伸展,對人情事理的認識更加深廣真切。本居宣長的“知物哀”正與孔子“詩可以群”一說貼合。縱觀人類歷史,當許多道德規訓缺乏這種情感基礎時,它的目的往往適得其反。作為應付人生的方法,道德能否合式,自然要看對人生的了解程度何如,沒有什么能比文藝帶給人類的人生觀照更深切動人。
若結合當時的思想氣候與歷史文化背景,本居宣長“物哀論”的建構并不單純是為了審美與人生,更摻雜了復雜的意識形態目的。直到豐臣秀吉時代前,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都一直保持著強大的影響,日本學者談論任何文化問題,都會拿中國文化作比,中國文化與文學曾一度是日本學者的價值尺度與模范;豐臣秀吉時代后,由于大明國力衰微并為清軍所滅,中國文化內部此時也出現了嚴重的僵化,相較之下,日本江戶時代整體發展繁榮,中國在日本人心中的偶像地位發生了動搖。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之下,不少日本學者企圖否定中華中心論,并嘗試從各方面論證日本文化的優越性,本居宣長就是其中之一,對日本文學經典重新闡發的背后,正是他們極力擺脫“漢意”的文化用意,“物哀論”正是在去漢化大背景下提出的。由于中國的去神化進程發生較早,周王代商之后,隨著人祭制度的消亡,諸神開始退場,一個重實用重知性的民族由此誕生,中國文化在情感表現上也趨于節制,文藝一直被看作道德倫理的載體;而日本的情況則有很大不同,未受中國文化影響之前,日本的神道文化非常發達,人們崇拜著伊邪那岐神和伊邪那美神,日本民族的情感趨向于不加節制的泛濫,文藝的載道色彩相對于中國較淡。立足于這樣的比較,本居宣長等人找到了日本文化的獨特性。
綜上所述,在本居宣長“物哀”美學論題的建構中,對于違背倫理道德之事的書寫恰恰指向本真的人情,而對自然人性與人情廣泛而深刻的了解,正是一切道德的基礎,這正是“知物哀”的最終價值。然而,正像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中指出的那樣,“道德”一詞與“政治”正相關,本居宣長對“物哀”論題的道德質素進行剝離,背后恰恰隱伏著強烈的意識形態用意。在“物哀”美學論題中,道德宗旨在退場中悄然復歸。
二、道德規訓的隱匿與顯現:對抗西方文明語境下的“陰翳”美學
“陰翳”一詞,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已出現,北宋歐陽修《醉翁亭記》中,“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就是為人熟知的例子。⑥[4]這里的“陰翳”是指繁茂的樹葉形成的綠蔭,這是此詞最原始的含義,不過,其中已內蘊著一些美學因子,比如光與影的交互之美,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最早將“陰翳”作為美學概念加以闡發的,是近現代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贊》一文中,谷崎潤一郎提到:“美,不存在于物體之中,而存在于物與物產生的陰翳的波紋和明暗之中。夜明珠置于暗處方能大放光彩,如果離開了陰翳的作用,就不會產生美。”⑦[5]這是一個文學化的描述,中國學者葉渭渠對此進一步闡釋道:“陰翳美從本質上而言,便是光與影的美學。陰翳的奧秘,便在于光與影的巧妙分辨。”⑧[6]
其實,在《陰翳禮贊》中,陰翳美所包羅的空間非常廣泛,他將生活、建筑、器物、音樂、工藝品、女性、文學藝術等娓娓道來,細細發掘蘊藏其中的陰翳之美。例如,“日本廁所更能使人精神安然,這種地方必定遠離堂屋,建筑在綠葉飄香、苔蘚流芳的林蔭深處。沿著廊子走去,蹲伏于門窗的反射,沉浸在冥想之中。”⑨[5]其中,最具深刻性的部分就是關于女性的部分。在《陰翳禮贊》一文中,谷崎潤一郎多次提及了幽暗中的女性之美,如“藏在黝黯的深閨里,珠簾繡幕,晝夜埋身于黑暗之中,只憑一張臉表示其存在”⑩[5],又如“對于黑暗中的她們來說,只要有一副慘白的面孔,胴體就不重要了。”(11)[5]當身體掩藏在層層衣物下,掩藏于光線似有若無的陰翳中,視覺上的若隱若現,反而平添了幾分想象的空間。
“陰翳”看似只是個偏向于描述性的印象式美學論題,但若深入分析,會發現其中內蘊著文藝與道德的復雜關系。日本民族為何鐘愛陰翳之美?與西方的直露相比,東方人更傾向于以含蓄內斂的方式表達感情,而日本民族更是這方面的佼佼者,長期形成的日本民族性格往往會以一種極度壓抑的方式表現出來。從孩童時代起,日本人就生活在克制守禮的文化環境下,受到道德的規訓。他們以不給他者帶來麻煩為準則,而直接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感情往往會給他者帶來麻煩,這是不被日本文化環境所允許的。心中的感情和欲望只能被暫時遏制,而永遠不可能被真正消除,未得到釋放的情感和欲望仿佛一股洶涌的暗流,總會以另一種形式顯現,而“陰翳”之美就可以看作這種顯現。就人的心理層面而言,“陰翳”表現為對人內心陰暗面以及隱秘欲望的保護,洶涌的情感和欲望找不到宣泄的出口,一些陰暗晦澀的想法就會在心中滋生,日本人所生活文化環境使得他們心中積攢下了“陰翳”,他們終其一生都在學習如何與“陰翳”共處,在美學方面,比起光明,陰翳之美更能讓他們找到共鳴。在其中,他們更能反觀內心被壓抑的欲望,平日生活里所受的道德規訓,在欣賞陰翳美之時,也可暫時隱匿。
在谷崎潤一郎的文學作品中,“陰翳”美學中文藝與道德的關系更能被認識。在早年作品《刺青》中,一雙轎簾后女子雪白的雙足讓文身師清吉向往不已;在《春琴抄》中,故意刺瞎雙眼的佐助將春琴的美麗永遠留在了記憶中,盲人的世界看似晦暗無光,但許多事物正因此增添了美麗。被壓抑的欲望潛藏在谷崎潤一郎的文學書寫中,完美呼應了其《陰翳禮贊》中提出的觀點,其中文藝與道德的復雜關系也得以凸顯。被文化環境壓抑了自身情感欲望的日本人,在對文藝作品的創作和欣賞中,可以暫時遠離平日所受的道德規訓,讓壓抑的欲望潛流浮出水面;而體現“陰翳”之美的情欲書寫背后,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規訓陰云也從未散去。道德規訓正如同形成“陰翳”的光影,在隱匿與顯現之間橫跳。
“陰翳”與“物哀”,這兩個美學論題聯系緊密。谷崎潤一郎有翻譯《源氏物語》的經歷,在他的自述中,他也提到受其影響很大。具有“物哀”美學風格的《源氏物語》對谷崎潤一郎“陰翳”美學論題的形成的確有重要影響。“物哀論”中對深廣人情事理的看重正與“陰翳論”相通,“陰翳美”也繼承了“物哀美”中文藝與道德的這種復雜關系。《末摘花》是《源氏物語》中重要的一卷,這卷講述了光源氏與一名官宦女子只隔著屏風說了幾句話,聽了一會兒女子的琴聲,未知該女子相貌如何,就在黑暗的空間中與這名女子交歡。在幽暗中,男子對女子的了解只能存在于縹緲的想象之中,而正是這種隔著多層的想象,為女子平添了幾分神秘的美感,這也是“陰翳”之美在《源氏物語》中的體現。偷情給人帶來的往往是復雜的情感,在這段有關光源氏不道德行為的情欲書寫背后,隱伏著的深刻復雜情感恰恰是一切道德得以可能的基礎;而光源氏與末摘花“陰翳”中的情欲,正是平日里被道德規訓所壓抑情感的體現。道德宗旨在這里顯現又復歸,道德規訓的陰云也始終處于顯隱之間。
在朱光潛《文藝心理學》中,“道德”也指“政治”,這里援引朱光潛先生之義更進一步分析文藝與道德的關系,谷崎潤一郎的“陰翳”美學背后,同樣潛藏著重要的意識形態意圖。谷崎潤一郎的時代,已不同于平安時代的上流貴族時代,而是大正末期的沒落豪族時代,所以,“陰翳”相較于“物哀”,內蘊著新變。在明治維新之后,西方文化對日本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美學方面,西方的光明之美已足以與日本的陰翳之美形成對抗,日本文化中傳統的陰翳之美正在消散。初登文壇時,谷崎潤一郎還是西方文化的擁躉,他處于受西方文明影響頗深的日本關東地區,早期的風格呈現出明朗的官能主義色彩,他追求對感官刺激的書寫,追求華美犀利的語言風格;在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之后,他被迫來到了保留著日本傳統風韻的關西地區生活。在京都,他得以親近平安王朝的古韻,欣賞傳統地道的木偶凈琉璃、能樂、三味線等藝術,與溫柔古雅的關西女性打交道,這些都喚醒了他心中深藏的古典基因。在《陰翳禮贊》中,透過燈光、廁所、建筑、藝術、女性等方方面面,對行將逝去的日本傳統美學的追思浮現筆端,這些細微的陰翳之美,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正在逐漸消逝,比如大都市里隨處可見的光污染,即是太過明朗所致,而體現大自然明暗光影的陰翳之美,已隨著城市化進程而減少。“陰翳”美學的背后,隱現著谷崎潤一郎的文化意圖和意識形態用意,他想將代表東方傳統美學的“陰翳”復蘇,以此來對抗西方的明朗之美,體現該民族的優越性。西方太過明朗的美學風格,崇尚感官刺激,而刺激的感官書寫體現著泛濫的情欲,過于泛濫的情欲常被人們認為有違倫理道德,這樣的美學風格沖擊著含蓄內斂的日本傳統美學,谷崎潤一郎用“陰翳”這一道德規訓色彩處于隱顯之間的美學論題,也是對西方明朗美學沖擊下的日本文化進行糾偏,他的文化用意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在谷崎潤一郎對“陰翳”美學論題的建構中,同樣可看出文藝與道德的復雜關系。情欲被掩藏于幽暗處,人內心壓抑的隱秘欲望在陰翳的保護中得到釋放,而不至于露骨地顯示在陽光下,道德規訓在這里暫時隱匿。然而,正是因為日常生活中道德規訓的存在,日本人才不得不借助于“陰翳”的保護來獲得一絲體面,道德規訓又在幽暗中顯現了。
三、日本近現代美學中文藝與道德復雜性的背后:主體性的缺失
通過上述分析,“物哀”和“陰翳”這兩個日本近現代美學論題中,文藝與道德的關系呈現出不同尋常的復雜性,而這種復雜性折射出的是日本文化背景中人之主體性的缺失。
這里需要對本文中“主體性”這一概念做出界定。本文中的“主體性”,是基于西方啟蒙運動的理性主體的,啟蒙運動的重要目的,是希望人類能夠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依附于他者。這里的“主體性”是一種個人主體性,而不是整個民族的民族主體性。日本戰后思想家丸山真男認為,日本的民族主體性根基太深,以至于阻礙個人主體性的形成,他曾“著力批判阻礙日本人近代主體意識形成的社會結構性病理”。(12)[7]
日本這個民族,從一開始就沒有主體性存在的土壤。日本神道教影響下的天皇制度從古代就存在,在這樣的制度下,是沒有任何“個體”“主體”可言的。人,以及一切人倫關系都緊緊地嫁接在“民族國家”之上,而“天皇”是民族國家的象征。日本人在發出一切行為之前,都要考慮是否符合“民族國家”的利益。于是,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評判一個行為道德與否,其標準就是是否符合天皇以及民族國家的利益,在這樣的標準下,日本文化語境下的“道德”一詞也變得曖昧起來。這樣的道德標準固然給日本民族帶來了團結的一面,但同時,也給人類歷史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在學者范國英對四川省建川博物館藏侵華日軍家書的研究中,他發現“在日本侵華時期,日本民眾的個體主體性已經被民族國家(天皇),以及體現民族國家(天皇)訴求的圣戰所蒙蔽,民族國家(天皇)和圣戰的訴求在侵蝕著日本民眾的情感、意志和欲望的同時,也成了支配那一時期日本民眾認識世界的基本框架。”(13)[8]由此可見,日本天皇制度下主體性的缺失從古代延續到近現代,在日本文化語境下,“道德”一詞的判斷標準也不同尋常,呈現出曖昧的特點。
文藝總是表現特定的社會現實與文化。在這樣的道德標準之下,文藝與道德的關系也變得復雜起來。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其他文明的民族,在古代,他們學習中國儒家文化;明治維新之后,西方以“理性”為代表的現代性思潮沖擊著日本傳統社會,日本將學習西方文化的路徑稱為“和魂洋才”之路。西方現代性思潮的根基是主體性,而這個主體性的根基從笛卡爾開始奠定,到康德和尼采那邊有了新變和裂解,但依然體現著主體精神,背后是一個能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和情感意志,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個體。而日本受神道教和天皇制影響頗深,這種影響已深入了日本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這種依附關系之下的主體性缺失也得以延續。從古代到近代,日本民族在多種文化文明之間搖擺,而每種文化都內蘊著其自身的道德準則,這些文化中內蘊的道德準則與日本文化中不同尋常的道德標準產生了碰撞,這些碰撞使得日本文化語境下文藝與道德的關系變得復雜起來。在日本近現代美學論題中,文藝與道德的復雜性得以表現,而這種復雜性的背后,折射的是日本文化語境長期以來的主體性缺失,無法責任自負的人在多重文化之間搖擺,卻找不到自身。
注釋:
①毛正天.古代詩學“應物斯感”論的建構歷程——中國古代心理詩學研究[J].學術論壇,2006(04),第1頁.
②毛正天.古代詩學“應物斯感”論的建構歷程——中國古代心理詩學研究[J].學術論壇,2006(04),第1頁.
③朱光潛.文藝心理學[M].中華書局,2012,第177頁.
④王向遠.感物而哀——從比較詩學的視角看本居宣長的“物哀”論[J].文化與詩學,2011(02),第6頁.
⑤朱光潛.文藝心理學[M].中華書局,2012,第178頁.
⑥王悅瀅.谷崎潤一郎的陰翳美論題研究[D].揚州大學,2019,第41頁.
⑦陰翳禮贊[M].谷崎潤一郎.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第12頁.
⑧葉渭渠.谷崎潤一郎傳[M].新世界出版,2005,第57頁.
⑨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贊[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第13頁.
⑩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贊[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第13頁.
(11)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贊[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第13頁.
(12)唐永亮.日本的“近代”與“近代的超克”之辯——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觀為中心[J].世界歷史,2017(02),第1頁.
(13)范國英.宏大話語下的主體性缺失——基于四川省建川博物館藏侵華日軍家書的研究[J].地方文化研究輯刊,2016(01),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