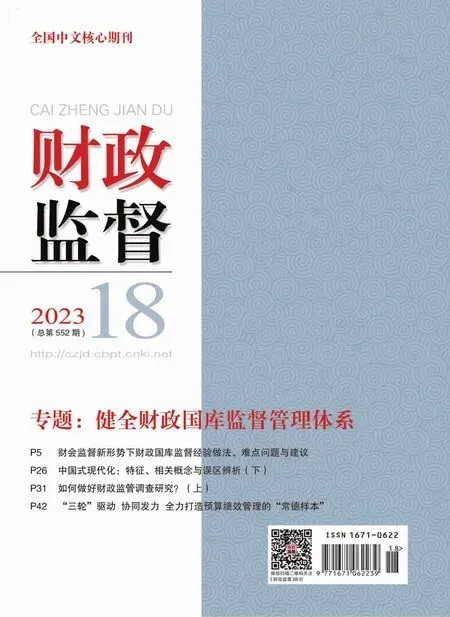中國式現代化:特征、相關概念與誤區辨析(下)
●賈 康
三、中國式現代化涉及的六個概念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早年孫中山先生面對著一個滿目瘡痍的中國,首先提出振興中華,其邏輯與當下所講的現代化, 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表述——振興中華就要現代化, 而這方面存在著一種只能順應、 不能違拗的世界潮流, 作為研究者, 筆者愿意將其表述為人類文明發展由客觀規律決定的主潮流, 這至少涉及六個概念。
首先, 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所有追求現代化的國家都必須經歷的發展。工業革命以后,中國嚴重落伍,必須迎頭趕上,而工業化方面的追趕,必然伴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 14 億中國人,其中的大多數以后一定都會生活在中心區域即大中小城鎮,改造城鄉分治格局、使社會成員便捷地取得市民身份勢在必行。 但歷經多年發展至今, 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才略高于45%,14 億中國人中的大多數, 還沒有取得市民身份。 前幾十年間進城的3 億多人,大多還被稱為“農民工及其家屬”(官方文件中稱之為 “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屬”), 他們在城市區域生活工作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早已脫離農村、農業,但是戶籍還在農村, 城鎮化推進過程還不足以使他們享受和其他市民同樣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待遇。究其原因,是由于有效供給和發展程度還不夠。以北上廣深為例,如果地方政府對戶籍管理有稍微放松的口風,就會有潮水般的人們涌入, 這是地方政府難以應對的。 客觀來看, 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工業化也有很大進展,但是還“大而不強”; 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雖然已經超出50%,但是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要低20 個百分點。我們的發展中有值得肯定的進步和成績, 也有十分明顯的短板和相當可觀的潛力與提升空間, 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質量地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實現升級發展。
另外四個概念, 即基本國策改革開放中的市場化、國際化,還有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表現的信息化(或稱高科技化),以及法治民主化(超越經濟視角的“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以及黨的二十大報告都反復強調“全面依法治國”“全過程人民民主”, 法治民主化可從這兩句話中提煉而來)。筆者認為法治與民主可掌握為一個合成概念——光講民主,容易落入所謂“多數人的暴政”;而“法治化”的“法治”,是法居于所有權力之上、體現人民公意的治理,而非只講制度條文的刀制(秦始皇時期就有秦律,是只講刀制的“法制”)。 應在法治化的框架下作出民主化的制度安排, 融合為一體。
以上六個概念, 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缺一不可。 這就是我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順應的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流。 進而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個性問題, 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統籌發展進程,掌握好系統工程。按照中央的表述,既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又要激勵地方企業和基層的首創精神,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深化改革的路上,攻克一個個難關、險關。 “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句話在當下的意義不言而喻。 從鴉片戰爭揭開中國近現代史的帷幕, 至今已有180 余年,終于看到了“從未如此接近”的民族偉大復興的曙光,但接下來不到30 年的時間段里, 挑戰性與歷史考驗性同之前的100 多年相比,至少要等量齊觀,而且可以說更有決定性的意義。 我們必須沖過這道“歷史三峽”,現在正是要爬坡過坎的時候,不進則退。 在“十四五”期間,我們所要接受的歷史考驗,是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十四五”末期使人均國民收入按照世界銀行可比口徑(美元計價),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水平。 從“十四五”初期算起,經過15 年,使經濟總量折為人均GDP,比2020 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 其后再經過15 年,到21 世紀中葉,即“第二個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需要攻堅克難、啃硬骨頭。比如,前文提到的促進共同富裕方面, 大多數人都存在“稅收厭惡”的房地產稅,能否按照現代化取向實施其改革, 讓社會接受而不引起大的震動?其他各種各樣的改革,又如何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又是別無選擇的。
四、 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誤區及解讀澄清
對于中國式現代化, 還有一些需要加以澄清的重要認識。 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重申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八字方針,筆者認為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看法和誤區進行“爭鳴”,很有現實意義。為充分領會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指導精神, 就要避免一些似是而非的話語引出的片面化認識,以防落入誤區,影響實際推進現代化的進程。筆者認為,有人把中國式現代化簡單概括為“不是資本推動下的現代化”,甚至對比式地下定義,講西方的現代化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這便是一種看似言之有理, 但實際上會產生嚴重誤導的說法。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央反復強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則, 毫無疑問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 但上述說法否定其視作對立面的所謂“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隱含著一個不能忽視的認識誤區。 為此, 筆者愿簡要地闡述自己的認識。
(一)對“資本”概念的基本認識
資本是供給側的要素之一, 和其他的要素——勞動、 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科技成果、制度與管理一樣,都是生產要素供給體系里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看待資本若要理論聯系實際,首先應與時俱進地肯定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生產要素,針對現實生活中對資本概念不當的貶義化、污名化、妖魔化,需加以正名和澄清。現代經濟生活中,國有資本、非國有資本以及外資,都是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 都必然發揮著要素供給的動力功能、推動作用, 并且參與按要素分配的流程,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的。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 確立了改革目標模式,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要構建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改革開放實踐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資本早已經被正名。 上世紀80 年代,“國營企業”改稱“國有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適當分開,承認企業有經營的自主權,國家雖然有產權,但是沒有必要對于這些企業在經營上一竿子插到底,即國有企業要運用掌握的資源做好做大做強,進而國企改革中原來“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表述,在深化改革中已經轉向“管資本”,這是一個不含貶義的表述。人們在全面討論“資本”的時候, 是絕對無法從中排除國有資本的。對國有資本以價值形態作出騰挪運營,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管資本”,必須追求更好適應生產力解放的機制,還要大力發展國資、非國資的混合所有制。 同時,“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財政,作為政府履行職能必需的分配體系,有建立現代預算制度的訴求,這其中就包括被稱為“國有資本預算”的組成部分。
所以一定要用系統論來認識資本的概念。 國有資本之外有民間資本,還有國外資本。 外資也是生產要素,應積極吸引其參與中國做大“蛋糕”的過程。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別無選擇,必須積極引進外資,“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這開始了中國認識商品經濟乃至市場經濟的過程, 了解國外的商業文明體系,對接國際商業化規則與法治化環境,引入市場機制下能使產品暢銷的供給解決方案,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資金、管理經驗以及商業文明意識。 中肯地說,這對于中國的發展是有貢獻的。所以也不能讓“資本”概念落在外資上就妖魔化了。 當下中央強調要“穩外資”和繼續積極引入外資,正是因為外資可能成為積極的推動力, 成為有利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生產要素的組成部分。 所以在高標準的法治化營商環境中,上世紀80 年代已有外資進入中國的PP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這些年又有中國本土上的大量國企、民企和政府合作PPP 項目, 一度作為創新中的“重中之重”。 民營經濟的資本,是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應該引導、 支持其健康發展壯大的經濟力量,當然也不應該貶義化。
由上述可知, 一個本應該中性看待的概念,卻被認為與“以人民為中心”相對立,正是陷入了認識誤區。 這種情況下,思想觀念的更新和創新就顯得尤為重要。從資本要素來看,以市場競爭中的“競爭中性”對應“資本中性”的概念,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理性看待資本,就應看到統一市場、公平競爭、競爭中性和資本中性這些屬性的表述, 是環環相扣而內洽的一個概念體系。 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各個生產要素對現代化共同表現出作用,不宜將這個資本要素直接關聯現代化概念,與并非要素的“人民”概念對立起來,作“誰為主導、誰為中心”的標簽式選擇討論。這種不當之論,會迎合社會上把“資本”僅僅理解為“非公經濟”的片面化認識,非常容易誤導社會輿論。 中國民營企業,會因此受到更多干擾,不僅吃不了“定心丸”,還會感到不安、惶惑、憂慮甚至心有余悸。所謂美國的、西方的現代化是以資本為中心的說法,看起來觀點鮮明,帶有批判之意,但是實際上不利于使實際貢獻早已不止 “五六七八九”(即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和新增就業量)的民營企業真正改善市場預期、樹立信心,反而帶來輿論場上的壓力,助長中央一再批評的社會上關于“兩個毫不動搖”錯誤議論的不良影響。 這其中的邏輯紊亂與偏差,下文將從學理角度再稍作闡述。
(二)對“資本”概念的學理分析
眾所周知,發展市場經濟,需要各個供給側的要素共同發力,價值取向之下,不宜以中心和非中心來區分這些要素。 經濟活動中會有一些直觀特征,比如對于“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表述,主要涉及科技含量的差異: 勞動密集型一般被認為科技含量較少, 而資本密集型科技含量更高。 但勞動密集型產業并不適用于所有場合, 畢竟經濟發展趨勢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趨于越來越多, 特別是在數字化以及人工智能突飛猛進的大背景下。 如果把技術性的概念貼上主義標簽和中心標簽,就會引出一些同常識不相符合的荒謬概念。比如我們不能說, 凡是資本密集型的經濟活動就是以資本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凡是勞動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的,這無關乎東方西方、姓資姓社的分野。
從資本的本性來說,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外資都要尋求發展,都有推動經濟發展的內在訴求。同時,資本就是要帶來增值額的資金力量,如果不能保值增值,就喪失了資本的屬性。 無論是國有資本還是非國有資本,都參與了發展,都要以保值增值為傾向發展擴張,都要參與和推動經濟生活。關鍵在于, 如何處理資本的功能作用所存在的雙重可能性——既可能無序擴張和發展,也可能有序擴張和發展。我國民營資本存在無序發展擴張的問題, 前幾年已經對此作出糾偏和整改。同樣,國有資本也存在一些無序發展擴張的問題, 這些年來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學者們, 一直在討論克服弊端、消除缺陷,要進行改造和改革,以解決無序問題。
因此, 關鍵在于遏制防范無序擴張并引導鼓勵有序擴張和發展。 中央對此已經作出了十分合適的表述,即“紅綠燈”的概念——“紅燈”制止無序擴張,“綠燈”引導和鼓勵有序擴張。這樣一來,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 對資本的態度就豁然開朗了。同時,我們也要以“紅綠燈”的原則推及與資本作用關聯的優化分配問題, 完善激勵和約束機制。
筆者認為,合乎基本學理的理性認識,是中國式現代化絕不排斥和否定資本的推動作用,應該在全面依法治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軌道上,以動態優化的良法為準繩,形成合理調控開紅燈和開綠燈的標準,以促使資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擴張中得到發揮。 這一標準建立的大原則是非常清楚的:全面依法治國,就一定要加快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 讓經濟活動、資本要素涉及的方方面面有法可依,而且要有良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不能讓少數人拍腦袋決定該開紅燈還是該開綠燈。 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全面依法治國大政方針。
又有學者提出,法律的建設和完善一般來說是有時滯的,創新往往就是要突破原來法律法規的條條框框,還應該考慮設置黃燈。 依據已有的法律規則,已經可以明確設置紅燈、綠燈,但是在還不知道應如何設置規則的創新伊始的領域里,需要有彈性的試錯區間。 “在規范中發展”和“在發展中規范”是一對矛盾,在創新概念之下,我們要時時注意,需留出一些試錯創新的彈性空間,否則,只講守住規則,不講創新發展,即使所有的事情看起來規則清晰, 那也是一個沒有動態創新觀念的、容易陷入僵化認識的守成狀態。 而創新發展,要通過試錯來沖破原有的一些條條框框。
由此應考慮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創新的、未知的領域里,首先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包容性,通過試錯進行發展,再建立規范,從而尋求更好的發展。創新和規范的重要性不分上下,但排序不能顛倒,在“創新是第一動力”的發展中,一定要先于 “發展中規范”, 再在 “規范中發展”。 否則沒有試錯的機會,就不存在創新發展。有調控管理職責的政府方面,對此要特別注意。 李強總理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會上專門提到, 要提高創造性執行能力,不能盡設路障、不設路標。路標可能是一個大方向,而政府要允許企業家去探索和試錯,并及時跟蹤,在“八九不離十”之時,推出必要的規則,再動態優化和細化。
五、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對于中國式現代化,實務當然要緊抓不放,思想認識上的創新也不可或缺,這對于中國發展“軟實力”的形成,也是意義非凡的。當下特別要注意改善市場預期, 爭取把經濟運行恢復和維護在合理區間內,對接長遠的新的“兩步走”戰略目標, 最終使中國夢夢想成真。 從警惕右、防止左的角度綜合考慮,在問題導向之下,必須堅定不移貫徹中央指導方針,高度重視相關的市場信心提升, 改善企業特別是廣大民營企業的預期, 支持民間資本在健康發展中壯大。 當下各地正在不約而同全力以赴拼經濟, 有希望出現一個疫情之后回到合理區間、 對接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 2023 年一季度和上半年的經濟數據公布后,雖然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也要警惕一些新的困擾, 但總體而言已經表現出中國經濟向好, 需乘勢發力走向新的局面。 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創造性貫徹中央方針的過程中, 應該力爭2023 年三、四季度的發展對接高質量發展,并在明后兩年即“十四五”的最后兩年維持好這一局面,對接“新的兩步走”發展要求。
要使得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卓有成效,一定要意識到,正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大家共同參與討論。 應正本清源,除了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還應該有思想觀念的創新。 學者們理應致力于相關基礎理論的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