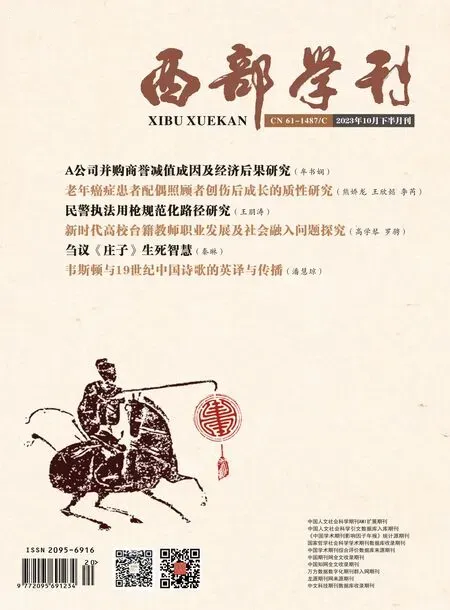從舊瓶裝新酒到兼容并蓄
——記近代南京基督教青年會會所的兩次中西文化融合與共生
孫 璨 陳 奕
(1.南京大學(xué) 歷史學(xué)院,南京 210000;2.東南大學(xué) 建筑學(xué)院,南京 210096)
基督教青年會會所,作為見證了自清末至民國時期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傳播發(fā)展的建筑遺存,是其進行四育活動的空間載體,其價值已不僅局限于建筑本體,還體現(xiàn)了當時西方傳入的教室、宿舍、球場、游泳館、禮堂、淋浴間、廁所等新建筑功能與中國傳統(tǒng)建筑形式之間的碰撞與融合。目前,全國范圍內(nèi)保留下來的青年會會所在功能上多已另作它用,因缺少關(guān)注與研究,使得這一曾對中國近代建筑史發(fā)展起到過重要推動作用的建筑類型,已逐漸不為人知。本文以南京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在發(fā)展變遷中的兩次轉(zhuǎn)型為研究對象,分析這一類新建筑是如何通過建筑師李錦沛的巧妙設(shè)計創(chuàng)作,取得兩者之間的和諧共生,為當時社會所認可,進而影響到整個中國在近代的建筑風格改變。
一、基督教青年會在南京的近代發(fā)展簡史
基督教青年會全稱為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為YMCA,1844年創(chuàng)立于英國,由喬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創(chuàng)立并在歐洲廣泛傳播。在長期的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從單純以宗教活動為號召的青年職工團體,發(fā)展成為以“德、智、體、群”四育為宗旨的社會活動機構(gòu)。基督教青年會自1870—1880年間傳入中國上海,早期以西方來華青年為主要服務(wù)對象,在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以學(xué)生為主的學(xué)校青年會和以職業(yè)青年為主的城市青年會。由于受到國民政府的許可與重視,以及來自北美協(xié)會的支持,民國時期中國的基督教青年會組織規(guī)模迅速擴大,甚至在周邊日本、朝鮮等國也成立了中國留學(xué)生在當?shù)氐姆謺?/p>
基督教青年會自清末至民國時期在中國大地迅速發(fā)展與傳播,借由青年會的傳播發(fā)展,帶來了與其辦會宗旨相匹配的空間載體——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建筑。青年會會所因契合當時中國精英“社會改良”的迫切需求而蓬勃發(fā)展,至20世紀20年代,全國城市青年會會所數(shù)量已達36座[1],學(xué)校青年會亦有一百多處,遍布各省中心城市以及沿海重要商埠。這些會所一般選址在城市中心地段,配置禮堂、教室、體育館、社交廳等多種功能空間,配合演講、授課、集會、體育訓(xùn)練、洗浴等多種活動,諸如籃球、排球、保齡球等體育運動項目就是由基督教青年會從美國引入的,從而吸引了眾多城市青少年的加入。其中1923—1933年間是會所建造的高峰期,建筑師哈利·何士(Harry Hussey)、亞瑟·亞當森(A. Q. Abamson)、李錦沛(Poy Gum Lee)、范文照、趙深、哈沙德洋行、伯捷洋行、永固工程公司等均參與其中。
南京從清末的重要城市發(fā)展至民國時期首都的過程中,基督教青年會的發(fā)展也伴隨其間,引領(lǐng)了南京的城市發(fā)展建設(shè)。其發(fā)展過程主要經(jīng)歷了初創(chuàng)—發(fā)展—停辦—恢復(fù)四個歷史時期。
初創(chuàng)期(1909—1911):南京基督教青年會胚胎于1909年,美籍傳教士魏德邁(Whitman)和海士(L. N. Herpes)到達南京,開始了南京YMCA籌建工作,當時在新街口附近租賃民房作為會所,條件簡陋但仍組織了中國首次現(xiàn)代體育運動會,還舉辦了多次科學(xué)演講。在1911年四月,受到當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支持,南京基督教青年會正式成立,并尋得花牌樓大街第一千九百八十六號前清道尹周子昂的宅邸,租賃作為會所。
發(fā)展期(1912—1936):自民國二年(1912)起,青年會進入了迅速發(fā)展階段,除會員迅速增加,會務(wù)工作日益繁忙,陸續(xù)成立智育部、童子部、會員部、學(xué)生部、德育部、軍警部、體育部外,還成立了求實學(xué)校、青年通俗學(xué)校等教育機構(gòu),組織童子模范團、牯嶺童子營等培訓(xùn)團體。在此期間,開始籌建新青年會會所,中華路新會所于民國十四年(1925)開始建設(shè),次年落成。此后,又陸續(xù)增設(shè)青年會中學(xué),并在保泰街增設(shè)分會所,同時還在九龍橋一帶設(shè)置游泳池,新街口附近租賃空地作為網(wǎng)球場,基督教青年會在南京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一片欣欣向榮之勢。
停辦期(1937—1945):抗戰(zhàn)時期,由于戰(zhàn)事原因,青年會的相關(guān)活動受到了極大的阻礙,在此期間南京YMCA總干事喬治·費奇與西門子公司的約翰·拉貝雖然領(lǐng)導(dǎo)國際紅十字會安全保護區(qū),保護了大批平民,但位于中華路的會所遭到日軍焚毀,大部分事業(yè)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相繼停辦,會所大樓經(jīng)過整修后曾作為當時的中國農(nóng)民銀行總管理部使用。
恢復(fù)期(1945—解放后):八年抗戰(zhàn)勝利結(jié)束后,1945年秋,南京青年會撥款重建,經(jīng)過整修,被日寇燒毀的會所大樓在1946年修復(fù)一新,青年會中學(xué)和各項社會服務(wù)事業(yè),也陸續(xù)恢復(fù),重新開辦起來。南京解放后,南京YMCA作為團體會員,積極投入“三自”革新運動(1)“三自”革新運動:全稱為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亦稱“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基督教新教為擺脫教會的半殖民地洋教形象,實現(xiàn)自治、自養(yǎng)、自傳,開展了團結(jié)全國教徒在愛國主義旗幟下,革新教會,積極參加國家建設(shè)的愛國愛教運動。,參加了南京市民主青年聯(lián)合會。
南京基督教青年會自初創(chuàng)時期租賃周宅作為會所,前后使用了約15年,再之后則籌建中華路會所并延續(xù)使用至新中國成立。兩座會所伴隨了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通過對它們的深度發(fā)掘研究,可以深刻體會到中西文化在建筑中的融合與共生。
二、基督教青年會會所在南京的初創(chuàng)與成熟
(一)初創(chuàng)期的花牌樓會所
南京花牌樓大街基督教青年會會所(以下簡稱花牌樓會所)
根據(jù)相關(guān)記載,此屋位于花牌樓大街第一千九百八十六號,是前清道尹周子昂的宅邸,因傳教士海士與屋主相識而租賃獲得,整個宅邸長327尺(109米),寬136尺(45.3米),共九畝二分五厘(6 167平方米)。其房屋占地面積約1 688平方米,花園占地約四畝(2 667平方米)。從保留下來的平面布置圖中(圖1),可見整組建筑群是典型的江南地區(qū)城鄉(xiāng)官式住宅布局,雖然從平面觀察有部分建筑缺失,但基本格局與流線仍完好。建筑群分為左中右三路,其中東路僅存兩組房間,一組位于東南角,是整個建筑群的大門,前有院,建筑面闊三間,中間作大門,兩側(cè)分別設(shè)總干事室與招待室。另一組位于東北角的兩間偏房,作為廚房與食堂用途。中路是會所的核心功能區(qū),沿中軸線自南往北的各進廳堂分別作為游藝廳、演說廳和課堂,兩側(cè)的偏房與廂房則作為辦公室、藏書室、寄物所、休息所等功能。最北端建筑應(yīng)是兩層的堂樓,作為會員寄宿舍。西路建筑也不完整,保存尚好的一棟五開間房子作為干事寓所,靠北側(cè)的幾間廂房則作為廁所使用。空地主要集中在建筑群的南側(cè)與西側(cè),南側(cè)的花園區(qū)除原有的荷花池,正對著的兩層茶樓以及西側(cè)偏門外。在花園的東側(cè)單獨開辟出了一塊室外排球場,花園北端緊靠游藝廳布置了浴室。西側(cè)則在原西路的空地處,分別設(shè)置了會員運動場與學(xué)生運動場。

圖1 花牌樓會所一層平面圖
(二)花牌樓會所的建筑利用與改造
1.利用部分
按照院落的前后分區(qū)進行相應(yīng)的建筑功能分區(qū),花牌樓會所的布置依托原城鄉(xiāng)官式住宅,在傳統(tǒng)的宅院內(nèi)較為有效的布置新建筑功能。結(jié)合多進院落式的建筑組合現(xiàn)狀劃分功能分區(qū),其主要的建筑功能可劃為三個分區(qū),一為向基督教青年會會員提供的活動與聚會交流功能區(qū),二為求實學(xué)校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住宿功能區(qū),三為干事辦公與住宿,以及其他廚房、廁所、大門等輔助功能區(qū)。
在布置時將距離大門較近的正廳區(qū)域作為供會員活動的功能空間,北側(cè)的后院女廳與堂樓區(qū)域則安置求實學(xué)校的教室與宿舍,東西兩路則布置其他輔助功能用房。
利用不同建筑空間對應(yīng)不同功能用途,利用傳統(tǒng)建筑群中原先不同的大空間與小空間,對應(yīng)布置不同的功能平面,如將原民宅的正廳大堂作為演說廳,利用最后一進堂樓的一、二層小開間房屋作為學(xué)生宿舍。同時在主軸線外較為零碎的建筑空間中設(shè)置廁所、浴室功能,解決會員與學(xué)生的生活使用需求。
2.改造部分
適當?shù)恼{(diào)整建筑流線,符合現(xiàn)代使用需求,對建筑原有流線進行了一定調(diào)整,但仍保留了原有中軸線通道,同時有效利用備弄的穿行作用,還在廁所等處設(shè)置了雨天路徑。
改造建筑與場地,增加配套服務(wù)功能區(qū),根據(jù)實際使用人數(shù)的需求,對原建筑內(nèi)的一些房間進行了改造,增加了配套服務(wù)用房的面積,設(shè)置了專門的浴室、餐廳。對空閑場地進行改造,形成專門且互相獨立的體育活動場所,滿足干事與學(xué)生住宿,會員使用需求。
(三)第一次融合——花牌樓會所的創(chuàng)新與問題
整個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的傳播,給中國帶來了全新的建筑功能,諸如運動場館、禮堂、社交空間、洗浴空間等的加入,使得中國的公共類型建筑在原先教堂、學(xué)校、醫(yī)院、郵局的基礎(chǔ)上又有了新的發(fā)展,成為中國現(xiàn)代城市空間中十分重要的公共場所。
花牌樓會所由江南地區(qū)傳統(tǒng)民居改造而來,利用舊的空間格局容納新的建筑功能,從建筑設(shè)計的角度而言,這是利用中國傳統(tǒng)建筑進行改造再利用的典型案例。但制肘于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排布形制與建筑單體構(gòu)造特點,在實際使用中仍存在不少不足之處。
受制于原來的多進式建筑布局,使用功能上未能做到會員與學(xué)生各自需求的完全分開,建筑出入口、衛(wèi)生間等均為共用,會員區(qū)域的使用面積較小,且位置位于整個建筑群的中部,會面臨著其他人員活動的干擾。
動靜空間未能有效分開,運動場地距離課堂過近,如花園區(qū)域的茶樓東側(cè)設(shè)置了排球場,會員及學(xué)生活動時,產(chǎn)生的噪聲必然會影響到茶樓中人們的休憩。
空間封閉性不足,由于傳統(tǒng)建筑中廳堂不設(shè)門窗的特點,功能中諸如演講廳、游藝廳都位于中軸線上且完全開敞,這在南京陰冷的冬天或是濕熱的夏天都非常的不適用。
使用面積不足,由于建筑用房無法滿足更多會員使用的需求,同時傳統(tǒng)民居空間哪怕經(jīng)過改造也并非完全適合新功能需求,因此自民國四年(1915)開始,基督教青年會便一直在籌劃建造新的西式青年會所,歷經(jīng)了10年的反復(fù)協(xié)商募捐,終于在民國十四年(1925)一償所愿。
(四)成熟期的中華路會所
南京中華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以下簡稱中華路會所)的選址曾幾經(jīng)周折,由于會務(wù)工作的日益壯大,亟需面積更大的新會所。民國七年(1918)時,江蘇督軍李純曾指撥臚政牌樓舊中協(xié)署為會所,但因為地點距離商場(即新街口一帶)較遠,于會所位置,不甚適宜,故并未啟用。臚政牌樓舊中協(xié)署之后曾經(jīng)作為童子模范團的用房,在軍警部成立后,則修葺臚政牌樓一部分的屋宇,辟為軍警招待部。
直至民國十三年(1924)呈準齊燮元督軍,以該署調(diào)換府東街舊鎮(zhèn)守使署余地,約11畝余,會所用地正位于南京的城市中心,內(nèi)橋大街西南,這里原是清代江寧府衙所在,在更早的歷史時期曾是三國的周瑜宅邸,宋代的大軍庫,明代應(yīng)天府衙所在地。
中華路會所的建設(shè)經(jīng)費由全國青年協(xié)會代向北美青年協(xié)會募得美金6萬元,南京本會方面籌募國幣兩萬元,民國十四年(1925)春興工建筑,十五年(1926)秋落成。建造時,還由中國紅十字會創(chuàng)立者并曾任蔣介石與宋美齡證婚人的余日章捐立奠基碑。
因是北美協(xié)會參與募集資金,因此他們派遣當時年僅24歲的華裔建筑師李錦沛主持指導(dǎo)會所的設(shè)計工作。李錦沛于1923—1927年間,受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的派遣,任駐華青年會辦事處副建筑師,協(xié)助當時的主任亞當森工作,在其任職期間,完成了上海西人青年會、海軍青年會、長沙、保定、濟南、南京、寧波、南昌、成都、福州、廈門、武昌青年會、上海八仙橋青年會、昆山基督教青年會的建筑設(shè)計[2]。
李錦沛的設(shè)計風格早期多為簡化的西方復(fù)古式樣,并且喜愛將中國傳統(tǒng)建筑式樣融于西式建筑之中。作為其早期設(shè)計的青年會會所,中華路會所采用了融合中西的設(shè)計處理手法,整體風格上仿照西班牙建筑樣式,細節(jié)造型中則處處顯露中國元素,建造完成的會所大樓,以其宏偉的造型,一時間成為南京城內(nèi)的標志性建筑。根據(jù)會史文件記載:“共有房屋四座,計正屋一,健身房一,演講廳一,茶樓一,屋之形式及顏色,系仿照西班牙國之建筑,幽雅適宜,輝皇美麗,允為寧垣所罕見。會所內(nèi)部之設(shè)備有演講廳、交際廳、游藝廳、體育館、教室、書報室、浴室、寄宿舍、食堂等等。此外尚有待建之屋多座,皆為工作所必需,因經(jīng)費關(guān)系,尚未實行。”(圖2,圖3)

圖2 中華路會所一層平面圖

圖3 中華路會所二層平面圖
根據(jù)現(xiàn)存李錦沛設(shè)計圖紙與實地勘察,可以認為民國十五年(1926)建成的新會所主樓,完全是按照其設(shè)計方案完成。

表1 兩座會所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對比
(五)中華路會所設(shè)計中的創(chuàng)新與改變
1.在原會所需求的基礎(chǔ)上進行創(chuàng)新,以西方現(xiàn)代設(shè)計手法表現(xiàn)建筑
中華路新會所的設(shè)計建造,雖根據(jù)南京基督教青年會報告中記載,曾經(jīng)擬以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會所為模板設(shè)計建造。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而是基于原花牌樓會所的實際使用狀況作出調(diào)整,由設(shè)計師李錦沛采用現(xiàn)代設(shè)計手法進行傳統(tǒng)創(chuàng)新的代表之作。建筑布局跳脫出中國傳統(tǒng)建筑院落形式,采用帶有采光中庭的建筑組合布局,整體風格上仿照西班牙建筑樣式,建筑直接面對中華路,以裝飾精美的大門吸引會員。建筑結(jié)構(gòu)則采用當時南京城內(nèi)少有的鋼筋混凝土結(jié)構(gòu)柱+磚墻+鋼筋硂密肋樓蓋+三角形豪式木結(jié)構(gòu)桁架的混搭形式,細節(jié)裝飾上采用新古典主義風格,滿足了當時的會務(wù)工作開展需求。(圖4,圖5)

圖4 中華路會所現(xiàn)狀測繪正立面圖

圖5 中華路會所現(xiàn)狀測繪剖面圖
2.功能分區(qū)上以多個建筑組合的形式,便于不同功能分區(qū)的排布與組合
在建筑功能布局上,在花牌樓會所的基礎(chǔ)上進行改進,采用了對稱式布局的合院造型,建筑中特別是主樓以四棟二層建筑圍合而成,通過優(yōu)化建筑空間,使得功能分區(qū)更為合理,同時吸取了花牌樓會所的建筑改造經(jīng)驗,主樓設(shè)計多個出入口與樓梯聯(lián)系室內(nèi)外與樓上下,樓上下劃分不同功能空間,一層以會員閱讀、聚會以及洗浴為主,西側(cè)可通往運動場地或會議廳,二層則以教室、餐廳等學(xué)校用房為主,確保各類活動的動靜分離,互不干擾[3]。
3.細節(jié)的設(shè)計中仍結(jié)合傳統(tǒng)建筑風格與元素
建筑風貌上雖采用西班牙建筑樣式,但是,歸究到細節(jié)的設(shè)計考量中,仍包含有大量的傳統(tǒng)建筑風格,如坡屋面、挑檐,中式的傳統(tǒng)建筑材料——青磚,灰瓦,乃至封檐板都采用了雀替的造型,似乎更多地偏向了中國固有建筑風格[4]。在最近的修繕工作中,我們發(fā)現(xiàn)其墻體的砌筑采用了大量城磚與普通青磚,以一定規(guī)律組合砌筑,這也體現(xiàn)了建筑師李錦沛在設(shè)計中對傳統(tǒng)元素、傳統(tǒng)材料的使用(圖6)。

圖6 打開內(nèi)墻粉刷層后可見墻體的砌筑方式
4.考慮后期的規(guī)劃發(fā)展,留有足夠空間
考慮后期發(fā)展,新會所的面積留有余裕,例如二層設(shè)置的房間可多功能劃分,基泰工程司就曾在會所中租用房間辦公。供會員運動后使用的洗浴空間也非常多樣,布置有更衣間、淋浴間、盆浴間。不過,七年后為了發(fā)展青年會組織,還是在城北保泰街以及新街口附近設(shè)置了分會,但均為租賃房屋,青年會的核心建筑仍是中華路會所。
(六)第二次融合——中華路會所體現(xiàn)的中國傳統(tǒng)元素
作為李錦沛的早期設(shè)計作品,在中華路青年會會所的設(shè)計中非常巧妙地將現(xiàn)代建筑公共功能與傳統(tǒng)建筑形態(tài)進行了融合,完美地解決了原先花牌樓會所中的兼容性不足問題。雖不似一年后呂彥直先生在中山陵國際設(shè)計競賽中那般驚艷世人,但亦可視為帶有中國固有之形式的建筑佳作。
建筑中所體現(xiàn)的融合與共生的方面是多元化的,諸如:(1)中軸對稱的平面布局,合院式的建筑組合方式,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建筑理念中的居中與圍合等觀念;(2)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單數(shù)開間與屋面大挑檐的構(gòu)造做法,但建筑各開間之間則以拱券及柱式作為裝飾,局部延續(xù)了清末至民國初年之間流行的外廊式建筑風格;(3)傳統(tǒng)建筑材料的組合使用,雖以現(xiàn)代鋼筋混凝土結(jié)構(gòu)+豪式木屋架作為主要結(jié)構(gòu)形式,但具體到墻身的砌筑用磚,挑檐的封護造型上,仍使用了中國傳統(tǒng)建筑材料;(4)中國化的細節(jié)裝飾,除主要門頭部位以及必不可少的基督教青年會LOGO外,也使用了不少傳統(tǒng)建筑裝飾元素用于檐口、窗下墻等位置,很和諧的與淡黃色拉毛墻面結(jié)合在一起[5]。
三、結(jié)束語
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前后兩座會所,代表了西方新建筑功能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的兩種方式,花牌樓會所的處置方式,沿用基督教新約中的話,就猶如“舊瓶裝新酒”般,雖試圖融合彼此,但最終還因掣肘太多無法兼容。而中華路會所則巧妙地尋找到了解決的方法,不純粹以西式建筑造型吸引會員,而是在設(shè)計中選擇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的建筑布局模式,同時在風貌中加入大量傳統(tǒng)建筑元素,以求得國人之精神上的共鳴,以建筑形態(tài)呼應(yīng)傳統(tǒng),符合南京作為六朝古都的歷史氣質(zhì),可謂最佳選擇。(圖7)

圖7 南京基督教青年會舊址修繕后現(xiàn)狀
正是由于20世紀20年代,以墨菲(H· K· MURPHY)、呂彥直、李錦沛為代表的一眾建筑師,在實踐中以新的西方建筑功能中融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元素,通過孜孜不倦的嘗試,取得了諸如中山陵、金陵大學(xué)規(guī)劃,以及包括基督教青年會眾多會所建筑的成功,才使得弘揚“中國固有之形式”深入人心,成為《首都計劃》中的重要規(guī)定,引領(lǐng)了數(shù)十年的中國建筑發(fā)展。
本研究在過程中得到彭長歆、冷天兩位教授提供的相關(guān)李錦沛設(shè)計圖紙資料的幫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