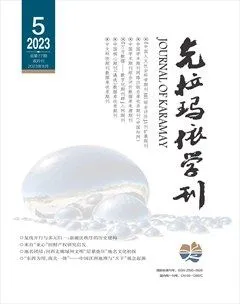地名團結:河西走廊綠洲文明“層累疊壓”地名文化初探*
李春斌
(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遼寧大連 116081)
地名學是研究地名的由來、語詞構成、含義、演變、分布規律、讀寫標準化和功能及地名與自然和社會環境關系[1]的一門綜合性、交叉性學科。河西走廊地名屬于文化地名學①的研究范圍。河西走廊的很多地名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民族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民族融合、民族團結的歷史文化內涵,是河西走廊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河西走廊很多地名,對社會共同體民族心理產生了積極影響,為維護地區穩定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對河西走廊地名的相關研究,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更是構成認知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地名活化石”。河西走廊諸多地名具有普遍的“層累疊壓”現象,真實反映出歷史華夏“漢胡互化”的民族融合面向,其所展現出的“地名團結”是觀察和詮釋民族交融、民族團結的重要切入點。
由于河西走廊是“活著的敦煌”②,具有典型“文明粘性”的特征,使得河西走廊地名具有明顯的“層累疊壓”現象。所謂“文明粘性”,是指在一種文明形態上,疊加多種性質不同的文化形態,從而聚合并顯示文明的多元共生性,并最終形成一種獨立的、多元一體的文明類型。③河西走廊的“文明粘性”,同時在內外部團結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雪域高原的高原文化、草原沙漠的游牧文化、西域中亞的綠洲文化。從這種內外部團結中,形成民族互動、民族團結、民族交融的新秩序,從而最終形成了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所謂“層累疊壓”,是指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具有文明粘性和處于文明樞紐④地帶的河西走廊,在歷史進程中,由于民族戰爭、沖突、征服、融合等均極為頻繁,從而使得同一地理區域被不同民族占領的現象不斷發生,將這種具有時間性的歷史信息承載于河西走廊特定地理空間,在地名上就表現出同一地理區域在歷史上的多種稱謂。這些稱謂,有的外露、有的掩蓋、有的適時變更、有的沿用至今,從而形成地名的疊壓、層累、覆置、堆積,顯示出明顯的“層累疊壓”特征。這種明顯具有時空交錯哲學意蘊的時間民族空間屬性的地名“層累疊加”現象,反映的正是一個時間民族的空間特質。
一、“皇城”:“斡耳朵古城”“牧馬城”“黃城兒”“皇城”等地名的層累疊壓
在河西走廊中部永昌⑤綠洲有一名為“皇城”之地,其地名就具有明顯的“層累疊壓”特征。“皇城”歷史上先后叫“斡耳朵古城”“斡魯朵古城”“干耳朵城”“牧馬城”“黃城兒”“皇城灘”等。
據明代洪武二年(1369)[2]編纂的《元史·太宗紀》載:“太宗八年,分賜諸王貴戚斡魯朵”。“斡魯朵亦名斡耳朵,即諸王之宮衛,亦即永昌城”。[3]清代順治丁酉年(1657)《涼鎮志·永昌衛·古跡》載:“避暑宮,城南一百二十里,地名黃城兒,譯語謂斡耳朵城,俗傳永昌王避暑于此,其遺址尚存。”“永昌王墓,城南一百二十里,地名斡耳朵城,俗傳元宗室永昌王葬處,其西又一墓,俗呼為娘娘墳,意為妃墓。”⑥成書于清代乾隆十四年(1749)的《五涼考治六德全志第三卷圣集·永昌縣志?地理志》載:“斡耳朵古城,縣東南一百二十里。俗傳為永昌王牧馬城,地名黃城兒。唐家沙溝南八十里,有永昌王避暑宮,遺址尚存。注云:斡耳朵古城,遺址在今永昌皇城水庫南岸,為元永昌王闊端所筑”。[4]《西陲今略》載:“黃城兒”在詹詹口南八十里。[5]
清代嘉慶二十一年(1816)修《永昌縣志·卷二·建置志·古跡》載:“永昌王宮殿原址在‘干耳朵古城’,今之皇城灘是也。其南居一舍有避暑宮,土累累猶可識,邑城中大衛又有邸基,蓋自初封以來,歷年多宜其頻建,但未知孰為先后,至武威西北三十里之永昌府為其行宮也。[6]清代宣統元年(1909)知縣楊鼎新、教諭雷致遠總纂的珍稀古跡《永昌縣鄉土志》載:“斡耳朵古城.....今皇城灘是也”。⑦1993 年編纂的《永昌縣志》載:“斡耳朵古城(古名黃城兒),位于今永昌縣城稍偏西南直距39公里的皇城水庫東南角,臨水庫。為元朝永昌王闊端所筑的牧馬城,并筑有永昌王避暑宮,附近有永昌王墓及王妃墓,遺址均存”。[7](見表1)

表1 “皇城”地名流變(制表:李春斌)
根據珍稀古籍《突厥語大詞典》的明確記載:“斡耳朵”,古突厥文,轉寫為“ordu”,漢語意思是“皇城”“宮 城”。[8]也轉寫為“orda”“orda”“ordo”“ordon”“horde”等,蒙古語為⑧,又稱斡魯朵、斡里朵、兀魯朵、窩里陀、斡爾朵、鄂爾多等,是突厥、蒙古、契丹等游牧民族的皇家住所和后宮管理、繼承單位。最早見于唐代古突厥文的碑銘。“斡耳朵(ordu)”原系突厥“牙帳”之意,后轉為“宮殿,王城”之意。比如可汗們居住的喀什噶爾城被稱之“ordu k?nd 斡耳朵城”。
“干耳朵”古城,顯然是“斡耳朵”古城的訛寫。“干”的繁體字“幹”與“斡”字相近,傳抄人不明“斡耳朵”實際上“ordu”的漢語音譯,故照貓畫虎,以訛傳訛。
將“皇城”改為“黃城”,以“黃”代“皇”,實因地方志編修纂寫者具有強烈的“夷夏之防”“胡漢之別”的傳統“中原正統”觀,將蒙元等少數民族政權視為夷狄、化外,不承認其地是具有政權屬性的“皇城”,而異寫為只有顏色意味的“黃城”。
至于叫“牧馬城”“避暑宮”,則是站在地方志書寫者的角度,就該地所具有的功能進行的表述。“牧馬城”,意味著該地具有很多草場,是牧馬的寶地。實際上,當今“皇城”遺址所在地,正是現在金昌市永昌縣和張掖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接壤處,該地正好處于歷史上吐蕃六谷部“東大河谷”和“西大河谷”⑨的中間地帶,水源和牧場資源優渥。
叫“避暑宮”,則是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依照時令進行冬夏“轉場”的“行國”⑩“四時捺缽”?等社會特征的表述。
顯然,從最早的古突厥語“斡耳朵”古城,到后來蒙元政權蒙古語“斡耳朵”城地名的沿用,然后再到漢語通過“皇城”“黃城”“牧馬城”“避暑宮”等不同稱謂稱呼同一地理區域,反映的正是同一地理空間不同時間段地名的“層累疊壓”現象。這種“層累疊壓”呈現的,恰恰是不同族群在同一地理空間內的文化交流和整合。從原來互不相識的異質文明,經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動、擠壓、平衡、妥協、整合,最后形成不同族群公認的新秩序。這個新秩序的形成標志,就是流傳千古、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民族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民族融合、民族團結的歷史文化內涵的當地“地名”。河西走廊中部永昌綠洲的“皇城”就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二、黨河:“敦薨之水”“氐置水”“甘泉水”“黨金郭勒”“黨河”等地名的“層累疊壓”
作為河西走廊最大的三條內陸河,敦煌市母親河“黨河”的地名來源,也充分體現了這種地名“層累疊壓”現象。
現在稱的“黨河”,根據《漢書·地理志》載,西漢時名“氐置水”[9],而根據《山海經》則知漢代以前舊名當為“敦薨之水”,而“敦薨”實乃民族部落語。有學者研究認為,“敦煌”應是“敦薨”一名的別譯,初為民族部落名,后成為地名。“煌”和“薨”讀音極近,初譯寫成敦薨,后來譯為敦煌。此“敦煌”一詞,就是《山海經·北山經》中“敦薨之山”“敦薨之水”所記敦薨一詞的異譯。以“敦薨”命名山名、水名、渚名、藪名,說明這個地區居住著一個人口較多的民族,這個民族,稱“敦薨”。敦煌和敦薨是同一語源,最早是一個民族的稱號,后來又以此命名地名,西漢開敦煌地,又以此為郡、縣名。這兩個地名雖然所指區域不完全相同,實際上是根據一個民族在不同時期居住的不同地方而稱的。[10]
有學者則進一步指出,有理由認為“敦薨”當為月支語或烏孫語。?自戰國以來“薨”字亦變音讀“黃”,而“黃”與“煌”同音,故知“敦薨”與“敦煌”同音。西漢時期“敦亮”與“敦煌”字異音同,互為對應,當非巧合。《山海經》所載的“敦薨”,無疑即張騫所說的“敦煌”。蓋因“薨”字非吉(《禮記·曲禮下》“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故諱言“薨”字),張騫因將“敦薨”改寫作“敦煌”。后在此地建縣建郡,遂名“敦煌縣”“敦煌郡”。東漢應韶不知“敦煌”原為月支語或烏孫語之“敦薨”,乃就漢語“敦煌”二字望文生義。[11]
又據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陽開渠”條透露,約在前涼時期,此水已名“甘泉水”,取代了漢代“氐置水”舊名。[1]“甘泉水”之名從北涼一直沿用到北宋。
元明兩朝,敦煌舊有居民陸續內遷,蒙藏及畏吾兒人先后入居,而其主體民族為蒙古族,故地名以蒙古語改名。于是改稱“甘泉水”為“黨金郭勒”。“黨金”,蒙語,泛指敦煌南境的黨河南山(祁連山脈西段);“郭勒”,蒙語“河流”之謂。清代雍正年間,從西北56 州縣遷來民戶2 400 戶至敦煌。新來移民皆操漢語,乃據漢語習慣簡稱“黨金郭勒”為“黨河”。?(見表2)

表2 “黨河”地名流變(制表:李春斌)
換言之,“黨河”這一地名經歷了從漢代之前以民族部落語言命名的地名“敦薨之水”,到漢代的“氐置水”,再到北涼至北宋的“甘泉水”,復到蒙元明代時期的蒙古語“黨金郭勒”稱呼。“黨金”,蒙語泛指敦煌南境的黨河南山,祁連山脈西段。“郭勒”,蒙語“河流”之意。用蒙古語音譯為“”?。根據最新研究成果,“黨金”“丹增”都屬于藏蒙語言合成詞,即“黨”“丹”為藏語,而“金”(果勒)是蒙古語,后來又有藏、蒙、漢三種語言合成詞的現象。?也就是說,“黨金郭勒”這一地名本身就是蒙藏漢三種語言的合成,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地名學證據。
至于清代雍正年間大量漢族居民內遷而將“黨金郭勒”簡稱“黨河”,呈現出從民族部落語言、漢語、蒙古語到蒙古語漢語簡稱的地名流變,所反映的正是“黨河”這一歷史地名的“層累疊壓”。
可見,這一著名歷史文化地名,揭示了黨河流域曾經被當時的民族部落“敦薨”占據的歷史事實。后來地名變更為蒙古語的“黨金郭勒”,則反映了當時草原民族和農耕民族間的戰爭、征服、貿易等重大歷史事件。清代雍正年間漢族居民遷入而用漢語習慣簡稱蒙古語“黨金郭勒”簡稱為“黨河”,則反映了歷史上漢蒙滿等不同族群共同管理和使用敦煌母親河“黨河”這一基本事實。
三、石羊河:孤奴河、羌谷水、馬城河、白亭河、五澗谷、三岔河、石羊河等地名的“層累疊壓”
歷史上,在河西走廊分布地域最廣、存續時間最長的民族部落當屬羌族,因此,河西走廊地區留下了大量的羌語地名。
作為河西走廊三大最重要水系之一“石羊河”名稱的由來,就與羌人有關。《漢書·地理志》載:“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縣十: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11]。這里的“谷水”也叫“羌谷水”,乃羌人放牧的牧場和水源所在地。“酒泉郡……縣九:福祿(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9]。這里的“羌谷”就是姑臧的“谷水”。
根據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梳理:河西走廊武威綠洲的“石羊河”,自西漢至東晉十六國時期標為“谷水”,南北朝至唐代為“馬城河”,五代十國為“白亭河”,宋遼夏金時期未標,元代為“五澗谷”,明清時期均為“三岔河”。?史籍中首次出現“石羊河”一名,見于乾隆《甘肅通志·水利卷》“涼州府”條載:“大河:在鎮番縣東南二十五里,其源有二,一為石羊河,發源于涼州城西北清水河灘之尾海藏寺”。[12]乾隆《五涼全志·鎮番縣志》則直接出現了“石羊河”一名,稱“鎮番水源有二:一發于武威縣之石羊河,二發于武威高溝堡之洪水河。石羊河東收清水、白塔,西收南北沙河各余流,匯入東北”。?有學者認為,“石羊河”命名權是不同地域比如武威縣和鎮番縣通過證明自身水權合法性的依據,[14]從社會學社會功能學派的角度而言,該解釋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該解釋依然沒有說明“石羊河”命名的源流。(見表3)

表3 “石羊河”地名流變(制表:李春斌)
有學者指出,“石羊河”古稱“孤奴河”,漢時稱“羌谷水”,近代才叫“石羊大河”。“孤奴”為匈奴語,“羌谷水”為羌語,這顯示了不同語言在不同時段上的層化現象。[14]這是很有道理的。
從表3 可以看出,石羊河從匈奴語的“孤奴河”,到羌語的“(羌)谷水”,再到不同時代的“馬城河”“白亭河”“五澗谷”“三岔河”,直到清代乾隆年間《甘肅通志·水利卷》“鎮番縣”條出現的“石羊河”,才將這個地名徹底定名。這實際上反映出同一地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古羌民族部落、匈奴民族部落及漢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團結現象。這對于維護河西走廊歷史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完整性,促進河西走廊歷史文化和現代生活的融合,連祖先之根,養先祖之根,展現古今社會生活的延續性,保持歷史文化底蘊,增強歷史文化自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更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載體。
實際上,除了“石羊河”,河西走廊直到現在仍然有大量的地名與羌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地名已經構成認知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地名活化石”。比如今河西走廊金城郡(今蘭州)永登縣境內的“伏羌堡”,天祝縣境內的“鎮羌河”“鎮羌灘”“鎮羌驛”等,武威城東的“黑羌塘”(今大河驛西盛家莊)、羊下壩,城北的羊同(今永昌鎮)、紅羌(今洪祥鄉)等地名[15],皆與羌人有關。
前文所述吐蕃六谷部西大河谷的支流“平羌溝”,直觀可見,與羌人有關。根據筆者2021 年寒假期間,對河西走廊中部武威-永昌綠洲地方鄉賢?的訪談,河西走廊張掖綠洲山丹的“繡花廟”,其實原來叫“定羌廟”,也與羌人有關。該廟在山丹硤口古城東面差不多二十里處,原來是中原王朝平定羌人而建,廟里有關羽、王進寶?將軍的畫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于民族團結的考慮,將原來“定羌廟”改為現在的“繡花廟”。根據《山丹縣志》的記載,清代詩人謝歷曾有《登定羌廟城樓有感》:“定羌古戍獨登樓,臨眺無端悵遠游。煙雨一天憑對酒,英雄千古幾封侯?塞鴻飄渺長空遠,羌管悠揚野草秋。為問漢家教射客,到今何用姓名留”。[16]更不消說,人所共知的唐代著名詩人王之渙《涼州詞》中所唱的“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了。可見,這些歷史地名、歷史典故及詩歌中反映的歷史人文信息,是當地歷史與現實聯通的重要手段和載體,對增強地方文化自信、厚重歷史,意義重大。
除此之外,現在甘肅省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有一個名為“泱翔”的藏族鄉及“泱翔寺”。檢拾史料?,我們發現,“泱翔”的歷史記載應為“卬羌”,而非“泱翔”。“卬羌”,才是正確寫法。實際上,該“泱翔”藏族鄉,是來自古代羌族西羌的古老部落名,是羌族的一個叫“卬”的部落。“卬羌”而非“泱翔”,與當地方言中對其稱呼也極為相符。比如河西走廊中部永昌綠洲方言中,就把皇城水庫邊上的民族叫“卬羌人”“卬羌兄弟”。當地牦牛肉的供應,就來自肅南的“卬羌人”。
四、疏勒河:籍端水、冥水、獨立(利)河、布隆吉勒河、疏勒(蘇賴)河等地名的“層累疊壓”
疏勒河是甘肅省河西走廊內流水系的第二大河,系前文所說的“黨河”、榆林河等其主要支流。《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敦煌郡條”下載:“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注曰:“冥水出北,入其澤。”[9]從該條可見,疏勒河在班固寫《漢書》之時稱之為“籍端水”,而在東漢應劭作注時,就已經改稱為“冥水”了。
唐代,曾經出現過“冥水”“獨立河”“葫蘆河”并稱的情況。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瓜州晉昌縣”條說:“晉昌縣(中下,郭下),本漢冥安縣,屬敦煌郡,因縣界冥水為名也。……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17]唐時有時也稱“獨利河”,敦煌遺書中記載其略。《沙州都督府圖經》(P.2005)記云:“源出瓜州東南三百里,流至敦煌縣東南界。雨多即流,無雨竭涸。”大致與現代疏勒河之經流相符。又有學者認為,“獨利河”非“疏勒河”干流。[18]唐時也有“葫蘆河”之稱。[19]
宋代又恢復到漢代所稱“籍端水”“冥水”。《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三·隴右道四》載:“籍端水,一名冥水。《地理志》云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冥澤’是也。[20]宋代《太平御覽·卷一百六十五·州郡部十一》載:“《漢志》曰:冥安,屬敦煌郡。冥水出焉,又名籍端水,出羌中,西入澤。冥安即晉昌地。”[21]
明代稱“卜隆吉河”。明代旅行記《西域行程記》載:“(永樂十二年正月)十七日,晴,過嘉峪關……二十八日,晴,平明起,過卜隆吉河,向西北行,入一平川。”?顯然,“卜隆吉河”就是后世清代所稱的蒙古語“布隆吉爾河”。布隆吉爾(勒)河,就是蒙古語“渾濁的河”之意,當為蒙元帝國征服西夏過程中所起地名。明代繼續沿用。
清代張寅在《西征紀略》載: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日至黑山滸,過峽口。……二十八日自柳溝劉草,二十九日七十里至橋灣(又名卜隆基)。?“布隆吉爾”在這里轉寫為“卜隆基”。《大清一統志》載:“南端籍水在今安西府源泉縣北。按輿圖及新志,今有蘇賴河,亦名布隆吉爾河,發源靖逆衛南山,曰昌馬河,北流轉而西,經舊柳溝衛北,會十道溝水,為蘇賴河”。[22]后世以來,蘇賴河、蘇來河[23]、疏勒河等都是該河不同音譯。民國以后注記為疏勒河,[24]并約定俗稱至今。
從表4 可以看出,“疏勒河”這一河西走廊歷史文化地名經過了“籍端水”“冥水”“獨立(利)河”“布隆吉勒河”“疏勒(蘇賴)河”等地名的“層累疊壓”。有學者指出,由于其本身語源還不太清楚歷史上先后入居于斯的不同民族又都曾以自己的語言音譯過這一地名,故其名稱十分復雜,很難統計出有多少種譯法。僅今天常見的對譯就有“蘇勒”“蘇賴”“蘇喇”“西喇”“錫拉”“西賴”“葫蘆”“瓠”“穹窿”等。在上述幾種稱謂中,以疏勒河一名分布最廣、影響最為深遠。[25]

表4 “疏勒河”地名流變(制表:李春斌)
據學者考證,“疏勒”是“sur”的音譯,“sur”很可能是阿爾泰語系的古老詞匯,被后來的蒙古語、突厥語繼承下來。[26]民國著名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岑仲勉先生在《外語稱中國的兩個名詞》一文中,引用了格爾德齊(Gardizi)于十一世紀旅游我國西北的珍貴資料。格爾德齊從吐魯番至敦煌中經“Bagh shura 地方,必須用船渡河”。岑仲勉先生認為:“Bagh shura 地方”即哈喇淖爾。其中的“shura”,就是“蘇賴河”,即今日的疏勒河。岑仲勉先生說:“蘇賴,今北音“Su lai”,蘇勒“Su le”,與“shura”合。審諸地圖,此河正橫亙哈密、敦煌之間,是否取意于蒙語之“黃”,今且勿論,第觀其音變不一,則“shura”為蘇賴河之古音,可無疑也。[27]這是說,無倫“sur”還是“shura”,其名很大可能來源于阿爾泰語系的古老詞匯,被后來的蒙古語、突厥語繼承下來。“疏勒”這一歷史地名中包含著蒙古語、突厥語的成分。
另據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所長李正宇教授對該河名稱研究認為,“籍端水”之“籍”,“獨立河”之“獨”,“蘇賴河”之“蘇”,讀音本同,至少古時非常接近。籍端、獨立、蘇賴是三個同音詞的不同用法,意思都是“黃”河,即河水濁黃之意。他還認為西域于闐、焉耆境內的“樹枝水”“大利水”“計式水”意思也同為“黃”河。他認為這是當地民族各見其境內之河夾土帶沙、渾濁不清,因而不約而同地起了個意思相同的名字。但它們與中原“黃河”皆不相通。此論給疏勒及相關問題研究增加了新的內涵。[28]換言之,李先生的意思是疏勒河之名實為當地少數族群共同對這一河水“黃”色特征的表述,并不獨自屬于某一個少數民族,而是屬于曾經占據過該地方的少數民族群體所共有。
有學者曾到肅南縣裕固族考察,發現裕固族“蘇勒都斯”一姓。裕固族是回鶻人的后代,唐代居甘、瓜、沙三州居多。“蘇勒”二字在唐代普遍使用,后來使用漢姓,“蘇勒”衍化為“蘇”。這說明,疏勒河之名附會于古國名、地名,在音和意及歷史背景諸方面,與其本名皆有巧妙的淵源關系。這是說,疏勒河可能與古國名、地名有很大關聯。
至于明清時期,叫布隆吉爾河,如前所述,當屬蒙元帝國征服西夏過程中對該河特征的表述,后世沿用。布隆吉爾河的蒙古語寫法是“”,意思就是“渾濁的河”。實際上蒙元時期有以河流、泉水、街巷命名地名的傳統,比如筆者的家鄉地名河西走廊中部永昌綠洲“毛卜喇”就是蒙古語(寫法為“”)“壞泉”“不好的泉”“苦澀的泉”之意的音譯。“驪靬文化”發現地“者來寨”地名中的“者來”就是蒙古語(寫法為“”)“街、巷”之意的音譯。
無倫“疏勒河”這一地名是來源于阿爾泰語系的古突厥語、古蒙古語,還是說曾經占據該地的少數民族部落語言,抑或來自古代國名、地名乃至古姓名,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是,該地曾被當時民族部落、古突厥、古蒙古、漢民族等族群長期共融共生,最后均為形塑中華民族共同體作出過自己的貢獻。
四、結語
基于河西走廊多民族部落交融的特性,羌、氐、月氏、匈奴、突厥、吐蕃、蒙古、黨項、回鶻等民族部落長期在河西走廊活動,這些民族部落遺留的文化因子,通過地名遺存的方式展現。根據學者的研究,河西走廊有阿爾泰語系的匈奴、突厥語族所屬的各族、有漢藏語系羌藏族所屬的各族,還有印歐語系東伊語支所屬各族,世界三大語系的民族曾在河西走廊活動、生息。[10]河西的許多地名如敦煌、張掖、祁連、居延、姑臧、觻得、昭武、驪靬等都源于少數民族語言,而效谷、壽昌、祿福、安西、武威、民勤、民樂、永昌等地名又帶有濃厚的漢文化特征。[29]在同一地理區域,不同民族部落長期通過貿易、戰爭、通婚、道路等不同方式融合,最后經過長時間沉淀,定型為具有明顯“層累疊壓”的歷史地名。這些歷史地名往往是重大歷史事件的遺存,也是不同歷史時期當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真實再現,對于現實社會與歷史社會的鏈接,增強地方文化自信,傳承歷史文脈,具有極其難能可貴的價值。
地名尤其是歷史地名,實際上是研究河西走廊民族融合、交融非常重要的切入點。這些歷史地名上附著的文化信息,通過地名團結、地名融合、地名層累、地名疊壓等方式展現的“層累疊壓”地名文化現象,深刻反映著歷史上中華民族的融合、溝通、交融、交流,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信息肉眼看得見的“活化石”,更是反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文化載體,是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寶貴文化遺產。將河西走廊綠洲文明的歷史文化地名“層累疊壓”所展現的“地名團結”文化現象,放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新秩序愿景中考量,更是對世界陸權時代曾經聯通世界、兼容并包、合作發展等人類美好歷史記憶的重新激活,也是當前我國為人類共同的世界新秩序重塑所作的重要努力。
注釋:
①有學者研究指出,“河西走廊地名文化”屬于“中國區域文化地名學”中“隴右地名文化”。參見牛汝辰:《中國文化地名學》,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 年版,第577-583 頁。
②③李春斌:《信仰團結:河西走廊綠洲文明“神婆燎病”民間俗信之田野調查》,徐勇、鄧大才主編:《政治科學研究.2020 年卷.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4 頁、第113 頁。
④關于“樞紐”的最好研究,在我的閱讀范圍內,當屬——施展:《樞紐:三千年的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林爾蔚、陳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⑤永昌在歷史上長期屬于武威管轄,間屬張掖管轄。1981 年2 月國務院(81)國函字14 號文件批準成立金昌市,將永昌縣劃屬金昌市管轄,并將金川鎮所屬的金川地區和寧遠、雙灣兩個公社從永昌劃給金昌市管轄,10月1日武威地區行署將永昌正式移交給金昌市。自此,在行政區劃上,永昌縣屬于金昌市。參見祝巍山主編、永昌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永昌縣志》,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64頁。但從文化歸屬及文化心理上,永昌一直是武威涼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乾隆時期著名的《五涼全志》就是包括“第三卷圣集永昌縣志”在內的六縣縣志(其他五縣志是:武威縣志、鎮番縣志、古浪縣志、平番縣志)。參見張可復,等校注:《五涼全志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清)蘇銑:涼鎮志·永昌衛·古跡,手抄本,清順治丁酉年1657 年;《丁酉重刊附涼鎮志附永昌縣志·地理志·古跡》,載何登煥編輯:《永昌縣志補編》,永昌縣人民政府1999 年鉛印本,第289 頁。
⑦(民國)楊鼎新、雷致遠總纂:《永昌縣鄉土志·古跡》,手抄本,宣統元年1909 年,作者自藏。據《稀見河西方志校讀記》載:《永昌縣鄉土志》一冊,存寫本,清宣統元年知縣楊鼎新輯。按:此冊現存臺北“中央”圖書館。參見張令瑄:《稀見河西方志校讀記》,《敦煌學輯刊》1995年第1期,第105頁。
⑧2023 年1 月16 日請教蘭州大學著名留日蒙古族學者白玉冬教授所得。
⑨據有關學者的考證,吐蕃六谷部中可以確定的四谷是:洪源谷(今古浪河)、陽暉谷(今金塔河)、浩門河(今大通河)、烏逆水(今莊浪河)。參見張凌山:《涼州吐蕃六谷部政權“六谷”之名考論》,《河西學院學報》2022 年第3 期,第44 頁。除了上述四谷之外,“再加上武威西南、永昌南山的東大河谷和西大河谷共六谷,這六谷和歷史上華熱的地域基本相符為六谷”。參見洲塔,喬高才讓:《甘肅藏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 年版,第116 頁。需要說明的是,東大河谷,并不在武威西南,而在今永昌縣東部。根據百度百科的資料:東大河,甘肅省河西走廊內陸河石羊河支流,因流經永昌縣東部,故名。上游有直河、斜河,均源于青海門源縣境內祁連山冷龍嶺大雪山,東北流經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皇城灘草原,出祁連山入永昌縣河西走廊平原。主河道過東寨、南壩至六壩鄉的南莊子附近分為三岔,即南二岔、北一岔。東大河發源于祁連山冷龍嶺北麓,主要支流有兩條:一是由老虎溝、干樹灣溝、金洞溝、鐵礦溝、倒腰溝,黑鷹溝、煤洞溝等匯流而成,名為直河,流程35 公里;二是由號塔寺溝、夾皮溝、大,小東溝、敖包溝,一棵樹溝、大、小柏樹溝、法拉溝、石峰崖溝等匯流而成,名為斜河,流程40 公里。直、斜兩河在皇城灘鏵尖交匯后始稱東大河。而西大河則是發源于冷龍嶺北坡垴兒墩。源頭主要支流在多條,以最長的腦兒墩溝為正源。腦兒墩溝(有支流馬折腰溝匯流其中),自冷龍嶺北永昌縣山丹軍馬場境內南端北流,進入永昌縣與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西的邊界。西大河的支流有大烏龍溝、小烏龍溝、鸞鴨溝、平羌溝、腦兒墩溝、馬折腰溝、古松林溝、大橫溝、小橫溝等,整體上市呼吁甘肅河西走廊內陸河石羊河水系支流,現在金昌市區的供水基本靠西大河水庫和皇城水庫。綜上,換言之,吐蕃六谷部分別是:洪源谷(今甘肅武威古浪縣古浪河)、陽暉谷(今甘肅武威南部金塔河)、浩門河(今青海東北大通河)、烏逆水(今甘肅天祝、永登的莊浪河)、東大河谷(今甘肅永昌縣東部的東大河)、西大河谷(今甘肅永昌祁連南山的西大河)。
⑩“行國”之名最早記載見于《史記·大宛列傳》:“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3160-3161頁)實際上《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雖未直接說“行國”二字,但其表達的是“行國”的意思。其原文是——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西漢)司馬遷:《史記:文白對照版:全四冊》,張大可譯,商務印書館,2019 年版,第1846 頁)。后來,在《漢書》中也有類似記載:“大月氏,本行國,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東漢)班固:《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中華書局,1962 年版,第3872 頁)最初的“行國”概念是指與農耕有城郭的“土著”相對應的逐水草遷徙、從事畜牧業生產生活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在學界,賈敬顏、史繼忠、李大龍、肖愛民、陳曉偉、李玉君等學者對該制度多有研究。在國內,最早對行國制度進行研究者為賈敬顏先生在1979年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的文章《釋“行國”》(收入《中國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集刊》中),后以《釋“行國”——游牧國家的一些特征》發表在《歷史教學》1980 年第1 期上)。對行國制度進行系列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李大龍先生,先后發表《試論游牧行國與王朝藩屬——多民族國家構建視角下游牧和農耕族群互動研究》(《中國邊疆學》輯刊2014 年版)《游牧行國和王朝藩屬的第一次碰撞和重組——多民族國家建構視野下的游牧與農耕族群互動研究》(《中國邊疆學》輯刊2015 年版)、《游牧行國的內涵及其特點多民族國家視角下游牧和農耕族群互動研究》(《煙臺大學學報2014 年第5 期》)《多民族國家建構視野下的游牧與農耕族群互動——以明代游牧行國與王朝藩屬的對峙為中心》(《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3 期)《多民族國家建構視野下的游牧與農耕族群互動研究——宋金時期游軟行國體制與王朝藩屬的第二次對峙和重組》(《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5 期)《行國體制的發展及其對中華大地上族群的整合——元代多民族國家建構視野下的游牧與農耕族群互動研究》(《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 期)等論文。
?“四時”即指一年中的春、夏、秋、冬。“捺缽”亦稱納巴、剌缽等指遼朝皇帝貴族們所從事的與契丹民族游牧習俗相關的行在、營地遷徙和游牧、漁獵等活動,是在遼朝初期“因俗而治”的二元政治體制下的客觀延續。參見穆鴻利:《關于契丹四時捺缽文化模式的思索》,《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5 年第6 期,第51-55 頁。關于遼朝契丹皇帝的特殊活動“四時捺缽”,凡是研究契丹遼朝歷史的論著,都有所涉及。進行開創性研究的是傅樂煥先生,他在《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中對春水、秋山及廣平淀等進行了具體考察。他認為捺缽“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遼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動在此,其國政中心機構在此”,“遼代的政治中心不在漢人式的五京而在游牧式的捺缽”。(傅樂煥:《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載《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36 頁)之后,陳述、姚從吾、李錫厚等先生都有同樣的觀點。目前學界基本上認為在中國古代所謂正統封建王朝中,統治者有類似于四時捺缽活動的肇始于遼朝其后金、元亦沿行不衰。參見肖愛民:《論遼朝“四時捺缽”的性質及其地位——從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談起》,馬永真、明銳、白亞光主編:《論草原文化》(第八輯),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第266 頁。
?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論“敦薨”即“敦煌”》,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學研究》(第五輯),新疆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561 頁。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論“敦薨”即“敦煌”》,《敦煌研究》2011 年第3 期,第80 頁。
?以上關于黨河地名流變,主要參考:李正宇:《“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地望考—兼論“敦薨”即“敦煌”》,新疆龜茲學會編:《龜茲學研究》(第五輯),新疆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60-561頁。
??該蒙古語表述,來自向遼寧省阜新蒙古族自治縣沙拉鎮人民政府蒙古族齊躍同學的請教。
?西北師大馮玉雷教授和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關于敦煌名稱來源的通新”中的說明,此處馮教授請教了新疆社會科學院懂蒙古語的土爾扈特人,才吾加甫研究員,參見馮玉雷、李正宇:“關于敦煌名稱來源的通新”,西北師范大學甘肅省地名研究中心“方輿研究院”公眾號,2022年3月17日。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1-8冊),北京:地圖出版社,第1-7 冊、第8 冊分別于1982 年、1987 年出版。轉引自許博:《塑造河名 構建水權——以清代“石羊河”名為中心的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1期,第117頁,注②。
?乾隆《五涼全志》第二卷《鎮番縣志·地里志·水利圖并說》,參見張可復等校注:《五涼全志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00 頁。
?筆者2021 年寒假(1 月15-18 日)期間對家鄉河西走廊永昌縣著名鄉賢張懷榮(金昌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先生的訪談。
?據百度百科詞條:王進寶(1626 年—1685年),字顯吾,甘肅靖遠人,清朝名將,河西四漢將之一。王進寶早年隸屬甘肅總兵張勇麾下,隨張勇轉戰湖廣、云貴,升任經略右標中營游擊。康熙二年(1663 年),王進寶改任甘肅提標左營游擊,后由參將、副將,累升至西寧總兵。三藩之亂時,王進寶在陜甘屢破叛軍,被授為陜西提督、奮威將軍、一等男爵。后奪取漢中、保寧,留鎮四川,因病返回固原。建昌失陷后,再次到保寧督軍,進封三等子爵。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王進寶病逝,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忠勇。
?卬羌是西羌中古老部落之一。《后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地少五谷,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母姓名為種號”。([宋]范曄撰,《后漢書·西羌傳·第七十七》,[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39頁)“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跡,兵臨渭首,滅狄?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宋]范曄撰,《后漢書·西羌傳·第七十七》,[唐]李賢等注,中華書局,1999 年版,第1943 頁】這說明,卬羌部落是無弋爰劍之孫,忍之季父卬在奉獻公時從湟水流域帶領出來的一個部落。另外,《居延漢簡甲編》381.1,甲1793 號簡文記載:“小月氏、卬羌人”。“卬”釋作“仰”。(轉引自王宗維:《漢代絲綢之路的咽喉—河西路》,北京:昆侖出版社,2001年版,157頁)簡文中“卬羌”與“小月氏”并列。“小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南山,依羌而居。小月氏居地正好在賜支河曲西千余里,與卬羌西遷的方向相符,可見小月氏人所依的南山羌,就包括“卬羌”。(王宗維:《漢代絲綢之路的咽喉—河西路》,北京:昆侖出版社,2001 年版,157 頁).
?(明)陳誠、李逞:《西域行程記》,載楊建新主編:《古西行記選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263—264 頁。
?(清)張寅:《西征紀略》,李競主編:《絲綢之路資料匯鈔(清代部分)》,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6 年版,第58-5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