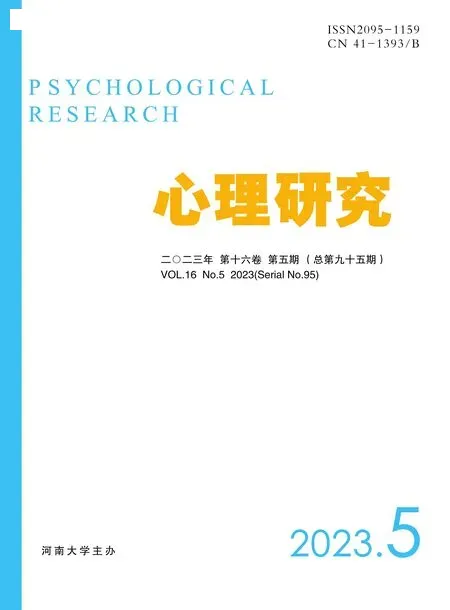“忠孝”與“背叛”:吳三桂矛盾人格的心理傳記學研究
李昱秋 吳昊瀚 劉 將 馬瑞佶
(云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昆明 650500)
1 引言
1644 年為農歷甲申年,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明、清、順、西,四個政權共現,大明朝的崇禎帝朱由檢、大清朝的順治帝愛新覺羅·福臨、大順朝的永昌帝李自成、大西朝的大順帝張忠獻,四帝并立。 在各路政治勢力的角逐中, 吳三桂成為明清交替時期的關鍵人物。
在一般大眾眼中, 吳三桂是一位聲名狼藉的歷史人物。 在明朝巨變時刻,君難不救,父死不顧,在明、清、順三方之間窺伺機會,以便坐收漁翁之利。為達私利,他不惜打開山海關大門,引清入關,斷送大明江山。這些天下百姓耳熟能詳的“丑聞”,甚至在影視劇作中也能看見。揭開歷史的面紗,吳三桂為人真如民間所說這般不堪嗎?通過勘查史料,我們把吳三桂的生命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少年英雄,甲申之變,封藩云南,起兵北伐。 可出乎意料的是,其在每階段都有“忠孝”品質的體現。《中國明朝檔案匯總》(左書諤, 1989)以大忠大義的英雄形象描述吳三桂,稱其“以報君橋之讎,以雪國家之難,以甦四民之困,揆此數行,千古之下可稱大忠、大義、大仁孝之圣賢也。 ”
那么, 是什么因素促使吳三桂從忠孝名臣逆轉為《逆臣傳》榜首人物? 又是什么因素導致他接連叛明叛闖又叛清呢?在討論這些話題時,人們往往將吳三桂反復背叛的原因歸結為“亂世求生”的結果。 然而, 在他為清朝打下半壁江山后, 社會已經趨于安定。此時清朝有意削藩,吳三桂倘若能像平南王尚可喜一樣, 選擇做一名退隱的開國功臣, 便能名垂青史。可他為何還要再次背叛清朝自立為王?這無疑與“亂世求生”的想法相沖突。因此,導致吳三桂反復背叛的原因不僅僅是外部因素, 其個人內部因素的作用亦不可忽略。 心理傳記學是心理學研究的一條路徑(Schultz, 2005),是介于心理學與歷史學之間,系統地采用心理學理論和方法對個別人物的生命故事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鄭劍虹, 2014)。 本文嘗試從心理傳記學的視角,對吳三桂“忠孝”與“背叛”的人生悲劇作出全新的闡釋。
2 吳三桂“忠孝”與“背叛”的表現
2.1 “忠孝”人格的表現
“忠孝”在新華字典中的釋義為:忠于君國,孝于父母。忠主要放在政治領域做解讀,儒家倡導的政治忠誠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強調臣民對君忠誠,要求臣民政治上忠誠于君主、服從于君主。二是強調君主要忠誠于天下,為天下謀福祉、贏得民心(胥仕元,2017)。中國傳統忠孝觀對我國幾千年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論語》中季康子曾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韓非子則指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可見,在傳統觀念中,忠孝觀念確實應由統治者自上而下倡導,而這會影響臣子對忠孝的秉持。 這一點在明代尤為突出,明以孝立國,法律對“孝子順孫”實行旌表(楊伯峻, 2017)。 如《大明令》規定,“凡是孝子順孫,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復,轉達上司正官,旌表門閭”(楊一凡, 2013)。 進一步而言,朱棣也提出:“夫孝,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蓋事君之忠,即事親之孝也。人惟父生而君食之,故事之如一也。”就此而論,忠孝兩種品質可以合一(陳寶良, 2013)。
體現吳三桂“忠孝”品質的事例并不鮮見,其中比較典型的有以下兩件。在《吳三桂全傳》(李治亭,2017)中,其在少年時期,就曾以“忠孝”“敢戰”聞名。十六歲時親率家丁二十人“闖圍救父”,在金兵數萬人的壓迫下成功救出吳父,稱其“孝聞九邊,勇冠三軍”。 成年時期,吳三桂在方圓四百里沒有任何支援的情況下,堅守寧遠孤城。皇太極接連兩次向他遞來橄欖枝,并授意已投降的親屬(祖氏、吳氏)和摯友勸降,吳三桂除了回復舅父祖大壽的兩封信外,都不予回應。孟慶來(2016)對吳三桂與祖大壽往來書信進行解讀,指出吳三桂在第一封回信中多敘甥舅之情。除此之外,吳三桂也直接表示誓要與清軍對抗到底。第二封回信則多談忠義, 面對諸位親友以“分茅裂土”“功名富貴”相勸,吳三桂堅持“唯有忠貞不二可得善終”的觀點,反復陳述不事二主的決心。 他在信中寫到“兒世承國恩”“受歷代圣明之恩養”“存二心之臣,如何全身而退。只求富貴,反先殞命”。 可見吳三桂面對皇太極的招降是明確拒絕的態度,以及“忠君報國”觀念在他心中的分量。吳三桂身為一名久經沙場的將領, 他清楚知道自己的選擇將會把他和吳軍推向斷糧和隨時被包剿的險境。 他的忠君思想相較于已投降的明官來說,表現得更堅定。 事實上,吳三桂的確是清入關以前最后一位降清的明將。 在清軍入駐北京城之后, 吳三桂在給清太祖的疏奏中也曾公開表達:“臣受前朝知遇最厚。”說明其早期在處理明與清的關系時,他更看重明朝的恩澤。
2.2 “背叛”人格的表現
“背叛”在新華詞典中的釋義有:背離,叛變。 即違背自己所屬方面的利益投向敵對方。 在儒家忠孝觀教導之下,背叛是令人鄙視的行為,甚至可能背上“逆臣”的惡名。 《清史列傳·逆臣傳》共收錄41 位逆臣,吳三桂則是被編入的首位人物。“逆”自古以來便有不忠、反叛、抵抗之意,逆臣即是指旗幟鮮明地反叛朝廷(王鐘翰, 2022)。
吳三桂“背叛”人格最典型的事例是降清后再叛清。 全國統一之后,吳三桂曾主動請奏,調動十萬兵馬向緬甸進軍, 目的是撲滅南明最后的殘存勢力——永歷帝。 不久,永歷帝被擒獲,暫扣于昆明幽禁。 云南距北京城路途遙遠,倘若押回京城,擔心途中會生變故, 因此朝廷授權給吳三桂讓他決定如何處置永歷。三桂當場果斷回答:斬首。 就連清將愛星阿也勸阻道:永歷曾為國君,斬首過于殘忍,應該賜予自盡保留全尸,始為得體。他沒有動搖,辯解道,只是奉旨“殺頭”,并非個人專斷獨行。在另外幾名清將的多次勸說下,吳三桂才表示同意。 不久,他親自部署和執行對永歷的處決, 永歷及其太子當場被弓弦勒死。此后吳三桂被晉封為“親王”,他是得此爵位的第一個漢人,此等殊榮是其他三藩無可比擬的。從一定程度上看, 斬殺永歷標志著吳三桂與舊明徹底劃清界限,表現出效忠清廷的決心。 但是,隨著朝廷愈發顧慮藩王勢大, 清朝統治階級集權的愿望也與藩王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 削藩只是時間問題。 而這對吳三桂來說意味著將從一個權勢顯赫的王爺跌落成無權無威的“富家翁”。為維護吳氏利益,吳三桂首立反旗,正式與朝廷決裂,并大量復印檄文傳送到各地,動員全國漢人反清,掀起了叛亂狂潮。不久,吳三桂在衡州登基為皇帝,國號大周。 從處死永歷帝到反清北伐,吳三桂的抉擇在迅速變化,這種反復無常的背叛也是他被納入《清史列傳·逆臣傳》榜首的原因。
除此之外,縱覽吳三桂的一生,分別在政治、軍事、家族取舍等決策上均表現出“忠孝”和“背叛”兩種矛盾人格的交織,詳細事件見表1。

表1 吳三桂矛盾人格表現事例表
3 “忠孝”人格形成的原因
3.1 傳統文化
儒家思想處于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歷代百姓生活在封建禮制之中,深受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儒家思想的影響。尤其到了明代,思想統治更為嚴厲。 傳統士大夫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 無不以忠臣孝子自期。 正如明初學者商輅(2012)所言,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士君子讀書學問,“所務者忠與孝而已”,可見忠孝觀地位突出。吳三桂也深受“忠孝”思想影響,年少時“闖圍救父”“冒險運糧”就有“忠孝”之名。根據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發展五階段, 五歲左右受父母灌輸的傳統價值和社會理想,個體會形成超我的人格結構,超我依據良心與自我理想兩個部分掌管獎與罰。 良心是兒童受懲罰而內化的經驗, 如果重復受罰經驗, 個體就會產生內疚。自我理想是受獎賞而內化的經驗,如果再次實施受獎賞的行為個體會感到自豪(郭永玉, 2011)。 兒童在潛伏期(6~10 歲)會對父母價值體系產生認同,不只是為保護自己遠離對父母懲罰而產生的恐懼,也幫助他們建立超我(Blackman,2011)。受傳統文化的影響, 吳三桂的舅父祖大壽與父親吳襄均表現出忠孝的品質。 例如,祖大壽作為明末悍將,曾在守御寧遠和捍衛錦州的抗清戰爭中立下顯赫軍功。 后又率兵收復被后金占領的河北永平等四城, 因軍功卓越被晉封為太子太保, 明廷稱贊其“壯烈忠膽”(潘喆,1991)。 此外,吳襄也在朝為官多年,在身處數萬金兵“圍剿”的困境中堅持不降。 二人的教導自然使吳三桂對“忠孝”的理解有更深刻的體會。 言傳身教之下,三桂認同和內化了“忠孝”作為良心和道德標準即超我,將此奉為至圣的準則。
3.2 地緣環境
生于遼東,猶如生于戰場,當地軍民長期面對刀光劍影,出于保護自己的心態,都練武強身。因此,整個遼東的尚武氛圍很濃,以武報國,保衛故土的思想扎根在遼東百姓心中。有些家庭幾乎滿門皆軍,如遼東明將李成梁的五個兒子,都積極投身行伍之中。三桂從小就刻苦努力, 面對父親嚴厲的訓練都堅持下來。 埃里克森的發展漸成說強調人在發展過程中自我與其社會環境相互作用。 在尚武和戰亂的社會環境中,許多青年男性以入伍為榮,而從軍最重要的精神之一為忠君愛國,所以與一般地區相比,遼東百姓對“忠孝”有更深的認識。 Erikson(2018)最早提出自我同一性,認為它是青年期所追求的核心發展主題,與社會精神氣質互相補充。萬增奎(2009)在Erikson的基礎上提出道德的觀念, 認為自我同一性和道德觀念可以由個體生活的文化世界所塑造, 人們把自己的道德整合進自我同一性更有可能引發道德信仰和道德行為。因此,從小在“尚武”“抗金”環境中成長的吳三桂,不僅練就了騎射本領,培養了愛國情懷和民族氣節,也樹立了從軍的理想。十六歲時吳三桂得中武舉,正式加入到保衛祖國抗擊金兵的戰斗中。與此同時,他面臨的不單單是更為嚴酷的訓練,還有軍隊“忠孝”思想更深入的教育。
3.3 角色楷模
Blackman(2011)認為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對理想老師等人物的認同具有強大的影響, 而在成人期對導師、 領導以及組織的價值認同也可以影響人的價值觀。 對處于青少年和成年期之間的吳三桂來說,也有一位理想中的導師,對他價值觀的塑造和改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此人正是明末愛國將領袁崇煥。 《袁崇煥傳》(閻崇年, 2016)中曾寫道:“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說明袁崇煥的作戰指揮能力極強,就連所向披靡的清軍也忌憚三分。 尤其是他指揮的寧遠和錦寧兩大戰役的勝利,打破了金兵不可戰勝的神話。在寧遠戰役前夕, 努爾哈赤曾釋放被虜漢人回到寧遠城,讓其帶口信規勸袁崇煥投降,卻遭到袁崇煥的嚴辭拒絕。 根據 《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吳元豐,2015)記載:“吾以二十萬兵攻此城,破之必矣! 爾等官若投降,即封以高爵。 ”寧遠道袁崇煥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 寧、錦二城,乃汗所棄之地,吾恢復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由此可見,袁崇煥堅守寧遠孤城的決心和他“忠誠”“敢戰”的品質。在這期間,吳三桂正值青春期,其舅父祖大壽是袁軍麾下的主將,父吳襄也在沙場上沖鋒陷陣, 吳氏一族對軍旅有著深厚的情感。耳濡目染之下,袁崇煥的事跡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之后同為“獨守寧遠”的選擇中可看出,吳三桂或許把袁崇煥當作了理想的認同對象。 成年后,面對孤立無援的軍情和皇太極的兩次招降,他態度堅決, 信中寫道 “不事二主”“又豈敢背叛圣明”(孟慶來,2016),明確拒絕了祖大壽的勸降,選擇了與袁崇煥同樣的堅守。
4 “背叛”人格形成的原因
4.1 早年安全感的缺失
吳三桂出生在一個充滿威脅的時代, 金兵窺伺邊疆,不時地發動戰爭,導致遼東秩序不穩定,局勢緊張。與此同時,天災不斷,糧食收成不佳,行軍所需的糧餉又不得不從百姓那里收取,百姓苦不堪言。加之明與后金的對戰接連失利, 遼東百姓逐漸對未來失去信心, 迫切希望能有一個穩定局面以此安養生息。
與遼東千萬百姓一樣, 戰事是吳三桂生活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生母早逝,正史中沒有詳細記載。之后,吳襄續娶名將祖大壽的妹妹為妻。 據李治亭《吳三桂全傳》中得知,吳襄在三桂十歲時中武舉,正式獲得在軍中任職的資格,從此吳氏家族躋身官僚,憑借軍績開始富貴榮華。隨后吳襄便有了與祖大壽接觸的機會。 經推斷,吳三桂至少十歲之前,有一段較長的時間處在沒有生母照顧、關愛的狀態。需要層次理論認為, 如果生理需要相對充分地得到滿足,接著就會出現一整套新的需要,歸納為安全類型的需要:安全,穩定,依賴,保護,免受恐嚇、焦躁和混亂的折磨,對保護者實力的要求等。兒童的安全感表現在他喜歡一種安穩的程序或節奏, 需要一個可預見的有秩序的世界。 擔心、恐懼、焦慮、緊張、不安都是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結果。 肖涵等人(2021)強調本體安全感是來源于個體在自己與環境互動過程中的心理感受。自然災害、戰爭會破壞人們長期以來在穩定環境中所形成的心理安全狀態。 回顧吳三桂的一生, 不難看出早年經歷的三件事可能導致其安全感的嚴重缺失,分別是:幼年喪母、戰亂不斷、親歷災荒。
父母之所以重要, 在于他們能修復個體因脫離子宮,不適應這個世界而帶來的心理傷害,同時還能為孩子重建原有的安全感, 讓孩子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有規律和可信賴的世界(舒躍育, 2018)。 在沒有母親庇護的童年成長環境中, 吳三桂與同齡孩子相比,缺少母親可提供的保護和安慰,他比別人更渴求安全的滿足, 需從別處獲取更多的安全感來替代或緩解不安。
處于亂世之中的人, 要想重建安全感就只有兩條出路: 一是消極避世, 通過遠離是非而重建安全感;二是成為能夠把控時事的軍政首領,通過對權力的控制重建自己的安全感(舒躍育, 2018)。年少時,吳三桂曾讀《漢記》感悟道:“仕官當作執金吾,取妻當得陰麗華。我亦遂此愿足矣”(李治亭, 2017)! 執金吾是負責保衛京城的官員,擔負京城內的巡察、禁暴、督奸等任務,既接近政治核心,又重握兵權,擔任執金吾的人必定是皇帝器重的親信,具有特殊地位。從中可看出吳三桂早期已懷有遠大抱負, 對權力和地位有所追求,其背后可能是對安全感缺失的彌補。岳寒飛(2019)認為,權力欲望從起源上來說可追溯到人對物質追求的欲望, 從物質欲到權力欲的轉向其實是物質欲的內化,權力雖然是一種無物的概念,但獲得權力者可以調動一定范圍內的資源來滿足自我需求,而這種需求往往出于物質、利益等的欲念。總而言之, 權力欲望可以被理解為物質利益欲望的內化結果。縱觀吳三桂的一生,不難看出他畏懼失去權力,極力把兵權、財富斂入囊中,通過控制兩者來重塑安全感。 例如,兵權方面,吳三桂在分封云南期間,利用朝廷所給權力,擴充和發展勢力。 在政治軍事方面,為加大軍事力量,首次提出設置“云南援剿四鎮”,同時改編投誠的明兵和農民軍的降卒,設立“忠勇營”和“義勇營”。甚至隱瞞朝廷,私自進購大批西藏戰馬。 此外,壟斷地方科舉,把藩屬弟子選入為官,形成“滿門文武皆吳氏”的局面。他成為集軍民財政文大權于一身的“云南代理人”。為維護特權,吳三桂在范承疇回京前請教“自固之策”。 范承疇答:“不可使滇一日無事(李治亭, 2017)。 ”三桂立刻領悟,實質就是要使云南始終呈現出緊張的狀態, 這樣朝廷就不會收回給予三桂的一切權力, 從而使自己的地位日益鞏固。
物質方面,他向朝廷索要大量銀兩和糧食,利用特權千方百計地聚斂財富。 開礦取利, 壟斷鹽井稅收,放高利貸和主張通市,這些都是謀取資本的重要手段。 居室方面,持續十余年增修王府,并且專門為陳圓圓修建野園,最終建成規模宏大的宮殿群。總而言之,吳三桂一心效仿世守云南的沐氏家族,在此基礎上建造“吳氏帝國”。
對兵權和物質兩方面的控制, 正是吳三桂彌補安全感的方式。 早年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個體未來的人格, 而人格又決定著個體在具體情境下的行為決策(Rsner, 1987)。 吳三桂成年之后,仍然迫切尋求安全感, 通過控制兵權和財富為自己創造一種穩定的秩序。但是他所處的時代變化莫測,想通過攬權、 斂財來彌補安全感, 就會隨時面臨易主的風險。 所以,當處于生死存亡或利益角逐的情景時,吳三桂便會產生“背叛”的想法,這是他“反復無常”的重要依據。
此外, 個體行為的產生還與個體行為的動機有關, 而對安全感和控制感的追求是人類行為的基本動機, 但是因早年經歷而導致過分缺乏安全感的個體, 可能會更加傾向于對安全感特別是權力的過度追求(舒躍育, 2018)。然而,吳三桂奪權的欲望異常強烈,以至于主動向清廷奏請“遠征緬甸生擒永歷”。之后,同為漢人的他全然不顧明朝舊恩,再次主動提議斬首最后一位漢族皇帝——永歷帝, 隨后他受封為“親王”,這件事標志著他與明朝徹底劃清界限。馬斯洛認為行為的背后一定有一種或幾種需要在驅使人行動。而吳三桂過度追求權力和地位的背后,可能是對安全需要的極度渴求。
除此之外,在吳三桂獲得“親王”顯赫的身份之后,他所追求的本不應該只是“衣食住行”的低層次需要,而應是馬斯洛所提出的“自我實現”最高層次需要。他的榮譽和人生價值不是幫百姓謀幸福,反而極其在意自身利益,沒有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清朝統一全國,結束了這個時代的混亂,社會開始趨于安定,百姓的生活和生產力正向積極的一面發展。但是他不顧世間蒼生,掀起“北伐”戰爭。這場戰斗不代表正義,僅僅是對自身“特權”的維護,再次使百姓卷入到戰爭的恐懼之中。身居高位的吳三桂,始終在安全需要和自尊需要之間徘徊, 難以自拔地通過權財來重建安全。在禍亂交興的光景下,吳三桂的悲劇在于對權力和財富的過度追求, 始終沒有脫離對匱乏性需要的追逐。
4.2 對認同者共情的結果
共情作為社會互動中的一種重要心理現象,是指個體對他人情緒感受的感知或想象, 并且部分體驗到他人感受的心理過程 (Singer & Lamm,2009), 具有狀態和特質的雙重屬性 (劉聰慧 等,2009)。研究者普遍認為共情可以分為情緒共情和認知共情兩類,前者包含原始情緒感染和同情關注,后者主要包含觀點采擇(楊曉凡, 胡平, 2020)。
一方面,在“闖圍救父”的經歷中,父親堅持不降,與后金長時間相持體現出吳襄“忠誠”的品質。但他看到父親的“忠誠”換來的竟是無兵援救,只好聽天由命。他痛哭流涕,甚至再三下跪請求舅父祖大壽出兵,祖大壽卻不予理會。 最后,他只好親率二十家丁闖圍救父。 可想當時的吳三桂替深陷險境的父親感到痛苦與無助。共情產生的基礎是情緒感染,而吳三桂的共情則顯得更為復雜, 其發生的過程有認知的參與。觀點采擇作為共情中重要的認知成分,指從他人的角度出發, 想象或推測他人感受或觀點的心理過程(Galinsky et al.,2006)。 此次經歷,第一次動搖了他對國家和君王“忠誠”的價值觀。 于國不再給予完全的信任,于己認識到勢單力薄,焦慮和不安再次在腦海中升騰。反觀祖大壽不出兵的策略,他意識到只有手握兵權才能掌控局面, 于是他找到一種彌補安全感的手段——爭奪權力。
另一方面, 愛國英雄袁崇煥接連兩次擊退金兵的猛攻,獲得寧遠大捷和錦寧大捷,對官心、軍心、民心有著巨大的振奮作用,給遼東,乃至全國帶來了希望。明天啟帝也宣旨稱:“此七八年來所絕無,深足為封疆吐氣”(閻崇年, 2016)。
幾年之后,皇太極率大軍繞道蒙古,企圖進攻北京。袁崇煥立刻派遣祖大壽帶兵入援,同時親率遼軍星夜疾馳趕往京師救援。 在北京保衛戰中贏得廣渠門和左安門兩場重要勝利。但此時,北京城內盛傳謠言:袁崇煥設計引后金入關,將脅迫皇帝簽訂“城下之盟”。崇禎被軍事反間計迷惑,袁崇煥被縛下獄。不久之后,明廷以“通虜謀叛”“擅自議和”“專戮大帥”“失誤封疆”等莫須有的罪名將袁崇煥殘忍冤殺。 從“忠誠”“敢戰”到“背叛”,袁崇煥的形象在一段時間內急劇變化。時年吳三桂十八歲,正值青春期。以“敢戰”聞名的他,立志在疆場上建立功績,坐上“執金吾”的權力之位。 但此時,他的價值觀第二次發生了改變。 忠君、忠國、敢戰就能當上“執金吾”,掌握重權嗎? 吳三桂早期形成的“忠孝”品質,因以“忠孝”而被冤殺的袁崇煥,在情緒和認知上受到強烈撼動,內心的價值體系之柱遭受重創。受認同對象共情結果的影響,他今后的“忠誠”傾向被削弱。 第一,他想要自保,即性命和吳家親兵的勢力;第二,他要爭取至高的權力和財富。 吳三桂余生的方向,在潛移默化中改道。
5 余論
吳三桂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早期生活經歷對他人格的形成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傳統文化、地緣環境和認同對象的影響下,“忠孝”思想根深蒂固,在每個時期都有彰顯出“忠孝”的行為品德。同時,早期的戰亂、幼年喪母和災荒,使其安全需要受挫。 他不得不尋找另一種途徑去彌補安全感的缺失。少年時期“闖圍救父”的經歷,使他意識到權力可替代不安感。 在“分藩云南”期間,繼續沿用早年彌補安全感的模式,建立起一種全權任他掌控的秩序, 安全需要得到全方位的實現。 然而, 他選擇在惡劣的局勢下匆忙稱帝,權力到達頂峰。 對帝位的貪婪沒有帶來安全感,反之, 隨時都會被清兵侵占, 他畢生修建的安全大廈,在焦慮中轟然崩塌。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
吳三桂的一生,在“忠孝”與“背叛”的交織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