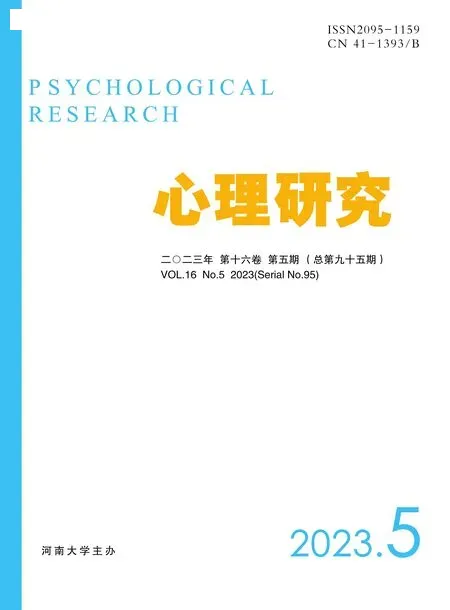未來時間洞察力對焦慮的影響: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的鏈式中介作用
龔映雪 李小保 楊藝琳 呂厚超
(1 西南大學心理學部,重慶 400715;2 中國時間心理學研究中心,重慶 400715;3 中國社區心理學服務與研究中心,重慶 400715)
1 引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在全球快速爆發和蔓延,直到現在,人類也未能完全走出疫情的陰影。 疫情不僅直接導致了居民的經濟損失和身體傷害, 還使居民產生了災難中的心理健康問題(趙國秋等, 2009)。作為全球性的威脅情境, 疫情是個體產生焦慮的重要影響因素(Michl et al., 2013),居民因此表現出擔憂、恐懼、焦慮等負性情緒。 有研究發現,在疫情期間,我國居民存在明顯的恐慌和焦慮等負性情緒(單格妍等,2020),焦慮檢出率偏高,對人們的生產生活造成消極影響。 根據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 焦慮是對自身的現狀和對未來的擔憂導致的, 對潛在的負面或有害事件的預期壓力狀態(Villavicencio & Bernardo, 2013)。 焦慮通常被認為對人們的工作、 生活有害, 與壓力密切相關(Bardeen et al., 2013), 妨礙個體取得成就(Pekrun, 2006);焦慮還會影響個體的認知判斷,導致個體對負面信息的注意偏向、 對應激事件的關注增加、降低幸福感(Waters et al., 2014);焦慮與抑郁有較高的共病率 (Jeon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05),極有可能同時誘發人們的抑郁狀態(Jacobson & Newman, 2014),嚴重損害身心健康。 在疫情期間,各類不實信息會加劇人群的恐慌,導致焦慮情緒普遍傳播; 疫情造成的沖擊也可能會降低居民對未來的積極預期, 引發對當前狀況和未來的擔憂,人們因此產生焦慮情緒。 所以,在全球性威脅事件的背景下, 從未來時間視角探究如何緩沖或降低應激事件帶來的焦慮等消極情緒, 探討其內在機制并對其進行正面引導是非常必要的。
1.1 未來時間洞察力與焦慮間的關系
疫情威脅著每個人的健康、未來和生命,因此可能會加劇人們對未來有限性的看法。 除了病毒的威脅之外,疫情期間的社會矛盾、金融衰退也會促使人們形成對未來有限性的態度 (Rupprecht et al.,2021)。 Carstensen 等人(1999)認為未來時間洞察力(future time perspective, FTP) 描述了個體對生活中剩余時間的感知和想法。 Carstensen 認為FTP 是個體感知到有限未來到無限未來的一種單維結構(敖玲敏等, 2011)。 感知到無限未來的個體認為,未來時間充足,更多關注未來導向的目標,在未來時間洞察力量表上的得分更高; 感知到有限未來的個體認為,剩余時間短暫,追求可以在短期內實現的目標,強調情感狀態,在未來時間洞察力量表上的得分更低 (Carstensen, 2006; Lang & Carstensen,2002)。 已有研究表明,FTP 會對個人的心理和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Charles & Carstensen, 2010),低FTP 不僅與低生活滿意度、 低主觀幸福感密切相關(Allemand et al., 2012; Hicks et al., 2012;Ramsey & Gentzler, 2014), 而且是影響焦慮的一個重要的個體因素 (Bluck & Liao, 2019)。 Rupprecht 等人(2021)的研究發現,疫情期間,居民的FTP 和預期壽命會下降,同時,死亡焦慮會增加。 以往的研究也表明,韓國大學生的FTP 與職業選擇焦慮顯著負相關(Jung et al., 2015),并且該結論在中美跨文化群體中得到了驗證(Boo et al., 2021)。 此外,根據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SST),在社會交往中,低FTP 個體傾向于與相對親近的人保持聯系(例如,家人、親密友人),他們在得到了更多可依賴的情感回報后, 才能優化自身情緒 (Carstensen et al., 1999), 提高幸福感(Carstensen, 2006)。否則個體會因為無法滿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從而產生焦慮、抑郁等消極情緒(敖玲敏等, 2011)。
作為一種防控疫情的手段, 居家隔離要求居民保持距離,人們因此會產生孤獨無助感(謝冬冬等,2021),并且出于對死亡的恐懼(孟祥寒等, 2021),個體可能難以實現高質量的正面社交互動, 較難通過與他人交往來實現自身情緒狀態的優化, 從而導致個體的消極情緒增加,焦慮水平上升。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FTP 能夠負向預測焦慮(H1)。 考慮到國內較少針對FTP 與焦慮的關系進行研究,且FTP 可能在焦慮情緒的產生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加之國內鮮少涉足FTP 影響焦慮的潛在作用機制,所以有必要對重要的中介變量進行探討。
1.2 未來時間洞察力、自我效能感與焦慮間的關系
自我效能感是指個體對自己做出足夠努力,成功完成具有挑戰性的任務的能力的感知信心(Luthans et al., 2005; Stajkovic & Luthans,1998),其概念的組成部分就有與信息獲取相關的維度(Walker & Tracey, 2012)。 Bandura 認為自我效能感對人的動機、 情緒和行為具有本質和普遍的影響(Coon et al., 1998)。 例如,自我效能感與愉快、希望和自豪呈顯著正相關,與生氣、焦慮、失望和厭煩呈顯著負相關(Pekrun et al., 2009);缺乏自我效能感會導致動機不足, 面對挫折困難難以堅持(Heuven et al., 2006), 所以自我效能感是一種重要的心理資源(Hobfoll, 2001)。 國內的研究表明,FTP 對自我效能感有顯著影響, 更有將自我效能感作為FTP 和其他因變量之間中介變量進行分析的研究(梁群君等, 2017)。FTP 之所以對自我效能感產生影響,關鍵就在于FTP 能影響個體知識和信息的獲取。 Carstensen(2006)認為,高FTP 會促使個體追尋知識,不僅能增強自信心,而且能提高個體解決問題的能力,自我效能感因此得到提升。
關于自我效能感與焦慮的關系, 近年來已有大量研究進行驗證, 根據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COR), 自我效能感等有價值的資源可以幫助個體有效地處理和應對情緒問題(廖化化, 顏愛民, 2014)。自我效能感在提高適應性和緩解焦慮等負面情緒方面起著積極作用 (Kestler-Peleg et al., 2020)。自我效能感與焦慮呈顯著負相關(Mills et al., 2006),自我效能感可以顯著提高個體對未來的積極體驗和積極情緒 (Caprara 等,2006),從而降低焦慮水平。 高FTP 的個體會努力獲得知識,知識是有價值的資源,這些資源有利于提高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從而獲得更高的控制感,提高對現在和未來的積極態度,降低焦慮水平。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自我效能感中介了FTP 對焦慮的影響(H2)。
1.3 未來時間洞察力、應對方式與焦慮間的關系
應對方式作為一種與情緒密切相關的概念,是個體為應對環境變化、使心理水平達到平衡狀態,所做出的有意識、 有目的的調節行為 (Joffe & Bast,1978)。解亞寧(1998)根據已有理論和實際觀察的結果,將應對方式分為“積極”和“消極”應對兩類,二者會同時存在。 傾向于采取積極應對方式(例如,尋求支持、力圖改變等)的個體,會將應激事件視為一種挑戰,從而更好地解決實際問題,進行有效的情緒調節;采取消極應對方式(例如,回避、發泄、自怨自艾等)的個體,傾向于逃避問題,個體可以獲得暫時的滿足(蘇靖雯 等, 2021)。 已有研究證實,FTP 與應對方式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 (Carstensen, 2006),SST 理論認為個體的社會動機和目標選擇是伴隨個體FTP 而不斷變化的 (敖玲敏 等, 2011), 因此FTP 可視為行為的決定因素。 擁有高FTP 的個體傾向于以獲取知識為目標, 渴望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得到更多的信息(Carstensen et al., 1999),改善自己的處境; 低FTP 的個體更關注短期內的情緒調節,表現為回避消極情緒(敖玲敏 等, 2011),更可能采取逃避等行為。國內外研究證實,FTP 較高的個體對未來充滿積極情感, 更傾向于采取以任務為中心的積極應對方式,調節當前狀態(Blomgren et al.,2016; 龐雪等, 2014)。
其次,對13512 名中國青少年學生的研究顯示,積極應對方式在生活壓力事件和焦慮等情緒的關系中起調節作用(Meng et al., 2011),應對方式是影響焦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廖友國, 2014)。 積極的應對方式,能夠緩解應激事件的消極影響,負向預測焦慮抑郁(Xu et al., 2013);消極的應對方式,會導致更消極的心境和更糟糕的外部環境, 與焦慮抑郁呈顯著正相關(范瑞泉, 陳維清, 2007)。 總的來說,FTP 作為一種人格特質, 既可以直接影響人們的焦慮情緒,也可能通過影響個體的應對方式,間接影響焦慮水平。 高FTP 的個體具有較強的自我調控能力,更傾向于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改善自己的處境,從而緩解應激事件的消極影響,情緒得到真正改善,焦慮水平下降;低FTP 的個體為了追求短期目標和愉悅, 更傾向于采取逃避、 自我安慰等消極應對方式,但并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只能使個體的焦慮水平暫時下降。 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應對方式中介了FTP 對焦慮的影響(H3)。
1.4 未來時間洞察力、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與焦慮間的關系
對自我效能感、 應對方式和焦慮的關系進行探討的研究發現, 童年期受創傷的大學生可以通過提高自我效能感,改善消極應對方式,從而緩和焦慮情緒(夏蕾等, 2020)。在對舉重運動員的研究中也發現,自我效能感不僅對焦慮有直接預測作用,還能通過解決問題、回避等應對方式起間接預測作用(陳洪波, 魏萍, 2014)。自我效能感高的個體認為行為的積極后果可以通過解決問題和設定目標來實現,更傾向于采取問題導向的應對策略, 焦慮情緒因此得到緩解; 而自我效能感低的個體傾向于采取情緒導向的應對策略(回避,發泄等),這只能暫時減輕心理壓力(Darvishmotevali & Ali, 2020)。 一個相信自己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 在生活中會更積極主動,反映出對環境的控制,控制感有助于降低焦慮情緒 (黃韻榛 等, 2019)。 總的來說, 根據SST,當個體認為未來時間充裕時,更有可能選擇擴展視野,增加對知識和信息的獲取,從而獲得可控感、減少不確定感,自我效能感因此得到增強,更有助于個體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提高對未來的積極預期,降低焦慮水平(Carstensen et al., 1999)。綜上所述, 本研究假設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能夠在FTP 與焦慮的關系中起鏈式中介作用(H4)。假設模型如圖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通過在線發放問卷的方式施測,共回收1444 份問卷。剔除作答時間過短、有規律作答以及不認真作答的無效問卷后,回收整理有效問卷1014 份。 被試平均年齡為39.07 歲(SD=12.08),詳見表1。

表1 被試基本情況表(N=1014)
2.2 研究工具
2.2.1 未來時間洞察力
采用Carstensen 和Lang(1996)編制的未來時間洞察力量表(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cale, FTPS),測量被試對自己未來的受限或開放的主觀感受。 量表由10 個題目組成 (如 “我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前方”),后三道需要反向計分(如“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覺得時間是有限的”)。 量表采用Likert-7 點計分,1 表示“完全不正確”,7 表示“完全正確”,所有題目得分的均值越高表示FTP 越無限。 在本研究中,本次測量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4。
2.2.2 自我效能感
采用Schwarzer 和Zhang(1997)修訂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來測量個體應付不同環境時的單一維度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適用于兒童、青少年和成人。 量表包括10 個題目(如“如果我盡力去做的話,我總是能夠解決問題的”),采用Likert-5 點計分,1 表示“非常不贊同”,5 表示“非常贊同”,所有題目得分的均值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強。 本研究中, 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4。
2.2.3 應對方式
采用解亞寧(1998) 編制的簡易應對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量表由20 個題目組成,包括2 個維度:積極應對(12 個題目,如“向親戚朋友或同學尋求建議”)和消極應對(8 個題目, 如 “幻想可能會發生某種奇跡改變現狀”)。 量表采用Likert-4 點計分,1 表示“不采取”,4 表示“經常采取”。 借鑒戴曉陽(2010)給出的個體應對方式得分的公式: 應對方式等于積極應對標準分與消極應對標準分之差。 如果應對方式得分大于0,則表明個體傾向于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應對方式得分小于0, 表明個體更傾向于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分值越高則越傾向于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本研究中, 積極應對、 消極應對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72,0.70,總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1。
2.2.4 焦慮
采用Spitzer 等人(2006)編制的廣泛性焦慮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來測量被試的焦慮情緒。 量表由7 個題目組成(如“對各種各樣的事情擔憂過多”),采用Likert-4 點計分,1 表示“完全沒有”,4 表示“總是”,所有題目總分越高就代表個體的焦慮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 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4。
2.3 程序
所有數據整理和分析均在SPSS 22.0 軟件中進行,中介檢驗采用Process3.5 宏程序進行分析。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報告法,因此采用了Harman 單因素法對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進行統計檢驗(周浩, 龍立榮, 2004),將所有項目進行未旋轉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大于1 的特征值因子有7 個, 第一個因子的累計方差解釋為22.32%,低于40%的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問題不嚴重(熊紅星等, 2012)。
3.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表2 列出了各變量的平均數、 標準差和相關矩陣。 相關分析發現,FTP 與焦慮呈顯著負相關,與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呈顯著正相關; 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與焦慮呈顯著負相關; 自我效能感與應對方式呈顯著正相關。

表2 描述性統計結果及變量間相關分析(N=1014)
3.3 中介作用檢驗
利用SPSS 中的Process3.5 宏程序,通過重復抽取5000 個Bootstrap 樣本估計中介效應的95%置信區間,在控制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的條件下,將FTP 作為預測變量,焦慮作為結果變量,以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為中介變量進行路徑分析。 從表3 來看,除了自我效能感對焦慮的路徑系數不顯著外,其他路徑系數均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性水平 (p<0.001):FTP 顯著正向預測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FTP 和應對方式顯著負向預測焦慮; 自我效能感顯著正向預測應對方式。 這表明在FTP 對焦慮的影響中,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顯著。

表3 中介模型檢驗
在統計力分析方面,F檢驗中的R2s分別為0.18(效能感為結果變量)、0.16(應對方式為結果變量)、0.16(焦慮為結果變量)。 根據Cohen 提出的R2值標準,研究的統計力在中等水平以上(R2=0.13)。
對中介效應直接檢驗結果表明(如表4 所示):在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產生的總間接效應中,Bootstrap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不包括0, 表明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在FTP 與焦慮間發揮著中介作用。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該中介效應包含三個間接效應:自我效能感的單獨中介作用、應對方式的單獨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的鏈式中介作用。 采用偏差校正非參數百分Bootstrap 檢驗,重復取樣5000 次,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與置信區間的估計,結果表明:間接效應1,FTP→自我效能感→焦慮,置信區間包含0,說明該路徑的間接效應不顯著;間接效應2,FTP→應對方式→焦慮,該路徑的間接效應顯著; 間接效應3,FTP→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焦慮,這條路徑的間接效應顯著(見圖2)。

表4 中介效應、總效應及直接效應分解表

圖2 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在未來時間洞察力與焦慮之間的鏈式中介
4 討論
4.1 未來時間洞察力與焦慮
本研究考察與民眾心理健康密切相關的FTP對焦慮的影響, 以及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 對FTP 和焦慮關系的檢驗發現,FTP 可以負向預測居民的焦慮水平, 這與以往對時間洞察力的研究結果一致 (Astr?m et al., 2014; Jung et al.,2015; Rupprecht et al., 2021),支持了假設1。 但對FTP 與心理健康的關系進行的大量研究也發現:低FTP 的個體(老人)表現出更高的主觀幸福感和更加積極的情緒,被稱為“老化的悖論(paradox of aging)”,是低FTP 者的交往對象選擇傾向與社會情緒管理策略導致的一種現象(敖玲敏等, 2011)。根據SST, 低FTP 個體在得到更多的情感反饋后才能優化自身情緒(Carstensen et al., 1999)。 但是疫情期間,居家隔離政策要求居民保持距離,人們因此難以實現高質量的正面社交互動, 難以通過與他人交往來實現自身情緒狀態的優化, 導致個體消極情緒增加(敖玲敏等, 2011),如焦慮水平上升。因此,在疫情期間,高FTP 對降低焦慮情緒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4.2 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在未來時間洞察力與焦慮之間的完全鏈式中介作用
研究結果發現,應對方式在FTP 對焦慮的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具體表現為,FTP 顯著正向預測應對方式, 應對方式越消極的個體越容易產生焦慮情緒,驗證了假設3。 Carstensen 等人(1999)認為,FTP與目標選擇密切相關,FTP 會影響人們的反應和行為。 高FTP 的個體以獲取知識為目標,對未來充滿積極情感(龐雪等, 2014),更可能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以得到更多的資源和信息 (Carstensen et al.,1999),改善自己的處境;而低FTP 的個體更傾向于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以實現短期內的情緒調節(敖玲敏 等, 2011)。 并且Xu 等人(2013)對應對方式與焦慮抑郁的關系研究發現, 積極的應對方式能夠緩解應激事件的消極影響,負向預測焦慮抑郁;消極的應對方式會導致更糟糕的心境和外部環境。 本文研究結果證實了應對方式在FTP 對焦慮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此外,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在FTP 對焦慮的影響中起鏈式中介作用,假設4 成立。 具體而言,高FTP 的個體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 促使個體采取更加積極的應對方式, 從而降低焦慮情緒。Carstensen(2006)認為,高FTP 會促使個體對未來目標的追求,有助于個體獲取知識和信息(Walker &Tracey, 2012),既可增強對自身的信心,也能提高個體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自我效能感。夏蕾等人(2020)的研究證實,應對方式在自我效能感對焦慮的預測中起到中介作用, 這解釋了為什么高FTP的個體往往會表現出更低的焦慮水平。具體來說,高FTP 的個體會選擇以未來為導向的目標(例如,獲取知識),從而提高自我效能感,鼓勵個體勇于探索、用積極樂觀的心態應對外界的挑戰和變化, 及時采取措施以使內部和外部達到平衡的狀態, 因此更有利于個體采取積極的應對方式, 提高對未來的積極預期, 從而緩解焦慮情緒。 綜上,FTP 通過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繼而影響焦慮的模型路徑具有合理性。
4.3 研究意義與展望
本研究證實了在重大應激事件的背景下,FTP對居民的情緒健康存在積極影響, 并且自我效能感和應對方式在FTP 影響焦慮水平中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結果對降低焦慮水平提供了實證依據, 以便科學地應對疫情期間居民的心理健康問題。 考慮到時間洞察力是較為穩定的人格因素, 兩個中介變量對于有效降低焦慮水平來講顯得尤為重要, 嘗試同時從認知和行為的角度緩解消極情緒是一條可行的干預思路。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是橫斷研究設計,無法確定四個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未來還需要通過實驗和縱向研究進一步探索變量間的作用機制,以增強結論的說服力。 其次,本研究的數據都是通過自我報告獲得的, 盡管共同方法偏差問題不嚴重, 但可能存在社會贊許效應和疲勞效應。 例如, 社會普遍對積極的應對方式有更高的贊賞,因此,被試可能會為了迎合這種主流,而更傾向于選擇積極的應對方式,未來的研究可以多方收集數據,采用更加客觀實際的指標。最后,本研究沒有發現自我效能感對焦慮的預測作用, 可能是由于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只有一個總的維度 (Schwarzer &Zhang, 1997), 而焦慮與情緒調節自我效能感的關系更加密切(蘇靖雯等, 2021),未來需要考察其他類型的效能感是否在FTP 與焦慮的關系中發揮著中介作用。
5 結論
(1)FTP 負向預測居民的焦慮;
(2)應對方式中介了FTP 對焦慮的影響;
(3)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在FTP 與焦慮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