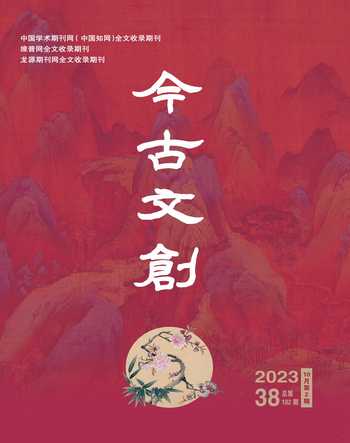儒家文化的有限表達和反思
【摘要】《白鹿原》是陳忠實的代表作,由于篇幅較長、人物眾多,改編成影視劇的難度可想而知。王全安執導的電影《白鹿原》把原著中白家和鹿家的人物關系加以簡化,將敘事重心放在黑娃和田小娥的愛情故事上,引發了較大的爭議和批評。電影缺點眾多,沒能展現原著的精髓,但也通過影視藝術中一些常用的表現手法和對原著情節的改動,對原著中的儒家文化進行了有限的表達和反思。
【關鍵詞】《白鹿原》;儒家文化;意象;女性命運;親子關系
【中圖分類號】J804?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38-008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8.027
《白鹿原》的故事主線是白鹿原上同出一族并共用祠堂的白、鹿兩家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家史和錯綜復雜的恩怨情仇,其中涉及眾多歷史事件和人物,一直寫到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五十年代。對如此轟轟烈烈的歷史的敘述到了兩個多小時的電影里,就不得不簡化為屏幕上跳躍出來的幾個年份:1912,1920,1926,1929,1938。這種以年份推進敘事的手法也令一些在原著中十分連貫的情節變得碎片化,一些情節還被刪減或改動過。本文將結合電影里能與小說對應上的部分情節來分析電影在視覺傳播的過程中如何削弱原著里對儒家文化的表達,以及如何通過人物的行為反思儒家文化。
一、儒家文化與特定意象
電影是不同于小說的藝術形式,必須進行內容上的取舍,運用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象來構建畫面空間,并通過這些隱藏著豐富意蘊的意象來推動情節的發展。祠堂作為最常見的建筑,在傳統上供奉著一個大家族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在涉及婚喪嫁娶等大事時,家族里的人是要齊聚祠堂的。在各種文藝作品里,懲罰犯錯了的子孫的手段之一就是跪祠堂。在白鹿村,進祠堂拜列祖列宗是一項極其莊嚴、隆重的事,田小娥從始至終被白鹿村人戴著有色眼鏡看待,到死都沒能進祠堂。盡管小說改編成電影后毀譽參半,依然有學者盛贊電影的改編,其中重要的依據就是祠堂的出現總是伴隨著規則的構圖、陰暗的色彩與緩慢的鏡頭運動,這些影像語言營造出肅穆的氣氛,傳遞的是一種壓抑沉悶、不容反抗的秩序。只有在黑娃和小娥帶人砸毀祠堂時,畫面的構圖才是不規則的,鏡頭才是運動的。[1]
說到祠堂就不能不提及與祠堂聯系緊密的鄉約。《鄉約》的應運而生離不開儒家傳統的價值觀。電影開場,祠堂光線較為昏暗,一群男人在白嘉軒的帶領下整整齊齊地站成隊伍,吟讀著《鄉約》:“德業相勸,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伺父母,能教子弟,能守廉潔,能救患難,能決是非,能解斗爭,能與利除害……”《鄉約》原文比電影里的更長、更全面,包括但不限于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等部分,是由朱先生這個儒家文化的傳播者、白鹿原的文化精神領袖親自書寫的。有了《鄉約》的存在,白鹿村的風氣煥然一新,并樹起了“仁義白鹿村”這塊石碑。“仁”是孔子闡釋過的學說,“義”是孟子在“仁學”的理論基礎上補充的,白嘉軒既是白家的族長,又是白鹿原人的精神領袖,他的為人處世一直踐行“仁義”這個儒家思想里的核心價值觀。[2]不過較為遺憾的是,電影里略去了白嘉軒看《鄉約》刻字的場景,而是通過嬉皮笑臉的鹿子霖不停地叫嚷著“革命啦”的話語快進到他擔任鄉約后設宴慶祝的熱鬧場景,體現不出白鹿村的風氣在學習《鄉約》后的煥然一新,自然也就弱化了“仁義”這一道德準則在白鹿村里的重要地位。
小說里的祠堂經歷了從翻修到毀壞再到重建的完整的過程,到電影里卻是抗戰爆發后的1938年,日軍的飛機投擲下來的炸彈炸毀了祠堂,故事結束。影片由于篇幅所限刪減了原著中的大部分情節,缺少了小說里白嘉軒翻修祠堂、黑娃迎娶高秀才之女高玉鳳后回祠堂祭祖等較能體現儒家宗法和家族文化令黑娃“回家”的情節,給讀者一種虎頭蛇尾之感。到了最后,祠堂被飛機投下的炸彈炸毀,人們慌忙逃竄,不管是好的壞的都湮沒在硝煙里,一切事物仿佛都被消解殆盡了。
麥田這個意象在電影里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影片開場的視角就是俯瞰著的金黃色麥浪翻滾著的大地,顯示出一派豐收景象;到了1912年的時間點,天寒地凍之下的田野被皚皚白雪覆蓋,農民們扛著農具進城抗議,這就是原著中的“交農”事件;為了抗議縣政府對糧食的橫征暴斂,農民們點火焚燒平時賴以生存的麥田,在一片灼熱中手舞足蹈。到了后面的情節,郭舉人家的長工們在麥地里蹲成一排邊吃面邊聊天,也是一派富有鄉村生活氣息的景象。小說的表達比電影更出彩的地方在于,農民起事是由白嘉軒提議的。電影里刪掉了這個情節,只是表達了白嘉軒對在宴席上大吃大喝的擔憂,再讓鏡頭一轉,突然使得鹿三父子倆當了“交農”事件的出頭鳥,白嘉軒則隱于幕后。徐先生也贊同白嘉軒的提議,認為“對明君要尊,對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并且“君子取義舍生。既敢為止,亦敢當之”,在電影里則完全沒有徐先生的這個情節。“取義舍生”顯然出自《孟子·告子》的“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彰顯了徐先生身上那種舊時代文人特有的,在濃厚的“忠君”思想影響下也不忘明辨是非、舍生取義的品德。
二、儒家文化與女性命運
“白鹿原上,最堅實的基礎不是別的,而是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存留下來的那一套倫理規范,幾千年文化積淀形成的那一種文化心理,幾千年相沿流傳的那一番鄉俗風情。”[3]白鹿原上的女性,除了進城讀書最后參加革命被冤殺的白靈,其他人都是被娘家拋棄到夫家的傳宗接代的工具,都或多或少淪為儒家倫理道德規范的犧牲品,典型的有吳仙草、冷秋月、小翠以及那個鬧饑荒時逃回家聽到父母對話被嚇瘋了的女人。正如羅莎莉所言,“盡管儒家道德作為國家所推崇的正統思想,但整個社會對女性的殘酷壓迫一直存在于前近代中國。”[4]電影刪去了白嘉軒娶七個妻子只為傳宗接代、冷先生的大女兒嫁到鹿家后被冷落患上淫瘋病又被父親毒死、孝義媳婦借兔娃的種懷孕的重要情節,只著重強調了田小娥與黑娃的故事。田小娥在原著第八章的后半部分到第十九章登場,原著對小娥的悲慘境況做了更為詳細的描寫,比如給郭舉人泡棗,在特定日子里當郭舉人發泄性欲的工具,還需要為郭舉人和大太太做好一日三餐,還要倒尿盆,除了頂著個小妾的名頭,其余與下人無異。黑娃初次見到小娥的場景是:“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頭發,黑油油的頭發從肩頭攏到胸前,像一條閃光的黑緞。小女人舉著木梳從頭頂攏梳的時候,寬寬的衣袖就倒捋到肩胛處,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小娥為錯過飯點的黑娃端來饃飯,二人相處的時候不知不覺就產生了情難自禁的感覺,原著對這個過程里的動作和心理描寫極其詳盡。
有學者認為電影過度突出了小娥的形象,該形象與原著大相徑庭。小娥本該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悲苦的底層女性,卻被改編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蕩婦,使得她悲劇命運的根源失去了文化解讀的意義。[5]這一點筆者認為有待商榷,因為電影里的田小娥成為“蕩婦”是有一個漫長過程的。她初次登場的時候穿著一襲大紅色的衣服,梳著姨太太的發型,手拿團扇,在輕紗翻飛的轎子里悠閑端坐。長工們蹲在地里吃面,一個多嘴的長工當著黑娃的面編排小娥,結果黑娃把碗筷一砸,跟他打起來了。黑娃提出辭工,說別的長工說小娥閑話,小娥卻直截了當地說是為了看他。在這個場景里,黑娃的眼睛一直不敢抬頭看小娥,小娥臉上的神情變幻莫測,十分微妙。小說里的黑娃對正在刷鍋洗碗的小娥說的是“娥兒姐,我黑間來”,到電影里就完全倒置,衣著體面的小娥在臥室的鏡子前對黑娃說的是“那你黑里來吧,我門給你留著”。小娥在電影里被郭舉人下令夾手指并打得昏死過去,在小說里不僅被郭家休棄,還被娘家無情拋棄,只得跟著黑娃離開。電影為了使人物更為鮮活,增加了黑娃帶著小娥一起見白嘉軒的場面,黑娃明確表達了“我是給自己娶媳婦不是給我爸娶媳婦”的想法,白嘉軒卻說:“那也是娶你爸門下的媳婦”。這里的黑娃語氣堅定,明顯流露出追求戀愛和婚姻自由的自我意識,比小說里為難地說“我一丟開她,她肯定沒活路了”的時候更有主見。回到白鹿村里的小娥也在學著改變,很快就適應了黑娃的媳婦這個身份。電影增加的細節不少,比如她主動跟白嘉軒搭話說黑娃很尊敬他,放下身段學著給黑娃洗手做羹湯,為了黑娃的事拎著雞蛋去求見鹿子霖。但黑娃走后,她還是被找上門來訴苦的鹿子霖強暴。相比起小說里她對鹿子霖的半推半就、欲迎還拒,電影里的她在事后眼神發直,面上更多了幾分絕望。電影的確對小娥在郭舉人家的生活進行了美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娥命運的悲苦程度,但若脫離開白鹿村人對她與生俱來的敵意得出她就是個蕩婦的結論,則顯失公平。
耐人尋味的是,電影比小說有意增加了一個細節:修完鎮壓小娥鬼魂的塔后,監工悄悄告知白嘉軒,小娥腹中懷著孝文的骨肉,若是直接封基,就得把白家的血脈一起鎮壓到塔底下。白嘉軒拒絕了監工提出的替換骨灰的建議,“大義滅親”地說:“你騙得了人,騙不了鬼,我就是落個魚死網破,也不能叫鬼把勢得去。”然而,再結合電影前半部分白嘉軒夫婦給孝文定娃娃親以及小說里白嘉軒娶了七個妻子的情節,可以看出白嘉軒對傳宗接代一事看得極重,那他為何又要不顧一切地讓懷著白家血脈的小娥永世不得翻身呢?其實這里正顯示出了儒家宗法倫理的悖論:女性是傳宗接代的工具人,但不是什么女性都有資格給大家族延續血脈。所謂的“七出”之條只能束縛被大家族接納的女性,即使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家閨秀”,也一定是家世和身體都清白的女性。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孩子的出現勢必導致小娥身份的曖昧性,進而殃及儒家倫理規范的純潔性。[6]沒有孩子作為血緣紐帶,小娥也就無法真正被白鹿村接納,上不了族譜,享受不到香火的供奉,永遠都是個游離于傳統家族秩序以外的孤魂野鬼。
三、儒家文化與親子關系
在整部電影中,白嘉軒依然是那個維護封建倫理的大家長。小說里的白嘉軒有三兒一女,鹿子霖和鹿三都有兩個兒子,電影為了集中表現重要情節里的戲劇沖突,就只保留了白孝文、鹿兆鵬、黑娃,以至于白靈認黑娃為干爹的情節被置換到了孝文身上。原著中的白嘉軒對白靈十分嬌慣,允許她不纏足、去學堂,甚至白靈偷偷跑到城里和表姐們一起上學,他也無奈地同意了,卻依然要給她包辦與王家的婚姻。在白靈逃婚后,他就不允許家里人再提起她,“全當她死了”。然而當“革命烈士”的牌匾送到家里來的時候,垂垂老矣的他卻又深深懷疑“是我把娃咒死了哇”。若是白靈的戲份沒被刪除,觀眾應當可以看到一對在儒家父權的桎梏下掙扎著的父女在時代洪流面前針鋒相對的精彩故事。
電影開場沒多久,幼年時的白孝文、鹿兆鵬和黑娃躲在矮墻后面偷看家畜交配的場景,還淘氣地往圈里扔石頭和土塊。這個情節對應小說里的第五章,但又跟小說有較大的不同。小說里,黑娃應學堂徐先生的要求去砍柳樹股兒,找借口讓孝文和兆鵬跟著去,三個人因為看白興兒給黑驢和紅馬配種耽誤了很長時間。他們回到學堂里才知道柳木棍兒是拿來做板子的,被徐先生責罰。他們的家長來了,鹿子霖先抽了兆鵬耳光,鹿三踹了黑娃屁股,電影里挨打的卻只有孝文。白嘉軒當著兩個大人和另外兩個孩子的面讓白孝文趴在凳子上,不顧勸說拿著藤條往他屁股上打,一邊打一邊嘴里念念有詞:“我要他知道,啥叫個族規家法,啥叫個禮義廉恥,啥叫個仁義。”小說里的三人在看配種時并未做任何出格的事,耽誤到放學后才回來就被責罰。電影增加了扔石頭和土塊的細節,很容易使觀眾認為孝文被責打主要是因為小孩子淘氣,而不僅僅是因為看了“不該看的”東西。
黑娃和代表著家族勢力的白嘉軒、鹿三等人最大的沖突主要體現在對小娥的態度上。對鹿三父子倆的沖突和結局,小說和電影給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方式。電影里的鹿三更為勇猛,他捅傷了黑娃手下的小土匪,最后被黑娃的其他手下擒拿。鹿三爽快地承認就是他殺了小娥,一身黑衣黑褲黑帽的黑娃一直站在陰影里看不清神情。在鹿三的叫罵聲中,黑娃拿槍桿子打了白嘉軒的腰,說了句“你腰挺那么硬有啥用么,盡害人了”,又含淚把父親推倒在地,割下他的一縷頭發,以示恩斷義絕后離開了。小說里白嘉軒被打斷腰的情節發生在第十六章,到電影里被置換成了黑娃討公道時順便干的事。鹿三孤身一人住在小屋里,最后上吊自殺,此刻屋內屋外的光線形成了一明一暗的分裂感明顯的場景,外面的景色是亮的,屋內是暗的,顯得意味深長。小說里的黑娃撞見門口的站著的父親時還有些許慌亂,鹿三卻十分理直氣壯,認為自己并未做錯,而是在肅正家風,“龜孫!你甭叫我大。我早都認不得你了!”他并未像電影里那樣上吊自殺,還活了很長一段時間。黑娃在第三十章歸順了張團長,迎娶高玉鳳,回鄉祭祖,在祠堂里對著白嘉軒跪下,高呼“黑娃知罪了”。也是在這一章里,鹿三強撐著與白嘉軒喝完最后一頓酒,就去世了。小說顯示了儒家宗法文化的強大力量,黑娃追求與小娥的自由戀愛終是不得,最后還得向養育了他的家族低頭,娶了家族認可的女子,開始讀以前沒認真讀過也未必認可的圣賢書。盡管小說這種“黑娃回家”的結局也是一種極大的諷刺,筆者還是比較欣賞電影對鹿三結局的改編,因為這種劇情走向更符合同情小娥的觀眾的心理預期,無疑是對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的一種反思。小娥并未做過什么罪大惡極的事,白嘉軒堅持不讓小娥進祠堂,鹿三甚至下手殺了她,老一輩的人在拼命維護屬于舊時代的封建倫理秩序,到最后卻還是落得個家破人亡、父子反目的凄涼結局。
四、小結
《白鹿原》的電影改編并未體現出原著那浩大的史詩性,刪除了朱先生和白靈這兩個對表現主題思想起到關鍵作用的精華人物,另一些在儒家的家族宗法文化和倫理規范下飽受壓迫的女性形象也沒有出現,因此說這部電影是《田小娥傳》絲毫不為過。當然,電影增加的小娥死時懷著孕、黑娃割下鹿三的頭發以示斷絕父子關系的情節也較為巧妙,增加了故事的波折,豐富了人物的形象,迎合了觀眾的心理,流露出對真實的人性人情的追求和對壓抑人性的儒家封建倫理秩序的反思。
參考文獻:
[1]吳輝,別君紅.得,遠大于失——也談小說《白鹿原》的電影改編[J].當代電影,2013,(09):98-102.
[2]朱澤偉,周敏.白嘉軒:儒家文化的踐行者與反噬者[J].名作欣賞,2022,(02):69-71.
[3]陳忠實.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6.
[4](美)羅莎莉.儒學與女性[M].丁佳偉,曹秀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15.
[5]農莉芳.《白鹿原》儒家文化的跨界傳播——從原著到影視改編[J].廣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20,35(06):75-79.
[6]張高領.性別、階級與儒家倫理——再論《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形象[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04):53-60.
[7]陳忠實.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作者簡介:
李子惠,女,漢族,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兼談歐美游客儒家文化認知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