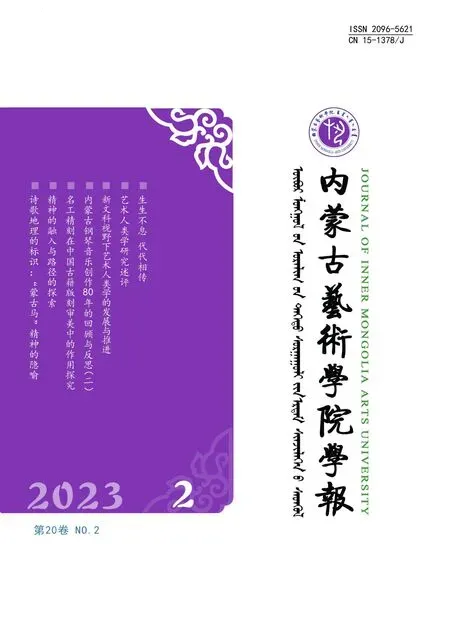民俗文化視閾下桐城歌的傳承發展研究
倪甜甜 楊 瑾
(1.安徽桐城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安徽 桐城 231400 2.浙江湖州師范學院 浙江湖州 313000)
“地域文化是以地域為基礎,以歷史為主線,在社會進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1](6)在對桐城歌的民俗文化進行探討前,我們應該先將目光放在桐城這片土地上,看看是怎樣的自然地理位置和人文歷史環境,造就了安徽省桐城地區特有的民俗文化特征,這是“桐城歌”誕生的物質文化基礎和精神文化底蘊。
桐城歷史悠久,因適宜種植油桐而得名。舊石器時代,就有先民生活于此。夏商周時期,桐城隸屬揚州。周置桐國,為楚附庸;敬王十二年(前508)夏,桐叛楚,屬吳;越滅吳后,桐屬越;周顯王三十六年(前333)楚滅越,桐國再度附楚。秦為舒縣,隸九江郡。西漢元封五年(前106)置極陽縣,漢武帝南巡至機陽,作《盛唐機陽之歌》。晉代, 陶淵明之曾祖陶侃曾任梑陽令。隋開皇十八年(598)改為同安縣。 唐至德二年(757),改同安縣為桐城縣,縣名一直沿用至今。1949 年2月分桐城縣為桐城、桐廬兩縣,桐廬縣轄區即今梑陽縣,1951 年改桐廬縣為湖東縣,1954 年桐廬縣治遷入梑陽鎮,1955 年,恢復漢時縣名——極陽縣。與機陽分治后的桐城縣,1979 年1 月,將南境楊橋區大部分地區劃入安慶市郊區(今宜秀區),2004 年5 月,又將羅嶺鎮劃歸安慶市宜秀區。[2](2)
正是由于桐城這樣獨特的地理位置——依山傍水,西臨大別山,南靠長江。境內有大別山余脈龍綿山,龍眠河蜿蜒而過。所謂“抵天柱而枕龍眠,牽大江而引樅川”……在這樣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中,誕生了許多具有桐城地方文化特色的代表性文人,如被稱為“桐城三祖”的姚鼐、方苞、劉大櫆。基于這些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積淀,桐城地區成為江淮一帶文化藝術的策源地,誕生了影響文壇的“桐城派”。基于豐厚、堅實的文化積淀和藝術氛圍,對該地民眾日常生活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當這些積淀的文化藝術因子深入到桐城當地民眾的生活中后,漸漸地,文化藝術的長久熏陶與普通民眾的現實生活逐漸融合,產生了文化底蘊極強的民俗藝術形式,“桐城歌”就應運而生了。地域文化優渥的客觀因素,給了桐城歌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而當地民眾的生活,又給了桐城歌實踐土壤與展示平臺。為此,其產生具有地域、歷史、文化等多元性特點。
一、桐城歌的民俗文化內涵
對明清民歌進行記載和傳承,可以讓我們從史料記載中探求其時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在那樣一個科技生活匱乏的年代,人們會將生活中的審美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的藝術載體里。檢索文獻史料,我們發現了不少對桐城歌相關內容的史料記載,它像一面鏡子,讓我們通過桐城歌曲調里演唱的歌詞,折射出明清之際的人們隱藏在生活中的勞動智慧、生活情趣。更能是我們站在“他者”的角度,從這些遺留的記錄中,勾勒出一幅幅其時當地民眾的日常禮俗、民間信仰、風土人情等社會生活畫卷。
(一)桐城歌中體現的民俗鄉情
桐城歌是流傳于桐城當地大街小巷里的民俗歌謠“……自明清以來,記載各種叫賣吆喝聲的文獻多了起來,既有文字的,也有繪畫的。俗話說賣什么吆喝什么,那些大街小巷的吆喝聲是可以分出腔調的,有高有低,有音有韻,猶如唱民間曲調一般。”[3](6)對于桐城歌的記載,明代的文豪馮夢龍,在其所編《明代雜曲集》一書《山歌》卷十中,專門用一卷,整理了24 首“桐城時興歌”。“‘山歌’并非大雅之物,而是帶著泥土氣息……”[4](97)而正是所謂的“泥土氣息”,使得它作為民間文化藝術的代表,將桐城歌作為民間層面和文學層面交融的一個載體,既受桐城派文學的影響,有桐城地域文化賦予它的儒雅之氣,又在桐城歌的歌詞語句中,體現出濃厚的桐城地區民眾生活的煙火氣息。如桐城歌中的《送郎》:
送郞送到五里墩,再送五里當一程。本待送郞三十里,鞋弓襪小步難行。斷腸人送斷腸人。
郎上孤舟妾倚樓,東風吹水送行舟。老天若有留郎意,一夜西風水倒流。五拜拈香三叩頭。[5](443)
這首“桐城歌”的歌詞中,生動地表現出當地青年男女送別時依依不舍的畫面場景:男子不得不踏上孤舟順江遠去,東風吹著小舟離去,但是女子不舍,希望一夜之間將東風變為西風,讓心愛之人的小舟能逆流而上,回到她的身邊。從這首詞中不難看出,桐城歌中處處體現著江南女子細膩的情懷,以及青年男女之間純真的情感。
在這曲歌詞中,也蘊涵著桐城這座小城的民俗鄉情:一幅女子江邊送郎的圖景展現在大家眼前。而且,在詞曲的最后,還提到“五拜拈香三叩頭”,既體現出女子對男子的送別不舍,又體現出盼歸之切,“五拜三叩首”作為明代的最高禮儀,將其用于桐城歌的詞曲創作中,可見明清文化的底蘊之深,將宮廷禮儀用在表達民間情愛時,也滲透出桐城文化的儒雅之感和含蓄之意。
(二)桐城歌中展現的人文形象
在桐城歌中無不體現著當地的人文風情,這些人文風情滲透在人們的衣食住行中。首當其沖,老百姓的關注度就是在“衣”上。明清時期,除了品官所穿的補服外,普通民眾對衣著的喜好可以從桐城歌中窺探一二,例如桐城歌《鞋》:
青緞鞋兒綠緞鑲,千針萬線結成雙。買尺白綾來鋪底,只要我郎來上幫。心肝莫說短和長。[5](441)
雖然在詞中青年女子“為悅己者容”的想法,溢于言表,但是可以從這首歌詞中看出明清時江南女子,對于青綠色的喜愛。綠色和青色,是明清之際民間百姓常用的服飾顏色,而對于品官甚至皇族,也對青綠色調,情有獨鐘,只是為了更顯威嚴并且和身份匹配,才大多采用了明度較低的青色。《大明會典》中,有“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邊緣以青。兩肩繡日月,前蟠圓龍一。后蟠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領與兩祛共龍文五九。衽同前后齊,共龍文四九。襯用深衣之制。黃色。袂圓祛方。下齊負繩及踝十二幅。素帶。朱口口口綠緣邊……”[6](18)之載,可見,在正史典籍中,更多的是記錄官員們的服飾裝飾、顏色以及體現的身份特征等,而出自民間并流傳民間的“桐城歌”,則真實地記錄了百姓的生活情趣及審美喜好,在補充正史不足的同時,也能讓我們感受、體味到其時更加真實的人間煙火氣。此外,“情歌”是桐城歌的重要組成內容,通過其柔美的曲調和押韻的旋律,我們能感受到每一首桐城情歌,都讓人體味到青年男女含蓄卻又真摯的感情。這些桐城歌中的情歌,有思念、有不舍、有擔心,如桐城歌《燈籠》:
一對燈籠街上行 ,一個昏來一個明。情哥莫學燈籠千個眼,只學蠟燭一條心。二人相交要長情。[5](440)
桐城歌中亦有通過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來比擬情懷,直抒胸臆的表達,并未過度隱喻,這類桐城歌是由民間歌謠的普適性造成的,當然,也和安徽桐城這一地域的開放、包容的社會氛圍有關聯,更體現出當地青年男女崇尚專一、長情的婚姻觀念。
(三)桐城歌中弘揚的傳統文化
在桐城歌中,還有不少體現當地傳統文化內容的歌。因為,人們對于文化的接受與傳播是基于審美習俗基礎之上的。所以,對于桐城歌在民間的傳唱度和后世的影響上來看,在民間層面,人們對“桐城歌”的詞曲韻律的接受度都是很高的。也正因為如此,而折射出桐城文學層面的知識積累與民間文化的切合度到達了完美的統一,他們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互為靈感。在馮夢龍編述的《明清民歌時調集》卷十“桐城時興歌”中,收錄有《新月》一首:
新生月兒似銀鉤,鉤住嫦娥在里頭。嫦娥也被鉤住了,不愁冤家不上鉤。欒圓日子在后頭。[5](441)
這首歌里面所說的“冤家”,字面意思本應是“仇人”,但是在民間生活中也經常被用作又愛又恨的復雜情感。在桐城歌中也用作第二層含義,表達男女之間的情愫。
有研究者引述宋人蔣津《葦航紀談》之《煙花記》云:
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系,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所謂冤家者一。兩情相系,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所謂冤家者二。長亭短亭,臨歧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所謂冤家者三。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所謂冤家者四。憐新棄舊,孤思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所謂冤家者五。一生一死,角易悲傷,抱恨成疾,迨與俱逝,所謂冤家者六。此語雖鄙俚,亦余之樂聞耳。[7]
此中對“冤家”的釋意可信,可見桐城歌押韻的五言歌詞中濃縮了民間文化的精髓,與桐城派文學作品中的精美辭藻起到了異曲同工的幷美之妙。而此中的“欒圓日子”則同“樂園日子”,即表達出對于美好愛情的向往,對于心上人的期盼之情。這些桐城歌的詞曲,在當地民間傳唱度很廣,不僅僅是青年男女對唱的情歌,很多老人和小孩也會時不時地哼唱。當地民眾這種無意識的傳唱,將濃厚的民間文化藝術形式,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傳承下來,從一個側面記錄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的需求,“桐城歌”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素帕》:
不寫情詞不寫詩,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顛倒看,橫也絲來豎也絲。這般心事有誰知。[5](437)
歌中提到的“素帕”,是寄托感情的物件,但卻有著濃厚的時代色彩與文化寓意。“素帕”作為女子的私人物品,具有定情信物的含義,一旦贈與他人,便是心許此人。這種寄情以物的愛情信仰,是桐城歌中所表達出的民間習俗和文化信仰的組成部分,更是對明清文化中“情”的解讀。
二、民俗文化視閾下桐城歌的傳承現狀
(一)傳統民俗文化與現代傳承機制的斷層
20 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曾經在名著《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提到“……‘歷史’并不主要指過去,而是出自這種過去的東西。”[8](23)因此,我們自從研究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初,就應當意識到這個問題,任何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都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說,簡單的依靠傳承人、媒體或者學術研究的努力,是無法達到“原生態”效果的。就像桐城歌,它的產生與流行和明清時代的社會歷史背景、桐城地域文化底蘊及桐城派文學強大的影響力密不可分。而桐城歌在當地的流行,也是基于一定的民俗背景下完成的。
這一歷史背景即是在明清時期,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思想交融,并且“……無論從史家自覺意識的增強,還是史學理論的豐富、史學方法的突破,乃至新的史書體例的創新,都把中國古代史學傳統推向了新的階段,也使史學出現了空前的繁榮。”[9](29)基于這樣的時代和學術背景,深受其熏陶的民間文化藝術自然會逐漸培養出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作品,桐城歌就是這典型的代表。研究者們尋找并對桐城歌傳承人進行口述史的研究,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探索路徑。但是在實地調查中,不少研究者發現,不管是口頭形式的傳承,還是文獻記錄的旁證,傳承人數量日漸減少,而留存資料卻沒有明顯增加,這是研究者必須要面對的一個現實。實際上,桐城歌作為民間藝術的載體,它既是一種過去式,又是一種現在時,比起將來,現在時距離我們更近一些。
觀之現如今的保護傳承方式,政府層面在推進傳承保護政策方面做出了積極努力,因為民間歌謠的形式,可謂全面展示了該地區過去的歷史文化及日常生活圖景,其史學價值、資料價值、民俗價值及藝術價值都很高。為了落實政府層面的傳承保護政策,民間層面則積極組織豐富的演出活動,如一年一度的“桐城文化節”,還有組織“桐城歌”中老年歌友會等,活動雖然精彩,但是從這些活動的參演人群中分析,我們也不難看出對于桐城歌喜愛的年齡階段多為中老年人,而更多的是將桐城歌作為興趣愛好進行表演,缺乏深層次的文化發掘。
于研究者而言,國內對于桐城歌的文獻史料記載,除去明代文人馮夢龍在《明清民歌時調集》中的卷十“山歌”中收錄了桐城歌24 首,另外則散見于《雜曲集》《萬花小曲》等文獻里,可發掘資源有限。而專門的研究著述,僅有周成強《明清桐城望族詩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論文著述較多的,是集中在討論桐城歌的音樂特色、傳承特點等方面。而在傳承人的研究記錄方面,桐城歌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上面登記的傳承人,僅有查月華一人。可見,在政府層面、民間傳承、學術研究以及傳承人之間并沒有搭建起行之有效的溝通橋梁,基本上是各自為政的。
(二)實踐表演與理論研究的割裂
地方民歌的形成,構建了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就像桐城歌,它的構成基于明清時期文人雅士匯集的民間文化因素而形成的民歌形式。桐城歌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不僅在特定時空中對群體審美進行了同化呈現,更重要的是它在當時起到了民俗文化認同的社會功能。而這些內容全都濃縮在桐城歌的韻律辭藻中,漸次流傳,綿延至今。現代的傳承基礎與依托,就是民眾對桐城歌中所表達出的地域審美文化的認可,這可以說是一種植根于草根的審美文化,與現代藝術形式如電影、流行歌曲及一些現代設計相比,桐城歌的流傳與表演是具有很明顯的時代印記和地方特色的。但令研究者感到欣慰的是,這種具有歷史感、深厚文化內涵及民俗意蘊的民間藝術形式,已經被一些學者注意到,并愿意深入研究其背后的社會、歷史、文化、藝術及審美價值。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傳承人,還是民間對桐城歌充滿熱愛的群體,他們的認知方式、傳承方式、表現形式,與理論研究者所呈現的研究成果之間,還是存在差距的。前者視其為日常生活的伴生物,后者視其為理論拓展的著眼點。這一認知上的差異,不僅存在于桐城歌民間傳承與理論研究的認知上,甚至可以推廣到整個傳統民歌的當代大眾的接受程度等問題上,即是如何協調“……將傳統民歌與當代大眾文化既‘共振’,又互為他者。彼此解構的文化模式,看作一種新型的大眾文化模式”[10](250)的問題。
對桐城歌地保護與傳承,更多的應該是強調整體性的保護,即更應該強調民族藝術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民俗環境。我們現在的“這種保護,盡管是一部分民俗文化形被保留了下來,并且可以作為講述歷史的感性憑證,但是當它們和人以其都脫離了原來的土地,脫離了往常人們對的交往關系,就只能作為像古代建筑,考古文物一樣的東西被人們觀賞,而不能作為他們用于情感交流的語言和手段……”[11](105)
三、桐城歌的創新發展思路
(一)突出地域文化特色
桐城地處安徽省西南部,其文化特質具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點“……安徽南部地處‘吳頭楚尾’,是吳國與楚國的交界地區;北部西接中原,北承齊魯,是吳文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齊魯文化的交匯區……”[12](3)兼并雜糅,是安徽文化的獨特之處,而“‘通變’成為安徽文化長期延續的重要內在因素……”[12](11)因此,在桐城歌的創新傳承思路里面,要將弘揚地域文化的特色做為一個重點的方向去傳承。在地域文化形成的過程中,會逐漸出現“趨同”的走勢,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與網絡技術的普及,全球文化同化趨勢明顯。大眾的審美情感也在發生變化,對于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桐城歌而言,自上而下的縱向保護力度還是很大的,無論從政策上還是從項目支持方面,都足以看到來自政府方面保護的決心。
因而,對于真正的落實者來說,是要去迎合大眾審美,還是去引導大眾審美,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當我們對桐城歌開展保護和傳承之際,其背后的桐城文化、安徽文化亦或更久遠的吳楚文化,都應該被一并提及并加以重視。沒有任何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割裂了其歷史發展脈絡而單獨存在的。因此,突出地域文化特點,是弘揚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文化傳承的基石。“文化傳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體內的社會成員中作接力棒似的縱向交接的過程。這個過程因受生存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約而具有強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終形成文化的傳承機制。”[13](2)將桐城歌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定位為地域文化傳承的實踐性藝術創作,可以實現對桐城歌更高維度的解讀,亦是對其民俗文化的穩定性和完整性所進行的多維共振。找到大眾審美接受的切入點,使傳承者和廣大民眾在文化認同上達成共識。這里所說的共識,不是表層的共識,而是整體社會層面對于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的共識,是無差別的共識,是通過桐城歌的藝術表現形式,對于地域文化進行的深度闡釋,以便達成更穩定的文化認同。
(二)推進桐城歌的數字化保護進程
“東方藝術善于將人與自然物作比,常用擬人化的藝術手段,將人的情感與自然物互滲,對生機勃勃的自然物加以贊美和欣賞……”[14](97)這一點,在桐城歌里也有所體現,因此要讓桐城歌在現代語境中得以傳承和發展不能割裂其時代性的表達。如何讓桐城歌符合現代社會民眾的審美觀念,從文化層面上與現在的受眾體互相連接,是我們要考慮的。
桐城歌的時代背景和文化習俗,在今天顯然是不可復制的,但是,我們可以借助多維度聯合的保護與傳承機制。即:將桐城歌的文本歌謠可視化呈現,利用數字技術將口頭傳承技藝進行轉化。這一數字技術,目前正在敦煌壁畫的保護中得以實施。在“數字敦煌資源庫平臺”中,記錄了敦煌莫高窟各個石窟中的壁畫,目前,該資源庫中收錄了30 多個洞窟的壁畫數字資源。因為工程量巨大且需要專業的數字技術加持,這一系統工程的數字采集工作還在繼續。通過攝影與計算機技術的結合,拍照洞窟中的二維壁畫,獲取二維信息,再結合三維建模技術,完整地還原洞窟中的壁畫,不僅進行了數據資源的保存,還可以使觀賞者身臨其境地領略敦煌壁畫的震撼之處。真正讓敦煌洞窟中的藝術實現了“永久保存,永續利用”的目的。
基于這一實踐案例,我們也可以對桐城歌進行數字化轉化,“文化遺產的數字化是指通過最新的數字圖像技術、虛擬現實技術、互聯網等技術的綜合運用,將文化遺產進行整理、 歸類, 并通過數字化技術記錄、 編輯、 管理和再現這些文物……”[15](35)將桐城歌的曲調、韻律進行全方位的數字化錄入,不僅僅是對桐城歌本身的錄制,而是對其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民俗人文語境進行全方位的立體呈現,進行“空間、文化、民俗、表現、載體”五位一體的記錄方式。我們可將重點放在永久保存上面,使得桐城歌的傳承方式除了外在表現的形式外,能進行多維度的文化詮釋與歷史解讀。
(三)結合多業態聯合發展
針對上文提及的實踐表演與理論研究割裂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進行轉向的互動思考。造成割裂的原因,是傳承人的表演與民間活動的呈現者大多是興趣愛好使然,就比如舉辦的“桐城歌”中老年歌友會、“桐城組歌”原創音樂會、慶“七一”文藝匯演等大型演出等,大多是由“桐城歌”作為主題展現形式而進行的民間活動,起到凝聚力量,振奮人心的功能即淺嘗輒止,并非是為了對桐城歌進行深入的理論文化研究;而高校的研究者,則是從學理層面進行文化分析及民俗背景的研究,實際上,目前真正能夠哼唱出原汁原味的“桐城歌”的學者屈指可數。上述這兩類人,本就沒有交集,這是造成“割裂”的問題所在。因此,我們需要打破行業壁壘,進行多領域、多層次的聯合機制,將“文化”與“生活”相結合,將傳唱性與專業性相結合,進行文化產業化轉變。這一轉變既要保留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性,也要滿足現代人們的娛樂屬性。這種轉變其實不易,如若轉變生硬,則容易被貼上文化資本化的標簽。我們可以將思路拓寬,例如和國產動漫相結合,近幾年,國漫的興起有目共睹,但是所用的素材都是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化解讀,再配合先進的電腦制作技術,從而獲得好評不斷。可見,對文化內容進行現代化的觀念轉變,并且結合多行業發展是具有可行性的。
桐城歌作為可以傳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結合院校、民間組織及政府間的聯合項目規劃,將其進行文化產業轉換,轉換包括對民間含義和民俗文化、曲調旋律的現代化解讀,可以通過視覺、聽覺記錄法進行呈現,“對遺產本身、遺產記錄及遺產與視頻記錄管理而言是一種明智的、負責任的制作方式”,[16](13)這里面研究人員、傳承人、業余愛好者、當地居民要進行緊密結合、共同探討,盡量使檔案資料全面。并且,進行文化產業化轉變的同時,減少觀賞者對民俗藝術的“同理性”約束,民俗文化是基于具體時空之上討論的,因此,減少“同理性”約束,增強“知識性”普及,使之達到“雅俗共賞”的境界,可以讓更多人去主動了解傳統文化,民俗風情。
結 語
桐城歌對于我們來說,是極具地域特色和藝術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的傳承在一開始是沒有物質形態的,全靠民眾的口口相傳。明代的大文豪馮夢龍以“山歌”的名義對桐城歌的歌詞進行了記載,才能讓我們有了更多有形的參照物。對我們而言,它依然是連接現在和過去的線索,桐城歌中展現的江南民眾的衣、食、住、行,包括愛情觀念和民俗文化,都是我們還原當時民間生活的有力佐證,更是史學、文學研究者可供參照的文獻資料。對于桐城歌的傳承與保護,更應該結合現代的科技,將依托于傳承人的活態傳承因素,轉變為依托于科技的物質形態傳承,這樣能有效地克服并擺脫傳承人短缺、傳承人老齡化,甚至無傳承人的困境。通過建立更科學、更高效的保護機制,在現有成果保護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更多維的智力支持,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民歌傳承和保護,提供可供借鑒的實踐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