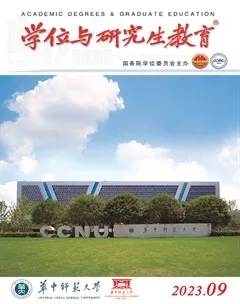“大學外”學位授予的日本模式——基于學位授予機構的歷史考察
朱文富 孫 雨
比較與借鑒
“大學外”學位授予的日本模式——基于學位授予機構的歷史考察
朱文富 孫 雨
在“第三次教育改革”背景下,日本于20世紀90年代初依托新創(chuàng)立的獨立于大學外的學位授予機構,為無法或不適宜通過大學獲取學位與繼續(xù)升學的多類群體成功探索并建立了獨具特色的“省廳大學校學位制度”和“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并以后者為發(fā)展重心。經(jīng)過30年的實踐與優(yōu)化,相關制度對日本終身學習體系、高等教育、職業(yè)教育及學位制度的整體發(fā)展均產(chǎn)生了積極作用,同時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局限性。這些方面既基于日本實際帶有特殊性,亦基于此類制度本身而帶有普遍性,而后者也為我國的相關探索提供了參考。
日本;學位制度;學位授予機構;終身學習;高等職業(yè)教育
學位授予機構(學位授與機構,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s)由日本文部省創(chuàng)立于1991年7月,是日本目前除高等學校外唯一具有學位授予權的機構。該機構歷經(jīng)學位授予機構時期(1991—1999年)、大學評價與學位授予機構時期(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University Evaluation,2000—2015年)①2004年完成獨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和當前的大學改革支援與學位授予機構時期(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的發(fā)展,至今已擁有學位授予、高等教育評價、教育調(diào)研、情報業(yè)務、大學設施費貸付等多項職能,是日本當前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促進機構之一。學位授予為其原始職能和主要職能。以此建立的學位制度使多類大學外求學者有了獲取學位與繼續(xù)升學的新通路,而其本身也成為日本學位制度體系中重要且獨具特色的組成部分。
一、關于設立學位授予機構的籌議
1984—1987年,在國內(nèi)外形勢變動下,作為首相咨詢機構的臨時教育審議會(簡稱“臨教審”)本著兼顧國家長遠利益和國民教育實際的出發(fā)點,用全國性調(diào)研的方式相繼完成了四次咨詢報告,以此作為推進“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基本方案。而關于“學位授予機構”的設立問題就是臨教審研討的重要項目。在1985年遞交的首次咨詢報告中,臨教審明確提出將“重視個性”作為本次改革的基本原則,并同時提出“擴大升學機會”和“向終身學習體系過渡”的改革原則[1]9-13,為學位授予機構設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1986年,臨教審在遞交的第二次咨詢報告中重點圍繞“向終身學習體系過渡”的原則展開闡述。臨教審指出,對于在人生初期未能獲得所希望的學歷和職業(yè)地位的各類人群,應為其創(chuàng)造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繼續(xù)學習的機會,因此要進一步沿著入學資格自由化、彈性化的方向,進行教育體制靈活化問題的深入探究[1]70-74。本著這一路徑,臨教審研究指出應建立“學分累積制度”及大學外高等教育機構與大學之間的“學分互換制度”[2],同時為了對那些通過學分累積已達大學畢業(yè)水準的學生進行評估認定和學位授予,應研究設立專門的學位授予機構負責相關事宜[1]116-117。這是關于學位授予機構設立問題的首次公開提出。
1988年起,在文部大臣的委托下,大學審議會和關于學位授予機構的創(chuàng)設調(diào)查委員會,相繼對學位授予機構及其學位制度的創(chuàng)設問題進行了研討,并在1991年2月分別遞交了《關于學位授予機構的創(chuàng)設》和《關于學位授予機構構想的概要》兩份咨詢報告,標志著學位授予機構正式進入籌建階段。同期,大學審議會還發(fā)布了《關于高等專門學校教育的改善》報告,建議高等專門學校應在承繼原有特性的基礎上效法短期大學設立專攻科,并由學位授予機構負責其畢業(yè)生的學位工作,此提議被政府采納[2]。
至于籌建學位授予機構的動因,首先即是新改革形勢下大學外學位授予方式空缺。在20世紀80年代,大學仍是日本唯一具有學位授予權的機構,盡管學士尚以“稱號”對待,但實際發(fā)揮著學位的作用,且其獲得者在就業(yè)和繼續(xù)升學上確有便利性。與此相對,各短期高等教育機構的畢業(yè)生卻在本體系內(nèi)存在無學位和升學困難問題。盡管短期大學自1958年以來就設有相當于本科層次的專攻科,但其畢業(yè)生既無學位亦無升學上的制度保障[2]。在當時,這些畢業(yè)生主要通過尚未成熟的編入學制度進入大學繼續(xù)修業(yè)以獲取稱號、學位和升學機會。同時,部分省廳大學校的實際辦學水準已達到甚至超過同級大學或研究生院的平均水準,但由于非《學校教育法》與文部省管轄范疇,致使畢業(yè)生一直與學位無緣。另外,還有大量社會人員需要學位卻難以通過現(xiàn)有方式獲得學位。總之,在當時有大量群體無法或不適宜通過大學獲取學位和繼續(xù)升學,而其中又有相當一部分人有相應的需求與能力。這明顯與20世紀80年代后日本高等教育的總體改革和發(fā)展趨勢相悖,嚴重阻礙了日本終身學習社會的構建。其次是受英國全國學位授予委員會(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1964—1992年)的影響,該團體的主要任務是審批大學外各高等教育機構開設的教育課程,對相關學校不同性質(zhì)的畢業(yè)者授予不同專業(yè)領域的各層級學位,其在推動英國大學外高等教育系統(tǒng)發(fā)展和促進繼續(xù)教育普及化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3]。
二、學位授予機構及其學位制度的建立與發(fā)展
作為日本本輪學位制度改革和數(shù)年來相關研討的結果,1991年7月修訂后的《國立學校設置法》《學校教育法》和《學位規(guī)則》(文部省令)正式施行,學位授予機構正式成立,“學士”也正式成為法定學位。
(一)圍繞“學位授予”的法定業(yè)務與組織運營
根據(jù)《國立學校設置法》,學位授予機構圍繞學位授予開展的基本業(yè)務主要有三項:一是根據(jù)《學校教育法》授予學位;二是對學位授予所需學習成果的評價進行調(diào)查研究;三是收集、整理和提供有關大學等各種學習機會的情報[4]9。根據(jù)《學校教育法》,學位授予機構應對兩大類群體授予相應學位:其一是從短期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畢業(yè)的人或與其水平相當?shù)娜耍诖髮W或在文部大臣指定的學習中繼續(xù)累積一定學分,并被認定為具有同于或高于大學畢業(yè)生的學力時,可被授予學士學位;其二是開展類學校教育且水準相當于大學或研究生院的教育設施②目前為止僅指部分“省廳大學校”。之所以稱其為“教育設施”,是因為省廳大學校是由文部省外的各中央省(廳)根據(jù)本系統(tǒng)的業(yè)務與職員需要以及省(廳)法令,自行開設與負責的實施類似學校教育的高等職業(yè)教育培訓機構,它不屬于《學校教育法》的范疇,也沒有統(tǒng)一規(guī)范的設置與辦學標準。由此,不同省廳大學校教育課程在命名和實施模式上也呈現(xiàn)顯著的多元性。的教育課程的畢業(yè)生,可相應地被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4]9。同期修訂的《學位規(guī)則》對第一類群體及其學位獲取方式作了進一步規(guī)定。首先,該群體即學位授予機構后來規(guī)定的“基礎資格者”(見表1)。其次,該群體可通過三類方式(見表1)再修業(yè),并在通過學位授予機構審查后獲取學士學位。上述方式所獲“學分”法律效力均等同于普通大學修業(yè)所獲學分。
在組織運營上,學位授予機構各時期均有專門負責學位工作的調(diào)研和管理部門,同時會同各國、公、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專家和相關人士組建了審查委員會及其下設的各專業(yè)領域的專門委員會,來協(xié)助機構共同開展有關學位授予的各種審查與認定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相關工作的專業(yè)性、效率性、廣泛性、中立性與公正性。
(二)學校外教育設施修業(yè)者的三級學位獲取——省廳大學校學位制度的建立與發(fā)展
1991年7月,在審查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學位授予機構制定了《大學或研究生院同等教育課程的認定規(guī)程》和《授予學位的規(guī)程》。前者規(guī)定了省廳大學校教育課程的認定條件,重點是對課程本身、授業(yè)教師及設備設施的要求。后者則對學位申請和審查方法進行了規(guī)定,即所有學位申請者均需出具校長頒發(fā)的學分完成和結業(yè)證明,并接受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其中碩士、博士學位申請者還需提交學位論文并接受3名以上專門委員的審查測試。兩項規(guī)程發(fā)布后,審查委員會隨即組建了各專業(yè)領域的專門委員會著手具體審查工作。截至1991年底,學位授予機構完成了對首批省廳大學校教育課程的認定工作。1992年3月,該機構進行了首次規(guī)模性學位授予[4]14。認定通過的教育課程應定期接受針對實施狀況的審查,且在有較大變更時需重新接受審查。
省廳大學校學位制度建立至今未有明顯變動,這一是因為它是仿照傳統(tǒng)大學學位制度建立的;二是因為只有部分確實具備類似大學或研究生院辦學模式和水準的教育課程才能獲得認定,且穩(wěn)定性較高。截至2022年4月,共有8所大學校的9個本科層次課程、4所大學校的6個碩士層次課程以及3所大學校的4個博士層次課程通過認定。累計有29884人獲得了學士學位、3066人獲得了碩士學位、692人獲得了博士學位[5]42-45,合占學位授予機構歷史學位授予總數(shù)的35%。
省廳大學校學位制度是日本依托學位授予機構,對文部省管轄外的類學校的高水平職業(yè)教育培訓機構的學位問題進行的一次突破性探索。此制度一方面強化了省廳大學校在日本社會及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存在度,另一方面也為其辦學提供了標準。30年來該制度未對日本大學的三級學位體制構成挑戰(zhàn),一是各級教育課程與學位審查要求并不次于同級大學或研究生院;二是涉及的大學校、專業(yè)領域和學位獲取者有限,且獲取者往往從事特殊領域工作或在特定政府部門就業(yè),并不與大學學位獲取者在就業(yè)上產(chǎn)生明顯沖突;三是省廳大學校的特殊性,使其學位制度本身很難也不必與大學學位制度置于同一范疇進行比照。
(三)“新學士之路”的開辟——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的建立與發(fā)展
1.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的建立與實施
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自學位授予機構設想提出以來即是相關工作的重心。基于此,學位授予機構明確了“短期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專攻科認定”與“學位授予程序”兩項中心任務。前者是由于不同學校的專攻科辦學良莠不齊,必須先認定相當于大學本科教育水準且適用此制度的專攻科。為此,審查委員會首先制定了《關于短期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專攻科認定的規(guī)程》(1991年12月施行),并隨即組建了負責各專業(yè)領域專攻科審查工作的各“特別專門委員會”,其審查要點主要圍繞課程和師資水準進行。審查認定需由相關學校自行向機構申請。1992年4月,首批22所學校的34個專攻科通過學位授予機構認定[4]16。這種專攻科即被稱為“認定專攻科”,以區(qū)別其他專攻科[2]。此后,專攻科認定規(guī)則未有大的變化,但認定專攻科非終身制,需定期接受再審查[6]26。
在學位授予方面,審查委員會制定了《授予學士學位的規(guī)程》(1992年1月施行),對學位授予的必要條件、申請與審查事宜及專業(yè)領域進行了規(guī)定。其中,必要條件包含四部分:①申請者要滿足基礎資格(見表1),即適用該制度的已有資質(zhì)。基礎資格者身份沒有明確的年齡、應屆及工作限制。②學分要求達標(見表1)。此前已獲學分為基礎資格學分,再獲學分為累積學分,二者合計為申請學位時的學分。合計一般要在124學分以上,這與日本一般的4年制大學是相當?shù)摹"弁瓿伞皩W修成果”,即與所修專業(yè)中特定課題有關的研究總結報告,類似大學的學位論文或畢業(yè)設計,藝術類等領域可選擇其他呈現(xiàn)方式。④通過由學位授予機構主持的考試,內(nèi)容一般與提交的學修成果相關,通常以小論文或面試形式進行。后二者的目的是檢驗申請者是否真正達到獲得該專業(yè)領域學位的水平。審查通過后由學位授予機構授予學位證。
規(guī)程施行后審查委員會隨即組建了負責各專業(yè)領域學位審查工作的各“學士專門委員會”③1994年,學士專門委員會、特別專門委員會及負責省廳大學校相關工作的專門委員會,按類似專業(yè)領域合并為同一專門委員會的原則進行了重組。。1992年4月,學位授予機構發(fā)布《新學士之路》手冊,向日本全國推介新型學位制度。9月,審查委員會制定了《關于學士學位授予所需學分的審查要點》,對學分審查要求按專業(yè)課學分、專業(yè)相關課程學分和其他學分進行了細化,并再次發(fā)布了補充后的《新學士之路》,而后每年更新一版。其中,為便于學位授予工作與社會認知,專業(yè)領域的劃定與大學基本一致。1993年1月,學位授予機構對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申請者進行了首次學位授予[4]20。5月,學位授予機構為方便認定專攻科畢業(yè)生能順利升入研究生院,專門設立了預期申請制度④滿足修業(yè)要求且即將畢業(yè)的學生可事先向該機構申請學位。而后,此類申請稱為“預期申請”,其余申請稱為“一般申請”。,并于10月受理了首次預期申請[4]25。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至此基本確立。
綜上,學位授予機構是以申請者在整個高等教育階段的系統(tǒng)性修業(yè)情況為審查對象,而非單純關注學修成果和考試等一時的學力反饋,此點上,學位授予機構和大學所授學位在實質(zhì)上是一致的[7]。更進一步講,除授予單位不同外,兩種學位在學位本身的學術屬性、教育屬性和管理屬性[8]等方面均沒有實質(zhì)差異,且授予標準相當、程序規(guī)范,由此前者被定性為學位是具備合理性的。而其延展出的非大學性與職業(yè)取向也并不觸及學位本質(zhì)。換言之,學位授予機構所授學位本身在學理上不會對傳統(tǒng)大學學位構成挑戰(zhàn)。
2.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的后續(xù)優(yōu)化
其一,起初該學位制度并不適用短期高等教育機構中體量最大的專門學校,這與其非“一條校”、非升學教育的初始定位及辦學質(zhì)量良莠不齊相關。鑒于市場與畢業(yè)生日益增進的需求,也為了終身學習事業(yè)與專門學校的向好發(fā)展,大學審議會于1997年提議為滿足一定條件的專門學校畢業(yè)生提供編入大學的機會,同時將其納入基礎資格者。1998年,隨著相關法令和規(guī)程被修正,自1999年起專門學校畢業(yè)生也可通過學位授予機構獲取學位。
其二,根據(jù)相關規(guī)程,申請者所修學分中至少要有16學分(約1學期)是在大學獲得,且其中8學分需與所修專業(yè)相關[4]27。此規(guī)定顯然是針對認定專攻科修讀者。其在實施之初就爭論頻仍[4]36,且學位授予機構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認定專攻科修讀者大都認為這一規(guī)定是不必要的,也并未因此而顯著受益[9]。事實上,該規(guī)定一是影響了認定專攻科本身學習的體系化與連貫性;二是認定專攻科的辦學水準并不亞于多數(shù)大學;三是多數(shù)大學的辦學理念和方式與認定專攻科并不契合,這在高等專門學校專攻科上尤為明顯。2001年,學位授予機構在大學審議會建議下廢止了相關規(guī)定。自此,認定專攻科學位制度與大學實現(xiàn)了分離。
其三,2011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從更準確掌握學生能力和進一步豐富修業(yè)者主體性的視角出發(fā),建議改進高等專門學校認定專攻科修讀者的學位審查與獲取機制。對此,學位授予機構在與文部科學省及相關學校反復協(xié)商后,決定優(yōu)化學位申請制度,于2015年實施了同時面向短期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認定專攻科畢業(yè)生的“特例制度”。具言之,學位授予機構將具有一定辦學業(yè)績的認定專攻科進一步認定為“特例適用專攻科”。其學分修讀要求與以往不甚相同,且其畢業(yè)生申請學位時也無須遞交前述學修成果及通過相應考試,而是滿足兩項新要求:一是按照學位授予機構事先認可的“認定科目表”⑤相關學校基于基礎資格階段與專攻科階段專業(yè)課程的同體系而形成的課程與學分系統(tǒng)。兩階段整體應相當于貫通的4年本科教育,前階段畢業(yè)后一般直接進入后階段,且后階段的學分需完全在特例適用專攻科中修完。完成學分修取;二是完成對基礎資格與專攻科兩階段學習進行總結的“學修總結科目”⑥在通過學位授予機構審查后,作為專業(yè)必修課開設于最后一學年,由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的專職教師予以指導,并由開設學校負責相關成績評定工作。,并據(jù)此自主設定與專業(yè)相關的課題進行探究。作為結果,需按學位授予機構規(guī)定,完成“科目修完計劃書”,并將探究成果轉化為論文或某種形式的作品后撰寫“成果要旨”,經(jīng)所在學校成績評定后提交學位授予機構,審查合格后即可獲取學士學位。此后,相關申請被定為“特例申請”。實施當年,特例申請者即占到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總申請數(shù)的56.4%,其中49.6%來自高等專門學校專攻科。而所有特例申請者中,87.6%的專業(yè)類別為工學[7]。2021年,短期大學認定專攻科特例適用率為32.3%,而高等專門學校則達100%[10]56。很明顯,以培養(yǎng)實踐型工程技術人才為主的高等專門學校及其畢業(yè)生為此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特例制度”的建立進一步提升了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的合理性,并由此提升了適用群體的修業(yè)成效與適用學校的辦學成效,而它也被學位授予機構視為學位授予事業(yè)建立以來之最大改革[7]。
截至2022年4月,獲取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的人數(shù)累計達61255人,占學位授予機構歷史學位授予總數(shù)的65%[5]42-44。其中,基礎資格階段為短期大學的有22034人,為高等專門學校的有31835人,為專門學校的有6019人,為大學的有1311人,為剩余各類的僅有56人[5]42-44。顯然,短期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的畢業(yè)生為基礎資格者主體,這也與初始制度設計相契合。同時,認定專攻科是兩類基礎資格者攻讀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的主要方式,二者分別有17583人和31779人是通過認定專攻科方式獲取的學位,合占兩類基礎資格者通過學位授予機構獲取學位總數(shù)的約92%[5]42-44。
三、“大學外”學位授予制度的積極意義與局限性
在30年的探索歷程中,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成為日本“大學外”學位授予制度的主要模式。這種制度給日本社會與教育發(fā)展帶來了積極意義,同時也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局限性。這不僅基于日本實際而言,亦基于制度本身而言。
積極意義上,其一,該制度為無法或不適宜通過大學獲取學位的各類應往屆群體開辟了(區(qū)別于傳統(tǒng)大學模式的)多樣化學習、獲取學位與繼續(xù)升學的新路徑,且可與工作、生活并行不悖,此為該制度之根本價值。而作為基礎資格者主體的短期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畢業(yè)生的家庭出身與經(jīng)濟條件普遍不及大學生[11],故新路徑帶來的機遇本身也具有一定社會意義。其二,居于該制度核心的認定專攻科學位制度是日本職業(yè)教育學位制度真正意義上的發(fā)端[12]。在2017年學士(專門職)學位制度創(chuàng)立前,它是在日本正規(guī)職業(yè)教育體系中獲取學士學位的唯一路徑[12]。其三,該制度鞏固了20世紀90年代后面臨危機的短期大學及其專攻科的制度存續(xù)價值,穩(wěn)固了新興高等專門學校專攻科的本科層級,并為二者提供了實際意義上的發(fā)展標準。其四,從學位獲取者反饋上看,無論是應屆生還是在職者,通過攻讀學位所帶來的個人提升與獲取學位本身均對其在就業(yè)、工作、升學、資格考試、成就感與自我實現(xiàn)等方面產(chǎn)生了有益影響。各類人群對此類學位的總體滿意度(10分制)常年維持在8分左右[7]。而更值得關注的是半數(shù)以上的人在獲取學位后還會以各種形式終身學習[13]。顯然,30年來該制度確實促進了日本在終身學習、高等教育、職業(yè)教育及學位方面的制度建設,具有一定的歷史突破意義及社會意義,也因此它在日本被譽為“新學士之路”。
經(jīng)過30年發(fā)展,該制度的局限性也日益凸顯。其一,受益專業(yè)領域過于局限。截至2022年,該制度涉及的專業(yè)領域共29個,但教育學(7%)、看護學(14%)、保健衛(wèi)生學(8%)、營養(yǎng)學(4.5%)、工學(52%)和藝術學(8.5%)等6個專業(yè)領域的學位獲取者就占據(jù)了總數(shù)的94%[5]42-44。其二,學位授予總體規(guī)模與數(shù)目龐大的基礎資格群體形成了鮮明對比,實際只有很少比例的基礎資格者能通過該方式獲取學位。從2013年起,此類學位年獲取人數(shù)在歷經(jīng)20年的增長后,開始穩(wěn)定在2500人左右,至今無明顯上升趨勢[5]42。其三,同專業(yè)修業(yè)者在不同機構的不同修業(yè)歷程下卻獲得相同學位,這一定意義上有悖公平性。其四,整體上,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相比大學學士學位在社會認可度上仍存在一定差距[7]。這一點在學位授予機構的歷次調(diào)查中也得到印證。其五,該制度的“靈活”導致一些學生在學習的體系化與連貫性上存在問題,以致這些學生無法真正獲得相當于大學畢業(yè)生的學歷,進而造成其學力水準無法得到切實保障,該制度的合理性受到一定質(zhì)疑。這主要體現(xiàn)于通過科目履修生方式修讀和脫離基礎資格階段較長的學生。其六,長期以來,基礎資格者都只能通過表1所列的三種方式獲取學分,而其他可獲取大學學分的諸多學習方式至今仍未得到學位授予機構承認[14]。由此,該制度本身的創(chuàng)立雖是一種突破,但其后續(xù)發(fā)展中的整體性突破卻是有限的且整體態(tài)勢是趨緩的。
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之所以存在上述局限性,從日本教育實際與該制度本身來看,可作以下五方面闡釋。
其一,學位授予機構本身的“有限性”。盡管有各類高校及各界的支持,但面對全國性學位授予工程時,單一機構本身的有限規(guī)模與國家層級的唯一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位制度本身的擴充與學位申請者的數(shù)目。
其二,制度的“依附性”。學位授予機構自身不具辦學功能且與教學部門完全分離,因此學位授予規(guī)模和受益專業(yè)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關聯(lián)教育機構的制度發(fā)展態(tài)勢、主要辦學性質(zhì)與專業(yè)側重、整體辦學實力、接納該制度的主觀意愿,以及制度適用群體的總基數(shù)及其意愿等外部要素決定的。而這些均是學位授予機構自身無法直接控制的因素。事實上,近些年學位授予人數(shù)趨穩(wěn)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少子化背景與新經(jīng)濟形勢下,短期大學數(shù)目與就讀人數(shù)的驟減,大學入學率的攀升,以及專門學校轉型發(fā)展[2]使其就讀者對修取大學學分興趣的下降。盡管據(jù)學位授予機構研判,由于老齡化與人均壽命延長,今后出于終身學習考慮的社會申請者有望增加,并由此影響申請者結構[10]57,但目前這種態(tài)勢尚不顯著。
其三,“包容性”帶來的必然格局。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是個性化、多樣化、開放化、彈性化、擴大升學機會、向終身學習體系過渡等“第三次教育改革”原則下的產(chǎn)物。因此,其應然也必然會關聯(lián)廣泛且多樣的高等教育機構或相關教育課程。然而,盡管學位授予機構會對其辦學水平進行是否相當于大學本科水平的嚴格審查,但根本上卻無法解決認定后其間依然存在的水平差異,由此也就無法解決同機構所授同學位背后的公平性問題。況且,科目履修生課程還由開設大學自行負責,本就不受學位授予機構的管控,故其間的差異更是難以消釋。
其四,兩種學位間的“不平等”難以消弭。首先,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的發(fā)展遠滯后于基于大學本身而建立的傳統(tǒng)學位制度,且前者在制度設計和操作方面均需參照后者,以此造成前者即便有法律和質(zhì)量的即時保障,但完善度、與相關教育機構的適配度以及社會認可度可能長期都難以企及后者。簡言之,前者存在顯著的后發(fā)劣勢。其次,單個機構的有限性使其在學位授予規(guī)模上根本無法企及大學群體的數(shù)量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兩類學位同等的社會認可度和影響力,并進一步制約了前者的發(fā)展?jié)摿ΑT俅危L期以來在日本獲取學士等同于大學本科畢業(yè),而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最先打破了這一觀念,同時也造成這種學位在社會價值評估中的困境。最后,這種“不平等”及其存在的長期性,根源于兩種學位背后的生源與學位差異。就生源而言,歷年來獲取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的基礎資格群體,大都為日本各短期高等教育機構中出于個人原因而無法通過大學獲取學位的應往屆生,而少部分來自大學的申請者也多為肄業(yè)生,其平均學力水準相對低于在讀大學生。就學歷而言,基礎資格階段的學歷加之學位授予機構進一步規(guī)定的本科學歷,無論基于哪種判斷,都不可能等同于常規(guī)的大學本科學歷。而對認定專攻科教育而言,其也不應背離特有屬性和價值而趨同于大學教育。以此來看,在傳統(tǒng)學歷主義影響下的日本社會,作為修業(yè)結果的兩種學位于社會認知上的“不平等”也就毋庸贅述了。此外,應當認識到這種“不平等”存在的前提是“新學士之路”的開辟,因此這種“不平等”并不與學位授予機構學位獲取者對此類學位的滿意情況相沖突。
其五,一定時期內(nèi),學分累積型學士學位制度的細則開發(fā)與實施存在客觀限制。據(jù)日本政府和一些學者的原初設想,落實后的此制度應遠比現(xiàn)在的基礎資格類別、學習形式、學分累積規(guī)則與考核方式等豐富且靈活許多。以學習形式為例,達到高等教育水準且可量化為大學學分的校內(nèi)外學習均可納入該制度,且依原初制度設計與相關法令,一些學習形式本就可歸為“文部(科學)大臣另行指定的學習”。若從終身學習社會的構建及充分發(fā)揮該制度的特有優(yōu)勢上看,相關意見確實具備一定合理性,且能使更多群體受益。然而,從日本教育實際、審查機制與審查成本上看,相關設想在一定時期內(nèi)并不具備落實的可行性。事實上,該制度若過于靈活豐富,本就會加重修業(yè)的非正規(guī)化、非體系化、非連貫性、非組織化與“投機”問題,進而造成學位獲取者學力水準的穩(wěn)定性無法保障、對學位基本價值的背離與學位制度本身合理性的弱化,并由此引發(fā)社會質(zhì)疑,故在靈活性問題上的利弊是相對的與需要結合實際折中的。換言之,在較大程度上脫離相對正規(guī)化、固定化和體系化的學校修業(yè),此制度于學理上、社會認知上和實際操作上均很難成立。況且,該制度在靈活性上已然是一個極大進步,且業(yè)已由此帶來了種種問題與質(zhì)疑。由此,為保障該制度的合理存在與順利實施,一定時期內(nèi)只能采用相對穩(wěn)定且經(jīng)檢驗后具備充分可行性與合理性的學習形式、適配規(guī)則與考核方式,而非在短期內(nèi)為實現(xiàn)終身學習社會,一味追求個性化、多樣化和開放化。畢竟構建終身學習體系是伴隨社會整體進步而具有長期性的,而傳統(tǒng)意義上學位頒授也是嚴肅而正式的。不過隨著人工智能和數(shù)字化技術的進展與學位授予機構的逐步引入[10]57-58,該制度在細則開發(fā)與實施上的限制可能會有所突破,而由此引發(fā)的學位理論的進一步延伸與社會認知上的改觀也可能會逐步實現(xiàn)。
綜上,盡管這種特別的學位制度尚待完善且存在固有局限,但從構建終身學習體系視角下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學位獲取者的實際受益上看,這確是一次成功的探索與突破。不僅是就日本而言,其作為一種經(jīng)驗與教訓亦是值得我國相關人員結合實際去斟酌的。畢竟當前正致力于終身學習體系構建的我國,也存在大量無法或不適宜通過大學獲取學位和繼續(xù)深造的各類優(yōu)質(zhì)在讀生及具有一定學力的社會人士,但切忌削足適履、曲為比附。
[1] 國家教委情報研究室. 今日日本教育改革[M]. 北京: 北京工業(yè)大學出版社, 1988.
[2] 朱文富, 孫雨. 日本本科層次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路徑與經(jīng)驗[J].外國教育研究, 2023(2): 101-115.
[3] 陳樹清. 英國學位授予委員會(CAN)評介[J]. 外國教育研究, 1985(3): 20-24.
[4] 齋藤安俊, 小野嘉夫, 神谷武志, 等. 學位授與10年のあゆみ[M]. 東京都: 大學評価·學位授與機構, 2001.
[5] 獨立行政法人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與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與機構概要[Z]. 東京都: 獨立行政法人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與機構, 2022.
[6] 六車正章, 瀧田佳子, 角田敏一, 等. 學位授與の20年[M]. 東京都: 獨立行政法人大學評価·學位授與機構, 2012.
[7] 山田道夫. 學位授與事業(yè)の25年—データから見る成果と課題[J]. 大學評価·學位研究, 2017, 18: 37-53.
[8] 康翠萍. 論學位的本質(zhì)[J]. 高等教育研究, 2005(7): 77-82.
[9] 橋本鉱市. 「新しい學士」の現(xiàn)狀と課題—學位授與機構による學位取得のプロフィール[J]. 學位研究, 1998, 9: 1-46.
[10] 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與機構30年史編集班. 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與機構30年のあゆみ(1991—2021)[M]. 東京都: 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與機構, 2021.
[11] 濱中義隆. 短期大學専攻科の研究: 大學評価·學位授與機構による専攻科認定制度との関係を中心に[J]. 大學評価·學位研究, 2005, 2: 49-67.
[12] 朱文富, 孫雨. 日本職業(yè)教育學位體系的構建歷程與經(jīng) 驗[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2(5): 87-93.
[13] 橋本鉱市, 濱中義隆. 學士學位取得者の現(xiàn)狀と意識— 1年後·5年後調(diào)査の分析結果[J]. 學位研究, 2000, 13: 57-84.
[14] 六車正章. 大學外學修の単位認定の可能性—大學評価·學位授與機構が行う學位授與事業(yè)に関連して[J]. 大學評価·學位研究, 2011, 12: 73-90.
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一般項目“戰(zhàn)后日本職業(yè)教育史”(編號:BOA190037)
10.16750/j.adge.2023.09.011
朱文富,河北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保定 071000;孫雨,河北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保定 071000。
(責任編輯 黃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