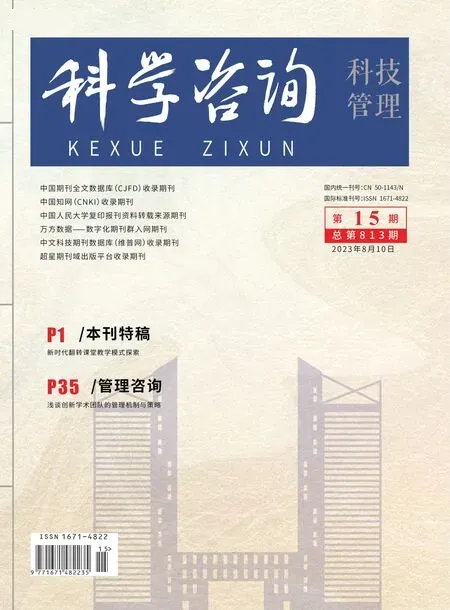論四位學者探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相關觀點及研究方法的比較
劉安彤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廣東廣州 510631)
近日,筆者拜讀了幾位學者所作魏晉南北朝時期關于門閥士族的文章,即唐長孺先生的《士族的形成與升降》、胡如雷先生的《門閥士族興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韓先生的《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以及嚴耀中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演變中的“成本”因素》。這幾位學者都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的形成與發展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筆者想通過介紹并比較這四篇文章的部分內容,來探究這四位學者在觀點上的異同以及有無相互啟發和一脈相承的內容,并談談自己對四位學者在研究方法有何特色上的看法。
一、文章內容的介紹與比較
(一)唐長孺先生的《士族的形成與升降》
唐長孺先生該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是,并不是所有的漢末大姓都能成為魏晉時期的士族,在此時期成為士族也多與祖上無關,多是“當世顯貴”[1]。士族制度發展到這個階段,其業已定型,王朝更迭也如晉之代魏,政治上沒有大的變化。“士庶之間,實是天隔”[1]的現象很少發生變化,但是在士族內部存在高下序列的升降。發展到后來,九品中正制逐漸為世家大族所利用,以保障士族的世襲特權。中正選官的“不公”和官場上的貪污腐敗現象維系著“當世顯貴”的士族的統治地位。
(二)胡如雷先生的《門閥士族興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
文章共五個小節,主要在第一小節和第二小節中談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內容,因此,我們主要介紹這兩節的觀點,并與前面所寫的唐長孺先生的觀點進行比較。
在關于門閥士族形成的社會條件方面,胡如雷先生既肯定史學界先輩所提出的“魏晉之交是門閥士族產生的關鍵階段,當時累世顯貴的大族往往就成為后來的士族或世族”這一觀點,也對其提出了異議——這只是說明一種現象,并不能從本質上解釋門閥士族產生的物質原因,并做出相關解釋:一是累世顯貴的現象歷代都有。例如兩漢和唐代,其都沒有因有這種顯貴的大族而形成門閥政治,唐朝時期的“世族”甚至在“累數世而屢顯”的風氣下走向衰弱。二是九品官人法作為解釋一切的原因是不確切的。胡如雷先生提及唐長孺先生所指出的:“九品中正制最初出現時也并不具有幫助門閥政治的目的,只是在之后被門閥士族所利用。但事實上,只要士族階層形成,實行任何選官制度都會被其所利用,好比唐朝實行的是科舉制,后期依然出現了世襲官僚的現象。”因此,我們不能對九品官人法為士族階層形成所起作用評價過高[2]。
之后,胡如雷先生也對此提出自己的觀點:“漢末商品經濟的嚴重衰落和自然經濟的明顯加強是導致門閥士族產生的主要社會根源。由此派生出一些其他的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2]門閥士族政治地位穩定的根源是其經濟地位長期相對穩定,而經濟地位的長期穩定則取決于自然經濟強化,涉及以下幾點。
第一,商品經濟衰落,土地交易減少,土地占有關系趨于穩定,土地所有者的經濟地位也得以穩定。
第二,戰亂、商品貨幣關系的破壞以及單個家庭無法完成南遷,導致破產農民無出路,只得依附地主。開發南方地區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促使地主與農民之間維持著緊密的聯系。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與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加強,超經濟強制加深。地主既穩定地占有土地,又穩定地依附農民,這種經濟地位的穩定性為等級制提供了物質前提,是門閥政治存在的主要基礎[2]。
第三,大部分地主聚族而居。不再遭受統治者的打擊。大族通過占有成片的土地得以聚居,同時又以此來鞏固其對于大片土地的占有。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具備自給自足的經濟條件,其也將“自給自足”作為治家的原則。
第四,大族在其內部強調禮法門風,不僅是為了便于進行管理,維系聚居一處的數百、數千戶人家,而且是為了保障其特權地位的長久持續。此時雖然存在等級承襲制度,但如果不能謹言慎行、潔身自好,也會招來禍害。禮法門風與商品經濟相對立,士族若被商品經濟所腐蝕,便極易出現敗壞禮法門風之事,也會因此走向衰敗。因此,大族的禮法門風得以長存也與自然經濟的加強有著一定的關系[2]。
關于“門閥士族衰弱的主要原因”,胡如蕾先生指出:“南北朝后期及隋唐時期士族走向嚴重衰落的原因是商品經濟的發展。”[2]主要論據如下。
1.地主階級生存的基礎被動搖
商品經濟發展將官僚地主卷入其中,“貴戚競利,興貨座肆”成為普遍現象,商品經濟的腐化使之“南畝廢而不墾”“講誦圈而無聞”,這在根本上危及其經濟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族的禮法門風被敗壞,大族聚居的情況逐漸減少。土地買賣、兼并隨之加劇,土地所有者對于土地的占有不再穩定,經濟地位也隨之不再穩定,其政治等級身份也不再穩固,世襲的等級特權難以維持,這是門閥政治走向衰落的主要社會根源。
2.大族分化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大族內部出現貧富分化,血緣紐帶削弱造成大族中的一部分家族徙居,而徙居又反轉來削弱大族的惡性循環。門閥士族就在這種惡性循環中走向衰落。
3.超經濟強制被削弱
“依附于大地主”不再成為破產農民唯一的活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減弱。均田制的出現使部分依附于大族的農民轉化為受田的編戶齊民,削弱了大族對勞動者的控制,從而削弱了超經濟強制。
當然,胡如雷先生也申明,即使在魏晉時期,經濟地位的穩定只是相對的而并非絕對。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有密切的聯系,但也不能一刀切。這與唐長孺先生在《士族的升降》中關于“當世顯貴”的說法一致。
胡如雷先生的探究的角度主要是經濟方面,其他方面也有涉及,內容與唐長孺先生所考究專注于“當世顯貴”和“九品中正制”而言較多。
(三)韓昇先生的《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
在造成士族政治長期延續的諸多原因中,文章著重涉及“文化”和“經濟”兩個方面,算是對之前學者研究的一種繼承。韓先生指出:“戰亂所帶來的國家文化中心的喪失以及學術的家族化是社會長期分裂和士族長期存續的文化因素,此時經濟與文化相關聯,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然經濟極易形成精英政治,具有家學淵源的世家大族此時占有絕對的優勢。”這與胡如雷先生“即使在士族衰弱之際,其也具備一定的文化優勢”的說法一致。
區別士族的標準就在于門第和門風,大族講究禮法門風并對其極其重視,由此形成“士業”的門風。其重視程度甚至到皇帝都擔心不合禮法而被士族恥笑的地步,可見其影響之大。這種風氣非暴力所能破除和掩蓋,具有持久穩定性,由此導致門閥士族的存續具有持久穩定性[3]。這一說法繼承了胡如雷先生關于士族用禮法維系其特權地位的觀點。
(四)嚴耀中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演變中的“成本”因素》
嚴耀中先生的這篇文章比較新穎,涉及范圍也較廣,其核心觀點是探究行政功能與維持其存在的耗費之間的效費比,即“成本”問題。在文章的摘要中,嚴耀中先生便指出該文是通過對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政治、民族融合中的語言文字、田制與專役制度等社會政治演變中的成本因素,以及南北軍事斗爭中的成本因素進行分析,來看這些成本因素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演變中發揮的作用[4]。
當然,行政成本問題以及行政系統效率無法量化,難以考查,嚴耀中先生主要通過一定的事件顯現出其是否有問題,如農民起義等社會動亂。
嚴耀中先生在文章的第三方面提及的關于民族融合中的語言文字的成本問題是對以往研究的突破。嚴耀中先生指出:“從‘永嘉之亂’到隋朝重新統一中國的兩百多年的時間里,‘五胡’與漢族已充分融合,游牧民族進入農耕社會,其原有的簡易的文字和語言不再適應農耕生產的需要,但其尚未形成完整的文字系統,這一現狀迫使想要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不得不接受、學習漢語言文字。”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正是對于語言成本的付出,加快了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融合速度與進程,反之則融合的速度會放緩。
在關于田制和專役制度的論述中,嚴耀中先生也談及其行政成本問題,但只是對其進行簡單解釋。在之前的幾位學者中,只有胡如雷先生對均田制進行了簡要的提及,這里我們也就不過多贅述。
包括關于“南北軍事上的斗爭成本”這一問題,嚴耀中先生所探究的角度也與既往的研究不同。嚴耀中先生通過分析當時的中國的一些地質上的自然條件和打仗所需的開銷,認為在中國古代軍事上,北強南弱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當然,嚴耀中先生在這之后提及了關于儒家思想的統治問題。儒學的自我約束和教化,使得其相比于法家而言,大大減少了相應的行政成本,這也是其能夠在中國社會長期居于統治地位的原因之一[4]。
嚴耀中先生的文章涉及的面較為廣泛,且思考形式較前面幾位學者有所不同,對前者的觀點有所繼承,也有所創新。
以上就是這四位學者所著文章的主要觀點及其之間的對比,四位學者的觀點有所異同,相互關聯,前者的研究成果對后來學者的研究有所啟發。同時,各學者也在不同的層面進行了探索研究,有所創新。
二、四位學者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探究
關于四位學者的研究方法上的聯系,筆者已在前文的論述中進行了描述。以下是筆者的一些拙見。
關于史學著述,不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都是人所書寫,而史事常是后人所寫,正如唐長孺先生在引用劉寔的文章中指出其文章“不似魏時所做,而應在晉初”這一問題。在后人所寫的這些史學著述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加上一些作者自己所想的方面。觀摩四位學者引用的史料、史學著述,從唐長孺先生到嚴耀中先生,我們可以看到其逐漸不再完全追究于正史,也會運用野史進行參考。正史與野史之間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是否為官方所著,而野史有的可能帶有一定的想象色彩,但其也是當時社會歷史形態的反映之一。筆者對歷史學上的研究不再拘泥于一種來源的史料持樂觀態度,史料引用范圍的擴大也便于我們對當時的歷史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