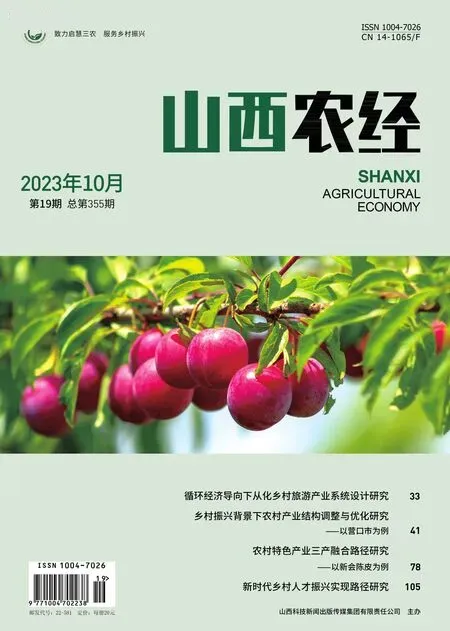山西省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影響因素研究
□蘭麗君
(山西省三農政策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1)
近年來,山西省委省政府針對農村集體經濟薄弱的實際情況,加大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統籌推進力度,推動村級集體經濟“破零率”和“增實力”雙提升。
2022 年3 月以來,山西省委印發《關于實施村級集體經濟壯大提質行動的意見》,在山西省開展“清化收”行動。9 月20 日省委召開山西省抓黨建促基層治理能力提升工作交流推進會,再次對推進集體經濟壯大提質進行安排部署。各地貫徹山西省委省政府要求,在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方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仍存在集體經濟發展質量不高、村級債務化解難度大等問題。文章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提出可行性建議,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健康發展。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可以充分盤活利用農村集體“三資”(資金、資產、資源),加強集體內部協作,促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包括經營收入、發包及上交收入、投資收益、補助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經營收入指村集體組織進行經營活動獲得的收入;發包及上交收入是農戶或承包單位上交的承包金與利潤;投資收益是村集體對外投資獲得的收益;補助收入是財政等部門給村集體的補助資金;其他收入是與村集體經營管理活動無關的收入。
丘永萍(2018)[1]研究了幾種因素會作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他指出各級財政投入占比、產業結構、市場化水平、生產要素投入及制度因素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
張瑞濤和夏英(2020)[2]指出,精英帶領、良好制度、基礎保障及村民認知程度中精英帶領在集體經濟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
王海英和屈寶香(2018)[3]分析了發達、欠發達和貧困地區的12 個村的情況,指出村集體經濟發展主要受資產利用效率、村莊精英、政府引導及農戶認知度的影響。
樓宇杰等(2020)[4]選取了村勞動力資源、村黨員人數、村集體土地總面積、政府對村財政補助、村總負債、村距縣城距離7 個變量研究村集體經營性收入的影響因素。
因此,文章基于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構成和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發現影響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勞動力、資產積累、資本、消費需求、體制改革和土地等因素,如資產積累、資本可能會影響經營收入;土地可能會影響發包及上交收入;勞動力、消費因素可能會影響投資收益;財政、改革因素可能會影響補助收入。
通過以上的分析,文章得出的研究假設為:如果勞動力多、集體資產積累高、財政傾斜多、消費需求高、產權改革順利、土地合理利用,可以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說明這些因素具有正向影響,可以帶動集體經濟的發展。反之,將會降低村集體經濟的收入,呈現負向影響,阻礙集體經濟的發展[5-6]。
2 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2.1 變量選取
文章根據實際調研情況和相關文獻,選取農村集體經濟收入、農業勞動力、集體資產、政府支出、社會消費、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集體農用地7 個變量,表1呈現了變量的類型、名稱、符號、衡量方法。

表1 變量說明
2.2 數據來源
文章采用的數據來自于《山西統計年鑒》(2016—2020 年)、《山西省農村經營管理統計資料》(2016—2018 年)、《山西省農村政策與改革統計年報》(2019、2020 年)。文章收集整理山西省116 個縣(區)(潞州區因數據缺失嚴重被剔除)2016—2020 年的面板數據,572 個樣本容量,并使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實證分析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要影響因素。在指標選擇上,主要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與可對比性。數據處理和建立模型工作均采用Stata 17 完成。
3 模型構建
文章設立如下回歸模型用于實證檢驗。
式中:Incomeit為被解釋變量,用人均集體經濟總收入表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情況;在分析的過程中,選取的核心解釋變量包括:Labit為農業勞動力情況,Ptait為村集體資產情況,Govit為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情況,Conit為消費情況,CNit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情況,Landit為集體所有農用地情況;εit代表誤差項;α代表待估參數;c為常數項;i和t下標分別代表地區和時間。
3.1 變量描述性統計
根據表2 可以看出,每組數據的最大值最小值與均值存在一定差距,說明數據具有一定的波動性。這一情況主要是各縣(區)發展存在一定差異導致,但通過查閱數據可知,對于各縣(區)內部而言,不同年份數據趨勢整體相對平穩,波動性較小。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3.2 相關性分析
針對文章的研究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之前,要對各變量進行皮爾遜相關系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相關系數表
通過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被解釋變量Income與解釋變量Lab、Pta、Con和CN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關系,皮爾遜相關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可以進行進一步回歸分析進行驗證。
3.3 多重共線性檢驗
考慮到變量間嚴重共線可能影響回歸結果的準確性,文章進行了多重共線檢驗。得到結果如表4 所示。可以看到,VIF 最大值為Land 的2.12,VIF 均值為1.63,均遠小于10,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可以進行進一步分析。

表4 多重共線性檢驗
4 基準回歸分析
4.1 豪斯曼檢驗
為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間做出選擇,在進行回歸以前,文章做了Hausman 檢驗,如表5 所示。卡方值為11.78,對應P值為0.067 1,統計上顯著性較低,故接受使用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因此,選取面板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

表5 面板Hausman 檢驗
4.2 面板回歸分析
通過上述面板數據模型選擇的檢驗,使用面板隨機效應模型對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要因素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結果如表6 所示。為保證研究穩健性,使用逐步增加變量的方式,得到回歸(1)~(6)。

表6 模型估計結果
可以看到,各回歸結果同一變量系數變化較小,可以驗證模型具有一定穩健性。從回歸系數檢驗來看,除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Lab)外,各解釋變量的系數均至少在5%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且為正,說明變量選取較為合理,且都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以結果(6)為例,具體來看,人均集體資產(Pta)系數為0.389 7,表明每增加1 個百分點,會導致農村集體經濟提升0.389 7%;人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Gov)系數為0.246 4,表明每增加1 個百分點,會導致農村集體經濟提升0.246 4%;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完成村數(CN)系數為0.018 2,表明每增加1 個百分點,會導致農村集體經濟提升0.018 2%;集體農用地(Land)系數為0.167 2,表明每增加1 個百分點,會導致農村集體經濟提升0.167 2%;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Con)系數為0.171 9,表明每增加1 個百分點,會導致農村集體經濟提升0.171 9%。農村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不顯著,可能原因是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進城務工,導致勞動力結構變化較小,同時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勞動力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影響較小。
5 結論及政策建議
5.1 結論
通過參考相關文獻,文章構建了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運用Stata17 處理數據,分析出各種因素對山西省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并通過穩健性檢驗來進一步驗證假設,得出本章實證結論。
除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Lab)外,各個解釋變量的系數均至少在5%顯著性水平上統計顯著且為正,且都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可以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帶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農村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不顯著,可能原因是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進城務工,導致勞動力結構變化較小,同時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勞動力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影響較小。此外,山西省各縣(區)同一地區的影響因素不是單一的,是由幾個因素共同影響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
5.2 政策建議
發展經濟有其自身規律,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一個長期過程,必須穩慎推進。
一是發揮班子和能人的帶動作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主體在村,關鍵在人。因此要充分發揮好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揮好農業企業的龍頭帶動作用,夯實村級集體物質基礎;采取辦班、上黨課、參觀學習、實踐鍛煉等多種形式,加強村干部培訓,把農村集體經濟帶頭人培訓納入鄉村人才培訓計劃,組織開展增強他們發展集體經濟、帶領群眾致富的信心和本領。同時,要結合職業農民培訓工程,指導村民掌握相關的技能,提高他們致富的能力。
二是匯聚多種主體力量共謀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不能僅依靠集體經濟組織自身的力量,需整合社會各方面力量為發展集體經濟鋪路助力。要做好產業發展規劃,謀劃一些好的項目,對于一些大的項目要聯合周邊村一起做。站在城鄉統籌發展的角度,引導更多的資源和要素向農村集聚,形成工農互動、城鄉互動的共贏發展格局。與此同時,引進一批優質經營主體與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進行深度融合,這樣就能對資金、技術等要素進行優化配置,加快集體經濟的發展。
三是完善收益分配制度實現“雙贏”。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通過分紅的方式讓所有的成員從中得利,保證成員有獲得感。堅持分配與積累并重,充分尊重農民群眾的意見,既不能把收益都分配出去阻礙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不能設置太高的公積金、公益金比例損傷農民積極性。引導集體經濟較為薄弱或處于發展起步階段的村集體,將更多的集體經濟收益滾動投入擴大再生產中,增強自我“造血”功能;要建立起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實現集體經濟發展、農民增收致富“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