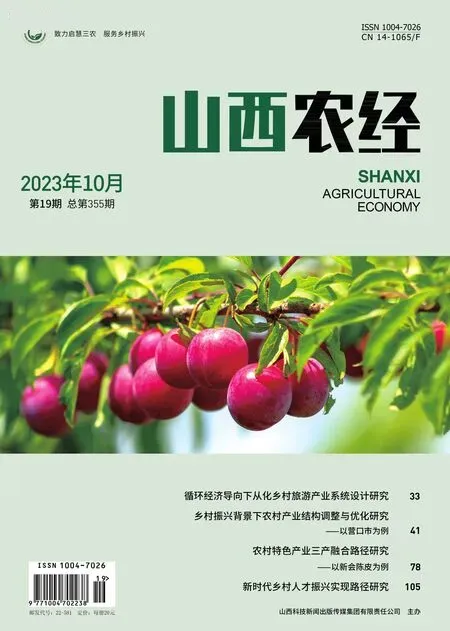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時空差異分析
□薛 玫,郭南克
(1.吉首大學,湖南 湘西 416000;2.信陽農林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6)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而農村集體經濟作為我國農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狀況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具有重大意義。近年來,學術界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研究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2 個方面。
定性研究主要圍繞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模式3 個方面進行。
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方面存在兩大困境,即農村土地細碎化嚴重和農民難以統一組織起來[1]。除此之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問題還包括產業結構單一、高負債率、正規融資難、過分依賴轉移性收入[2],以及空殼村增多、產權結構封閉、治理結構亟待優化等[3]。而建立歸屬清晰、權能完整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必然舉措[4]。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產權明晰到組(組織)、股份明晰到人,以確權到人為主要特征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有助于提高集體經濟組織的運行效率,推動集體經濟發展[5],并且相關學者們用實證檢驗證明了這一研究結論[6-7]。在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和模式方面,學者們通過實地調查進行了經驗總結。
丁波(2020)[8]基于皖南多個村莊的實地調研,結合農村集體經濟的演進邏輯,提出農村集體經濟的3種類型,即外生型、合作型和內生型。
賀衛華(2020)[9]基于中部某縣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調研,從黨建引領、政策扶持、規劃引導、因村制宜等方面創新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
屠霽霞(2021)[10]通過實地調查發現,浙江省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要模式包括村村聯合抱團發展、村企聯合抱團發展、“飛地”抱團發展、單位包村幫扶發展。
鄭世忠等(2023)[11]以地處欠發達地區的遼東山區寬甸縣青椅山鎮為研究對象,發現青椅山鎮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路徑主要包括承包經營、龍頭企業帶動、飛地經濟、自主經營、集體資產租賃等。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相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數量不多,且大多集中在分析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因素,比如大學生村官對農村集體經濟的推動作用[12]。也有學者用實證模型檢驗了農村集體經濟能顯著提升農民幸福感[13]、促進共同富裕的發展等結論[14]。
近年來學者們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方面[15-17],定量研究的學者和文獻數量不多,而有關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分布空間特征的研究很少涉及,從新經濟地理學視角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的空間布局,既能夠了解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政策如何影響其在分布上的區域性差異和時空變化,也有利于構建符合農村實際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方式[18-20]。
1 研究方法
通過隨機調研的方式,取得了2020 年和2023 年湖南省1 150 個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數據。在問卷調查中將農村集體經濟收入水平分為6 個等級:5萬元以下、5 萬~10 萬元、10 萬~20 萬元、20 萬~30 萬元、30 萬~50 萬元、50 萬元以上,每個等級分別賦值為:1、2、3、4、5、6,某縣城中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運算公式如下[21-23]。
式中:C代表的是某縣城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Ri表示該縣城位于某個收入等級的被調研村的數量;i表示等級賦值;n代表該縣城被調研村的數量之和;a表示處在某個等級收入水平的調研村的數量。
1.1 核密度估計法
為獲得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空間分布特征,文章采用了核密度估計工具來估計給定區域點格局的密度,核密度估計法能夠直觀地反映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在局部地理空間下的集聚型分布特征,具體公式如下。
式中:fp為代表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核密度估計值;n代表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調研村的數量;i代表第i個調研村的位置;(p-pi)為待估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調研村的位置到圓心的位置;h表示搜索半徑,即以p為圓點的曲面在一個空間范圍內的延展范圍,h的取值不固定,通過多次試驗,選擇的搜索半徑h為0.5。
1.2 空間格局分析方法
利用ArcGIS 軟件進行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通過計算全局Moran's I 指數和局域Moran's I 指數來反映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空間關聯性,全局Moran's I 指數可以用來反映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總體關聯度,局域Moran's I 指數可以用來測算湖南省某縣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同其周圍縣域間是否存在關聯性。其中,全局Moran's I 取值[-1,1],正數說明該空間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分布呈正相關,負數說明該空間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分布呈負相關,而0 代表該空間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不存在空間相關性,呈現出隨機分布的特征,數值越大說明其自相關程度越強。可以通過局域Moran's I指數將空間自相關類型劃分為HH、HL、LH、LL 型4 種,具體公式如下。
式中:xi、xj代表湖南省縣域i和縣域j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發展水平;是湖南省各縣域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均值;wij是空間權重矩陣,用來表示湖南省各縣域的空間關系;s2是xj的離散方差;n是研究湖南省縣域單元總數。
2 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空間分布動態分析
2.1 空間集聚分析
利用ArcGIS 10.8 中的Spatial Analyst 工具生成2020 年、2023 年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核密度圖,可以揭示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空間集聚指向。從總體上看,2020 年、2023 年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在空間上呈集聚分布。從分區來看,2020 年的長株潭地區是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核心集聚區,湘中地區以邵陽市和婁底市為中心屬于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次密集區,湘西地區的吉首市和湘北地區的岳陽市是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三級密集區。和2020 年相比發現,2023 年的主要變化是個別縣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集聚現象消失,比如張家界的永定區和慈利縣、常德市的武陵區、郴州市的汝城縣、懷化市的靖州縣。
2.2 空間關聯性分析
空間自相關能檢驗農村集體經濟收入水平的相關性,全局自相關指數可以衡量縣域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空間集聚的整體特征,運用ArcGIS10.8 軟件計算出2020 年和2023 年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全局Moran's I 值。從表1 可以看出,2020 年和2023 年的全局Moran's I 指數均大于0,且Z 檢驗顯著,都在90%以上,說明湖南省各縣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在空間上呈集聚分布態勢,具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即農村集體經濟收入高的縣域,其周圍縣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也高。反之,農村集體經濟收入低的縣域,其周圍縣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也低。通過對比2020 年和2023 年的指數可以發現,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空間自相關性和空間集聚分布的狀態在逐年增強。

表1 2020 年、2023 年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全局自相關情況
局部Moran's I 指數可以區別局部空間格局類型,該值大于0,表明該空間單元與鄰近單元的屬性值相似,類型分為“高—高”或“低—低”;該值小于0,表明該空間單元與鄰近單元屬性值相異,類型分為“高—低”或“低—高”。該值越大,說明區域單元對相鄰單元的輻射效應越大。
HH 型代表該縣域與相鄰農村集體經濟收入高的縣域間互相推動,從表2 可以看出,2020 年和2023 年,該類型區集中分布在瀏陽市、寧鄉市、韶山市、平江市、赫山區,他們不僅自身農村集體經濟收入較高,并且與近鄰其他縣域可相互推動發展;HL 型說明該縣域農村集體經濟收入高但阻礙了鄰近縣域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增長。2020 年該類型區集中在衡陽縣、衡南縣、寧遠縣、洪江市,2023 年只有衡陽縣、衡南縣;LH 型是指雖然該縣域農村集體經濟收入低,但是對鄰近其他農村集體經濟收入高的縣域具有促進作用,2020 年和2023 年,該類型區集中分布在湘陰縣;LL型則是自身農村集體經濟收入低并與鄰近其他縣域相互制約,從表2 中可以看出,屬于該類型的縣域數量比較多,并主要分布在株洲市、衡陽市和郴州市的縣域。

表2 2020 年、2023 年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局部空間格局類型的變化
3 研究結論
文章基于2020 年、2023 年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統計數據,通過核密度估計法、空間格局分析法對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時空格局變化特征進行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首先,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在空間上呈集聚分布,核心集聚區在長株潭地區,這主要是因為長株潭位于湖南省中東部,屬于湖南省經濟發達的核心地帶,優越的區位條件和交通條件為該地區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質支撐,并且長株潭地區城鄉融合度較高,城市經濟發展能夠帶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其次,與2020 年相比,2023 年的湖南省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在空間上的集聚分布沒有變化,只是個別縣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集聚現象消失,比如張家界的永定區和慈利縣、常德市的武陵區、郴州市的汝城縣、懷化市的靖州縣。
再次,湖南省各縣域的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在空間上呈集聚分布態勢,具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和2020 年相比,2023 年的空間自相關性增強,而且從局部空間格局來看,以高高和低低相鄰分布類型居多,高高相鄰分布類型主要分布在長沙、湘潭、岳陽、益陽的部分縣域;低低相鄰分布類型主要分布在株洲、衡陽、郴州的部分縣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