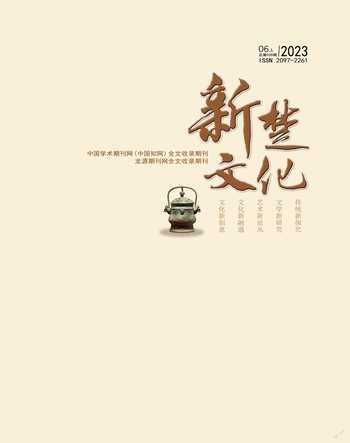町人、士人、教書人
【摘要】日本江戶時(shí)代“儒者”身份的社會(huì)意義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伊藤仁齋作為古學(xué)派儒學(xué)的代表人物,其儒者觀相繼受到町人之出身、士人之理想、教書人之身份的綜合影響。在古義學(xué)體系形成前,仁齋理想的儒者形象體現(xiàn)著對(duì)町人逐利特性的強(qiáng)烈反抗,而古義學(xué)形成后其對(duì)中國(guó)士人文治的憧憬,又因德川社會(huì)的重武輕文而落入困境。最終,仁齋通過教育事業(yè)統(tǒng)一了士人的責(zé)任意識(shí)和町人的生活方式,并與德川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之間達(dá)成了一定程度的和諧。
【關(guān)鍵詞】伊藤仁齋;儒者;町人;士;教育
【中圖分類號(hào)】G13/17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2097-2261(2023)16-0076-05
一、引言
伊藤仁齋(1627-1705)是日本江戶時(shí)代前、中期的著名儒學(xué)家,他反對(duì)重視自然哲學(xué)的朱子學(xué)體系及其權(quán)威,通過對(duì)《論語(yǔ)》和《孟子》的重新闡發(fā),建立了“古義學(xué)”思想體系,奠定了“古學(xué)派”儒學(xué)的基礎(chǔ)。目前對(duì)仁齋的研究,大都從經(jīng)學(xué)的角度觀察其思想內(nèi)部。由于仁齋本人出身于町人階層,沒有參與政治活動(dòng),所以丸山真男在其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仁齋思想具有“非政治性”①的特征。自那以來(lái),多數(shù)學(xué)者基本沿襲了這個(gè)主張,而對(duì)其思想、自我認(rèn)知與社會(huì)之間關(guān)聯(lián)的研究并不多。
當(dāng)然,自丸山氏以來(lái),也有一些學(xué)者對(duì)這個(gè)問題進(jìn)行了重新思考。其中許多學(xué)者重視其成長(zhǎng)環(huán)境,即“町人/市井”因素的影響。石田一良在其著作《伊藤仁齋》中,運(yùn)用古義堂文庫(kù)所藏文獻(xiàn)對(duì)仁齋的出身和京都的市井環(huán)境進(jìn)行了詳細(xì)考察,認(rèn)為其對(duì)仁齋的思想與生活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相良亨在同名作品《伊藤仁齋》中指出,仁齋之所以拒絕參與幕府政治,主要原因在于他對(duì)町人的“孝”與“家業(yè)”倫理的重視②。
但在筆者看來(lái),或許是由于日本學(xué)者的立場(chǎng)和角度,上述的分析以及結(jié)論似乎過于強(qiáng)調(diào)“家世、出身”等日本傳統(tǒng)家庭觀念帶來(lái)的影響。誠(chéng)然,仁齋受到了町人倫理與文化氛圍的影響。但同時(shí),伊藤家作為上層町眾,具有一定特異性,仁齋本人對(duì)儒學(xué)這一“異國(guó)”思想的認(rèn)識(shí)和情感也曾經(jīng)歷變化。在這些復(fù)雜因素的作用下,仁齋又如何思考作為個(gè)人的自己,以及作為群體的“儒者”在德川社會(huì),這一不同于儒教發(fā)源地中國(guó)的環(huán)境中的理想生存方式呢?
經(jīng)過研究,筆者認(rèn)為仁齋在受到其出身、教育、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影響后,其儒者觀和自我認(rèn)識(shí)事實(shí)上形成了某種結(jié)構(gòu),而這種結(jié)構(gòu)在“古義學(xué)”思想體系的形成前后又經(jīng)歷了一些變化。所以本文將用以下三個(gè)關(guān)鍵詞——“町人”之出身,即奠定仁齋思想底色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士人”之理想,即仁齋研究與追求的中國(guó)傳統(tǒng)儒學(xué)的理想人格;“教書人”之身份,即仁齋實(shí)現(xiàn)自身理想并與社會(huì)謀求和諧的立身之業(yè),來(lái)理解仁齋儒者觀的結(jié)構(gòu)及其變化。
二、町人:仁齋的出身與反抗
伊藤仁齋出身京都的上層町眾,理所當(dāng)然受到町人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但京都有著不同于江戶、大阪等其他都市的特征,伊藤家自身也有自己不同于一般町人的特點(diǎn),另外,仁齋自身對(duì)于“儒”的傾心與町人固有價(jià)值觀之間也存在著沖突。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以上因素,重新思考仁齋在出身與價(jià)值追求之間的取舍。故本章將討論在“古義學(xué)”體系確立以前,“儒學(xué)”和“儒者”對(duì)仁齋來(lái)說(shuō)究竟有怎樣的意義。
江戶時(shí)代初期的京都不同于作為武士權(quán)力核心的江戶,以及擁有漫長(zhǎng)商業(yè)發(fā)展史的大阪,依然是一座以天皇的存在和貴族文化為傲,具有濃郁文化氛圍的城市。隨著江戶時(shí)代趨于泰平,京都開始遠(yuǎn)離戰(zhàn)亂和實(shí)權(quán)爭(zhēng)奪,作為經(jīng)濟(jì)都市的功能得以發(fā)展③。其中特別以豪商為首,町眾階層的自主性和影響力都逐漸增強(qiáng)。但同時(shí),幕府并沒有對(duì)這個(gè)由公家、豪商、町眾所引領(lǐng)的自由都市采取放任態(tài)度,于江戶初期即設(shè)置了京都所司代作為地方官,并公布了如《禁中并公家諸法度》《京都町眾可令觸知條條》等法令以抑制公家和豪商的發(fā)展。伊藤家正是處在這樣一個(gè)歷史過程之中。據(jù)仁齋的長(zhǎng)子伊藤東涯所著《家系略草》《家系私記》的記述,伊藤仁齋的祖父了慶本是居住于攝津的商人,因躲避戰(zhàn)亂而遷往京都。了慶審時(shí)度勢(shì),在商業(yè)上取得了成功,并在京都堀河兩岸各購(gòu)置了一處房產(chǎn),開設(shè)了一家名叫“鶴屋”的商店④。
關(guān)于伊藤家的特點(diǎn),有兩點(diǎn)需要特別指出,一是其注重文化教養(yǎng)的氛圍和涵蓋公卿、文人的交友圈;二是其家道中落的過程。伊藤家從了慶一代開始,就注重和歌、儒學(xué)等中日雙方的文化教養(yǎng),藏有數(shù)量不菲的書籍④,且其次子伊藤了室之妻,即仁齋之母那倍是著名連歌師里村紹巴的孫女。成長(zhǎng)于擁有如此深厚學(xué)養(yǎng)家庭的那倍,也將其與公家和著名文人往來(lái)交游的習(xí)慣帶到了伊藤家,這對(duì)于仁齋的成長(zhǎng)自然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
然而,伊藤一族的衰落也正是從了室一代開始的。了室是家中次子,長(zhǎng)兄伊藤了心是否繼承了家業(yè),目前不得而知,但了心之子棄商從醫(yī)確是事實(shí),而了室家的營(yíng)商狀況也并不樂觀,這點(diǎn)在伊藤家當(dāng)時(shí)的相關(guān)記錄,包括下方仁齋本人的回憶中也得到了印證。可以想見,這種情況或許與上文提到的幕府對(duì)町人的打壓政策有一定程度的關(guān)聯(lián)。仁齋自幼愛好儒學(xué),好學(xué)程度非常人之可及。但在家道中落的背景下,家中的長(zhǎng)輩卻一致強(qiáng)迫熱愛儒學(xué)的仁齋成為一名醫(yī)生,理由自然是醫(yī)生的收入更高。年長(zhǎng)之后的仁齋回憶起當(dāng)時(shí)的狀況,痛苦之狀仍然躍然紙上——
“吾嘗十五六歲時(shí)好學(xué),始有志于古先圣賢之道,然而親戚朋友以儒之不售,皆曰為醫(yī)利矣。然吾耳若不聞而不應(yīng)。諫之者不止,攻之者不衰。至于親老家貧,年長(zhǎng)計(jì)違……愛我愈深者,攻我愈力。其苦楚之狀,如囚徒之就訊也。”⑤
可以想見,家人們的目的大抵在于改善家中的經(jīng)濟(jì)狀況。但一心求學(xué)的仁齋既不可能,也沒有回應(yīng)家人的期待,此時(shí)的仁齋所表現(xiàn)出的,是相當(dāng)劇烈的苦悶與反抗。青年時(shí)期的仁齋所愛好的,是以李延平、朱熹為代表的宋學(xué)。在當(dāng)時(shí)的作品《敬齋記》中,仁齋曾說(shuō):“幸嘗讀李延平、朱熹……而信之益久,融然得盡忘懷利祿之念、功名之志,且自以為遯世不被知而不悔,固學(xué)者之常分也。”⑥與成熟后的仁齋學(xué)重視“實(shí)”和“人倫”不同,此時(shí)他所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奮力逃離利祿世界的純粹學(xué)者姿態(tài)。但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仁齋在不久之后對(duì)于朱子學(xué)務(wù)“虛”的特點(diǎn)產(chǎn)生了質(zhì)疑,希望找到一種超越朱子學(xué)的價(jià)值體系。在思想的彷徨和身體的羸弱中,他在二十九歲“俄罹羸疾驚悸弗寧者殆十年”⑤,墮入了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之中,并離家十年,過著隱居的生活,直到三十八歲。在隱居中,他曾嘗試投身于心學(xué)、佛學(xué),甚至“白骨觀法”一類的玄學(xué),而這些努力并沒有使仁齋成功克服精神危機(jī),直到他從孔孟之中重新發(fā)現(xiàn)儒學(xué)之“古義”。
通過觀察青少年時(shí)期仁齋所處的社會(huì)背景,對(duì)其思想的形成過程進(jìn)行梳理,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古義學(xué)”體系形成之前,儒學(xué)對(duì)與仁齋來(lái)說(shuō),是一種絕對(duì)無(wú)法舍棄的志趣,更可以說(shuō),儒學(xué)是他逃離自己厭惡且難以直面的“利祿”現(xiàn)實(shí),求得內(nèi)心安寧的一種必要方式。“町人”身份為仁齋賦予了較好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接觸文化教養(yǎng)的環(huán)境,但家族的沒落及其帶來(lái)的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利益的執(zhí)著,也給他造成了相當(dāng)程度的苦悶。在這種情況下,仁齋義無(wú)反顧地埋頭于理學(xué)等,不斷嘗試“求道”,但此時(shí)的他所求之“道”與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之間并沒有具體的關(guān)聯(lián),他更沒有閑心和余力去改變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可以說(shuō),此時(shí)仁齋所憧憬的理想“儒者”,應(yīng)當(dāng)就是他在《敬齋記》中所說(shuō)的“遯世不被知而不悔”的,遠(yuǎn)離利祿俗務(wù)的純粹學(xué)者。
三、士人:仁齋的理想與困境
如果我們要討論“儒者”的自我認(rèn)識(shí)和群體意識(shí),回溯到傳統(tǒng)中國(guó)儒學(xué)的起源,去追問儒學(xué)家們世代追求的理想儒者形象,勢(shì)必離不開“士”這一重要概念。《說(shuō)文解字》中對(duì)“士”字有如下解釋:“士,事也。數(shù)始于一,終于十,從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段玉裁注)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稱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辡然否,謂之士。”⑦結(jié)合段氏注解,我們可以把握“士”的幾個(gè)基本特征:這種身份和群體懷有極強(qiáng)的“任事”社會(huì)責(zé)任感,且能通過自己的知識(shí)能力“事其事”,同時(shí),他們的知識(shí)能力又不被局限在于某項(xiàng)特定的技能,而具有一定的廣泛性。
顧頡剛認(rèn)為,最初的士作為下層貴族要具備文武兩種能力,后來(lái)受到孔子影響而重視文的,就成了“儒”,而重視武的士則演變?yōu)榱恕皞b”⑧。余英時(shí)曾引用《榖梁傳》中“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nóng)民,有工民”的表述,論證了春秋時(shí)期的下層貴族“士”與一般的“民”進(jìn)行階層融合,即“仕”的過程⑨。閻步克則認(rèn)為,“士”概念在西周秦漢之間經(jīng)歷了復(fù)雜流變,他指出在兩漢帝制形成前,“士”既指過成年男子,也曾是所有貴族官員之總稱。戰(zhàn)國(guó)由于客卿、養(yǎng)士制,又產(chǎn)生了“凡有一技之長(zhǎng),一學(xué)之得皆可稱士”的概念擴(kuò)大⑩。雖然諸家解釋不同,但可以肯定的一點(diǎn)是,具備一定教養(yǎng)和能力(六藝)的潛在“士人(士君子)”,要想在社會(huì)中實(shí)現(xiàn)自身價(jià)值,通過“仕”成為真正的“士大夫”,是一條必經(jīng)的道路。可以看出,“士”在廣義上可以理解為一種抱有面向他者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積極參與社會(huì)事業(yè)的知識(shí)階層;而狹義地說(shuō),“士”的最終目標(biāo),是要通過出仕獲取官職,躋身統(tǒng)治階層從而實(shí)現(xiàn)自身的社會(huì)理想。
然而,對(duì)身處江戶時(shí)代的伊藤仁齋來(lái)說(shuō),“士”則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德川社會(huì)雖然依據(jù)儒家的話語(yǔ)體系,建立了“士農(nóng)工商”的社會(huì)階層,但這里的“士”單指握有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武士階層。此外的町人,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幾乎沒有參與治理的權(quán)利。那么在這種環(huán)境中,仁齋作為一個(gè)“異國(guó)思想”的信奉者,是如何理解“士”這一理想形象的內(nèi)在精神,又是如何理解“出仕”這一問題的呢?當(dāng)然,由于仁齋與中國(guó)式“士大夫”的身份無(wú)緣,且其開始關(guān)注“仕”的問題是在反對(duì)朱子學(xué)之后,所以接下來(lái)要討論的,還是仁齋重視的廣義“士君子”精神,而討論范圍也集中于仁齋經(jīng)歷思想轉(zhuǎn)換,越過宋學(xué)求道于孔孟之古義,并在三十八歲回家開設(shè)“古義堂”,確立了其重視“人倫日用”的基本方針之后。
或許是由于對(duì)武士階層的忌憚和自身町人身份所限,仁齋的著作、文章中難見對(duì)“士”概念的專門論述。其文中出現(xiàn)的“士”,更接近于具備教養(yǎng)的廣義知識(shí)階層,有時(shí)指代范圍甚至不限于儒家。如他在贊美京都的學(xué)風(fēng)時(shí)說(shuō)到“禮樂文物之盛,賢智才藝之富,莫興于京。故四方游學(xué)之士靡不魚貫而入,輻奏相繼而至”⑤。這里的“四方游學(xué)之士”,顯然超過了信奉圣人之道的儒者。這種現(xiàn)象與德川初期儒學(xué)的社會(huì)地位也不無(wú)關(guān)系。與“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的中國(guó)不同,儒學(xué)并未成為德川幕府正式的“官學(xué)”,它與佛教、神道的實(shí)際地位并無(wú)二致,只是幕府為了鞏固自身統(tǒng)治所嘗試采用的意識(shí)形態(tài)其中之一,甚至只是一種傳播廣泛的一家之言罷了。
那么,仁齋如何理解以儒為本的“士人”“士君子”對(duì)社會(huì)的參與呢?首先,我們需要觀察仁齋對(duì)儒學(xué)中所追求的根本理想——“道”的理解。事實(shí)上,仁齋所主張的“道”概念中,是有積極且明確的社會(huì)參與意識(shí)的。他在《語(yǔ)孟字義》中寫道:“道者,人倫日用當(dāng)行之路。非待教而后有,亦非矯糅而能然……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販夫馬卒跛瞽者皆莫不由此而行。唯王公大臣得行而匹夫匹婦不得行則非道。”⑥這里仁齋心中理想儒學(xué)的根本問題,既包含了普通人之間的人際關(guān)系,又與日常生活有著非常緊密的聯(lián)系。這明顯是一種強(qiáng)烈的面向社會(huì)和他者的意識(shí)。
另一方面,仁齋對(duì)于“仕”,即為官?gòu)恼膽B(tài)度是復(fù)雜的。他一生拒絕為官,但這并不代表著他對(duì)“仕”持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仁齋在《孟子古義》中對(duì)孟子“仕。士之失位也,由諸侯之失國(guó)家也”?的論述評(píng)價(jià)道:“論仕進(jìn)之道,此章盡之矣。后世或不論其道與否,皆以隱為高,以顯為濁,以處為崇,以出為卑,大非圣賢之意。”?當(dāng)然,這個(gè)評(píng)價(jià)明顯劍指宋儒以來(lái)專事性理而遠(yuǎn)離日常的“空說(shuō)”,但并不能因?yàn)槿数S本人一直拒絕從政,就對(duì)仁齋這里贊成“仕進(jìn)”有過多的懷疑。從仁齋的弟子中多有為官之人甚至武士來(lái)看,仁齋對(duì)于“仕進(jìn)”的價(jià)值選擇本身并沒有持完全的否定態(tài)度。
但同時(shí),仁齋本人確實(shí)是終其一生拒絕出仕的。一個(gè)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在寬文十二年(1672),46歲的仁齋以照顧病重的母親為由,拒絕了細(xì)川越中侯求其為官的邀請(qǐng)。相良亨認(rèn)為,仁齋之所以拒絕,其主要原因在于町人相對(duì)于武士,不受主君的恩惠和控制,所以格外重視“孝”這一侍養(yǎng)父母的倫理②。但筆者認(rèn)為,除此之外,應(yīng)當(dāng)還有一個(gè)重要的理由,就是仁齋對(duì)德川社會(huì)以“武”為主的體制存在較大的不滿。少年仁齋成長(zhǎng)于文化氛圍濃厚,與公家交往頗深的町人家庭,他對(duì)長(zhǎng)年壓制公家、町人的武士階層并無(wú)太多好感。至于晚年,他依然在為學(xué)生講解“治道之要”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文勝其武,則國(guó)祚修。武勝其文,則國(guó)脈蹙。賞勝其罰,則刑罰清,民心安;罰勝其賞,則刑法亂,民心搖。”?可以看出,他所憧憬的理想環(huán)境,更加接近以儒家禮樂教化為核心的中國(guó)式文治社會(huì)。而對(duì)于以“武/罰”為主的社會(huì)形態(tài),他是持有強(qiáng)烈批判態(tài)度的。此外,他和朋友在書信往來(lái)中也曾感嘆,德川社會(huì)的風(fēng)氣“世澆實(shí)喪,圣遠(yuǎn)道湮。濟(jì)世之念,不勝其求進(jìn)之心,道德之實(shí),或輸夫功利之末”⑤,德川社會(huì)過于重視功利而輕視道德,是遠(yuǎn)離儒家的理想社會(huì)形態(tài)的。將孔子奉為圭臬的仁齋,不會(huì)不懂“邦無(wú)道則卷而懷之”的道理,也不會(huì)對(duì)現(xiàn)有的德川社會(huì)隨意妥協(xié)。
四、教書人:仁齋的堅(jiān)持與調(diào)和
在偏離儒家“文治”,以“武”為主的江戶社會(huì)中,仁齋并不具備憑借儒家理念參與政治的條件。那么他是如何在貫徹自身理念,對(duì)社會(huì)施加影響的同時(shí),又避免與德川社會(huì)體制發(fā)生正面沖突的呢?在筆者看來(lái),在其中發(fā)揮巨大作用的正是仁齋所從事的教育活動(dòng)和他“教書人”的身份。仁齋拒絕繼承家中事業(yè),也并未走上仕途。在做出這些選擇后,仁齋事實(shí)上已經(jīng)成了一個(gè)既不參加社會(huì)治理,也不參與商業(yè)活動(dòng)和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不屬于德川社會(huì)“士農(nóng)工商”中任何一個(gè)階層、沒有穩(wěn)定身份依托的存在。在這種條件下,使仁齋得以安身立命,甚至獲得極高社會(huì)地位的,正是以古義堂、同志會(huì)為代表的教育活動(dòng),和“教書人”這個(gè)一以貫之的身份。
同志會(huì)始于仁齋在隱居期間與友人的交游,而古義堂是他在結(jié)束隱居后開設(shè)的家塾。在仁齋“古義學(xué)”初步形成后,正是古義堂的成功使他聲名鵲起,得到了許多公家、大名的青睞。那么從其自身思想來(lái)看,“教師”這個(gè)身份究竟為何如此重要呢?這里需要引入仁齋繼承于孟子的“孔子賢于堯舜說(shuō)”加以說(shuō)明。
“堯舜天子也……然治績(jī)不過九州,子孫之襲封亦不及后世。仲尼匹夫也,旅人也。然道德遠(yuǎn)暨,不可限量……凡有文字之國(guó),莫不尊崇夫子之教。”?在仁齋看來(lái),孔子之所以比堯舜先王更加偉大,是因?yàn)樗敖倘艘缘馈钡墓?jī)已然超越了具體的時(shí)空,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將孔子視為至圣,又將其教育成果《論語(yǔ)》奉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書”的仁齋,自然憧憬“師”的身份與“教”的事業(yè)。與孔子類似,仁齋也是一介“匹夫”,是平凡的被統(tǒng)治者,但他的學(xué)生除了商人、公卿,還有山口勝隆等武士,可以說(shuō)他憑借自身教育活動(dòng)給社會(huì)施加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已然跨越了階層。
雖然仁齋的生活以教書人這一身份為核心,但他自始至終沒有脫離町人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忘記儒學(xué)“士人”的責(zé)任意識(shí)。據(jù)石田一良考證,仁齋晚年的交友圈非常廣泛。他的學(xué)問在商人、公卿中受到極大歡迎。他還參與了詩(shī)社、讀史會(huì)等多種形式的文化活動(dòng)④。這自然與仁齋重視“市井/日常”的傾向密不可分,也與他幼年接觸的町人生活和價(jià)值體系有很大關(guān)系。在仁齋的日常教學(xué)中,也體現(xiàn)著町人的風(fēng)氣與習(xí)慣。如他在《同志會(huì)式》和《同志會(huì)籍申約》中規(guī)定:“會(huì)而學(xué)日進(jìn),而情日通,志日起,而得日熟……凡吾同盟之人講習(xí)之間,務(wù)相謙下,優(yōu)柔引接,勿爭(zhēng)門戶……奢不可以致遠(yuǎn)……從節(jié)儉,一茗一果不許設(shè)其余。”⑤可以看出,這些要求一方面體現(xiàn)了町人對(duì)不同觀點(diǎn)、不同立場(chǎng)的開放態(tài)度和重視人際和諧的習(xí)慣,也貫徹著町人勤儉節(jié)約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仁齋也一直通過教育對(duì)社會(huì)加以引導(dǎo)和影響,始終秉持關(guān)注社會(huì)治理的“士人”的責(zé)任感。他在教育弟子時(shí),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階層應(yīng)當(dāng)通過學(xué)習(xí),盡到對(duì)社會(huì)的義務(wù)。他在談?wù)撟x書時(shí)說(shuō)道:“大凡關(guān)學(xué)術(shù)政體者,皆當(dāng)講究。其他知亦好,不知亦無(wú)害。禮樂兵刑治天下之具,不可不講。”?他很具體地用“學(xué)術(shù)政體”和“禮樂兵刑”的范圍,強(qiáng)調(diào)了積極學(xué)習(xí)與社會(huì)治理相關(guān)的知識(shí)內(nèi)容。正是這種來(lái)自中國(guó)傳統(tǒng)儒學(xué)“事其事”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讓他受到許多大名的重視,也培養(yǎng)出了如荒川景元等一些走向現(xiàn)實(shí)政治治理的出色學(xué)生。
此外,仁齋還特別主張儒者不同于其他社會(huì)職業(yè)的特別之處。在《儒醫(yī)辨》中,他對(duì)德川社會(huì)中部分醫(yī)生為抬高自身社會(huì)地位,假儒之名自稱“儒醫(yī)”的現(xiàn)象進(jìn)行了強(qiáng)烈批判,最后他總結(jié)道:“且天地間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茍大人而行大人之事,小人而為小人之事,則各得其所,名稱允諧,亦君子之所不廢也。”⑤與醫(yī)生這種以特定技能獲取利益的群體不同,儒者是與天下萬(wàn)人萬(wàn)物的“大道”,息息相關(guān)的“大人”。雖然仁齋并沒有斷定“大人之事”相對(duì)于“小人之事”具有絕對(duì)的優(yōu)越地位,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對(duì)儒者自身身份認(rèn)同的高度強(qiáng)調(diào)。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在古義學(xué)思想成型之后,仁齋將“町人”的市井生活方式、“士人”的儒家社會(huì)理想通過“教書人”的身份予以統(tǒng)一,以此在德川社會(huì)“文”與“武”的沖突之中保持了自己作為儒者的獨(dú)立、自尊,貫徹了儒者的價(jià)值觀和責(zé)任感,同時(shí)實(shí)現(xiàn)了與現(xiàn)實(shí)體制之間的和諧共處。
五、結(jié)語(yǔ)
本論文基于伊藤仁齋所處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和社會(huì)背景、所持的學(xué)術(shù)志向以及其直面的困難,對(duì)他的儒者觀及其變化進(jìn)行了結(jié)構(gòu)化分析。伊藤仁齋生于一個(gè)與公卿和知識(shí)階層關(guān)系密切的上層町眾家庭,受到了町人生活方式和中日兩國(guó)文化的影響。但隨著家道中落,長(zhǎng)輩強(qiáng)迫他學(xué)醫(yī)以補(bǔ)貼家用,這與他自身的志趣產(chǎn)生了沖突。因此,仁齋表示出了對(duì)町人以利為主的價(jià)值觀的強(qiáng)烈反抗,傾心于宋學(xué)等超脫世俗的學(xué)問,表現(xiàn)出了逃離現(xiàn)實(shí)的傾向。對(duì)于此時(shí)的仁齋來(lái)說(shuō),理想的儒者是與現(xiàn)實(shí)的功名利祿保持距離,遠(yuǎn)離世俗雜務(wù)的純粹存在。
然而,他在對(duì)宋學(xué)產(chǎn)生懷疑,試圖轉(zhuǎn)向而未果之后,陷入了長(zhǎng)時(shí)間的精神危機(jī)。在隱居中,他發(fā)覺只有孔孟古義才是儒學(xué)之真義,大幅改變了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認(rèn)識(shí),將“人倫日用”置于學(xué)問的核心位置。自此,仁齋的儒者觀中開始顯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儒家理想中“士人”這一形象所蘊(yùn)含的精神,即強(qiáng)調(diào)參與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高度責(zé)任感。但由于以“武”為主的德川社會(huì)過于脫離仁齋主張的理想“文治”,使得仁齋一生都拒絕直接參與武士主導(dǎo)下的德川政治。
在社會(huì)以“武”為主的狀況下,仁齋找到的理想儒者形象,便是作為教書人的“師”。他運(yùn)用“師”這一身份,既貫徹了自己對(duì)孔孟的信仰,對(duì)社會(huì)施以影響的同時(shí)維護(hù)了儒者身份的獨(dú)立,與德川社會(huì)之間保持著某種程度的和諧。當(dāng)然,教書人的生存方式并不意味著他就此脫離了“町人”和“士人”。從仁齋的生活、交際、教育內(nèi)容來(lái)看,他是在以“教書人”的身份去統(tǒng)一“町人”的生活方式和“士人”的社會(huì)理想。
本文試圖將伊藤仁齋置于特定的歷史社會(huì)環(huán)境下,去討論其特定身份及其所學(xué)、所思的文化內(nèi)涵。在今后的研究中,筆者還將會(huì)以伊藤仁齋這一重要人物為端緒,繼續(xù)觀察江戶時(shí)代的那些既不依賴于武家政權(quán),又不依靠于町人龐大財(cái)力,僅以自身學(xué)問立身于社會(huì),特立獨(dú)行的“儒者”們,去不斷追問他們特別生存方式的內(nèi)涵及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
注釋:
①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學(xué)出版會(huì),1952,第52頁(yè)。
②相良亨:《伊藤仁齋》,ぺりかん社,1998,第258頁(yè)。
③有關(guān)這段歷史過程,可以參考林屋辰三郎的著作《町眾:京都的“市民”形成史》第八章。
④石田一良:《伊藤仁齋》,吉川弘文館,1960。
⑤伊藤仁齋著,三宅正彥編《近世儒家文集》,載《古學(xué)先生詩(shī)文集》,ぺりかん社,1985。
⑥吉川幸次郎、清水茂編《日本思想大系33:伊藤仁齋、伊藤東涯》,巖波書店,1971。
⑦許慎撰,段玉裁注《說(shuō)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0頁(yè)。
⑧顧頡剛:《史林雜識(shí)初編》,中華書局,1963,第85頁(yè)。
⑨余英時(shí):《士與中國(guó)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5頁(yè)。
⑩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第38-63頁(yè)。
?伊藤仁齋著,關(guān)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注釋全書·孟子古義》,東洋圖書刊行會(huì),1926。
?伊藤仁齋著,清水茂編《童子問》,巖波書店,1970。
參考文獻(xiàn):
[1]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M].東京:東京大學(xué)出版會(huì),1952.
[2]石田一良.伊藤仁齋[M].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
[3]林屋辰三郎.町衆(zhòng):京都における「市民」形成史[M].東京:中央公論社,1964.
[4]伊藤仁齋.童子問[M].清水茂,編.東京:巖波書店,1970.
[5]渡邊浩.近世日本社會(huì)と宋學(xué)[M].東京:東京大學(xué)出版會(huì),1985.
[6]相良亨.伊藤仁齋[M].東京:ぺりかん社,1998.
[7]余英時(shí).士與中國(guó)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子安宣邦.伊藤仁齋的世界[M].東京:ぺりかん社,2004.
[9]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
[10]澤井啟一.伊藤仁齋:孔孟の真血脈を知る[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22.
作者簡(jiǎn)介:
董同罡(1999.6-),男,漢族,河南洛陽(yáng)人,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北京日本學(xué)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