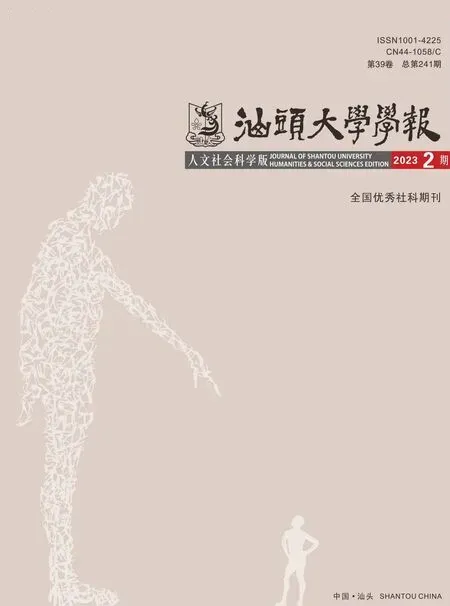以朱子論“中”觀其“萬物一體”
魏子欽
(安徽大學哲學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0)
陳榮捷以“中字六說”認定“中”居于儒家哲學的核心地位,不僅依此判定“三代以前‘中’字為思想熱烈討論之點”,也認定“中”字“貫乎(儒家)經籍之中,可謂盛矣”[1]。從儒家哲學發展史看,作為“集孔子以下集學術思想之大成”[2]23者,朱子對“中”字也有鞭辟入里之發揮。關于學界對于朱子論“中”的研究,主要存在兩種方向。一是概念解析,陳來先生以朱子理學的“已發未發”[3]闡明“中”背后的朱子心性論;二是經典詮釋,張立文先生以朱子經典詮釋為內容,提出“倫理道德”[4]234的理學思考;劉學智先生也從經典詮釋入手,討論朱子與洛學及“關學關系”[5]的學脈繼承問題。從上述研究看,朱子對“中”的理學詮釋,主要集中在朱子心性論、朱子理學的傳承問題,但從《四書章句集注》看,朱子對“中”的理學闡釋,主要是從詮釋方法、詮釋內容、詮釋視角進行展開,目的是通過對“中”的闡釋落實“萬物一體”的圣人之境。有鑒于此,筆者通過朱子對“中”做出的概念界定、言語表征及其命題判斷的理學詮釋,透視由朱子論“中”展開的理學語言圖景,揭示朱子對儒家之“中”的理學分析,期以展現朱子論“中”背后的理學境界。
一、以“跨越漢學”論“中”
“中”是儒家哲學的核心概念,“集理學之大成”[2]23的朱子也曾論“中”。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6]19
從漢學角度分析,朱子對“中”的理解,并未借鑒漢唐經學的學術成果。在漢學的訓詁中,漢唐經學家是以“大本”注“中”。例如《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鄭玄注曰:“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7]1422孔穎達疏曰:“言情欲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7]1424漢唐經學家對“中”的注釋主要落實在人性、情欲上,認為“中”是“禮與政教生發與制作的根據”[8],是從禮由心生的角度進而解釋王道教化的禮樂政治問題。
從鄭玄到朱子,盡管可以說朱子接受漢唐經學家以“大本”注“中”的講法,但也可以說朱子是從《中庸》本身思考以“大本”釋“中”的詮釋。而且,就算說朱子是借鑒漢唐經學家注“中”的學術成果,但是朱子也改變漢唐經學家的詮釋向度。一方面,朱子以“未發”闡釋“中”,認為“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6]20。另一方面,朱子指出:“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6]20“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6]21朱子對“中”的闡釋,并未采取漢唐經學家對“中”的訓詁,也未專意于鄭玄等經學家的王道教化問題,而是轉向未己未發、天命之性、道體等理學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朱子在闡釋“中”時采取“跨越漢學”的方式,是因為朱子不滿漢唐經學家對《中庸》的注釋。
“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中庸》)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后其學布于天下。”[9]3639朱子認為孔門傳授心法的《中庸》因“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9]3639。所以,到了漢唐學者那里,《中庸》或是被用作思想比附,或是僅作通釋考義。董仲舒、鄭玄等“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9]3639,唐代“李翱,始知尊信其書(《中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9]3639所以,朱子認為真正得《中庸》之義是周敦頤、二程兄弟。從“道統”而論,朱子將孟子之后的漢唐學者對《中庸》注釋與闡釋之貢獻加以剔除,以此確立濂溪、二程在儒家道統的正統位置,繪制一條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的理學道統譜系。
從學術繼承看,朱子論“中”的理學闡釋,主要繼承二程的理學思想。程頤說:“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中。”[10]160(《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程顥也說:“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10]122(《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對此,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說:“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6]17面對二程先生的學術思想,朱子并未緊跟先生之旨而亦步亦趨,而是認為“不偏不倚”“不過不及”與二程“不偏不易”稍異,即“以‘平常之理’(朱子)較‘正道定理’(二程)規模大。”[4]237不僅如此,朱子也吸收呂大臨對“中”的認識,即“無過不及”和“不倚之謂中”。呂大臨說:“圣人之學,以中為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又說:“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10]608(《河南程氏遺書》卷九《與呂大臨論中書》)。可見,朱子對“中”的闡釋跨越漢唐經學的思想成果,在二程子、呂大臨的理學建樹上推進一步。可以說,“中”在朱子的理學闡釋下也獲得新發展。朱子曾說:
“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9]548(《朱子全書·第六冊·中庸或問》)
朱子認為程子論“中”有“在中之義”(未發)與“中之道”(已發)二義,是根據程子此說加以推進,認為“不偏不倚”即是未發之前的在中狀態;“無過不及”是已發之后的中之道。在《朱子語類》中,朱子曾用“未發之中”與“隨時之中”解釋過“中”之二義。“至之問: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書,本只是說隨時之中,然本其所以有此隨時之中,緣是有那未發之中,后面方說時中去。”又言:“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11]1584朱子認為“未發之中”是“不偏不倚”、“隨時之中”是“無過不及”。
從“未發之中”看“不偏不倚”,“不偏不倚”是指不偏向任何一方,表示中立、公正。朱子曾言:“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11]1614從修養論出發,“學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焉。”[6]82“不偏不倚”代表一種內在平衡之“中”,可將其理解為“喜怒哀樂之未發”“不偏不倚”的狀態,強調人不斷修養而逐漸豐滿內在之“中”,看做是一個內在于人心的且趨于無限的空間。
從“已發之中”看“無過不及”,“無過不及”是指做事情做的不過頭,不會超過也不會不如,恰到好處。“學者要學得不偏,如所謂無過不及之類,只要講明學問。”[11]245從文質論看,“禮貴得中,奢易則過于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6]62從為學立場看,“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11]2556可見,“無過不及”代表一種外在平衡之“中”,這在文質關系上強調既不能側重繁瑣之文,也不能偏向淳樸之質,而是要追求文質彬彬,恰到好處。
朱子對“中”的概念界定,不僅跨越以鄭玄為重的經學高峰,也立足以二程為首的理學立場,在拓寬儒家論“中”詮釋向度同時,肯定周敦頤、程顥、程頤在儒家道統地位,依此重建儒家道統譜系,完成對朱子理學合法性的確立與討論。
二、以“理一分殊”論“中”
朱子認為《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由于朱子弟子未能理解《中庸》之旨,朱子曾在《朱子語類》中,以“中”對《中庸》展開細致解釋。
問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云云。
曰:“如何說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里面?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你逐一理會過,方得。所謂‘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以為‘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于我。”[11]1594
“一理”散則包含萬事,合則匯聚“一理”。“散”只是“一理”運動變化的中間過程,其最終目標是為實現“合”的豁然貫通。從運動過程看,“一理”的運動形式以“散”與“合”的形式呈現,它既可在萬事萬物中分化顯現,又可在萬事萬物匯聚后合為“一理”。從學術繼承看,朱子對《中庸》的闡釋繼承程顥的思想。《朱子語類》指出,明道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朱子語)“雖曰‘合為一理’,然自然有萬事在。”[11]1713朱子在程顥、楊時基礎上推進一步,以“理一分殊”完善“散為萬事,合為一理”。故而,朱子得出以“中”為核心的語言表征:中行、中正、中和、中庸、中道。
“中”從外在禮儀看,存在“中行”的語言表征。“中行”出自《論語·公冶長》,主要指行為舉止。朱子認為,由于孔子推行天下大道的愿望未能實現,便將此愿寄于后世,“于是始欲成就后學,以傳道于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于道也。”[6]80在朱子看來,“狂士”的言行并不符合“中”,盡管志向高遠,但容易超越“中”而淪為異端,無法順利完成傳道天下的大命。換言之,只有言行舉止,才能守住“中”。只有做到“中行”的無所偏失,士君子才能順利地得道傳道。
“中”從內心存養看,存在“中正”的語言表征。“中正”主要指為行為規范,屬于道德問題。朱子言:“毫厘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6]53朱子強調“中正”,即禮義規范要符合“中”,主張將“中正”之理應真切地應用在禮義,使其作為禮義的內在要求。在《滕文公章句下》中,“言圣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于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于污賤而可恥。”[6]252中正是一個非常嚴格甚至苛刻的規范,想要符合禮,就必須做到嚴謹且從容,和諧而有節制,而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差錯,過或者達不到都是不符合禮的,否則就會失去中正,偏向一方。
“中”從未己未發看,存在“中和”的語言表征。“中和”討論性情的問題,屬于心性論。“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6]20朱子認為心之“未發”則性,心之“未發”謂之中,若“未己未發”都合規則,便是端正,無所違背,便可順天地之正氣,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另外,朱子也認為“中和”是就內在性情而言的,但朱子談“中和”多指圣人孔子,“惟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氣”,[6]91“惟圣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于容貌之間者如此”[6]98,“中和”這種看似輕松平常的愉悅狀態,如孔子圣人才能精微體察。
“中”從不學不慮看,存在“中道”的語言表征。“中道”是指思想與行為相協調的內外狀態,《中庸》言“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11]2996。朱子進曰:“圣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6]32朱子以天理闡釋中道,認為中道是圣人氣象的真實流露,并認為若欲實現“中道”,以學思并舉通向成圣之路。朱子還指出,“蓋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6]138,圣人教人學思并重就是以“中道”為內容,只是掣肘于現實,只能退而求其次,與時偕行,“故圣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于中道而已。”[6]120
“中”從涵養心性看,存在“中庸”的語言表征。“中庸”主要指禮義德行層面的問題。《四書章句集注》指出,“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6]21可見,“中和”偏內在性情,“中庸”言心性德行,故“中和”內在于“中庸”。朱子言:“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6]21可見,欲見“中庸”需回人倫日常之間,“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6]24
在《中庸》中,“中”散為萬事,分化出中行、中正、中和、中庸、中道的理學言語表征,但這些理學言語表征又可復合為一理,其同一性歸納即為“誠”。首先,關于“誠”的內涵,朱子曾作解釋:“誠,實也。”[7]19“天下至誠,謂圣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6]34其中,誠也有天理的含義:“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6]32其次,朱子在揭示“誠”的同時,也展開對“實理”之誠與“中和”“中庸”之中的關系討論。朱子言:“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9]594朱子認為把握“實理”之“誠”是踐行“中庸”“中和”的關鍵問題。“中和”是“誠”這一實理的體用義描述,“中庸”是“誠”這一實理的平常義運用,“天地位,萬物育”則是發揮“誠”這一實理的境界展現形態。相較之下,朱子認為“過與不及”的兩種狀態,便是沒有真切地認識“實理”的體用義、平常義與境界展現,反向突出“中”“不偏不倚、不過不及”的理學內涵。
從“誠”與“中”的關系看,朱子言:“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11]1588從內外關系出發,“‘誠’是‘中’的根本,而‘中’是‘誠’的外在顯發”[12]的道理。在《朱子語類》中,也曾記載朱子與其弟子曾對話:“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答:“此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也。”[11]1588可見,“中”與“誠”不僅體現內外關系,也是不同視角轉折的一體兩面,即以“理本體”為核心對“誠”與“中”予以闡釋。所以,朱子從“理一分殊”論“中”,即揭示“中”散為“中正、中行、中和、中庸、中道”的理學言語表征,復合可為“天理之本然”的運動過程。
三、以“通權達變”論“中”
為指明“中”字之重要,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引程頤之語:
“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6]334
按朱子之義,欲真同情之理解儒家之“中”,須是注意“默識心通”。從空間位置看,中可以是指廳之中央,但從家看,廳之中便不再是中,中是以堂為中,而在國而論,中又有了變化。所以,程朱理學指出“中”的靈活性與變動性,表明“中”是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故而需要“默識心通”,即通過求諸自我內在,以心領神會的方式獲得“中”之義理。
從廳堂之喻看,之所以朱子強調“默識心通”,在于朱子十分注重儒家的“經權時變”。自儒家創始以來,就提出“與時偕行”“因時損益””等儒家經權觀。從“經”的概念界定看,“經”在《說文解字》中:“經,織,從絲也。”段玉裁注曰:“織之縱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后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13]644朱子指出:“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6]39“經”就是常道、常則及大經大法。從權的概念界定看,“權”在《說文解字》中:“權,黃華木。從木雚聲。一曰反常。”段玉裁注曰:“《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后有善者也’。”[13]246朱子言“權”:“程子曰:‘權,秤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6]110可見,“權”是指權衡,即符合于“義”的衡量輕重、權衡利弊。最后,從經與權的關系看,
問:“經、權不同,而程子云:‘權即經也。’”(朱子)曰:“固是不同: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時多。”(朱子)又曰:“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11]1061
朱子否定程子對經權關系的判定,認為經、權不同。“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道是個統體,貫乎經與權。”[11]1061不僅如此,朱子以道貫經權的同時,也對踐行經權的主體做出說明。“所謂權者,于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11]1064“所謂經,眾人與學者皆能循之;至于權,則非圣賢不能行也。”[11]1061即“權”乃為圣賢方可行之、用之,朱子突出踐行“權”的難度與高度。所以,“權”作為千變萬化之法,朱子強調只有做到“默識心通”,才能把握“時中”,踐行圣人之言,明曉變通,不為迂闊。總之,正因朱子領會儒家“通權達變”,所以在解釋“中”字時,強調切不可流于文字表面,須“默識心通”,如比尋一廳、堂、國之“中”,須隨時而論,亦如《孟子》言: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淳于髡)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6]265
孟子以權變回應淳于髡的詰難,認為男女不親手遞送東西是禮法,即經也。但若是此女子為嫂子,嫂子溺水不去救,便是枉為人;伸手去救助溺水的嫂子,是對“男女授受不親之經”的變通。對此,朱子在孟子論證“權”的立場上,提出“權而得中”的說法,認為“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6]265。換句話說,朱子認為“嫂溺援之以手”的說法,體現孟子“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的權變道理,即以“通權達變”論“中”。所以,這樣也就不難理解朱子以“蓋權而得中,則不離于正矣”[6]268闡釋孟子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后也,君子以為猶告也”[6]268。
緊接著,朱子在借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以“通權達變”論“中”的同時,又深化孟子所批評之“子莫執中”,確定“中”的詮釋區間。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6]334
朱子判定“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一方面,朱子言:“楊墨之失中也,故度于二者之閑而執其中。”[6]334又言:“執中而無權,則膠于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6]334又引程子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6]334朱子主張“權而得中”,這是指對“中”不應執一,而是應以權應事,從情境意識出發,強調根據具體情景做出符合“中”的選擇。另一方面,朱子認為“不得中”“執中”遮蔽“時中”,有礙“中”的真意。“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于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6]334朱子認為楊墨二者因為不得中而皆失“中”、子莫執中而偏離“中”。楊朱“為我”過于利己而執于自身;墨子“兼愛”則是不分厚薄與親疏,兩者都沒有在權變思想上踐行“中”。子莫看似“中”,實則此“中”無“權”,此三者看似求“中”實則害“中”。《朱子語類》言“時中”: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個中執之。”(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義。這個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朱子)曰:“然。”[11]1550
從“已發”看“時中”,“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11]442另外,朱子對“時中”也有界定,“時中”是指“無過不及”,“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11]904在此基礎上,朱子指出“‘中庸’之‘中’,本是無過無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中,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11]1584朱子認為“中庸”之“中”是在“已發”范圍的“無過不及”,其大旨核心在“時中”。“時中”內部包含的“中”,是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未發”之中。從體用關系看,“時中”內部包含的“中”是本體,即性情之中、未發之中;“時中”的這個“中”字是發用,即德行之中,已發之中。對此,朱子指出“時中”之“中”字也包含“未發之中”,即兼具內外,容納“中和”。
朱子以“通權達變”鎖定“中”的詮釋區間,認為“不得中”、“執中”,皆是離“中”、害“中”。若想識得“中”字,須是“默識心通”“權而得中”,但是朱子也強調踐行“權”的難度與高度,認為“權”乃圣賢方可行之、用之。所以,若能以“時中”隨時應事,便為圣人之學、圣人之境。
結語
問“時中”。(朱子)曰:“自古來圣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個物事。”[11]1629
“時中”,即“中”之“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朱子認為“時中”乃圣賢講學之所在,故弟子欲學此圣賢道,須以“默識心通”儒家之“中”字,隨時取中,“便無所用力,自是圣人教化如此。”不過,在《朱子語類》中,朱子弟子曾提出“致”是偏離“時中”的疑問。
問:“中有二義:不偏不倚,在中之義也;無過不及,隨時取中也。無所偏倚,則無所用力矣。如呂氏之所謂‘執’,楊氏之所謂‘驗’、所謂‘體’,欲致力于不偏不倚之時,故先生于或問中辨之最詳。然而經文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之一字,豈全無所用其力耶?”
曰:“致者,推至其極之謂。凡言‘致’字,皆此意。如大學之‘致知’,論語‘學以致其道’,是也。致其中,如射相似,有中貼者,有中垛者,有中紅心之邊暈者,皆是未致。須是到那中心,方始為致。致和亦然,更無毫厘絲忽不盡,如何便不用力得!”[11]1625
朱子弟子認為朱子強調“中”的“無所用力”。所以,朱子在其或問中,批評呂氏之執,楊氏之驗與體,認為這些人皆是致力偏倚,是不得中、失中、害中。只是,從儒家經文看,弟子不解的是,為何《中庸》要講“致中和”,要強調“致”之用力工夫。對此,朱子從極致境界解釋“致”字,認為“推至其極”謂“致”,“致中”如同射箭射中靶心。“致和”如同無縫罅,盛水不漏。亦如朱子所言之“‘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11]1624。又言之“‘致中和’,須兼表里而言。致中,欲其無少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失;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11]1624。所以,“致中和”之“致”,并非是指工夫之極致,而是境界之極致,如此之“中”便是無所用力,故圣人以“時中”契入此道,深諳此理。可見,朱子以極致之境界解釋“致”字,解開弟子對“致中和”是偏離“時中”的疑惑。
針對踐行“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的有位者而言,有朱子弟子曾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11]1627可見,朱子對“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有位者的理解,不是以政治視角看待,而是以儒家仁學目光加以審視。《朱子語類》載:
元思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指在上者而言。孔子如何?”(朱子)曰:“孔子已到此地位。”[11]1627
朱子以有德者居之的“圣人之身”認定“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的為位者,否定弟子以“政治上位”認定“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的為位者,認為孔子以“圣人之身”實現“致中和”之效:即“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11]1626。孔子也以“圣人之身”實現“萬物育”之效:即“自謹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6]20由此,朱子進言“萬物一體”。朱子曰:“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于如此。”[6]20朱子認為“萬物一體”并未向外做功夫進以求取最高境界,而是復其己性之初。換言之,因萬物均氣而同體,故我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是以“時中”踐行“為己”,在己之位行己之事,實現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驗效“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敞開“萬物一體”的圣人之境。
朱子站在二程與呂大臨的理學基礎上論“中”,給出不同漢代經學對“中”的界定,認為“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與此同時,從“道統”而論,朱子以“跨越漢學”論“中”,朱子剔除孟子之后的漢唐學者對《中庸》注釋與闡釋,依周敦頤、二程論《中庸》重建儒家道統,呈現一條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的道統譜系。另外,朱子以“理一分殊”論“中”,生成出一系列以“中”為核心的理學言語表征,呈現出散為“中正、中行、中和、中庸、中道”之萬事,復合為“誠”之一理的運動過程。其中,“誠”與“中”的關系是一山之兩景,用朱子的話則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從詮釋觀念看,朱子以“通權達變”論“中”,強調“默識心通”,以“權是時中”批判楊墨“失中”子莫“執中”。按朱子之意,只有把握“時中”,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效驗“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的圣人之學,以“圣人之身”踐行“天地萬物自然安泰”的圣人之教,依此敞開“萬物一體”的圣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