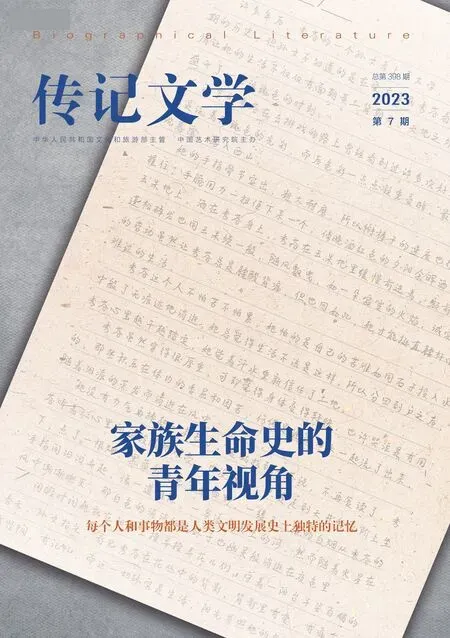八十年代師大校園里的先生們(七)
與 之

20 世紀(jì)80 年代的北京師范大學(xué)辦公樓
一
20 世紀(jì)80 年代的高等教育,因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恢復(fù)和發(fā)展而煥然一新。一大批碩士、博士研究生成為教學(xué)、科研的骨干,走上了課堂第一線。我們的專業(yè)課,許多都是由這些中青年教師承擔(dān)的。
雖然是研究生畢業(yè),不過因?yàn)椤拔母铩保眯├蠋熆缛敫咝V畷r(shí)已經(jīng)年近中年。他們拖家?guī)Э冢U居在師大光線暗淡的筒子樓里,與后來的“北漂”無異,不過他們大都淡然平靜,甚至信心十足。這一份底氣應(yīng)該來自于人們對(duì)新時(shí)期中國(guó)發(fā)展的憧憬與期待。今天在高校中特別流行的一些說法,諸如“青椒”“內(nèi)卷”或者“躺平”“佛系”等,我認(rèn)為完全無法描述那個(gè)時(shí)代的困難和選擇。前后差距懸殊,其根本原因還在于那時(shí)的“青教”大都經(jīng)歷過“文革”,曾經(jīng)的困境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一種人生的堅(jiān)韌。所以,這一批研究生教師的治學(xué)和教學(xué)都是比較成功的,因?yàn)樗麄儾粌H有前沿知識(shí),更有與共和國(guó)歷史轉(zhuǎn)折共節(jié)奏的人生感受,學(xué)術(shù)和生命完全打通了。
王富仁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文化批評(píng)和現(xiàn)代西方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方法結(jié)合起來閱讀魯迅,他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他的“立人”凝結(jié)著對(duì)自我人生的深切感受,這是能夠震撼我們的根本原因。
藍(lán)棣之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的碩士,師從現(xiàn)代文學(xué)學(xué)科創(chuàng)立人之一的唐弢教授。他將西方的精神分析學(xué)說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知人論世結(jié)合起來,開辟出一條獨(dú)具特色的中國(guó)式“癥候式分析”之路。
李復(fù)威是北京大學(xué)的碩士,他的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直接瞄準(zhǔn)新時(shí)期的文學(xué)“新潮”,帶給我們關(guān)于當(dāng)代文學(xué)最新動(dòng)態(tài)的豐富信息。
曹曉喬當(dāng)時(shí)剛剛從師大碩士畢業(yè),是黃會(huì)林教授的女弟子,相當(dāng)年輕。她對(duì)曹禺、田漢等現(xiàn)代戲劇家的講述細(xì)膩又不落俗套。曹老師后來去了美國(guó),師從舞動(dòng)治療先驅(qū)簡(jiǎn)·西格爾女士,據(jù)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高級(jí)心理咨詢師、高級(jí)舞動(dòng)治療師、阿米塔健康系統(tǒng)行為醫(yī)學(xué)院(AMITA Health Behavioral Medicine)表達(dá)藝術(shù)治療中心主任,也是師大研究生一個(gè)不斷進(jìn)取的樣板。
王一川是北京大學(xué)的碩士,師從有“文藝美學(xué)教父”之稱的胡經(jīng)之先生,在師大又繼續(xù)在職攻讀文藝學(xué)博士,導(dǎo)師為黃藥眠教授與童慶炳教授。他穿行于現(xiàn)代西方美學(xué)、現(xiàn)代漢語美學(xué)與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學(xué)之間,不斷開拓體驗(yàn)美學(xué)、修辭論美學(xué)、形象詩(shī)學(xué)、現(xiàn)代學(xué)等新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顯示了當(dāng)代文藝美學(xué)最具活力的路徑。在我們的大學(xué)時(shí)代,正是老師“體驗(yàn)美學(xué)”的探索期,這是他博士論文的題目,也是他“文藝美學(xué)”選修課的基本內(nèi)容。王老師上課,很少糾纏于一些抽象的概念和理論系統(tǒng),更喜歡從中外文藝現(xiàn)象中提煉獨(dú)特的藝術(shù)感悟,最后創(chuàng)造出一些新鮮的術(shù)語重新命名。其實(shí)“命名”本身就是學(xué)術(shù)思想拓展的重要標(biāo)志,王老師的創(chuàng)新精神是其課堂魅力的重要體現(xiàn)。王老師上課尤其重視對(duì)學(xué)生藝術(shù)“體驗(yàn)”的培養(yǎng)和訓(xùn)練,他常常在課上讓我們閱讀一些中外詩(shī)歌散文,然后組織大家展開討論,自由發(fā)揮,暢所欲言。有時(shí)候,他還安排一些課后的小論文,讓大家盡情展開思維的翅膀,然后挑選出一些有特色的文字在下一次課堂上朗讀講解,這對(duì)大家鼓勵(lì)很大。那個(gè)年代的本科課堂,討論還不流行,這樣的思維訓(xùn)練還是罕見的,同學(xué)們都頗感新奇,也興味盎然。
王老師是學(xué)術(shù)上的銳意創(chuàng)新者,但與我們交流時(shí)卻十分謙和,絕無絲毫的傲慢之態(tài)。因?yàn)樗撬拇ㄣ宕ㄈ耍矣侄嗔艘环萼l(xiāng)情,常常向他請(qǐng)教。一些重要的著作在圖書館借不到,有時(shí)也斗膽跑到王老師家中,在他的書柜里翻翻找找;向王老師求助,他也一律有求必應(yīng)。三年級(jí)的春季學(xué)期,王老師向我打聽:“從重慶乘船去三峽容易購(gòu)票嗎?我還沒有去過三峽,如果可能,今年夏天回四川之后,打算借道重慶去看看。”能夠?yàn)槔蠋煄兔κ菍W(xué)生最高興不過的事了,我當(dāng)即滿口應(yīng)承,大包大攬,說服他放心。那個(gè)年代,輪船和火車一樣,都是交通的大難題,一般都難以順利購(gòu)票。見我答應(yīng)得如此輕松,王老師似乎并不相信,一再叮囑不要勉強(qiáng)、不要為難。當(dāng)年暑期,我早早回家,在重慶等候。又提前許久到處打聽船期消息,動(dòng)員家中的親戚朋友尋找能夠通向港務(wù)局的線索。到8 月中旬,王老師從沐川老家給我寄來一信,說聽說夏天到三峽的旅客很多,購(gòu)票不便,他幾經(jīng)考慮,還是放棄旅行,讓我“警報(bào)解除”,安心在家過暑假。說實(shí)在的,失去了回報(bào)老師的這次機(jī)會(huì),我還是頗感遺憾,失落不已。當(dāng)然,以后與王老師交流多了,也慢慢知道,他本來就是一個(gè)細(xì)致、體貼的人。此番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因?yàn)椴辉附o我找麻煩。
二
雖然從80 年代開始,研究生就已經(jīng)逐步成為了高校最倚重的師資力量,但是在那個(gè)更加重視學(xué)術(shù)思想的新時(shí)期之初,學(xué)歷本身也還沒有成為人們傲視他人的理由。我們的研究生老師們,不乏個(gè)性鮮明、鋒芒畢露的人,但卻難以找到那種僅僅因?yàn)閷W(xué)歷、身份就驕矜自得的。相反,這些剛剛進(jìn)入師大的“青教”,大都高調(diào)做事,低調(diào)為人。
我們的現(xiàn)代文學(xué)老師錢振綱就是一位格外謹(jǐn)慎低調(diào)的人。錢老師1985 年于山東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導(dǎo)師是孫昌熙先生,那天由王富仁老師領(lǐng)進(jìn)教室介紹給大家。王老師說:“這是我的山東老鄉(xiāng),大家多關(guān)照啊!”說完呵呵地笑,錢老師也隨之不好意思地笑,倒好像是王老師的研究生一般。
錢老師是一位十分嚴(yán)謹(jǐn)求實(shí)的老師,治學(xué)上言必有據(jù),加之性格忠厚嚴(yán)肅、不茍言笑,授課時(shí)接著王富仁老師的課繼續(xù)上,不能不說是有壓力的。因?yàn)橥趵蠋熓谡n激情澎湃又邏輯嚴(yán)密,大開大合之間,歷史已經(jīng)越過了千山萬水,這與錢老師的謹(jǐn)慎小心迥然不同。剛剛從王老師的課堂上沉醉過來,一時(shí)間還多少有點(diǎn)不適應(yīng)。于是,課堂氣氛慢慢有了點(diǎn)變化,先前的熱烈逐漸轉(zhuǎn)為沉悶,曾經(jīng)的主動(dòng)參與也變?yōu)橄麡O躲避。細(xì)心的錢老師顯然也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diǎn)微妙的改變,不過他絲毫沒有批評(píng),也沒有煩躁,反而是更為認(rèn)真地備課、講課,課間還常常走到同學(xué)中間征求意見:“你們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嗎?都可以提出來,我們一起探討吧。”如果真有同學(xué)對(duì)課堂內(nèi)容發(fā)表不同觀點(diǎn),錢老師都會(huì)非常認(rèn)真地聽,不會(huì)立即反駁,也從來沒有流露出輕蔑不屑或者以勢(shì)壓人的強(qiáng)硬。他總是說:“你這個(gè)觀點(diǎn)也有意思,我們都再想想看,想想看。”當(dāng)然這也不是一種推脫或敷衍,錢老師是一個(gè)格外認(rèn)真的人,回過頭他真的就會(huì)去查找資料,重新提出更合適的論述或者一一回答那些疑問。其實(shí),有的同學(xué)的問題他自己也不一定想清楚了,就是那么即興一說,但錢老師一律鄭重其事,絕不馬虎。幾周下來,大家都開始為之折服了。
新時(shí)期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課堂,開始輸入一些新的視野和知識(shí)。例如,因?yàn)橄闹厩宓摹吨袊?guó)現(xiàn)代小說史》、司馬長(zhǎng)風(fēng)的《中國(guó)新文學(xué)史》這兩種史著,我們知曉了一些新的作家作品,認(rèn)知框架也因此大有不同。王富仁老師授課是以點(diǎn)帶面,僅魯迅一人就足足講了半個(gè)學(xué)期,其他好多作家都只能點(diǎn)到即止,寥寥數(shù)語帶過;錢老師的嚴(yán)謹(jǐn)決定了他的另外一種風(fēng)格,既不離開文學(xué)史教材太遠(yuǎn),又努力增加新的課程內(nèi)容,讓我們?cè)诜€(wěn)妥有序中掌握更多的文學(xué)史知識(shí)。當(dāng)時(shí),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推出了張愛玲的《傳奇》和錢鍾書的《圍城》,錢老師興沖沖地在課堂上廣而告之,表示他的住家離出版社不遠(yuǎn),愿意為大家購(gòu)買圖書。于是,連著好幾周,錢老師都提著沉甸甸的兩大包書籍穿過北京東西城,為大家捎來這新鮮出爐的文學(xué)著作。
錢老師90 年代后期在職讀博,師從王富仁老師,與我成了同門師兄弟,于是,這“輩分”就有點(diǎn)亂了,待我新世紀(jì)回到師大工作,我們又成了同一個(gè)教研室的同事。以后見面,我始終以當(dāng)年的“錢老師”相稱,只是錢老師堅(jiān)持以師兄弟視我,一來二往,也增添了另一份親近。
酸性氯化銅蝕刻劑,主要成分為氯化銅(CuCl2)和稀鹽酸(HCl),其原理與堿性法類似:利用二價(jià)銅(Cu2+)的絡(luò)離子將銅版氧化為一價(jià)銅(Cu+),實(shí)現(xiàn)腐蝕作用,并通過補(bǔ)充氧化劑(如雙氧水、氯酸鈉等)實(shí)現(xiàn)溶液的再生利用。酸性氯化銅的腐蝕速度很快,側(cè)蝕程度非常低,也更為耐用。但制版過程會(huì)釋放鹽酸氣體,有一定危害。
三
1997 年,王富仁老師在《戰(zhàn)略與管理》上發(fā)表了一篇很長(zhǎng)的論文《影響21 世紀(jì)中國(guó)文化的幾個(gè)現(xiàn)實(shí)因素》,其中提出了一個(gè)重要的判斷:“20 世紀(jì)末葉中國(guó)教育制度中發(fā)生的最巨大、有最深遠(yuǎn)文化意義的變化是研究生招生制度的確立。”“研究生在受教育階段完成的是從‘學(xué)習(xí)’到‘研究’的過渡。‘學(xué)習(xí)’是重要的,但對(duì)于一個(gè)研究生,它不是目的。如果‘學(xué)問’產(chǎn)生不了‘思想’,‘學(xué)問’對(duì)他是無用的。他的‘思想’不是由他學(xué)習(xí)所得的‘學(xué)問’自身所有的,而是他自己的思維活動(dòng)的結(jié)果。它不是選擇性的,而是創(chuàng)造性的;不是二元對(duì)立的形式,而是多元生一的形式。他做的主要不是在原有的正確與錯(cuò)誤、好與壞、善與惡、有價(jià)值與無價(jià)值之間進(jìn)行平面的選擇,而是在眾多有相對(duì)合理性的文化成果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自己的獨(dú)立創(chuàng)造。”[1]在那些年輕的研究生教師身上,我們感受最深的就是這樣的創(chuàng)造性,是他們突入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前沿的發(fā)現(xiàn)讓我們目睹了這個(gè)熟悉的世界的諸多驚喜,激發(fā)了我們由衷的好奇,也示范了獨(dú)立思考、獨(dú)立創(chuàng)造的可能路徑。
作為當(dāng)代文藝思想的挑戰(zhàn)者,童慶炳老師所率領(lǐng)的團(tuán)隊(duì)以集體沖鋒的姿態(tài)不斷在本科生里造成驚呼般的效應(yīng):王一川老師的“審美體驗(yàn)”、羅鋼老師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藝思想與西方文學(xué)理論的匯流”、孫津老師的“基督教與美學(xué)”……直到80年代最后畢業(yè)、就要留校任教的陶東風(fēng)老師的“文學(xué)批評(píng)”,莫不如此。

王富仁老師的題簽
但最讓我們意外驚喜的卻是古代文學(xué)專業(yè)年輕的研究生們。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古代文學(xué)的知識(shí)系統(tǒng)與價(jià)值傳承天然與現(xiàn)代文化的發(fā)生構(gòu)成某種歷史的隔膜甚至沖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以古代文學(xué)為“中華文化當(dāng)然的象征”,而視“五四”新文化為傳統(tǒng)的破壞者這樣的說辭。其實(shí),就像王富仁老師所深刻指出的那樣,真正的文化創(chuàng)造恰恰是走出了二元對(duì)立,是在古今中外的巨大歷史情景之中展開的自由思想與自由創(chuàng)造。在這里,每一個(gè)從師大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中承受教育又成長(zhǎng)起來的學(xué)子都可能有著深深的感激,因?yàn)槲覀兯邮艿幕緜鹘y(tǒng)文化教育從來就沒有制造過文化的割裂與文明的對(duì)立,寬闊的視野和自由的創(chuàng)造是深植于師大沃土的學(xué)術(shù)品格,今天所謂的“章黃國(guó)學(xué)”同時(shí)包含著傳統(tǒng)小學(xué)的功力與現(xiàn)代民族關(guān)懷的情志。
1984 年10 月,王富仁老師的博士論文答辯在師大舉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歷史上第一次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答辯,出現(xiàn)在答辯委員席上的專家既有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權(quán)威唐弢、嚴(yán)家炎、王士菁,也有古代文學(xué)的權(quán)威郭預(yù)衡、民間文學(xué)的權(quán)威鐘敬文,這就是師大學(xué)術(shù)的格局和氣度。郭預(yù)衡先生是中國(guó)古代散文研究大家,自稱“平生為學(xué),服膺魯迅”,傳說他招收的古代文學(xué)研究生,入學(xué)以后都必須通讀《魯迅全集》。
當(dāng)年,擔(dān)任師大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課程的研究生老師就為我們展現(xiàn)了這種迷人的師大風(fēng)格與師大氣派。謝思煒老師講授唐宋詩(shī)歌,論及杜甫的自傳詩(shī),擴(kuò)展到中國(guó)和西方的自傳詩(shī)傳統(tǒng)問題,令大家眼界大開。他對(duì)西方的闡釋學(xué)和文本細(xì)讀也時(shí)有借鑒,講起李商隱膾炙人口的《夜雨寄北》,他提出了一個(gè)問題:“古典詩(shī)歌往往都是惜墨如金的,有時(shí)同一字出現(xiàn)兩次都會(huì)被當(dāng)作敗筆,而這里詩(shī)人卻讓‘巴山夜雨’四字重復(fù)了兩次。這是為什么呢?是作者詩(shī)才的匱乏嗎?”大家都立即精神一振,洗耳恭聽。來自川東巴山之地的我,對(duì)這首詩(shī)歌所描寫的“夜雨”場(chǎng)景是再熟悉不過了,聽謝老師細(xì)細(xì)道來,更感到親切別致,大受啟發(fā)。記得那一天,謝老師通過詩(shī)歌語言修辭的剖析告訴我們,正是因?yàn)檫@四個(gè)字的重疊,李商隱盡現(xiàn)了人生命運(yùn)的重復(fù)與回環(huán),這就從時(shí)空的疊印變化中呈現(xiàn)了人間的悲歡離合,是詩(shī)意的“鏡像之美”。
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郭英德老師,他為我們講授元代文學(xué)時(shí),關(guān)于元雜劇的論述引起了我們這批戲劇愛好者的濃厚興趣。當(dāng)時(shí)的課代表是魏崇武,我們偷偷商量,能否請(qǐng)郭老師為我們對(duì)比講一講元雜劇與西方古典戲劇如莎士比亞戲劇。當(dāng)然,我們也知道,這個(gè)要求可能比較苛刻,因?yàn)楣蠋熅褪菍iT研究元代文學(xué)的,他沒有義務(wù)也很可能沒有時(shí)間再去考察西方戲劇,比較文學(xué)更不是他的研究方向。沒有想到的是,在魏崇武大膽請(qǐng)求之后,郭老師竟然十分爽快地答應(yīng)了。在約好的一個(gè)周五的下午,我們一行數(shù)人按時(shí)來到位于主樓6 樓中文系的古代文學(xué)教研室,郭老師已經(jīng)提前端坐在辦公桌前等候了。也沒有多余的客套,郭老師就操著一口“福建普通話”開講了,他自由穿梭于中國(guó)文明與西方文明,深入淺出,旁征博引,娓娓道來之間,一幅中西戲劇文化的精彩圖畫徐徐展開。令人驚訝的是,他對(duì)西方戲劇,特別是莎士比亞戲劇的了解和熟悉,絲毫不亞于元雜劇,而且因?yàn)楸容^文學(xué)視野的引入,傳統(tǒng)中國(guó)的文化與西方的文化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開掘和發(fā)現(xiàn)。這一場(chǎng)“學(xué)術(shù)小灶”進(jìn)行了兩個(gè)小時(shí)。郭老師講畢,我們相互對(duì)視,暗自贊嘆,沒想到在古代文學(xué)的課堂上還會(huì)有如此驚喜的收獲!
從此以后,在我寢室的個(gè)人書架上,除了現(xiàn)代詩(shī)歌和魯迅的收藏之外,也悄悄增添了元代文學(xué)的內(nèi)容,而我的朋友魏崇武則在本科畢業(yè)后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xué)元代文學(xué)大家李修生教授的碩士,碩士畢業(yè)后,再投郭英德老師門下,成為了元代文學(xué)與文獻(xiàn)研究的博士。如今的魏崇武也是師大文學(xué)院一名優(yōu)秀的古代文學(xué)教授,指導(dǎo)元代文學(xué)方向的博士、碩士研究生。我推崇“五四”,他熱愛古典,我們學(xué)術(shù)方向有別,但從來沒有覺得彼此有過明顯的文化對(duì)立與精神隔膜,他對(duì)我們當(dāng)年共同的本科老師王富仁同樣深懷敬仰,就像我對(duì)他的元代文學(xué)方向依然興趣盎然一樣。后來我們每每相見,還不時(shí)提到郭英德老師當(dāng)年課堂上的種種,也會(huì)憶起當(dāng)年中文系古代文學(xué)教研室中的那堂小課,盡管80 年代的主樓早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而我們也都年過半百了。

郭英德老師在師大授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