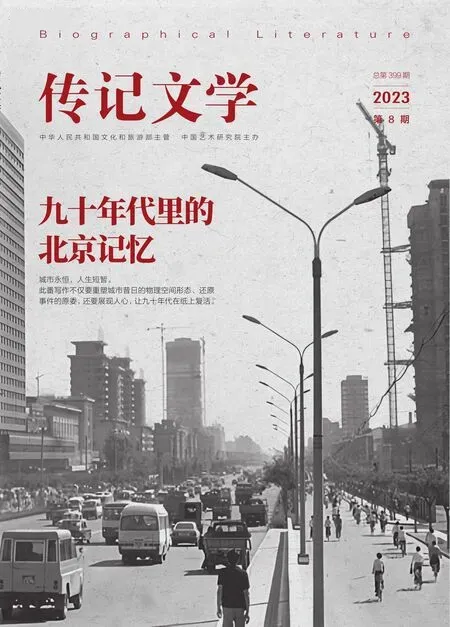八十年代師大校園里的先生們(八)
與 之
一
新時期之初的1980 到1984 級,師大中文本科教育都是五年制。這樣的制度在當時設計之初有過什么樣的豐富考量不得而知,但是與今天的教育學制相比,專業課程時間更長、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更多,卻是無疑的。在本科畢業時召開的就業大會上,負責老師都用“準研究生”來激勵大家,至少在那一瞬間,我們也多少有點自命不凡的感覺了。
那個年代,出現在本科生課堂上的都是中文系最優秀的師資。除了一批剛剛碩士、博士畢業的青年教師,主力擔綱的還包括一大批于60 年代中文系畢業任教的中年教師,他們學問扎實,學風穩健,如古代漢語的崔樞華老師、現代漢語的李大魁老師、語言學概論的岑運強老師、古代文論的李壯鷹老師、寫作學的侯玉珍老師。50 年代畢業任教的老師則已經是學術帶頭人了,他們也親授本科基礎課,例如先秦兩漢文學的聶石樵老師、鄧魁英老師、韓兆琦老師,古代漢語的許嘉璐老師,外國文學的陳惇老師、陶德臻老師,當代文學的劉錫慶老師,兒童文學的浦漫汀老師、張美妮老師,中文工具書使用法的祝鼎民老師,甚至更資深的前輩啟功先生、鐘敬文先生、陸宗達先生等都還不時舉辦講座。這些國內中文的大師級人物、優秀學者從根本上提升了80 年代大學教育的境界,真的讓一批本科生找到了“準研究生”的感覺。
那時,師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教育是怎樣的呢?可能不同的學科、導師各有特點吧,不過在當時我們的口耳相傳中,最有名的說法還是“放羊式”,據說并沒有一成不變的課堂教學,導師對研究生的指導主要是在談話、聊天中進行,當然這樣的談話也是不定時、不定點的,常常臨時起意,隨機而行,甚至主題也不固定、不預設。楊占升老師帶領王富仁、金宏達赴史家胡同求教于李何林先生時,可能還有相對確定的時間安排,而王富仁老師在80 年代后期自己指導碩士生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固定的課程了。后來,有其他高校的學者向王老師討教指導博士生的經驗,咨詢都應該開設哪些課程,王老師哈哈一樂:“都考上博士生了,還需要我上課嗎?!”直到千禧之年我再回師大,師從王老師讀博,因為已經熟悉當時的研究生培養規則,所以對課程的按時完成還是相當重視的,但是王老師還是沒有開課的意思。學期結束,我未免心中忐忑,找到王老師主動詢問課程與成績的事情,王老師說得輕描淡寫:“你交兩三篇論文給我,我根據你的論文打個分數即可。”于是,我趕緊上交了早已經寫好的幾篇論文,王老師翻了翻,一篇名為《論“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學運動》,他說:“這一篇就記作‘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課程成績吧。”另有一篇談穆旦詩歌創作的則記作了“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成績,最后一篇《中國現代文學史課程改革芻議》讓老師猶豫了一會兒:“哎呀,我們也沒有教育改革之類的課程啊,這一篇就算啦,有兩門課的學分就夠了!”雖然我對師大的研究生教育方式還算了解,但也沒有想到它一直堅持了二十來年,當時還是有點意外的,更沒有想到課程成績甚至課程名目還可以根據學生上交的作業情況靈活確定。80 年代的教育傳統一直延續到新世紀初年,在我已經重回師大工作之后,才開始調整和“規范”起來的。
新時期之初,師大研究生課程教育的這一模式當然不只是屬于現代文學專業,教過我們宋代文學的謝思煒老師也是出身師大的研究生。他在回憶中提到,師大古代文學導師對學生的指導是具體的,不過“我們那個時候上課是不太多的,也不像后來規定你必須要修多少學分,必須得開多少課。這種要求當時都不是很死。老師就是布置一些這學期要讀什么,最后每學期都要提交一些讀書報告、小論文”,“那個時候老師指導我們更主要的一個方式就是和我們討論問題,我們如果有什么問題也隨時都可以問老師。像啟先生,他有什么想法都會跟我們講。這種方式對于學生來講是很有幫助很有收獲的。你會經常接觸老師,去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而且老師也經常會想要聽聽我們的看法,聽聽我們對問題的了解,也會讓我們介紹一些學術上新的觀點。沒有什么固定的討論,都是一些日常性的交流,老師也沒有要求你必須什么時間要來參加討論”[1]。
沒有了程式化模式的約束,師大研究生的“教育”實際上就是以最靈活多變的方式對人的興趣、思維的激發,是思想在日常性的滋養中發展,是創造能力在思想的激蕩中增長。沒有固定的時間,因為自我的成長隨時都可以開始;沒有確定的地點,因為生命的感悟需要靈活多變的環境;沒有管理制度的僵硬規則,因為人的發展各不相同,研究生、本科生、進修生、旁聽生都可能出現蛻變的要求和機緣。是的,師大的教育開放曾經給許多人一種平等的機緣,讓他們得以越過層層的關隘,直接受惠于名流大師的熏陶和關愛,讓中文教育史上我們這些特殊的“五年制本科生”也大受鼓舞,一度產生了“準研究生”的幻覺。
二
我們都是80 年代與老師們頻繁交談的受益者,現在想來,這種旁聽交談或參與交談所獲得的信息量可能要遠遠大于今天的研究生課程,它的自由、靈活,它對個性化思想及人的情緒情感狀態的寬容,更是后者難以呈現的。
當然,這樣的情形能夠出現,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老師們的思想交流得允許本科生加入。無論是在家里還是其他場合,老師沒有輕視他們,愿意與這些年輕幼稚的孩子分享思想;學者也胸懷寬廣,沒有把自己封鎖在自己營造的小圈子之中。學術交流不分年齡、身份,一律平等。我不知道今天的專家學者是不是都有這樣的雅量,但至少在80 年代,在我們師長們那里是理所當然的。80年代初,啟功先生家是誰都可以敲門而入的。1978 級的趙曉笛就曾在文章《啟功先生對北師大78 級學生的厚愛》(收錄于周星主編的自印班書《歲月靜好,情誼悠長——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78 級3 班40 年記憶》)中回憶,在不勝其擾的時候,啟功先生可能阻擋社會上的造訪者,在大門上貼出“大熊貓,病了,請勿干擾”,但對本科同學的訪問卻不會拒絕,他還不厭其煩地為畢業的同學一一題字留念:“我們畢業時,許多同學登門求字,啟先生都熱情接待,還根據每個學生的畢業去向,選擇不同內容的題詞,加以勉勵。”直到我們的大學時代,都還有機會進入先生的家中。
中青年老師,特別是那批剛剛畢業任教的研究生老師,更是對學生來者不拒。在80 年代如火如荼的思想啟蒙浪潮中,在師大校園的許多簡陋的教師公寓里,到處都圍坐著許多大學生,他們認真傾聽老師們的精辟論述,也不時斗膽提出自己的見解;或相互辯駁之后,祈請老師的指點,探尋更有深度的答案。這種求知求真的執著和主動,已經遠遠超過了本科課堂的學習,就是90 年代以后日漸成熟和規范的研究生課堂討論也可能無法比擬。因為前者更帶有一種由衷的激情,是發自內心的不可遏制的精神的求索、靈魂的探險。85 級本科出身的作家楊葵始終記得藍棣之老師家的聚談所造成的精神震動:“藍老師家里經常坐滿一撥又一撥的學生,從早到晚。我同寢室一個同學,一天深夜回來,臉上放著光,問他哪兒打了雞血,答曰剛在藍老師那兒長談。那一夜這位同學翻來覆去睡不著,神經病一樣地反復念叨:藍老師了不起。”[2]
思想交流只是自我發展的第一步,邁出了這一步,個人的成長也就有了不可逆轉的趨勢。今天的大學生,可能在一開始就被假定為基礎知識的接受者,根本與學術的創造無關;只有到碩士研究生階段,才有了一些個性化的期許;進入博士研究生之后才被賦予了創造的使命。而80 年代的大學教育,則顯然打破了這樣的標準化程序,老師常常將所有走近他學術領域的學生平等對待,直接從本科學生中物色、發掘和拔擢優秀的學術苗子。受到老師的鼓勵之后,本科學生也信心滿滿,很早就立下雄心壯志,試圖在自己喜愛的學術領域中一展身手。這里最重要的可能還不是時間和教育階段上的跨越,而是一種學術心性的“養成”。當學術之路不再是個人學習的一種程序化選擇,不是未來就業壓力的一種解決方式,那么作為個人理想的意義就得到了更多的保留,它首先關乎自我的興趣、情感的關切,以及生命的目標。在大學,我們常常以羨慕的口吻談論那些才華橫溢的同學,例如陳雷對現代新詩的評論如何得到了藍棣之老師的褒獎,他本科三年級寫下的關于馮至詩歌的論文被藍老師推薦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我們下一個年級的同學楊葵也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了關于卞之琳詩歌的論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對今天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生來說,是“高不可攀”的核心期刊,對80 年代的大學生來說,卻是完全有機會嶄露頭角的陣地。每當議及陳雷、楊葵,大家只有贊嘆,沒有嫉妒,因為這學術上的成果一時也無法轉化為看得見的利益競爭,更多的還是個人思想與才華的自由展示。學術,只有在純粹才華的自我欣賞之中,才會給大家帶來情感的愉悅。除了這幾位“早慧”的青年學人,我們前前后后的同學徐可、余翔、魏崇武、過常寶、張生、魏家川、葉世祥等也都是少年才子,英氣逼人,而1985 級的一批詩人則簇擁在藍棣之、任洪淵老師的周圍,最后形成了當代詩壇上霸氣的“新口語詩派”,當然也都是這一思想氛圍的正常結果。

曾經的樂群餐廳

曾經的服務樓書店
三
不僅是課外的思想交流,就是原本規范嚴謹的大學課堂,也因為有這一教育氛圍的存在而顯得與眾不同了。
大學一年級的課程以寫作、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及文學概論為主,總體上還是規則清晰的,與剛剛從中學課堂走過來的想象差不太多。但是,進入二年級,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因為現代文學課帶來的思想沖擊,慢慢地,似乎我們的認知方式、學習方式也逐漸開始了蛻變。
最大的一次震驚出現在大學二年級上半學期的現代文學課的考試中。應同學們的要求,主講教師王富仁專門安排了一次“考前輔導”。本來這也是師大中文課的常態,老師們平時授課大多十分嚴格、一絲不茍,不過臨到考前,一般都不會故作矜持,以莫測高深的姿態令大家精神緊張,他們大多會安排一次“考前輔導”或“答疑”,其實就是劃定一些考試范圍,讓大家放松心情、輕裝上陣。每當這個時候,平時不茍言笑的老師也都和顏悅色,對同學們刨根問底的追蹤有問必答,對那些明顯旁敲側擊的試探微笑回應,也不回避適當的暗示和指引。這一天,王老師的考前輔導也吸引了很多同學,大家一如既往地準備好了各種各樣的推測和試探,準備在答疑環節連環發問,捕獲最充分的信息。然而,就像他的“啟蒙第一課”那樣,王老師再一次讓大家震動不已。
那天,在全班同學熱烈的目光中,王老師不疾不徐地走上講臺,翻開一個筆記本,微笑著看了看臺下,然后有條不紊地開始了介紹,他并沒有和其他老師一樣,重復說明考試的意義、回顧學期的重點等,而是直截了當地交代起了現代文學考試應該掌握的題型,包括史實填空、名詞解釋、簡答與論述四大板塊,然后繼續推進,有哪些史實我們可以進一步熟悉,哪些名詞解釋值得強化記憶,哪些文學史常識可以簡要梳理作答,又有哪些重要的論題需要我們認真思考、詳盡展開。一開始,大家還只是飛速記錄,生怕漏掉了什么暗示,結果發現,這里根本就沒有任何多余的暗示,有的都是簡潔明了的陳述。越到后來,大家反而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從數量上看,幾乎就是一套完整無缺的“真題”,可能嗎?王老師的期末考試可能如此寬松嗎?待全部問題道完,大家面面相覷,不知道是該熱烈鼓掌還是繼續發問,以釋心中疑慮。王老師好像猜中了大家的心思,輕輕地合上筆記,講出了最后的要求:“就是這些問題了,需要大家在考試中認真回答。題目都不難,你們盡可以放下包袱,盡情發揮。如果能夠拋開死記硬背,不受教材觀點的束縛,特別是能夠提出與我上課所講的不一樣的思想,那就是大家本學期最大的收獲。”這一句總結真的是擲地有聲,言至于此,好像所有的試探、推測都失去了意義,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創見,這就是最后真正的考試,連對老師講述的習慣性背誦都被輕輕地推開了,而我們也再不好意思向此時此刻的王老師“套題”了。這樣的“考前輔導”如此溫暖體貼,卻又如此嚴肅認真,它的公開、它的大膽、它的獨創、它的嚴謹,可能在我們考試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王老師說完,在同學們的欣喜、感激以及一時還難以表述的新的忐忑中離開了。接下來的那幾天,則是我們既興奮又忙碌的日子,大家都紛紛鉆進圖書館,查閱各種資料,盡快努力充實自己,期望在最后的考場上一展才華,贏得老師由衷的青睞,雖然依然忙碌不已,但是與其他的考前狀態不同,這里沒有了莫名的焦慮,反倒多了幾分內在的激昂、幾分深切的期待。也是在那一次,我認認真真梳理了對現代文學的思考,勉力提出了一些大膽的概括和自認為還算新穎的設想,最后得到了進大學以后的第一個高分:97 分。少年人年輕氣盛,后來還向王老師發過問:“這3 分都扣在哪里了?”那時,王老師已經對我相當熟悉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這還用問嗎,怎么可能給出100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