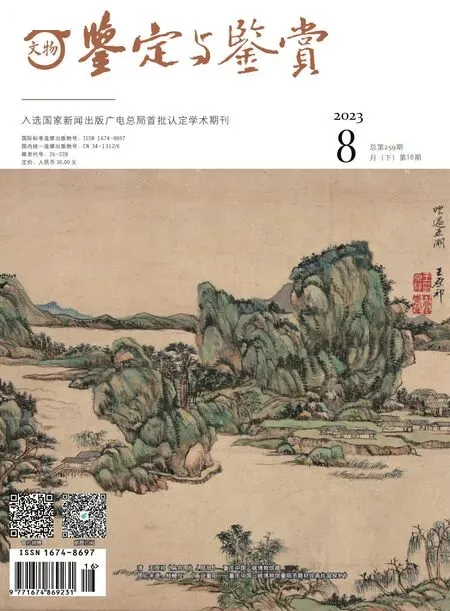遼契丹出土手飾研究綜述
孫倩
(西北大學,陜西 西安 710119)
經過與中原文化深入交流融合后,遼契丹族建立了一個具有特色的王朝(916-1125)—遼朝。在其興盛時期,遼朝掌握了現今中國東北、內蒙古、河北等地區,與南北宋朝交往頻繁。遼國的藝術風格受到了唐代文化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獨特的藝術特色。遼契丹手飾作為重要的個人裝飾品,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審美觀念、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
1 遼契丹手飾的出土發現
本文中所涉及的“手飾”一詞,其概念借鑒于《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中關于首飾的定義,“首飾,裝飾品的總稱。包括發飾、耳飾、頸飾、手飾等。”①在《中國服飾名物考》一書第七編專題內容也稱“手飾考”,因此手飾意指裝飾手部的飾品,如臂飾、手鐲、戒指等。本文主要關注散布于內蒙古、遼寧、河北等地的數十座遼代墓葬,對于已發表并可查閱的墓葬資料及發掘報告進行系統的整理和概括。近年來,遼代墓葬的大量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諸多豐富的研究資料,其中又以含有圖像資料的墓葬最為重要。盡管有不少考古發掘簡報已經發表,但關于遼契丹手飾的相關資料仍有許多尚未及時公開發表,我們僅能從主要的期刊書目網站或前人的研究中探尋一二。
另外較為惋惜的是,部分墓葬明顯有后人擾動的痕跡,丟失情況較為嚴重,使原墓葬中陪葬物全貌已不可考,原先是否有手飾也難以考證。這些有明顯被盜痕跡的遼代墓葬有遼寧建平朱碌科遼墓、二八地M2遼墓、后劉東屯M2遼墓、葉茂臺M8遼墓、葉茂臺遼肖義墓、梯子廟M3遼墓、梯子廟M4遼墓、科右中旗雙龍崗M3遼墓、義縣清河門M3遼墓等。據不完全統計,遼代墓葬所發現手飾共83件,其中手鐲28件(圖1)、戒指43件(圖2)、臂飾12件。

圖1 遼寧建平朱碌科遼墓鏨梅花紋金手鐲②
2 遼契丹手飾的研究現狀
遼契丹手飾作為遼契丹文化中的重要裝飾品之一,其出土數量不少,然而,與耳飾、發冠、帶銙等服飾研究相比,對于遼契丹手飾的專題研究在現有文獻中幾乎尚未涉及,其研究范疇往往被納入金銀器或服飾、首飾研究的討論中。有關遼契丹手飾及反映其文化內涵的研究文獻,大致可分為三類。
2.1 遼代金銀器研究
朱天舒先生在其圖書專著《遼代金銀器》(1998)中,收錄了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初發現和發掘的30余座墓葬和寺塔地宮中出土的遼代金銀器,依據遼墓的分期研究成果,對這些金銀器進行了分期劃分和演變規律總結。他還對遼代金銀器的工藝裝飾和紋樣進行了分章論述,共分類出26種紋樣。在文化探討一章中,他提出遼代金銀器文化的豐富與發展是其廣泛吸收外族文化的結果,除了有構成其主體的唐文化和宋文化因素以外,還有突厥文化、中亞文化等成分。較為特別的是,在該著作最后一章專門討論了遼代金銀器的來源和制作。可惜的是,在遼代葬具和服飾一章中著重探討了遼冠和帶飾,對于手飾部分的敘寫較少,只點出遼契丹手鐲和戒指形制非常有特點。此外,整部書作對遼代金銀器的研究偏重于造型藝術,且收集的資料不夠全面。
《論遼代早中期金銀器的唐代風格》(1999)一文中,張景明先生通過對遼代金銀器的對比研究,將遼契丹金銀器進行分期,并對各期特征加以論述,在與唐代金銀器的器形、裝飾和工藝對比后,認為遼代早中期金銀器的發展吸收繼承了唐代金銀器風格。文中提及手飾較少,但首先認識到遼金銀器與唐代金銀器的風格關聯,對后來者啟發較大。在后續手飾研究中,可延續此思路對比研究,探索遼契丹手飾與唐代手飾的內涵關系和演變。
《契丹族金銀器的動物紋飾》(2003)一文中,黃雪寅先生以出土資料為證,對遼契丹金銀器上展現出的動物紋樣進行分類論述,共總結出18種動物紋。在個別動物紋樣類別中提及了手飾并以其為典型文物舉例列出。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將契丹動物紋樣與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如匈奴、鮮卑族和突厥等進行比較,最后得出結論:遼契丹的動物紋飾既有草原獨特風格,又在與其他民族和地區的文化融合交流中大量吸收中原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動物紋飾,遼代是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金銀器發展的高峰。
趙運龍在其碩士論文《遼代墓葬出土金銀器歷史學研究》(2011)中,采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結合考古學、歷史學、民俗學、類型學、統計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對遼代墓葬出土的金銀器進行系統研究。文章分為緒論、正文和結語三部分。緒論主要介紹了該文研究的概況、特色和意義。正文分五個部分,依次闡述了遼代墓葬出土金銀器的分布情況、類型及特征、斷代分期、歷史淵源以及在遼史研究中的作用。結語對全文進行了概括,指出遼代墓葬出土的金銀器體現出了契丹多元文化的發展和融合,以及契丹族固有的民族特色,同時也展示了金銀器在遼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張景明《遼代金銀器研究》(2013)專著中,借助較為豐富的文物資料,在以往論文研究的基礎上,對遼金銀器進行了分期分類研究,并對遼代金銀器的文化內涵和外來因素做出探討,分析并總結出遼代金銀器所反映出的社會生活與風俗習慣。
樊進在其博士論文《遼代金銀器設計研究》(2017)中,從歷史淵源和文化因素、日常使用和生活方式、材料和工藝特點、造型和紋飾特征、審美和文化意義等五個方面探討了遼代手工藝和金銀制品,并運用設計藝術學理論,參考考古學的分類方法,綜合運用藝術學、美學、圖像學、工程學、人類文化學、社會學等多種研究方法,研究和探討遼代金銀制品的設計理念、生活時尚和審美文化。通過對遼代金銀制品的全面研究,闡釋了遼代金銀制品創作背后的設計目的、設計理論和特色,展現其獨特的設計智慧,豐富了中國傳統造物設計的文明成果。
王春燕《遼代金銀器研究》(2020)一書是在其博士學位論文《遼代金銀器研究》(2015)的基礎上,以對遼代金銀器考古資料的初步整理為依據,對遼代金銀器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探討,將遼代金銀器分為人體裝飾品、工具、馬具、容器、葬具五大類,通過對這五大類分型與組合的研究,初步建立起遼代金銀器的大體構成體系。然后,探索了遼代金銀器中不同器形、不同材質、不同種類金銀器在歷史分期中的差異和變化。最后,通過分析對遼代金銀器所揭示的社會性和文化因素進行探索,認為遼代金銀器的文化因素由契丹文化因素、唐文化因素、宋文化因素、佛教文化因素、道教文化因素、西域胡文化因素和鮮卑文化因素共同構成。
2.2 遼代服飾和首飾研究
相對遼代金銀器研究而言,遼契丹首飾專題研究更少,僅有兩篇碩士學位論文。除此之外,便散見于遼代服飾研究中。另有一些關于遼代文物圖錄的出版,大大豐富了遼代首飾文物資料,為后續研究提供了較大的便利。如香港私人收藏展覽集《金翠流芳—夢蝶軒藏中國古代飾物》(1999);內蒙古博物院舉辦“文明之旅—中國北方草原古代文明攬勝”“草原牧歌—契丹文物精華展”精品展,出版圖書圖錄《草原華章:契丹文物精華展》(2010)(圖3、圖4)。

圖4 雙龍紋金手鐲⑤
在《遼代契丹人的冠帽、鞋靴與佩飾考述》(1994)一文中,張國慶先生通過對文獻和遼代墓葬出土的服飾、佩飾等考古資料的研究,深入探討了契丹人服飾文化的形制和內涵。在文章末段簡略提到了遼契丹的手飾和臂飾。
在《契丹佩飾考述──契丹衣飾文化研究之四》(1998)一文中,田廣林先生對契丹的帶飾、頭飾、項飾和手臂飾進行綜合性考述,進一步加深對于契丹衣飾文化的理解和認識。同樣,手飾和臂飾只出現在文章末段,并簡略介紹帶過。
許曉東先生的《契丹人的金玉首飾》(2007)一文,首次對遼代契丹族的金玉首飾進行綜合性研究。文中以遼文化圈內墓葬、窖藏所見金玉首飾為依據,結合傳世品,對契丹人的頭飾、耳飾、瓔珞、項飾、手鐲、指環等作初步的梳理。文章共分為五個部分,手鐲、戒指各占其一,結合高清彩色圖片,向讀者清晰展示了遼契丹手飾特色和瑰麗之姿。
張倩在其碩士論文《遼代契丹族女性首飾研究》(2015)中,使用考古學、歷史學、文物學、工藝美術學和民族學的多元研究方法,全面整理了遼契丹女性首飾的相關文物資料,并對這些女性首飾的類別和形制、裝飾紋飾以及材質、制作工藝等進行逐一梳理,并將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資料相結合,對遼代契丹婦女首飾的文化內涵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馬青青在其碩士論文《遼代首飾研究》(2021)中,以發掘所見的遼首飾文物資料為基礎,結合遼墓壁畫、墓志和碑刻等圖像資料和文字資料,對遼代首飾進行時空雙重劃分,研究分析遼首飾造型裝飾藝術與材質工藝,對其所反映的遼代社會家庭生活和精神追求進行探討,提出遼代首飾可反映出契丹人漢化與漢人契丹化,認為遼代契丹人漢化是有選擇性的螺旋上升的過程。
2.3 個例墓葬研究
對遼契丹個例墓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陳國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和吐爾基山遼墓等,因其墓主身份高貴,出土了較為豐富的隨葬品,它們均被評為當時的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但牽涉到手飾的墓葬有僅有陳國公主墓和耶律羽之墓。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哲里木盟博物館所編著的《遼陳國公主墓》(1993)中,對陳國公主墓的發掘進行詳盡報告,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隨葬品被一一記述,并基本都有配圖。在報告后面,另附有一篇關于陳國公主墓的初步研究,對墓葬形制、隨葬品和墓中壁畫進行了詳細討論。
《探尋逝去的王朝—遼耶律羽之墓》(2004)以耶律羽之墓的發掘過程為線索,以出土實物為例,對遼契丹王朝進行了詳細而全面的介紹。文中配有大量彩圖,可謂雅俗共賞。
《遼代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出土的首飾及其文化內涵》(2014)一文中,對契丹貴族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首飾進行梳理,對頭飾、耳飾、項飾、手臂飾進行了簡單的工藝分析,并對其文化內涵展開思考。
3 遼契丹手飾研究展望
遼契丹手飾的研究歷來都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前人在對其進行研究時,往往將它們與金銀器、服飾等雜糅在一起,缺乏系統性和深度。因此,對于遼契丹手飾的獨立性、特殊性和研究價值的認識亟待提升。遼朝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多民族融合的朝代之一。契丹族作為遼朝的主要族群之一,契丹族文化對遼朝的發展和歷史留下了重要的印記。為了更好地探討遼契丹手飾在文化和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開展更多的專題研究,對其類型組合、特有紋飾等方面進行深入分析。對遼契丹手飾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3.1 分期分型研究
根據遼史和遼墓研究成果,可以將現有出土的遼契丹手飾進行分期分型研究,并加入地域因素的考慮。如可以按照手飾的材料、形狀、紋飾等進行分類,同時考慮地域因素,比較各地出土的手飾在材料、形狀、紋飾等方面的異同,從而推斷出各地區的文化特點和文化交流情況。
3.2 結合墓葬信息研究
對遼墓發掘報告的整理十分重要,對可查閱的所有遼墓發掘報告進行整理,并結合墓主身份、墓室年代等墓葬信息,同時結合遼契丹手飾進行研究,它們可以相互佐證,或許能得出某些新結論。比如,可以研究不同身份墓主所佩戴的手飾類型和手飾數量的差異,探究契丹族社會的等級制度和階層差異,分析契丹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情況。
3.3 造型工藝研究
通過手飾的紋飾和工藝可以窺見遼契丹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遼契丹手飾的紋飾多為幾何圖案和動植物形象,這些圖案和形象不僅具有美學價值,還反映了當時的宗教信仰和生產生活習慣。同時,遼契丹手飾的工藝精湛,主要采用金、銀、銅等貴重金屬,并結合寶石等材料制作而成。這些手工制品不僅展示了遼契丹民族的工藝水平,也反映了遼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對整理出的遼契丹手飾,要深入分析其紋飾和制作工藝,這對揭示遼契丹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3.4 社會價值和文化內涵研究
結合壁畫、文獻等資料,對手飾的社會功用和文化內涵進行深入探討。例如,遼契丹手飾中常見的龍形圖案和動植物形象具有一定神話色彩和精神象征意義,這明顯反映出當時遼契丹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特征。另外,參考金銀器研究成果,將遼契丹手飾與其他民族和朝代的手飾進行比較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唐宋文化、突厥文化和鮮卑文化等對遼契丹文化思想的具體影響。通過對比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遼契丹文化的多元性和開放性,以及它在我國歷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注釋
①高春明,周汛.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J].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
②馮永謙.遼寧省建平、新民的三座遼墓[J].考古,1960(2):13.
③項春松.克什克騰旗二八地一、二號遼墓[J].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00):80-90,6-7.
④⑤山西博物院,內蒙古博物院.草原華章:契丹文物精華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