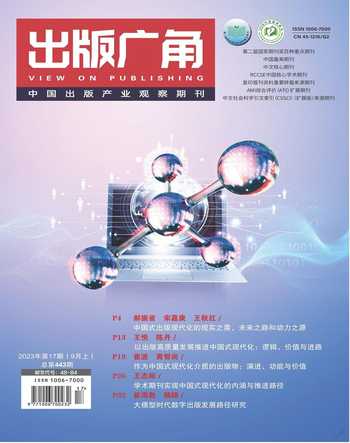文化記憶視域下主題出版的技術進路與價值旨歸
劉暢?胡作法
【摘要】時代出版打造的“覺醒年代”系列圖書,取得市場和口碑雙效俱佳的業績。分析其技術進路:黨史群像的記憶建構、記憶之場的文化喚醒、從劇本到小說的經典化處理,可總結其價值旨歸,即主題性是文化記憶的呼應與表達,藝術性是文化記憶的內在要求,人民性是文化記憶的基本內核。以文化記憶的視角分析指導主題出版的技術進路,有助于深入理解主題出版的價值旨歸,為實現中國式出版現代化提供理論支持。
【關? 鍵? 詞】文化記憶;主題出版;覺醒年代;進路;價值旨歸
【作者單位】劉暢,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巢湖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胡作法,安徽出版集團,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圖分類號】G232【文獻標識碼】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17.011
主題出版是圍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黨和國家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動、重大題材、重大理論等進行的選題策劃和出版活動[1]。隨著主題出版工程的深入推進,眾多精品主題出版圖書成為構建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
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重大事件往往會成為記憶建構的重要節點,這些節點可勾起人們的“記憶之錨”。2020年,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點燃了建黨記憶,引發了當代青年的情感共振。面對這一社會熱點,時代出版旗下安徽人民出版社主動作為,搶抓機遇,在電視劇《覺醒年代》熱播之際,迅速跟進挖掘其中的文化資源,聯系編劇龍平平策劃長篇小說版《覺醒年代》,立項青少年版讀物《細說覺醒年代》。根據整體策劃,圖書內容“高品質、高站位、廣讀者”,2021年兩版圖書順利出版,成為口碑與銷量俱佳的現象級主題出版物,也帶動了其他出版機構對以“覺醒年代”為契機的建黨記憶的疆域開拓。
建黨記憶是中華民族繼往開來的文化基因。圖書出版面對這一主題要有擔當,同時也面臨如何處理同質化問題的挑戰。而“覺醒年代”系列圖書案例,為回應這一挑戰提供了經驗。
一、文化記憶與主題出版的適配性
在主題出版概念提出后近20年的實踐過程中,主題出版的內涵不斷延展,選題類型日益豐富,體裁更加多元,內容從早期集中關注重大理論、重大事件和重大戰略的政治類讀物向多元敘事類讀物轉型,這些變化的最終指向都是為了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發揮匯聚民心、增強民族認同感的作用。
文化記憶理論的文化連續性和身份認同與內涵豐富的主題出版具有高度契合性,出版物是文化記憶的典型載體,文本閱讀是塑造文化記憶的重要方式。應用文化記憶理論切入主題出版領域展開研究,符合《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對主題出版做強做優,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同時也為主題出版的業務開展提供了路徑選擇。
二、“覺醒年代”系列圖書雙效俱佳的技術進路
小說版《覺醒年代》充分彰顯了時代出版對主題出版重大選題遴選的洞察力,對重要時間節點和優質內容創作的把控力,對重大題材項目的營銷力,并且很好地詮釋了主題出版的運作思路和模式。該項目的成功,除了借力同名電視劇的熱播流量,更是對優質內容持續拓展的生動嘗試,這背后隱含著重要的技術進路——文化記憶。
1.熱回憶:黨史群像的記憶建構
文化記憶理論奠基人揚·阿斯曼把回憶分為“冷回憶”與“熱回憶”,他強調“熱回憶”對文化記憶傳承創新的重要性[2]。百年黨史波瀾壯闊,當中的革命志士宛如繁星,熠熠生輝。主題出版能否將久遠的歷史人物成功塑造成鮮活、有感召力的革命者形象,讓塵封已久的歷史記憶在經媒介化處理后成為熱回憶,為未來指明道路、增加信心,是其成功的關鍵。小說版《覺醒年代》在電視劇的基礎上,以陳獨秀、李大釗從相識相知到建黨的故事為敘事主軸,并由此牽引出蔡元培、魯迅、胡適等一大批文化大師以及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陳喬年、陳延年等一大批革命青年的精彩故事。他們在國家與民族沉淪的至暗時刻,不惜赴湯蹈火、壯烈犧牲的生命追求和道路選擇,在觀眾心中烙下何為“覺醒”的深刻認知。相較于電視劇,小說給了作者更廣闊的處理空間,表現為在編輯加工中進行了諸多巧妙的處理,原劇中與建黨主題關聯不多的人物或事件被大大壓縮,關于李大釗及其夫人的家庭生活則得到較多的增補,用以豐富人們對建黨精神的理解,深化了偉大建黨精神的主題呈現。
小說版《覺醒年代》通過逼真的歷史再現,回答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時代成因。這些記憶形象的形成,會產生持久深入、感動人心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受眾對當下時代的思考,特別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之路——中國式現代化的思考。在此進程中,《覺醒年代》促使人們增強愛國精神和文化自信,召喚人們建設國家的愛國心和自覺心,讓新時代的文化覺醒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
2.歷史與記憶:記憶之場的文化喚醒
出版物全面立體地展現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脈絡,形成文化記憶,激發讀者審視歷史的興趣,促使讀者產生深度共鳴,投身新時代建設,是當下主題出版的應有之義。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皮埃爾·諾拉以集體記憶為基礎,提出了記憶之場的概念,認為“記憶根植于具象之中,如空間、行為、形象和器物”[3]。為了書寫統一的建黨記憶,“覺醒年代”系列圖書在電視劇的基礎上,更細致、全面地將故事場景放置在不統一的眾多因素和發展的背景下敘述,將歷史重新喚回人們的記憶之中。北京大學作為推行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和眾多革命人物匯聚的歷史場所,其自身演進的跌宕起伏是革命進程的真實寫照。它是建黨歷程的目擊者,是整段歷史最具象征意義的記憶之場,同時也是敘事的主線,穿插起上海、天津、長沙、廣州等鐫刻一方記憶與功績的土地,使得記憶所依附的歷史和文學形態始終并行不悖,彌合了現在與過去之間的裂痕,避免讓歷史僅僅成為歷史。
就賡續文化記憶而言,如果沒有紀念的意識,歷史很快會將這些場所掃蕩一空。當下,“覺醒年代”的余熱仍在持續生發中:以“續寫覺醒篇章,對話時代新人”為主題的圖書主創人員校園行活動,所到之處無不掀起“強國復興有我”的熱烈討論。以“覺醒年代”為主題的系列圖書持續創作并陸續出版,將這一題材的內容挖掘、研究整理工作推向深入。“覺醒年代”主題出版活動建構了新一輪的記憶之場,以席卷之勢蔓延至全國各大高校和黨政機關,分享與互動本身創造了一種文化,而這種文化構成了一個群體賴以生存的基礎,它順應了人們需要歷史同時渴望擁抱現實溫暖的需求。
3.可讀性:從劇本到小說的經典化處理
文化記憶并不與文字有必然聯系,它可以借助儀式、神話、圖像和舞蹈保存下來。但在有文字的文化里,文字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文化記憶主要是借助文字和書寫傳播的[4]。文學經典不一定是最具有價值的文本,但一般會兼具最強的傳播力度、最廣泛的接受群體與最明顯的接受效果。顯然,容易為讀者接受的文字可以促進文化記憶的生成和傳播。電視劇本《覺醒年代》在轉化為小說的時候,創作者考慮到讀者靜態閱讀的需要,巧妙地把分散在劇本各處的不同片段組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事件[5]。
主題出版的目的是向讀者傳達解讀國家的時政方針、重大理論。在做主題出版時,首先要明確市場受眾的定位,堅持語言大眾化、通俗化出版。主題讀物要做到有吸引力、感召力和可讀性,才能吸引讀者去關注、理解和內化其意義,才能真正走進讀者的內心。而要獲得這樣的效果,必須透析讀者心理,了解讀者需求,改變說教式的敘事風格,以通俗易懂、貼近生活的表述,打造出符合讀者期待的出版物。
《覺醒年代》中的許多人物出場時都不到20歲,青春、熱血、理想、奮斗是他們的標簽,向往光明、追求進步、報效國家是他們可貴的特質。因此,小說版《覺醒年代》從一開始就鎖定年輕人特別是學生群體,以他們為目標讀者,為突出青春底色,采用符合青年讀者審美趣味的表達方式,保留了原劇中大量的精彩對話和演講,語言簡練而富有鏡頭感,激發了年輕讀者的深度共鳴,這為實現文學的大眾化寫作提供了路徑。
在青少年版《細說覺醒年代》中,編創者選定了南陳北李如何相約建黨、陳獨秀父子關系究竟如何等49個在電視劇中交代比較簡略,卻又特別關鍵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為主題進行“細說”,以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相關背景知識,更好地理解劇情邏輯。在創作過程中,編創者牢牢把握青少年讀者定位,摒棄說教,以講故事為主,用青少年易于接受的表達方式,準確傳遞了“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這一鮮明主題。
由此可見,優秀的主題出版物要盡可能貼近讀者,增強出版物的可讀性,努力做到小切口、新角度,把大道理變成大白話,把有意義做得有意思,才能激發讀者的共情體驗,最終實現主題出版的審美價值。
三、“覺醒年代”系列圖書雙效俱佳的價值旨歸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作品。”[6]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創作提出的要求,也是做強做優主題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從“覺醒年代”系列圖書雙效俱佳的技術進路來看,其在對文化記憶資源的挖掘與淬煉過程中,盡力幫助大眾理解當下主題出版行業的價值旨歸。
1.主題性:文化記憶的呼應與表達
顧名思義,主題出版就是有主題的出版,其第一要素就是主題。好的主題是稀缺資源,決定著出版物在多大程度上獲得成功。但主題并非空穴來風,也不是妄加揣測即可得之。一般來說,主題的遴選一定要圍繞黨和國家的重點工作、重大活動,把握好重大節慶日、重要時間節點,聚焦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方面的重大題材,提前謀劃,提早布局。選題的尋找離不開專業出版的積累和培育,不僅關乎編輯的眼光、能力和水平,也關乎出版單位的品牌、實力和決心,可以說是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的綜合比拼。比如,慶祝建黨百年是2021年的出版大主題、大方向,黨的百年風華一定會以各種形式在圖書中呈現。在文化記憶的構建過程中,主題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存在。文化記憶往往是歷史政治事件的具體折射,偶爾表現為個體成長過程中的點滴經歷,因此,隱藏于其背后的成長歷程、情感、態度會引起讀者的共鳴與反思。
小說版《覺醒年代》在策劃之初,就要求做到5個“必須”,排在首位的是“必須在百年黨史中擁有重要地位,必須在宣傳百年偉業上發揮深刻影響力”。安徽人民出版社在具體操作中,始終將主題作為第一考量,將小說版《覺醒年代》以精彩的內容演繹、深刻的思想認識、生動的表現形式予以呈現。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這樣一個重要節點,《覺醒年代》的主題意義不言而喻——是對一百多年前中華民族從黑暗混沌走向黎明覺醒的一次喚醒,是對中國共產黨誕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回望,是對隱含于重大歷史事件中偉大建黨精神的一次致敬,也是對這一特殊歷史階段賦予“覺醒”這一文化意象的固化。由此構建的文化記憶無疑又將這一主題提升到更加廣泛而深刻的高度。
2.藝術性:文化記憶的內在要求
揚·阿斯曼認為,可將文化視作記憶,而記憶是有選擇性的,所有那些被認為對當下無足輕重的東西將被忘記。由此可見,在記憶選擇的過程中,只有那些更具藝術性的表達才更容易被選擇,最終成為文化記憶。也就是說,藝術表達是文化記憶生成的內在要求。
主題出版具有出版的一般屬性,承載著記錄時代、謳歌時代、激勵奮斗的使命。主題出版在具有“鮮明的導向性”(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同時,還應該具備打動人心的藝術性。出版單位要配備最好的資源、最強的人力,讓精品意識、工匠精神、人文情懷互相激蕩,切實保障主題出版的藝術性,從而鍛造經典,并使其成為一代人的文化記憶。
在小說《覺醒年代》從策劃到出版的5個“必須”中,有“必須在藝術創作水平上站得住”的明確要求。在具體文本創作時,出版方與編劇龍平平進行了多次細致的溝通,確定了小說文本創作的整體風格和方向,既尊重傳統小說應有的敘事手法,盡可能多地采用靜態的文字論述與細節描寫,又兼顧劇本中原有的場景描寫和大量精彩的人物對話,對劇本中場景、人物、對話等進行恰如其分的轉化。在此過程中,安徽人民出版社先后約請4位作家擔任第一輪文學編輯和進行最后的細節完善工作,并在安徽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聯合中國作協召開改稿會,約請中國作協副主席閻晶明和文學評論家施戰軍、賀紹俊等,對書稿提出修改意見,以增強小說文本的文學氣質,保證作品的藝術性。
3.人民性:文化記憶的基本內核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宏大主題,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歷史記憶。這種宏大的主題極有可能演變為文化記憶,隔著時光的長河,為另一個時代所讀取和回應。文化記憶之所以能夠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群體的共享。因此,文化記憶必然是人民大眾普遍關注的、凝結集體情感的文化主題。這一點與主題出版“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訴求高度一致。
“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文化工作者的初心所在和使命擔當。出版單位要始終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出版導向,秉持為人民出好書的出版理念,強化“為民”的文化擔當,自覺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關注百姓生活,基于大眾、面向大眾、貼近現實策劃選題。以人民群眾所想、所需、所求為基本內核,以人民的滿意度為衡量標準,以鮮明的思想導向、接地氣的主體內容為創作宗旨,以期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部品質優良的主題出版物,一定是經得起人民評閱、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優秀文化產品。正如“覺醒年代”系列圖書,用極具感染力和思想力的表現形式,回答了一個真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強盛中國。從文化覺醒到行動覺醒,再到道路覺醒,不只是獨自開辟道路的中國共產黨的必由之路,也是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總結、銘記并走好這條歷史之路,正是主題出版之于時代之問、人民之問、中國之問、世界之問的最好答卷。
|參考文獻|
[1]楊國祥. 淺談主題出版的特征與策劃[J]. 出版廣角,2013(11):66-68.
[2]金壽福. 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J]. 外國語文,2017(2):36-40.
[3]皮埃爾·諾拉. 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M]. 黃艷紅,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
[4]揚·阿斯曼. “文化記憶”理論的形成和建構[N]. 光明日報,2016-03-26.
[5]何軍民,劉洪權. 抓好四大關鍵環節,打造主題出版精品:以長篇歷史小說《覺醒年代》為中心的考察[J]. 出版發行研究,2022(12):47-51+99.
[6]習近平.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 人民日報,201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