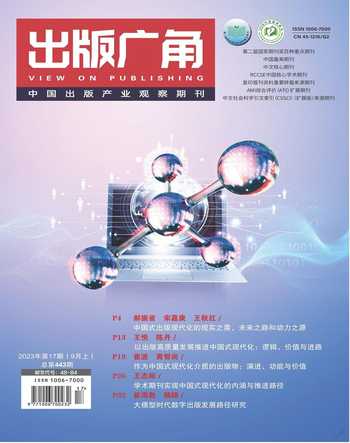媒介空間理論視域中公共閱讀空間參與鄉(xiāng)村文化創(chuàng)新的演進(jìn)軌跡
【摘要】20世紀(jì)后半葉至今,隨著空間由單一物質(zhì)性向融合性發(fā)展以及“空間媒介性”的理論轉(zhuǎn)向,公共閱讀空間參與鄉(xiāng)村文化創(chuàng)新的角色也日益清晰。從媒介視角重審公共閱讀空間價(jià)值可見(jiàn),以公共圖書(shū)館、實(shí)體書(shū)店、農(nóng)家書(shū)屋等為主要構(gòu)成要素的公共閱讀空間在參與鄉(xiāng)村文化創(chuàng)新的歷史演進(jìn)中,呈現(xiàn)以空間為媒介傳承鄉(xiāng)土文脈,以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激活區(qū)域文化,進(jìn)而喚醒村民身份認(rèn)同的新型文化生產(chǎn)機(jī)制。同時(shí),重新梳理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實(shí)踐史也為我們探索新時(shí)期“城鄉(xiāng)文化再造”的創(chuàng)新路徑提供了新思路。
【關(guān)? 鍵? 詞】公共閱讀空間;空間媒介性;鄉(xiāng)村文化創(chuàng)新
【作者單位】張萱,湖北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
【中圖分類(lèi)號(hào)】G258.2【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17.012
21世紀(jì)以來(lái),我國(guó)在全民閱讀和書(shū)香社會(huì)的推進(jìn)中,一種由政府主導(dǎo)、社會(huì)參與共建共享的公共閱讀空間進(jìn)入探索和發(fā)展新階段。公共閱讀空間是政府、企業(yè)、社會(huì)組織或個(gè)人在圖書(shū)館、文化館、實(shí)體書(shū)店、街道、社區(qū)等空間獨(dú)辦或合辦的個(gè)性化、公益性讀書(shū)類(lèi)公共文化服務(wù)平臺(tái)。城市書(shū)房、智慧書(shū)屋、現(xiàn)代書(shū)局這些名稱(chēng)各異的文化空間,如今已成為城市文化的新地標(biāo)與學(xué)術(shù)研究的新熱點(diǎn)。那么,在推進(jìn)城鄉(xiāng)公共文化服務(wù)一體化的建設(shè)中,作為物質(zhì)性空間存在的公共閱讀空間在鄉(xiāng)村文化創(chuàng)新進(jìn)程中發(fā)揮了怎樣的功能?它是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的一種擴(kuò)張和移植,還是作為一種現(xiàn)代性符號(hào)介入鄉(xiāng)村文化的“點(diǎn)綴”?
筆者以媒介空間理論為視角,通過(guò)梳理我國(guó)近百年來(lái)鄉(xiāng)村中公共閱讀空間的發(fā)展軌跡,以圖書(shū)館、實(shí)體書(shū)店、民營(yíng)書(shū)店和農(nóng)家書(shū)屋4種類(lèi)型的公共閱讀空間為研究對(duì)象,針對(duì)其中具有較高社會(huì)影響力的典型個(gè)案進(jìn)行分析,提出我國(guó)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可劃分為三個(gè)發(fā)展階段:前萌芽期以空間賦形歷史、萌芽期以文藝定義空間、發(fā)展期以空間標(biāo)識(shí)地方,由此本研究認(rèn)為“空間的媒介性”是重拾與重構(gòu)公共閱讀空間參與鄉(xiāng)村文化創(chuàng)新的理論新視角。
一、前萌芽階段(20世紀(jì)初—2013年):空間賦形鄉(xiāng)史,延續(xù)鄉(xiāng)土文脈
從書(shū)肆到書(shū)院、書(shū)局、圖書(shū)館、書(shū)店……公共閱讀空間在名稱(chēng)上的變動(dòng)是社會(huì)商業(yè)化程度不斷提升的結(jié)果。清末民初時(shí),我國(guó)鄉(xiāng)村市場(chǎng)化尚未形成,誕生于鄉(xiāng)村中的書(shū)店主要是村民牽頭捐贈(zèng)的公益性圖書(shū)館形態(tài)。20世紀(jì)至21世紀(jì)初,百年時(shí)間里公共閱讀空間的地域分布極為零散,以云南和順圖書(shū)館、無(wú)錫天上市村前圖書(shū)館以及北京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2014年改名為“籬苑書(shū)屋”,下文仍稱(chēng)為“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等最為典型,其文化輻射范圍多為本地區(qū),故稱(chēng)為“前萌芽階段”。
1.圖書(shū)館形態(tài)的公共閱讀空間:百年建筑與現(xiàn)代教育的交匯處
誕生在云南一座古鎮(zhèn)中的和順圖書(shū)館被稱(chēng)為“中國(guó)農(nóng)村第一座書(shū)店”“中國(guó)最大鄉(xiāng)村圖書(shū)館”。百年來(lái),和順小鎮(zhèn)作為茶馬古道的一部分,留下了8萬(wàn)多平方米明清時(shí)期的建筑群和民國(guó)時(shí)代的民居,和順圖書(shū)館的發(fā)展史就是當(dāng)?shù)匚幕涣髋c文明碰撞的產(chǎn)物。該圖書(shū)館舊址為漢景殿,建于明代隆慶時(shí),1905年村里同盟會(huì)成員聚集成咸新社創(chuàng)辦了面向公眾的閱覽室。1924年和順本地青年成立了和順閱書(shū)報(bào)社,1928年和順閱書(shū)報(bào)社與咸新社合并成當(dāng)?shù)氐谝患視?shū)店和順圖書(shū)館[1]。這段歷史見(jiàn)證了鄉(xiāng)村圖書(shū)館與平民教育之間的交匯,既是文明進(jìn)步的社會(huì)性選擇,也是空間發(fā)揮媒介性勾連歷史的文化性選擇。時(shí)間因空間而“凝固”,百年建筑與現(xiàn)代教育的交匯處體現(xiàn)了“空間賦形鄉(xiāng)史”的最初功能,空間的媒介性?xún)r(jià)值因此發(fā)揮了鄉(xiāng)土文脈的歷史傳承功能。和順圖書(shū)館在文化傳播、知識(shí)教育、進(jìn)步文明的傳遞中發(fā)揮的積極作用,使它成為我國(guó)早期公共閱讀空間的雛形。20世紀(jì)初,普通村民面對(duì)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文化碰撞,和順圖書(shū)館幫助他們消除了不確定性,由此成為幫助村民形成自身認(rèn)同與外界想象的重要媒介。
和順圖書(shū)館以“空間即媒介”的存在方式呼應(yīng)了當(dāng)下媒介空間理論的兩種進(jìn)路:一是從文化研究和符號(hào)學(xué)理論,延伸空間的社會(huì)文化意義;二是從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理論對(duì)空間形態(tài)從實(shí)體到關(guān)系轉(zhuǎn)型的發(fā)現(xiàn)[2]。這兩個(gè)維度的共性在于認(rèn)同“媒介空間是在一定社會(huì)范圍內(nèi),由人們共同參與的媒介活動(dòng)所形成的公共傳播情境,以及在該情境中聚合的公共傳播網(wǎng)絡(luò)。其功能主要是信息分享、社會(huì)交往、情感維系、文化認(rèn)同”[3]。從這個(gè)意義上理解,媒介性空間可被理解為一種社會(huì)關(guān)系。因此,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空間意義在于構(gòu)建了更為持久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特別是在這些早期鄉(xiāng)村圖書(shū)館的代際傳承中有所體現(xiàn)。最初的村民多從受惠者成長(zhǎng)為地方文化的反饋者、施惠者,以反哺形成了鄉(xiāng)土文化的良性循環(huán)。就像云南邊陲的村民們第一次通過(guò)和順圖書(shū)館里的書(shū)報(bào)看見(jiàn)了外面的世界。抗戰(zhàn)時(shí)期,當(dāng)?shù)厝A僑捐贈(zèng)給圖書(shū)館的收音機(jī)成為創(chuàng)辦《和順圖書(shū)館無(wú)線(xiàn)電三日刊》的契機(jī),基于此,村民成為整個(gè)云南鄉(xiāng)村地區(qū)中最早了解戰(zhàn)局戰(zhàn)況的民眾。1937年,許多已經(jīng)走出鄉(xiāng)村的先生捐款捐物幫助圖書(shū)館渡過(guò)戰(zhàn)時(shí)困境。在和順圖書(shū)館和村民的共同維護(hù)下,村民們對(duì)知識(shí)的渴望與閱讀習(xí)性逐漸內(nèi)化為一種地方精神。20世紀(jì)末,這個(gè)不足8000人的鄉(xiāng)村中有近3000人在和順圖書(shū)館中辦理了借書(shū)證。2021年,和順圖書(shū)館館長(zhǎng)在央視《開(kāi)講啦》節(jié)目中被問(wèn)及:“一個(gè)鄉(xiāng)村圖書(shū)館想要吸引更多的讀者,最關(guān)鍵的是什么?”館長(zhǎng)回答:“閱讀是需要觸發(fā)和觸動(dòng)的,當(dāng)很多人離書(shū)或遠(yuǎn)或近時(shí),只要給他機(jī)會(huì)接觸到書(shū)籍,他就可能終生愛(ài)上書(shū)籍。”
2.公益性公共閱讀空間:鄉(xiāng)土文脈地方感的新表達(dá)
2011年,誕生于北京市懷柔區(qū)雁棲鎮(zhèn)智慧谷交界河鄉(xiāng)村的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是21世紀(jì)延續(xù)“空間賦形鄉(xiāng)史、傳承地方文脈”特征的當(dāng)代樣本,并且開(kāi)拓了鄉(xiāng)土文脈轉(zhuǎn)化為地方感的表達(dá)方式。
一方面,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跳出了鄉(xiāng)土文脈依托原有歷史建筑的空間范式,創(chuàng)造性地以就地取材作為地方感的空間符號(hào)方式。2011年10月,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竣工并交付使用,它由清華大學(xué)建筑系教授李曉東設(shè)計(jì)并捐建,香港陸謙受信托基金和清華大學(xué)教育基金出資修建,海外華僑出資捐書(shū)。與和順圖書(shū)館空間再造的差異在于,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以本地木柴作為鄉(xiāng)史的重要象征元素,如外墻取材于當(dāng)?shù)卮迕竦牟窕穑陜?nèi)裝修用料為本地杉木,店前的水面、水邊棧道、卵石平展的鋪排以及籬笆取自漫山的劈柴,當(dāng)?shù)卮迕癯S玫牟窈桃脖徊贾迷诓A粔螅瑖铣蓵?shū)屋的外圍空間[4]。讀者進(jìn)入書(shū)屋需脫鞋著襪,通過(guò)身體感受木質(zhì)書(shū)架、木墻、地板和臺(tái)階的材質(zhì),木質(zhì)感由此成為讀者與鄉(xiāng)土聯(lián)結(jié)的一種身體性媒介。在這個(gè)媒介空間中,充滿(mǎn)了以木質(zhì)感官體驗(yàn)為主的符號(hào)運(yùn)作與象征性實(shí)踐,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塑造的符號(hào)空間是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從地方汲取文化養(yǎng)分形成地方感的最初范本。
另一方面,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的地方感還體現(xiàn)在其運(yùn)營(yíng)服務(wù)中,讀者與空間的關(guān)聯(lián)越密切,在地性就越強(qiáng)。圖書(shū)館規(guī)定,管理者中必須有1—2名常駐村民,讓村民參與其日常運(yùn)營(yíng)。這條規(guī)定將地方感建立在空間與人的關(guān)系中,聯(lián)結(jié)起村民與周邊市民、大學(xué)生、公司白領(lǐng)的人際關(guān)系,家庭閱讀活動(dòng)、北京周末一日游以及企事業(yè)團(tuán)建活動(dòng)等以空間聯(lián)結(jié)人的關(guān)系思維在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最初的運(yùn)營(yíng)目標(biāo)中就已明確。如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早期采用“圖書(shū)漂流活動(dòng)”豐富店內(nèi)圖書(shū),即建議讀者帶三本書(shū)來(lái),離開(kāi)時(shí)可任選一本書(shū)帶走。如此既保證了藏書(shū)量有所增加,也以書(shū)為媒帶動(dòng)了讀者交流。這一方案在后續(xù)書(shū)籍運(yùn)作中雖然面臨所獲圖書(shū)為盜版圖書(shū)、珍藏圖書(shū)流失等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但柴舍公益圖書(shū)館在發(fā)揮20世紀(jì)公共閱讀空間對(duì)鄉(xiāng)土文脈延續(xù)的功能上,創(chuàng)造了空間賦形鄉(xiāng)史的在地性,更具本鄉(xiāng)本土的地方元素逐漸成為延續(xù)鄉(xiāng)土文脈的符號(hào),構(gòu)成了人與鄉(xiāng)村的連接。
縱覽20世紀(jì)至21世紀(jì)初,處于前萌芽階段的公共閱讀空間依托的空間載體——建筑,使本地歷史的呈現(xiàn)、再現(xiàn)和傳遞有了具體介質(zhì),并逐漸形成以地方感為要義的空間營(yíng)造思路。這一時(shí)期的公共閱讀空間以空間為媒介,將建筑、書(shū)籍與人的聯(lián)結(jié)作為呈現(xiàn)本地文化的生產(chǎn)動(dòng)力,被城市隔絕在外的鄉(xiāng)村文脈在其間悄然生成并代代傳遞。
二、萌芽階段(2013—2017年):文藝定義空間,再現(xiàn)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
2013年,以先鋒書(shū)店進(jìn)駐鄉(xiāng)村為標(biāo)志,知名民營(yíng)書(shū)店再現(xiàn)鄉(xiāng)土美學(xué)成為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鮮明符號(hào)。相較于前萌芽階段,萌芽階段的重要特征是空間從依賴(lài)實(shí)物的地方感轉(zhuǎn)向虛實(shí)交融的場(chǎng)景感。虛擬與現(xiàn)實(shí)空間邊界日漸模糊是21世紀(jì)數(shù)字化技術(shù)迭代發(fā)展的產(chǎn)物[5],當(dāng)具身與擬像、在場(chǎng)與離場(chǎng)、城市與鄉(xiāng)村的二元結(jié)構(gòu)皆因技術(shù)而抹平成為社會(huì)常態(tài)時(shí),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內(nèi)涵重點(diǎn)便從邊界的討論讓渡給內(nèi)容本身。
1.民營(yíng)書(shū)店:首創(chuàng)文藝范兒的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
2014年,南京先鋒書(shū)店首次進(jìn)入擁有100多座明清時(shí)期民居和祠堂的安徽黟縣碧山村,將一座擁有200多年歷史的祠堂啟泰堂改造成先鋒書(shū)店·碧山書(shū)局。祠堂的木質(zhì)架構(gòu)、天井格局和老牌匾都被保留下來(lái),廢棄的木材被改造為書(shū)架、書(shū)桌。當(dāng)它們重新被組合在同一空間中,就像一個(gè)沉寂了多年無(wú)法言說(shuō)的古老軀殼,以現(xiàn)代話(huà)語(yǔ)方式又開(kāi)始進(jìn)行自我展現(xiàn)與表達(dá)。先鋒書(shū)店將長(zhǎng)期以來(lái)對(duì)實(shí)體書(shū)店“文藝范兒”的執(zhí)著表達(dá)延伸到鄉(xiāng)村景觀中,公共閱讀空間的美因此有了新標(biāo)準(zhǔn)。
先鋒書(shū)店·碧山書(shū)局開(kāi)業(yè)一年后,2015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桐廬縣莪山鄉(xiāng)戴家山村先鋒書(shū)店·云夕圖書(shū)館開(kāi)業(yè)。此圖書(shū)館的主體由兩座比鄰的畬族民居改造而成,改造后的圖書(shū)館保留了老民居的木石結(jié)構(gòu),一幢為藝術(shù)咖啡館,一幢為書(shū)店和活動(dòng)空間。圖書(shū)館內(nèi)書(shū)架和桌椅的材料幾乎都由施工團(tuán)隊(duì)就地取材而來(lái),施工團(tuán)隊(duì)通過(guò)做舊的手法既還原了畬鄉(xiāng)古老器物的原貌,又恢復(fù)其實(shí)用價(jià)值。在書(shū)店中,村民既能感受到熟悉的土坯墻、瓦屋頂、老屋架,又能在書(shū)籍或地方民俗專(zhuān)題圖書(shū)陳列、鄉(xiāng)土歷史攝影展等主題活動(dòng)中被喚醒某種集體記憶。現(xiàn)代美學(xué)理念成為再現(xiàn)村民日常文化的載體,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由此形成。
傳統(tǒng)意義中的鄉(xiāng)土美學(xué),因根植于中國(guó)千年的鄉(xiāng)土文明,并在中國(guó)城市化高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美學(xué)體系中誕生,便形成了城市文明對(duì)農(nóng)業(yè)文明的一種力奪、反觀[6],這是一種他者視角下促使落后美學(xué)向文明美學(xué)進(jìn)步的邏輯。相較而言,先鋒書(shū)店的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實(shí)踐,則以空間為媒介展示了兩種文化狀態(tài)的并存與互動(dòng),其核心在于跳出了二元邏輯中的取代、推倒和重建。作為一種新的鄉(xiāng)土文化美學(xué)觀,它強(qiáng)調(diào)建筑是鄉(xiāng)土文化的重要載體,因其凝結(jié)了當(dāng)?shù)貏趧?dòng)人民千百年的智慧與勞作痕跡,故而成為鄉(xiāng)村傳統(tǒng)美學(xué)可延續(xù)的重要載體。先鋒書(shū)店在對(duì)建筑空間的改造中,創(chuàng)新了一種可被稱(chēng)為回歸與重塑的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范式。回歸意味著對(duì)歷史時(shí)間留下的痕跡進(jìn)行凝固性再現(xiàn)。先鋒書(shū)店以搶救性方式保護(hù)了很多廢棄的明清建筑,空間的建筑結(jié)構(gòu)、材料、物件都是“凝固”歷史的重要存在,時(shí)間在此“休止”,書(shū)店就像一個(gè)重啟按鈕,讓歷史得以再現(xiàn),而非被取代。值得重視的是,先鋒書(shū)店在依托建筑空間進(jìn)行文化創(chuàng)新的過(guò)程中,還發(fā)掘出鄉(xiāng)村與城市不同的美學(xué)價(jià)值,即將美的范疇超越建筑的物質(zhì)性空間,最大程度發(fā)揮鄉(xiāng)村自然風(fēng)光的泛地理空間價(jià)值,是一種重塑。麥克盧漢的感知空間理論曾提出,視覺(jué)空間和聽(tīng)覺(jué)空間是基于主體的視聽(tīng)感官,都屬于感知空間,它們可用來(lái)闡釋空間的偏向性,成為人完整審美的基石。就像這些坐落在山谷田野間的書(shū)店,大自然中一切能夠被感官獲取的信息,都可成為書(shū)店再造審美的部分,風(fēng)聲與雨聲、山林的綠與天空的藍(lán)、不同時(shí)節(jié)和氣象中的色彩和漸變,呼應(yīng)著以書(shū)籍為主要內(nèi)容和氛圍的民營(yíng)書(shū)店。
這種以回歸與重塑為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的公共閱讀空間改造理念,隨著之后先鋒書(shū)店的每一家分店深扎于鄉(xiāng)村文化土壤中,以千店千面的鄉(xiāng)土展現(xiàn)著每一個(gè)村莊特有文化,城鄉(xiāng)二元對(duì)立的美學(xué)邏輯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的傳播被廣泛分享并成為新共識(shí)。
2.藝術(shù)鄉(xiāng)建:共筑場(chǎng)景感的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正式提出“實(shí)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在2013年先鋒書(shū)店加速布局江浙滬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同時(shí),一批先鋒藝術(shù)家也在安徽、貴州等地開(kāi)始了藝術(shù)鄉(xiāng)建的實(shí)踐,且形成了較成熟的模式。2015年,在貴州鄉(xiāng)村誕生的“茅貢計(jì)劃”是藝術(shù)家依托項(xiàng)目構(gòu)建的一種“空間+文化+產(chǎn)品文化生產(chǎn)”組合模型,開(kāi)創(chuàng)出具有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的文化經(jīng)濟(jì)模式。該模式在跳出城鄉(xiāng)二元邏輯的美學(xué)表達(dá)基礎(chǔ)上尤其強(qiáng)調(diào)空間與人的關(guān)系,因此與民營(yíng)書(shū)店共同筑造出客觀存在與主觀感受交融程度更強(qiáng)的“人場(chǎng)合一”場(chǎng)景感。
從客觀存在的空間營(yíng)造來(lái)看,藝術(shù)鄉(xiāng)建與民營(yíng)書(shū)店都擅長(zhǎng)構(gòu)建空間與物的關(guān)系,“茅貢計(jì)劃”的第一個(gè)項(xiàng)目“糧庫(kù)藝術(shù)中心”就選擇茅貢鎮(zhèn)一個(gè)舊糧庫(kù)為改造對(duì)象,設(shè)計(jì)師用傳統(tǒng)侗族的木構(gòu)形式增加庭院的空間,將舊糧庫(kù)改造為能最大程度包容當(dāng)?shù)卮迕窈陀慰偷拈_(kāi)放性藝術(shù)中心。就像藝術(shù)家們將現(xiàn)代藝術(shù)內(nèi)容和展演方式帶入鄉(xiāng)村廣袤的田野或建筑空間中,以民居、祠堂甚至豬圈、牛欄等為“畫(huà)布”一樣,書(shū)店設(shè)計(jì)師也以建筑為基礎(chǔ),利用本地自然和人文資源,如木材、方位、氣候等將書(shū)店盡量融入周?chē)沫h(huán)境。
從體驗(yàn)者主觀感受的空間營(yíng)造來(lái)看,藝術(shù)鄉(xiāng)建與民營(yíng)書(shū)店在構(gòu)建空間與人共生的關(guān)系上如出一轍。糧庫(kù)藝術(shù)中心有兩個(gè)常規(guī)展覽:1980年的侗族鄉(xiāng)土建筑與百里侗寨風(fēng)貌志。負(fù)責(zé)日常工作的館長(zhǎng)吳章仕認(rèn)為:“鄉(xiāng)鎮(zhèn)文化建設(shè)的難點(diǎn)和關(guān)鍵是怎么能夠真正把文化保育和改善村民生活統(tǒng)一起來(lái)。從目前已經(jīng)影響的對(duì)象來(lái)看,受鄉(xiāng)鎮(zhèn)文化建設(shè)影響最大的也許是茅貢中學(xué)的學(xué)生。”
與此同時(shí),民營(yíng)書(shū)店在空間與人的關(guān)系營(yíng)造上也表現(xiàn)類(lèi)似的思路,書(shū)店與藝術(shù)鄉(xiāng)建融合與互構(gòu)的創(chuàng)新性尤為值得關(guān)注。如,2015年,浙江湖州市德清縣首座鄉(xiāng)村文創(chuàng)園“庾村1932”項(xiàng)目,設(shè)計(jì)了包括青年旅社繭舍、竹棚自行車(chē)主題餐廳、萱草書(shū)屋等多個(gè)文藝性公共空間,書(shū)店與藝術(shù)鄉(xiāng)建基于文化氣質(zhì)上的同源性,成為空間組合中的最佳拍檔。再如,“大南坡計(jì)劃”負(fù)責(zé)人左靖曾說(shuō):“做鄉(xiāng)建,書(shū)店是首選。”不僅因?yàn)闀?shū)店與文化天然契合,更重要的是鄉(xiāng)村教育永遠(yuǎn)是最重要的[7]。秉持著修復(fù)鄉(xiāng)村而非創(chuàng)造新村理念的先鋒書(shū)店藝術(shù)家與鄉(xiāng)村書(shū)店的經(jīng)營(yíng)者,如百年來(lái)中國(guó)鄉(xiāng)建的實(shí)踐者們一樣,基于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責(zé)任與使命感,以探路者的身份主動(dòng)參與鄉(xiāng)土美學(xué)實(shí)踐,其審美表達(dá)的背后蘊(yùn)含著一種執(zhí)著、樸素的家國(guó)情懷。
縱觀2013—2017年萌芽階段,文藝定義空間成為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基本革新范式,在國(guó)家政策與政府的支持下,實(shí)踐主體逐漸從地方政府、民營(yíng)組織和民間力量的單打獨(dú)斗走向多元合作。鄉(xiāng)村中多樣化的公共閱讀空間開(kāi)始呈現(xiàn)文藝之美,在深耕鄉(xiāng)土美學(xué)與文化服務(wù)的基礎(chǔ)上,激活了相對(duì)匱乏的鄉(xiāng)村文化。隨著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成型,新時(shí)期鄉(xiāng)村文旅融合發(fā)展的路徑也逐漸清晰。
三、發(fā)展階段(2017年至今):空間標(biāo)識(shí)地方,重建文化生產(chǎn)力
2017年至今,國(guó)家政策性扶持和全民閱讀工作力度持續(xù)加大,新華書(shū)店與農(nóng)家書(shū)屋聯(lián)合地方圖書(shū)館、地方政府黨群服務(wù)部門(mén)加速鄉(xiāng)村網(wǎng)點(diǎn)建設(shè),相較于萌芽階段地理上散點(diǎn)分布狀態(tài),進(jìn)入發(fā)展階段的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在數(shù)量上顯著增長(zhǎng)。2022年6月,我國(guó)已有農(nóng)家書(shū)屋58.7萬(wàn)家,數(shù)字農(nóng)家書(shū)屋16.7萬(wàn)家[8]。公共閱讀空間進(jìn)入全國(guó)地域均衡發(fā)展的新階段,“一村一店”的格局使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成為所在地方的空間標(biāo)識(shí)乃至文化創(chuàng)新的生產(chǎn)媒介。
1.“新華書(shū)店+”:“小連鎖”模式點(diǎn)亮地方標(biāo)識(shí)
2017年以來(lái),全國(guó)各省各地方新華書(shū)店進(jìn)入鄉(xiāng)村門(mén)店拓展和建設(shè)新時(shí)期,隨著數(shù)量的激增,模式化需求開(kāi)始顯現(xiàn),浙江新華書(shū)店探索出的“小連鎖”便成為一種可全國(guó)復(fù)制的新模式。該模式在服務(wù)和補(bǔ)充地方文化的同時(shí),以“新華”這一主流文化符號(hào)為標(biāo)志將現(xiàn)代性審美與地方性文化結(jié)合,在提升新華書(shū)店品牌與鄉(xiāng)村文化振興的關(guān)聯(lián)度同時(shí),提高了當(dāng)?shù)卮迕駥?duì)本地文化的認(rèn)同度。
2018年,浙江省蕭山區(qū)新華書(shū)店與蕭山區(qū)河上鎮(zhèn)政府的合作項(xiàng)目綠野書(shū)舍建成,近700平方米的書(shū)店成為河上鎮(zhèn)的第一家書(shū)店。該書(shū)店采用“新華書(shū)店+”的基本模式,由新華書(shū)店提供書(shū)籍(與培訓(xùn)管理),鎮(zhèn)政府補(bǔ)貼一半資金,同時(shí)免除書(shū)店首期五年房租,允許書(shū)店經(jīng)營(yíng)方在書(shū)賣(mài)出去之后再結(jié)款,避免書(shū)店擁有囤貨、進(jìn)貨、配送、壓倉(cāng)等負(fù)擔(dān)[9]。此后,浙江新華書(shū)店集團(tuán)在構(gòu)建全省公共閱讀服務(wù)網(wǎng)絡(luò)一體化的過(guò)程中,將城鄉(xiāng)文化同步發(fā)展構(gòu)建全省文化地標(biāo)作為整體布局,“小連鎖”經(jīng)驗(yàn)很快遍布全省。據(jù)統(tǒng)計(jì),2018年“小連鎖”書(shū)店在浙江省鄉(xiāng)村中達(dá)到514家,營(yíng)業(yè)面積6萬(wàn)余平方米,居全國(guó)首位。通過(guò)“浙江經(jīng)驗(yàn)”的輸出管理,目前該模式已成為全國(guó)新華書(shū)店深入基層,特別是深入鄉(xiāng)村的基本方式,促使許多鄉(xiāng)村開(kāi)設(shè)了當(dāng)?shù)氐谝患倚氯A書(shū)店。2019年,由湖南省益陽(yáng)市黃家湖新區(qū)與湖南新華書(shū)店集團(tuán)共同打造的湖南益陽(yáng)首家紫薇村鄉(xiāng)鎮(zhèn)書(shū)店開(kāi)業(yè);2020年,江蘇省首個(gè)村級(jí)新華書(shū)店云霧書(shū)房落地江蘇省通安鎮(zhèn)樹(shù)山村6組大石塢10號(hào),“新華書(shū)店+文化+旅游”的文化賦值探索,迅速提升通安鎮(zhèn)“書(shū)香樹(shù)山”的文旅品牌價(jià)值。“小連鎖”模式的成功從表面上看是新華書(shū)店經(jīng)營(yíng)模式上的創(chuàng)新,實(shí)則為空間與地方關(guān)系的重塑。
一個(gè)建筑空間一旦成為一家書(shū)店,它就變成一個(gè)有序且具有意義的“地方”。文化地理學(xué)者段義孚認(rèn)為,地方依賴(lài)于人的經(jīng)驗(yàn)、感知而形成,如果說(shuō)空間意味著自由,那么地方則意味著熟悉[10]。將空間的地理屬性轉(zhuǎn)向地方的人文屬性,是“新華+”小連鎖模式通過(guò)大量復(fù)制在全國(guó)鄉(xiāng)村的一場(chǎng)以空間標(biāo)識(shí)地方的鄉(xiāng)土文化實(shí)踐。在這一進(jìn)程中,地方意識(shí)被激發(fā),各鄉(xiāng)村中的新華書(shū)店與所在村的歷史文化、民俗民生緊密關(guān)聯(lián)。空間媒介性?xún)r(jià)值中地方感的突出,和而不同的書(shū)店風(fēng)格,讓每一家鄉(xiāng)村新華書(shū)店都以村民熟悉的內(nèi)容和異質(zhì)的形式喚醒村莊的文化活力。山東、江西、青海等地新華書(shū)店均在不同程度上以“小連鎖”模式為基礎(chǔ),陸續(xù)發(fā)展為當(dāng)?shù)貙⒋迕裨俣染酆掀饋?lái)的新型公共文化中心。2020年,云南新華書(shū)店集團(tuán)在全省開(kāi)始打造“云上鄉(xiāng)愁書(shū)院”品牌,第一個(gè)落戶(hù)鄉(xiāng)村的云南省臨滄市滄源佤族自治縣勐角傣族翁丁云上鄉(xiāng)愁書(shū)院被評(píng)為“年度公共閱讀空間”,到2022年,云南省已建成了168家“云上鄉(xiāng)愁書(shū)院”。“一店一景”的鄉(xiāng)村書(shū)店不僅具有提供閱讀服務(wù)的空間功能,更植根于村民的感知體驗(yàn)與文化認(rèn)同心理,成為激活鄉(xiāng)村文化自信的一個(gè)“地方”。
2.“農(nóng)家書(shū)屋+”:微地標(biāo)創(chuàng)新空間文化生產(chǎn)
農(nóng)家書(shū)屋工程自2005年試點(diǎn)至今已有18年,是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由國(guó)家組織實(shí)施的參建部門(mén)最多、投入最大、下沉最深、覆蓋最廣、規(guī)模最大的一項(xiàng)國(guó)家級(jí)基礎(chǔ)公共文化設(shè)施工程,在服務(wù)中國(guó)鄉(xiāng)村文化、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隨著中國(guó)現(xiàn)代鄉(xiāng)村文化發(fā)展和治理新需求,由于農(nóng)家書(shū)屋與村民密切關(guān)聯(lián)度、傳播效果等局限性逐漸顯現(xiàn),農(nóng)家書(shū)屋曾一度陷入無(wú)人進(jìn)屋的困境。2017年,海南省在“農(nóng)家書(shū)屋+”新華書(shū)店的合作基礎(chǔ)上,探索更具開(kāi)放性的“海南模式”,以“農(nóng)家書(shū)屋+”為基礎(chǔ),以“空間即地方”的文化賦值方式,使書(shū)屋逐漸成為鄉(xiāng)村文化的微地標(biāo)。一店一特色的“微地標(biāo)”意味著見(jiàn)微而知著,空間成為個(gè)人與地方的關(guān)系紐帶,通過(guò)連接村民與本地文化呈現(xiàn)地方的可見(jiàn)性,書(shū)屋在其中表現(xiàn)高度的創(chuàng)造力與整合能力。
一方面,書(shū)屋定位為本地文化的生產(chǎn)空間,極大提升了農(nóng)家書(shū)屋作為主體性角色進(jìn)行創(chuàng)新的可能性。如鳳凰海南書(shū)坊火山口閱讀分享中心根據(jù)當(dāng)?shù)胤N植火山石斛、菠蘿蜜,養(yǎng)殖黑山羊較多的實(shí)際情況,主動(dòng)協(xié)調(diào)新華書(shū)店增加相關(guān)農(nóng)業(yè)科技類(lèi)圖書(shū)的投入,以服務(wù)村民切實(shí)的信息需求。2018年在荒廢7年的嶺西小學(xué)原址上改建的火山書(shū)吧,命名就取自其地理位置為馬鞍嶺火山口腳下,書(shū)吧重點(diǎn)推出集旅游、自行車(chē)運(yùn)動(dòng)、農(nóng)業(yè)、教育于一體的創(chuàng)新性經(jīng)營(yíng)項(xiàng)目“人民騎兵營(yíng)”,成為海南“農(nóng)家書(shū)屋+”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營(yíng)的典型代表。在吸引村民重新走進(jìn)書(shū)屋、構(gòu)建村民身份標(biāo)識(shí)的過(guò)程中,人的流動(dòng)豐富書(shū)屋在文化生產(chǎn)方面的多元性。
另一方面,“農(nóng)家書(shū)屋+”探索出多種組合,以書(shū)屋為中心將微地標(biāo)進(jìn)一步“活化”,拓展了地域文化的可見(jiàn)性。2017年溪邊書(shū)屋首創(chuàng)“農(nóng)家書(shū)屋+”旅游景點(diǎn)的新組合,同年,海南省定安縣將全縣108家農(nóng)家書(shū)屋改建為文化村郵服務(wù)站,打造“農(nóng)家書(shū)屋+”村郵站的組合[11]。2018年,三亞市天涯區(qū)西島漁村將廢棄漁船改建為海上書(shū)房,在“農(nóng)家書(shū)屋+”旅游景點(diǎn)組合的基礎(chǔ)上,場(chǎng)景化構(gòu)建漁鄉(xiāng)文化成為吸引外地游客的新樣本。海南地方文化的多元與豐富首次以農(nóng)家書(shū)屋為撬點(diǎn),超越了曾經(jīng)僅以風(fēng)景為地方文化標(biāo)志的單一性。
以農(nóng)家書(shū)屋作為鄉(xiāng)村文化微地標(biāo)的支點(diǎn),已被實(shí)踐證明其推廣的可操作性。在這一過(guò)程中,不少農(nóng)家書(shū)屋在連接人與地方的親密關(guān)系中創(chuàng)新了書(shū)店空間的文化生產(chǎn)力。如雅安市天全縣新華鄉(xiāng)永安村農(nóng)家書(shū)屋管理員淡青、巴中市平昌縣鎮(zhèn)龍鎮(zhèn)萬(wàn)家村農(nóng)家書(shū)屋管理員劉秀娟,均入選2023年“鄉(xiāng)村閱讀推廣人”[12]。她們以書(shū)屋為媒介,發(fā)揮空間媒介性更具人情味的文化生產(chǎn)意義。隨著書(shū)店管理員與書(shū)店故事的傳播,“農(nóng)家書(shū)屋+”在四川省內(nèi)各農(nóng)家書(shū)屋的全局建設(shè)上已開(kāi)始探索更多創(chuàng)新,省內(nèi)聯(lián)動(dòng)就是其典型產(chǎn)物。2022年,四川省率先升級(jí)了全省運(yùn)行管理系統(tǒng),將省內(nèi)農(nóng)家書(shū)屋進(jìn)行數(shù)字化管理,進(jìn)一步整合資源,加強(qiáng)分散在省內(nèi)各個(gè)鄉(xiāng)村書(shū)屋資源的共享,將“農(nóng)家書(shū)屋+”的服務(wù)試點(diǎn)延伸至婦女之家、鄉(xiāng)村學(xué)校少年宮、圖書(shū)館等,實(shí)踐了農(nóng)家書(shū)屋由新聞出版行業(yè)運(yùn)維管理向公共文化服務(wù)空間的轉(zhuǎn)變路徑。
2017年至今,全國(guó)新華書(shū)店和農(nóng)家書(shū)屋以公共文化服務(wù)主體全面參與鄉(xiāng)村文化振興,無(wú)論在數(shù)量、體量還是質(zhì)量上,公共閱讀空間都已經(jīng)成為我國(guó)鄉(xiāng)村中具有地方標(biāo)識(shí)文化的新型空間主體,在重塑當(dāng)代中國(guó)鄉(xiāng)村文化內(nèi)涵的進(jìn)程中發(fā)揮了奠基性與標(biāo)桿性的價(jià)值。
四、公共閱讀空間的鄉(xiāng)村文化創(chuàng)新路徑:雙向奔赴的文化創(chuàng)新機(jī)制
公共閱讀空間在鄉(xiāng)村中的實(shí)踐歷史,伴隨著現(xiàn)代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持續(xù)發(fā)展與更新,空間的邊界感在物質(zhì)與虛擬范疇中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dāng)人們?cè)竭^(guò)鄉(xiāng)村與城市的地理區(qū)隔,空間漫游一般的雙向流通成為新的表征,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便逐漸從城市與鄉(xiāng)村以平行且單向的路徑關(guān)系,轉(zhuǎn)向兩條路徑的重疊且多向度流通,由此也成為“城鄉(xiāng)文化再造”的孵化場(chǎng),雙向奔赴的文化創(chuàng)新機(jī)制由此顯現(xiàn)。
1.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以“歷史”為核心價(jià)值,促進(jìn)城鄉(xiāng)流動(dòng)方式的轉(zhuǎn)變
縱觀我國(guó)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百年多的實(shí)踐歷程,空間媒介性?xún)r(jià)值貫穿其中,并高度體現(xiàn)在空間的歷史價(jià)值上。從公共閱讀空間建筑的實(shí)體角度看,20世紀(jì)初公共閱讀空間多為明清建筑再利用,建筑精湛的工藝及其曾經(jīng)作為文化中心象征的精神價(jià)值借由書(shū)店形態(tài)再生時(shí),村民對(duì)故鄉(xiāng)的熟悉與親切,便自然地移情到舊有的建筑實(shí)體中。卡斯特認(rèn)為,空間是一個(gè)物質(zhì)產(chǎn)物,相關(guān)于其他物質(zhì)產(chǎn)物(包括人類(lèi))而牽涉于“歷史地”決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之中。該觀點(diǎn)指出物質(zhì)性空間的核心在于歷史,歷史價(jià)值則在于社會(huì)關(guān)系而非空間屬性,因此無(wú)論是早期的和順圖書(shū)館,還是21世紀(jì)以后涌現(xiàn)的先鋒書(shū)店、方所書(shū)店等民營(yíng)書(shū)店、新華鄉(xiāng)村分店,都不無(wú)例外地首選鄉(xiāng)村中頗有年代和歷史價(jià)值的建筑作為書(shū)店主體,并將其延伸為對(duì)鄉(xiāng)村中更多歷史性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再利用。
在這一實(shí)踐進(jìn)程中,公共閱讀空間以建筑體為歷史要素展演方式,逐漸從早期的直接使用轉(zhuǎn)向符號(hào)利用。規(guī)劃者和設(shè)計(jì)師最初多以現(xiàn)代鄉(xiāng)村美學(xué)觀念改造傳統(tǒng)歷史建筑,之后便不再局限于對(duì)建筑的直接利用,而是將廢舊民居、祠堂作為公共閱讀空間對(duì)接城市和全球,公共閱讀空間成為鄉(xiāng)土美學(xué)與現(xiàn)代美學(xué)的媒介。歷史符號(hào)通過(guò)其文化象征意義,包括民俗元素轉(zhuǎn)化、村民參與方式等對(duì)鄉(xiāng)土元素予以保留和再現(xiàn)。當(dāng)歷史價(jià)值依托空間的物質(zhì)性向融合性發(fā)展時(shí),一個(gè)公共閱讀空間就成為一個(gè)活化的歷史。
回溯20世紀(jì)初,我國(guó)公共閱讀空間多以圖書(shū)館為基本形態(tài),發(fā)揮了傳承地方歷史與文化的基本功能,通過(guò)提供書(shū)報(bào)和新聞信息的方式傳播新知,延續(xù)村民以建筑空間為中國(guó)文明象征物的認(rèn)同。在這個(gè)意義上表現(xiàn)列斐伏爾關(guān)于“第三空間”的闡釋?zhuān)暗谝豢臻g關(guān)注的是具象的物質(zhì)性空間,第二空間緣起于精神或認(rèn)知形式中的想象空間,第三空間發(fā)端于物質(zhì)和精神的二元論,同時(shí)又不同于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它是真實(shí)和想象的混合”。早期鄉(xiāng)村圖書(shū)館作為“第三空間”極大拓寬了我國(guó)平民教育和無(wú)差別科普的范圍,發(fā)揮了將本地村民“向外送”的教育功能。隨著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逐漸步入第二、三階段,以民營(yíng)書(shū)店創(chuàng)造“新鄉(xiāng)土美學(xué)”的空間表達(dá)為轉(zhuǎn)折,以新華書(shū)店、農(nóng)家書(shū)屋在更大范圍內(nèi)復(fù)制并豐富了這種空間文化生產(chǎn)范式為條件,“向內(nèi)吸”的渠道和動(dòng)力因此疊加在“向外送”的基礎(chǔ)上。城市市民特意驅(qū)車(chē)來(lái)到鄉(xiāng)村逛書(shū)店、住宿、旅游,曾經(jīng)離開(kāi)的村民也回到村里擔(dān)任書(shū)店負(fù)責(zé)人,參與書(shū)店管理和推廣。鄉(xiāng)村以公共閱讀空間為中心使流通方式發(fā)生轉(zhuǎn)變,不僅使流通方式更為暢通,而且使其互相交融。在歷史符號(hào)持續(xù)強(qiáng)化的閱讀空間中,流動(dòng)的關(guān)系產(chǎn)生文化的創(chuàng)新力,包括村民參與書(shū)店的修繕,書(shū)店主動(dòng)與地方文化部門(mén)、教育機(jī)構(gòu)合作,以黨建為中心搭建多功能的公共閱讀空間等,城鄉(xiāng)文化再造的孵化功能在此顯著增強(qiáng)。
2.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調(diào)節(jié)城鄉(xiāng)文化的失衡狀態(tài),構(gòu)建情境價(jià)值的文化創(chuàng)新動(dòng)力
數(shù)字化技術(shù)從根本上顛覆了空間與地理的關(guān)系,現(xiàn)實(shí)地點(diǎn)在虛擬空間中成為無(wú)差別對(duì)象,隨著人的流動(dòng)與商業(yè)驅(qū)動(dòng),曾經(jīng)因地理差異而導(dǎo)致的城鄉(xiāng)文化失衡狀態(tài),在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參與下得以調(diào)試并互為構(gòu)成。由此可見(jiàn),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首先經(jīng)由地理媒介的轉(zhuǎn)型,彌合了城鄉(xiāng)文化的失衡狀態(tài),進(jìn)而將人際—信息—商品三者納入空間文化生產(chǎn)范疇,形成了一種具有典型情境的文化創(chuàng)新結(jié)構(gòu)。
隨著移動(dòng)智能手機(jī)、定位導(dǎo)航技術(shù)以及社交媒體普及,地理媒介的鄉(xiāng)村實(shí)踐被納入其中,城市與鄉(xiāng)村的邊界在虛擬與現(xiàn)實(shí)中被逐步弱化。斯科特·麥夸爾提出地理媒介的四個(gè)維度,包括無(wú)所不在、位置感知、實(shí)時(shí)反饋與融合傳播。在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實(shí)踐中,地理媒介的四個(gè)維度集中體現(xiàn)為中國(guó)城市與鄉(xiāng)村在信息、人流、商業(yè)、文化全維度上的流通與再造。當(dāng)媒介與特定地點(diǎn)的綁定關(guān)系被打破,移動(dòng)和植入式設(shè)備與數(shù)字網(wǎng)絡(luò)將地理上千里之隔的鄉(xiāng)村與城市納入同一層級(jí)的媒介空間中,地理位置便從一種限制變成多種資源。每一個(gè)攜帶著包含定位軟件設(shè)備的個(gè)人都是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移動(dòng)光標(biāo),在流動(dòng)的過(guò)程中,那些積蓄已久的鄉(xiāng)史傳承、民俗保護(hù)與歷史記憶等,都成為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中具有傳播和經(jīng)濟(jì)雙重價(jià)值的文化商品。社交媒體的使用者只需標(biāo)注一家公共閱讀空間的地理位置,附上簡(jiǎn)短文字介紹、圖片或視頻,這個(gè)公共閱讀空間便成為一個(gè)與城市文化空間無(wú)差別存在的象征。隨著大量網(wǎng)民在地圖導(dǎo)航中對(duì)其定位后經(jīng)社交媒體分享傳播,這個(gè)地理標(biāo)記便從虛擬走向現(xiàn)實(shí),成為一種消除城鄉(xiāng)隔閡的流行文化符號(hào)。伴隨著人的具身行動(dòng)與虛擬傳播同步進(jìn)行,難以計(jì)數(shù)的信息生產(chǎn)者在融合傳播系統(tǒng)中多角度參與,既顛覆了傳統(tǒng)意義上事件先行、傳播在后的文化范式,也使得實(shí)踐與反饋交織成為一種全新的動(dòng)態(tài)且緊密聯(lián)系文化生產(chǎn)機(jī)制。許多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品牌與影響力甚至超過(guò)了城市同類(lèi)書(shū)店,它們?cè)诩嬗形幕a(chǎn)者、信息傳播者、鄉(xiāng)村服務(wù)者多重身份的語(yǔ)境下,以文化媒介的角色在城市與鄉(xiāng)村話(huà)語(yǔ)權(quán)的博弈中獲得了某種平衡。
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在賦予城鄉(xiāng)文化獲得平衡通路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出一種具有典型情境特征的空間文化生產(chǎn)力。傳統(tǒng)意義上,文化創(chuàng)新結(jié)構(gòu)由商品流通、信息傳播、人際關(guān)系三者構(gòu)成。公共閱讀空間在這一結(jié)構(gòu)范式內(nèi)突出空間的媒介價(jià)值,其角色是兼具精神產(chǎn)物的空間再生產(chǎn)關(guān)系主體,由此成為改變鄉(xiāng)村歷史、人與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空間媒介。它基于空間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完善了人際—信息—商品的三重流動(dòng),將自身嵌入整個(gè)文化市場(chǎng)的流通網(wǎng)絡(luò),形成了一種新的空間關(guān)系再生產(chǎn),并產(chǎn)生了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所營(yíng)造的一種典型情境。最初提出情境概念的社會(huì)學(xué)家威廉·托馬斯認(rèn)為,情境并非環(huán)節(jié)、場(chǎng)合和場(chǎng)景的綜合整體,而是一種“現(xiàn)實(shí)的建構(gòu)”,是“主客一體”共同作用下的態(tài)度和價(jià)值的一體兩面[13]。在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各種類(lèi)型中,其文化的生發(fā)與活躍多是基于典型的情境,文化創(chuàng)新以情境為條件,又以情境為動(dòng)力,人際、信息與商品同時(shí)在場(chǎng)產(chǎn)生的生產(chǎn)價(jià)值更為顯著。如,先鋒書(shū)店舉辦的“作家駐村計(jì)劃”活動(dòng),在村民與村外人進(jìn)行人際互動(dòng)的同時(shí),將作家駐村作為一個(gè)事件和持續(xù)狀態(tài),既是信息也是文化商品,三者在鄉(xiāng)村文學(xué)再生產(chǎn)這一情境中相互作用產(chǎn)生了新的文化內(nèi)容和形式。再如,方所書(shū)店·大南坡藝術(shù)中心每年舉辦的“南坡秋興”文化節(jié),以音樂(lè)為典型情境,實(shí)現(xiàn)了大南坡即將失傳的地方戲劇與五條人現(xiàn)代音樂(lè)共同在場(chǎng),催生了全新的大南坡地方文化產(chǎn)物。經(jīng)過(guò)近十年的發(fā)展,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在經(jīng)歷建設(shè)、升級(jí)、經(jīng)營(yíng)范圍擴(kuò)大、監(jiān)督管理加強(qiáng)的一系列完善后,其對(duì)地方民俗的保護(hù)和留存,通過(guò)各類(lèi)常態(tài)化的鄉(xiāng)土文化孵化項(xiàng)目,為鄉(xiāng)村提供了文化輸入、精神陪伴,這些都成為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在營(yíng)造典型的鄉(xiāng)土情境中的文化創(chuàng)新產(chǎn)物。
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下,托馬斯“主客一體”的情境觀進(jìn)一步為“媒介即情境”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實(shí)踐契機(jī)。媒介技術(shù)滲透于人際傳播、大眾傳播、虛擬與現(xiàn)實(shí)交融的多種情境疊加之中,因此,鄉(xiāng)村公共閱讀空間的情境維度更加豐富,將主流文化宣傳納入這一情境并豐富其內(nèi)涵是一種文化創(chuàng)新方式。新華書(shū)店、農(nóng)家書(shū)屋在全面進(jìn)駐鄉(xiāng)村后,在國(guó)家文化宣傳方面以公共閱讀空間實(shí)現(xiàn)了現(xiàn)代鄉(xiāng)村文化的普及,在建立村民與國(guó)家關(guān)系、培育未來(lái)一代村民的現(xiàn)代性意識(shí)等方面探索出多種路徑。如,2017年在新集村圖書(shū)館初步成功的經(jīng)驗(yàn)上,新集村政府進(jìn)一步與黃淮學(xué)院建立戰(zhàn)略合作聯(lián)盟,雙方在新集村又建設(shè)了第二家書(shū)店拙匠書(shū)院,將公共閱讀空間以感官審美呈現(xiàn)的空間體驗(yàn)深耕于更廣泛的社會(huì)服務(wù)范疇。該書(shū)院既是黃淮學(xué)院服務(wù)新集村鄉(xiāng)村振興工作的一個(gè)平臺(tái),又是學(xué)院實(shí)踐教學(xué)與創(chuàng)新的基地,在運(yùn)作中持續(xù)匯集設(shè)計(jì)師、藝術(shù)家、建設(shè)者多方主體,僅一年時(shí)間就為新集村制訂了“三院七坊”建設(shè)計(jì)劃。拙匠書(shū)院在融入新集村鄉(xiāng)民的文化生活的同時(shí),讓村民的收入也得以增長(zhǎng),有效促進(jìn)了鄉(xiāng)村第二、第三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真正實(shí)現(xiàn)了國(guó)家主流文化、進(jìn)步文化的宣傳與提升地方經(jīng)濟(jì)效益的雙贏。
五、結(jié)語(yǔ)
20世紀(jì)20年代至20世紀(jì)30年代,梁漱溟發(fā)起的“儒學(xué)下鄉(xiāng)運(yùn)動(dòng)”、晏陽(yáng)初與陶行知寄希望于教育與文化改造鄉(xiāng)村,體現(xiàn)了近代知識(shí)分子對(duì)鄉(xiāng)土文化革新的思考[14]。在鄉(xiāng)村文化創(chuàng)新這個(gè)時(shí)代命題中,公共閱讀空間從一束搖曳的亮光,逐漸發(fā)展為星火燎原之勢(shì)。如今,那些在鄉(xiāng)村古舊建筑原址上修舊如舊、重獲新生的公共閱讀空間在實(shí)現(xiàn)自身嬗變的同時(shí),也映射著周邊村民的房屋修繕觀念,影響鄉(xiāng)村政府對(duì)征地拆遷的方案,甚至改變了地方文旅定位和發(fā)展的思路。現(xiàn)代美學(xué)觀念、智能科技的人文關(guān)懷也借由書(shū)店這種媒介性空間破除舊邊界,建構(gòu)新關(guān)系,城市與鄉(xiāng)村的雙向再造正以一種美的方式重新記憶歷史和書(shū)寫(xiě)未來(lái)。
|參考文獻(xiàn)|
[1]耿達(dá). 鄉(xiāng)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生成機(jī)制與發(fā)展路徑:基于扎根理論的云南和順圖書(shū)館的案例研究[J].中國(guó)農(nóng)村觀察,2019(5):53-70.
[2]關(guān)琮嚴(yán). 屬性轉(zhuǎn)移、邊界消弭與關(guān)系重構(gòu):當(dāng)代鄉(xiāng)村媒介空間的轉(zhuǎn)型[J]. 新聞與傳播研究,2021(4):57-72+127.
[3]李彬,關(guān)琮嚴(yán). 空間媒介化與媒介空間化:論媒介進(jìn)化及其研究的空間轉(zhuǎn)向[J]. 國(guó)際新聞界,2021(5):38-42.
[4]鄧玉祥. 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下鄉(xiāng)村圖書(shū)館建設(shè)研究[J]. 河北科技圖苑,2021(4):9-13.
[5]潘霽. 作為媒介研究方法的空間[J]. 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22(5):91-98.
[6]鞏淑云. 藝術(shù)何以鄉(xiāng)建,鄉(xiāng)建何以藝術(shù)?[N].農(nóng)民日?qǐng)?bào),2023-05-22.
[7]陳定方. 民營(yíng)書(shū)店也能擔(dān)當(dāng)公共文化服務(wù)[N]. 光明日?qǐng)?bào),2014-03-09.
[8]大江南北? 書(shū)香濃濃[EB/OL].(2023-05-
19)[2023-08-01]. https://www.zgnjsw.gov.cn/booksnetworks/contents/399/341061.shtml.
[9]浙江新華書(shū)店:“小連鎖”織起農(nóng)村文化服務(wù)“大網(wǎng)絡(luò)”[EB/OL].(2021-12-12)[2023-08-01].http://www.ce.cn/culture/whcyk/gundong/201112/12/t20111212_22910536.shtml.
[10]段義孚. 空間與地方:經(jīng)驗(yàn)的視角[M]. 王志標(biāo),譯. 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7.
[11]“農(nóng)家書(shū)屋海南模式”獲國(guó)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肯定[EB/OL].(2018-06-15)[2023-08-01].http://lwt.hainan.gov.cn/jdhy_55360/xwfbh/201904/t20190428_2548520.html.
[12]以農(nóng)家書(shū)屋為載體? 四川創(chuàng)新深入推進(jìn)鄉(xiāng)村全民閱讀[EB/OL].(2023-04-24)[2023-08-01].
http://www.leshan.cn/html/6A4DEEDADC39436D/2023/04/24/view_B85EC191DF1C55AE.html.
[13]曹?chē)?guó)東,劉越飛. 從“情境”概念再出發(fā):威廉·托馬斯的傳播思想探究[J]. 新聞春秋,2023(1):85-95.
[14]錢(qián)理群. 志愿者文化叢書(shū):梁漱溟卷[M].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