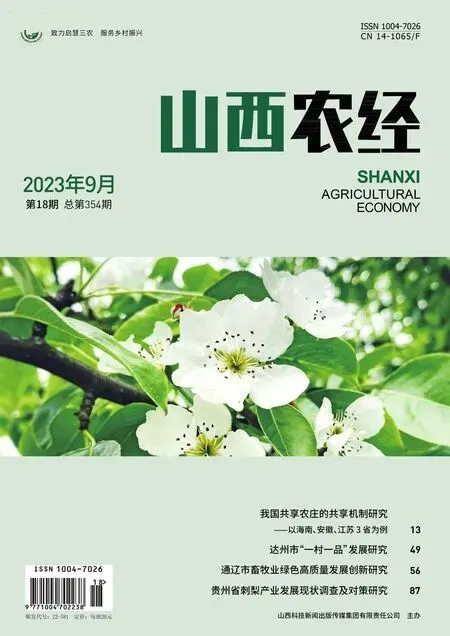政策和法律視角下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黃曉懿
(成都職業技術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在鄉村振興進程中,農村土地高效流轉是解決農村土地問題、實現農民致富、推進鄉風文明、引領農業振興的必要舉措。在影響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諸多因素中,政策和法律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有必要梳理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相關政策和法律。
1 農村土地流轉相關政策和法律概述
1.1 政策方面
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加快,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格局發生巨大變化,農村土地流轉和利用問題逐漸進入黨和國家的政策視野。
《2012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化農村改革,健全農村土地流轉配套服務組織,推進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業規模經營。
《2013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化農村改革,以農村土地確權試點為契機,全面推動農村土地確權頒證。
《2014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定農村土地產權關系長久不變,賦予農民更多的土地權利。
《2015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培養職業化農民,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業規模經營,推動農業現代化。
《2016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鼓勵農戶通過股份合作形式進行農村土地流轉,從政策層面扶持新型農業經營者。
《2017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完善農村土地“三權分置”辦法。
《2018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農村土地承包權到期后再延長30 年。
《2019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培育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推廣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成果。
《2020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扶持適度規模經營主體,加強農戶社會化服務。完善鄉村產業發展用地保障政策。2021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決守住“18 億畝耕地紅線”,劃足劃實永久基本農田,切實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開展好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 年整縣試點[1]。
從近10 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可見,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已經走向規范化,為推動農村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政策保障[2-7]。
1.2 法律法規方面
自1986 年開始,國家陸續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允許和規范農村土地流轉。
圖7為沉管近、遠場的應力應變滯回曲線,由圖可見,沉管底板處海床由于發生液化,剪應變達到0.1%。土骨架曲線大幅衰退,而對應的遠場海床剪應變僅達到0.013%(未達到液化狀態)。
1986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允許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法定承包期內由經營者進行適當調整。該法以“適當調整”描述農村土地經營權的變更行為,表明國家已經逐步承認農村土地經營權的調整行為,并且法律文本中已經初步涉及農村土地經營權調整的若干規定,為后續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出臺奠定了基礎。
2002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在集體所有制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多種形式進行流轉,但不得改變農村土地農業用途,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優先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讓和互換方式改變了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其流轉對象包括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其他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這種農村土地流轉行為必須由當事人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請登記。其提出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概念,強調了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農村土地流轉的前提,規范了農村土地流轉的原則、要求和形式,促進了農村土地流轉的有序有效開展。
2005 年頒布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2021 年3 月開始施行《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的同時該辦法被廢止)規定,允許普通農戶或者法律允許的從事農業經營的組織或個人參與農村土地流轉,但本村成員擁有農村土地優先受讓權且不能改變農村土地農業用途。如若受讓方再次流轉土地,需要獲得原承包方的同意。該管理辦法從流轉形式、流轉合同和流轉管理、權利義務等方面詮釋了農村土地流轉政策,促進了農村土地流轉規模的擴大。
2007 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規定,在法定承包期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通過抵押、入股等方式實行流轉,未經法律允許不得改變其農業用途。其實現了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后的價值,增加了農戶獲得財產性收入的概率。隨著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發展,農村土地流轉規模得以擴大,由農村土地流轉引發的矛盾糾紛日益增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于2009 年頒布,規定農村土地流轉糾紛的處理辦法主要包括當事人之間的和解、村委會調解或申請仲裁,也可直接向法院起訴,旨在維護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秩序與社會穩定發展。
2 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和法律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政策和法律是影響我國農村土地流轉的重要因素。國內學者對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和土地承包權定位與農村土地流轉之間的關系作出了相關研究。
臧公慶和龔鵬程(2015)[8]認為,信托公司的運作可以更好地為耕地流轉主體提供經濟激勵。
林文聲和羅必良(2015)[9]、胡霞和丁浩(2015)[10]指出,人地關系、嵌入社會關系的交易機制和戶籍是土地流轉非市場行為的主要原因。
蔡昉和王美艷(2016)[12]指出,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制度性約束使農村勞動力難以徹底轉移,人地比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導致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和兼業化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村土地流轉,制約了農業經營規模擴大。
葉劍平等(2018)[13]認為,土地確權工作已經初見成效。
戴青蘭(2018)[14]指出,土地確權破除了集體經濟發展的障礙。
仇童偉和羅必良(2018)[15]基于土地產權理論認為,國家賦權是勞動力和農村土地要素配置的主導因素,國家賦權的強度影響勞動力非農就業和農村土地流轉。
王士海和王秀麗(2018)[16]認為,土地確權對增強農戶的產權意識有幫助,能提高農戶參與農村土地流轉的意愿。
寧靜等(2018)[17]認為,土地確權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戶收入,改善其經濟狀況。
應瑞瑤等(2018)[18]指出,穩定的地權有助于激勵農戶持續開展農業生產投資。
曲頌等(2018)[19]認為,土地確權能明晰農村土地產權,賦予農民權能,但激發了農民解決土地權屬爭議的訴求,使農村的歷史遺留問題顯現出來。
仇童偉和羅必良(2018)[20]認為,土地產權穩定性的改善會抑制農戶種植農作物。
Ye L 等(2018)[21]認為,工業用地權利由于國家和集體土地所有權并存,能在不同的土地租賃條款之間轉移,會造成工業用地的利用效率下降。
楊宏力(2018)[22]指出,當前的土地確權模式可能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后果。
陳慧妮(2018)[23]結合城鎮化階段鄉村的基本矛盾,分析J 村農村土地流轉帶來的機遇和危機之間的矛盾、鄉村整體利益和村民利益多元化之間的矛盾、鄉鎮行政管理權和村民自治權之間的矛盾,認為農村土地流轉政策是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支點之一,農村土地流轉對農民利益產生深遠影響,提出了尊重鄉村內生秩序、提高村鎮干部工作積極性、增強村莊凝聚力、煥發村莊自身特色等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執行路徑。
孟繁瑜和陶建芝(2020)[24]從宏觀、中觀和微觀3 個層面研究我國農村土地金融創新政策的實踐和理論演化,分析我國農村土地金融創新政策構建,提出完善我國農村土地金融政策制度的對策建議。
李停(2021)[25]認為,我國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改革為農村土地金融創新提供了可行性,激發了農村土地金融需求,促進了農村土地金融供給。
姜松和樂季(2021)[26]分析了農村土地金融創新的內在邏輯與目標偏差,提出了農村土地金融創新發展路徑。
3 結束語
從近10 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可見,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已經走向規范化,為推動我國農村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政策保障。相關法律法規的陸續出臺不斷規范和促進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有序開展。對此,國內學者對農村土地流轉的政策和法律影響因素作出了相關研究。雖然學者們研究的視角與方法各不相同,但普遍認為通過相關政策和法律引導可以提高農村土地流轉參與主體的積極性,進而推動農村土地流轉。出臺并落實相關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規,能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村土地流轉產生積極影響,同時也存在不同的認識和結論。現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