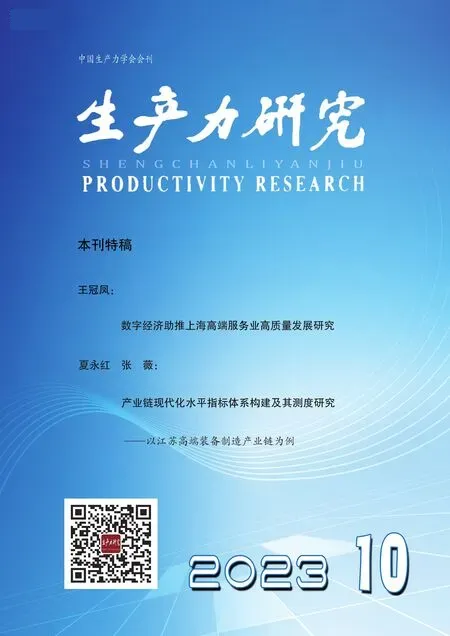基于SRP 模型榆林市生態脆弱性評價及時空演變研究
王成軍,羅昕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5)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自然和人為因素對于生態環境的壓力日益增大,人類生活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受到了巨大的反噬影響[1-2]。面對大量涌現的生態與環境問題,生態脆弱性研究已成為全球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焦點[3-4]。生態脆弱性有三層含義:其一,一定時空條件下生態系統內部自有的不穩定性;其二,在外來擾動的脅迫下,該系統僅靠自我恢復能力難以修復;其三,該系統因受外界擾動對偏離原始平衡狀態的敏感性[5]。脆弱性概念由最初著重于自然生態系統到20 世紀90 年代之后從社會系統角度開展研究,涉及農、林、牧、漁等生產部門[6]。21世紀以來,脆弱性研究內容傾向于與其他領域交叉研究的人地耦合綜合性系統[7],考慮耦合中的相互作用,影響系統對其脆弱性的反應[8]。國內對生態脆弱性的研究由中科院在“八五”期間開展的生態環境綜合整治和恢復技術研究拉開了序幕,從多元化方向發展生態脆弱性研究[9],由單一擾動向多重擾動,由靜態脆弱性分析向動態脆弱性分析方向轉變[10]。在生態脆弱性評價概念模型上,使用頻率較高的有VSD(暴露度-敏感性-適應能力)模型[11]、SRP(敏感度-恢復力-壓力度)模型[12]、PSR(壓力-狀態-響應)模型[13]等。其中,基于“社會-自然”耦合系統,充分體現生態脆弱性內涵的SRP 模型更適用于區域綜合性的生態脆弱性評價[14]。在研究區域多集中在喀斯特山區[15]、高原區[16]、內陸流域[17]等地勢條件較差或人為干擾劇烈的區域,但對于受氣候條件影響的半干旱區域研究甚少。
陜西省榆林市位于西北半干旱區,地處毛烏素沙地向黃土高原過渡地帶。區里存在嚴重的土壤風蝕、水土流失和頻繁干旱等問題,是我國典型的生態環境脆弱地區。隨著區域經濟與城鎮化進程發展,快速增長的人口和經濟對原本就比較脆弱的生態系統造成了巨大的擾動和壓力。同時,1995 年以來當地政府針對該區的生態問題,開展了退耕還林還草、防風固沙林帶等大規模生態修復工程,生態系統特征已發生顯著變化,因此對其展開生態脆弱性評價具有重要科學價值和實際意義。
綜上,基于本文SRP 概念模型,構建榆林市生態脆弱性評價體系,對研究區的生態脆弱性綜合評價進行定量分析,把握脆弱性總體時空變化趨勢與規律,研究脆弱性空間相關性與導致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并提出針對性的生態發展對策,以期為榆林市生態保護與修復工作的持續推進提供數據支持和建議參考。
二、研究區概況
榆林市位于陜西省最北部(見圖1),地處北緯36觷57'~39觷34'和東經107觷28'~111觷15'之間,轄1 市2區9 縣,戶籍人口385.59 萬人,總土地面積為42 920.2 km2,屬于溫帶大陸性半干旱氣候,年降雨時空分布不均,平均溫度約10℃。整體地貌特征呈風沙草灘向黃土溝壑過渡,以古長城為界,古長城以北地區是以風蝕沙化為主的毛烏素沙漠南緣風沙區,古長城以南地區是以水蝕作用為主的南部丘陵溝壑區,水土流失現象嚴重,屬于陜西省水土流失重點治理區。隨著礦產資源加大開發和城鎮化加速發展,榆林市作為國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進一步加重了環境沖突對原本脆弱的生態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使得區內生態環境更加復雜化[18]。

圖1 研究區地貌區分布
三、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榆林市數字高程模型(DEM)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氣象數據來自國家地球系統科學數據中心共享服務平臺;土地覆蓋類型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植被數據由MOD13和MOD17 產品的處理得到;土壤風蝕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數據》;土壤數據來源于世界土壤數據庫(HWSD);社會經濟數據來自《榆林市統計年鑒》。本文所使用的數據覆蓋2000 年和2020 年2 個時期,不同分辨率的多指標柵格數據通過ArcGIS 10.8 進行重采樣處理,空間分辨率設定為1km×1km,統一投影至wgs 1984-zone-49n 地理坐標系,其中土壤水蝕數據通過USLE 方程[19]計算得到,干燥度采用丁一匯和王守榮(2001)[20]提出的作為劃分我國西北地區干濕氣候區公式。
(二)生態敏感性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通過考慮研究區經濟、人口、環境及生態狀況,結合《生態環境狀況評價技術規范(試行)》以及相關研究,同時根據科學性和可獲取性等指標體系構建原則,綜合從生態系統敏感性(S)、恢復力(R)和壓力度(P)3 個維度,選取13 個指標構建研究區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生態敏感性表征生態系統受外界影響時引發環境問題的可能性[21],受區域本身生態系統類型和特征影響,高敏感性的地區,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可能性越大,生態環境往往越脆弱,因此選用氣象、地形、地表、土壤因子。生態恢復力是生態系統受到外界干擾破壞時所表現的自我調節能力和修復能力[22],因此選擇植被覆蓋率和凈初級生產力(NPP)等指標作為影響恢復力的植被因子。生態壓力度由人類生產活動等產生的外部擾動對生態系統的壓力,受外部擾動越多,脆弱性就越高,在此用人口密度、人均GDP 和土地墾殖率等社會經濟因子表征區域發展的生態壓力。

表1 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
(三)評價指標數據標準化
由于評價指標的量綱及其物理意義存在差異,無法原封不動地用于脆弱性評價,需要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參數不可比的問題[23]。采用極差法和分等級賦值法分別處理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見表1),范圍在0~10 之間。
1.極差標準化。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采用不同的標準化公式:
式中,Zi為第i 個指標的標準化值,xi為第i 個指標初始化值,xmax、xmin分別為指標i 標準化前最大值和最小值。
2.分等級賦值法。對于土地覆蓋類型、土壤水蝕模數和土壤風蝕模數等定性指標,根據相關研究成果[24-25],結合研究區實際特征對指標按照分等級賦值法進行2、4、6、8、10 五個級別的量化賦值(見表2)。

表2 分等級賦值標準
(四)構建脆弱性評價模型及等級劃分
本文通過空間主成分分析法,采用生態脆弱性指數(EVI)來定量化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程度[26]。空間主成分分析(SPCA)法是在GIS 系統支持下,通過旋轉原始空間坐標軸,將相關的多變量空間數據轉化為少數幾個不相關的綜合指標,以實現用較少的綜合指標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來較多變量所反映的空間信息[27],結果如表3 所示。提取累積貢獻率大于85%以上且特征值大于1 的前6 個指標作為主成分因子,依據公式(3)和公式(4)分別計算得到2 期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指數。

表3 各期空間主成分分析結果
式中,EVI 表示生態脆弱性指數,其值越大,生態脆弱性程度越高;PC1~PC6分別表示每個時段從13 個初始變量中提取出來的貢獻率在85%以上且特征值大于1 的6 個綜合性主成分。
對EVI 展開進一步標準化處理以便進行比較和分析,計算公式如下:
式(5)中,EEVIi表示第i 年的生態環境脆弱性標準化數值,范圍在0~10 之間;EVIi表示第i 年的脆弱性指數;EVImax和EVImin分別表示脆弱性指數最大值和最小值。
參考相關生態脆弱性分級研究,將標準化后的生態環境脆弱性指數劃分為五個等級,即微度脆弱(0-2)、輕度脆弱(2-4)、中度脆弱(4-6)、高度脆弱(6-8)和極度脆弱(8-10)五個脆弱等級[28]。
(五)生態脆弱性空間自相關分析
本文通過測算研究區生態環境脆弱性的全局莫蘭指數和局部莫蘭指數,研究其在空間上是否聚集以及如何聚集。莫蘭指數可以分析某一變量在不同尺度上的集聚程度,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在空間上是否有聚集特征可用全局莫蘭指數量度,局部莫蘭指數可用于衡量研究區生態環境脆弱性的空間聚集方式[29]。
(六)生態脆弱性演變驅動力分析方法
由王勁峰和徐成東(2017)[30]提出的用于研究空間分異性與驅動機制等方面的地理探測器(Geo Detector)應用十分廣泛。本文借助其中的因子探測器探測分析影響研究區生態脆弱性與其各驅動因子之間的定量相關性。該模型用因子解釋力Q 進行度量,Q 值越大則評價指標對生態環境脆弱性指數的貢獻越大,反之越小[31],公式如下:
式(6)中,Q 為評價指標對生態脆弱性的解釋力,范圍在0~1 之間,n 為樣本數,L 為指標分類數,nh為h 層樣本量,表示h 層生態脆弱性指數的方差。
四、結果與分析
(一)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等級時空分布特征
從空間分布狀況看(見圖2),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指數整體分布空間差異十分明顯,呈現出西北高、東南低的趨勢。研究區極、高度生態脆弱區主要出現在研究區的北部、西北部以及西南等地區,整體呈收縮趨勢,主要分布在人口聚集,人類活動劇烈、資源開發程度高、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設的神木市和榆陽區與位處高海拔,生態環境惡劣的定邊縣等生態系統所承受的壓力大,生態系統自身恢復能力相對較弱的地區。其中,府谷縣、靖邊縣和橫山區內極、重度生態脆弱性等級出現大范圍降級,演變成中度脆弱甚至出現零星輕度脆弱。生態脆弱程度較低等級的區域主要分布在氣候相對適宜,有植被大面積覆蓋,整體生態質量保護較好的東南地區,并有向外蔓延發展的空間特征趨勢,其中微度脆弱等級集中在吳堡縣和清澗縣,黃河沿線地區生態環境有所好轉,生態脆弱性等級由中度轉向輕度和微度。

圖2 2000 年(a)和2020 年(b)生態脆弱性等級分布圖
從時間變化上看,由表4、表5 可知整體上2000年和2020 年2 期生態脆弱性等級主要分布在輕、中及高度脆弱區之間,尤其是中度脆弱區。微、輕度脆弱區面積大幅度增加,變化量面積分別占總面積的6.33%和15.44%,中度及以上區面積呈下降趨勢,中度和高度脆弱區減少面積變化量占比分別為10.56%和10.68%。相較于2000 年,2020 年中度以上脆弱區占比雖然有所下降,生態環境形勢轉好,但是其占比仍超過一半。二十年間研究區各等級生態脆弱性相互轉化的面積總和為23 619.93km2,總體上看,中度以上脆弱區轉入更低度脆弱區的面積明顯高于微、輕度脆弱區轉入更高度脆弱區方向轉移的趨勢。這主要是由于榆林市一貫嚴格執行環境保護措施,實施退耕還林還草、水利水保等多項生態修復工程,使生態環境得到穩定有序的發展。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正向轉移面積大于負向轉移面積,整體生態狀況呈好轉趨勢,反映出研究區生態狀況的改善趨勢。

表4 不同等級脆弱性面積對比

表5 生態脆弱性等級面積轉移矩陣(km2)
(二)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空間自相關性
2000 年和2020 年全局Moran's I 值分別為0.798、0.829,數值呈上升趨勢,都通過了P<0.01 的顯著性水平檢驗,且Z 值均大于2.58,表明在99.9%置信度下的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生態脆弱性指數在空間分布上存在顯著集群現象,生態脆弱性指數與地理位置之間有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通過計算局部莫蘭指數,由圖3 可以看出,2000 年和2020 年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的集聚結構差異較小,“高-高”聚集型地區在收縮,“低-低”聚集型區域不斷外擴。“高-高”聚集型地區主要集中在定邊縣中部和北部、靖邊縣和橫山區的北部以及榆陽區和神木市的大部分地區,這些地區生態環境狀況差,生態調節功能不足。“低-低”聚集型區域大致分布在南部佳縣、米脂縣、子洲縣、吳堡縣、綏德縣和清澗縣,這些地區生態條件較好。總體空間聚集分布情況與同一時期的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分布圖大致相同。“高-低”和“低-高”地區主要分布在“高-高”和“低-低”聚集型地區周邊,表明研究區的生態脆弱性相對穩定,不太可能發生突然急劇改變。

圖3 2000 年(a)和2020 年(b)生態脆弱性LISA 集聚圖
(三)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時空格局變化驅動力分析
利用地理探測器中因子探測模型對2000—2020 年導致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時空分布發生變化的各驅動因子進行統計分析,其各個驅動因子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指數解釋力的大小如表6 所示,p值都為0,說明13 個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標通過顯著性檢驗。2000 年從指標層方面,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影響最大的3 個因子為年降水量、植被覆蓋度、干燥度,其次是人口密度、土地覆蓋類型、高程、年均氣溫,其他因子對于研究生態脆弱性的影響相對較小。可知,整體范圍內年降水量和植被覆蓋的程度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定量解釋力最大,即年降水量與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結果之間呈現最大的空間分布相似性,植被、干燥度、人口密度、土地覆蓋類型等因素次之。氣象因子和植被因子等自然驅動力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變化起到主導作用;人為驅動力方面,人口密度等社會經濟因子和開發利用程度較大的土地覆蓋類型因子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影響程度次之,說明了人為因素同樣不容忽視。2020年,因子解釋力由高到低主要為年降水量、年均氣溫、植被覆蓋度、人均GDP、干燥度、凈初級生產力、高程等,剩余因子影響相對較小。兩年結果對比表明,這些驅動因子對于生態脆弱性的解釋力略有不同,但主要因子基本相同,氣象因子和植被因子等自然驅動力依舊起主導作用,且對研究區生態脆弱性的解釋力加強。

表6 生態脆弱性地理探測器解釋因子Q 值結果統計表
五、討論與結論
本文基于SRP 評價概念模型,從自然和社會兩個角度出發,建立由3 個準則層指標,6 個要素層指標,13 個指標層指標構成的榆林市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標體系,通過空間主成分分析法進行指標權重賦值,提升了評價結果的客觀程度,增加體系結合GIS技術在地理信息系統軟件的支持下,構建榆林市生態脆弱性評價指數模型和指數分級標準,使得成果能充分反映該地區生態環境基礎特點。通過運用空間相關性方法和地理探測器模型為榆林市生態脆弱性評價工作提供技術途徑,對其時空分布特征及演變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一是從空間上,榆林市生態脆弱性指數整體呈現出西北高、東南低的趨勢。極、高度生態脆弱區主要分布在古長城以北的風沙草灘區,生態脆弱程度較低等級的區域主要分布在南部六縣,并有向外蔓延發展的空間特征趨勢。時間上,2000—2020 年榆林市生態脆弱性等級主要處于輕度、中度及高度脆弱區之間,其中,中度以上脆弱區面積不斷減少,生態脆弱性正向轉移面積大于負向轉移面積,整體生態狀況呈好轉趨勢。
二是榆林市生態脆弱性空間聚集性整體上逐漸增強,生態脆弱性指數與地理位置之間有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高-高”聚集型地區在收縮,“低-低”聚集型區域不斷外擴,這與同一時期的研究區生態脆弱性分布圖基本一致。
三是從榆林市生態脆弱性演變驅動力分析來看,各指標對生態脆弱性的影響均為顯著,區內自然驅動因子對生態環境脆弱水平的作用相對地區人為因素而言占據主導地位,特別是年降水量、植被覆蓋程度、年均氣溫、干燥度、土地覆蓋類型等的驅動作用;驅動因素中人均GDP、人口密度、凈初級生產力、高程也對地區生態環境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作用。植被覆蓋度,土地覆蓋類型變化,土壤水蝕和風蝕程度、土地墾殖率甚至降水氣溫都間接或直接受到人類各種不合理甚至過度活動的影響,人類應提高生態保護意識、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工程的實施,這樣地區生態環境質量才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