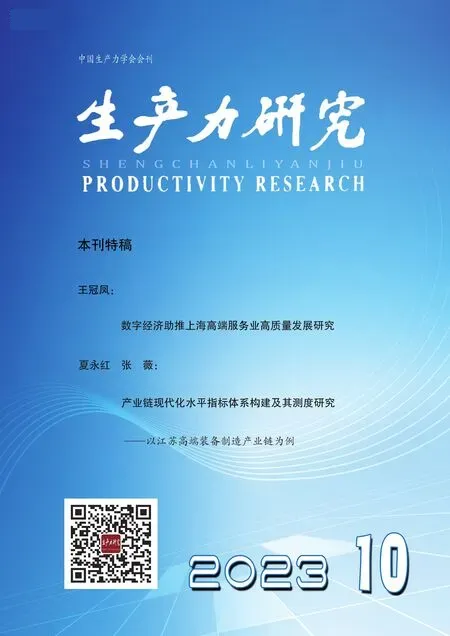產業結構升級、創新人員集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黃 清,陳鈞浩
(寧波大學 商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迅速,然而在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創新能力的不足、生態環境的惡化等。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要更加重視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對新時代新征程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出了一系列戰略部署。2018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具體指出了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途徑與方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思路[1]。經濟高質量發展概念未提出之前,經濟學界討論經濟增長“質”的概念時,主要采用經濟增長質量,但經濟增長質量并不能完全概括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含義更加寬廣。科技創新、人力資本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2],創新人力是創新能力的重要部分,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可忽視的要素。分析產業結構升級、創新人員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回顧
(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與衡量指標
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產業結構[3]、人力資本[4]、融資約束[5]等。人口質量是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可忽視的一大因素,其中勞動力的質量對經濟發展質量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技術進步不僅僅包括數量也有質量,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樣不可忽視技術進步質量的重要作用;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創新驅動發揮著重要作用,創新質量也不可忽視[2]。
關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衡量指標有學者建立多維指標評價方法,也有學者采用單一的指標來衡量,全要素生產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使用率較高的單一指標。余泳澤等(2019)[6]采用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分析高質量發展狀況,并采用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 模型進行測算。也有學者傾向于采用綜合化指標來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代理指標。周少甫和陳亞輝(2022)[7]考慮到采用單一指標來衡量經濟高質量水平無法全面反映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采用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共享發展和風險防控五個一級指標、十個二級指標,對各個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運用熵權法綜合測算。楊孟陽和唐曉彬(2023)[8]結合已有研究成果,構建了包括經濟運行、創新發展、文化教育等七個維度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標來研究京津冀13 個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二)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一方面產業結構的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推動作用。產業結構升級推動著技術的進步,形成產業的集聚和資源要素的集聚,推動區域發展競爭力的提升[9]。產業結構升級,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推動著要素由低效率部門流向高效率部門,社會生產水平的提高帶來“結構紅利”,推動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產業結構的升級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從粗放型的要素驅動發展方式轉向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發展方式,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10]。產業結構的升級能提升各部門之間的運轉效率,降低資源浪費率,推動經濟協調運行,帶來經濟高質量水平的提升[11]。另一方面,也有學者研究發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可能會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抑制作用[12]。
(三)產業結構升級、創新人員集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
創新人員集聚主要是指政府通過補貼政策發布、資金補助等方式吸引人才流入,匯聚高能力人才,以此提升城市創新能力。創新人員的集聚給城市帶來高技術人才,拉動城市經濟活力,為地區創新能力增長奠定人才基礎,進一步推動地區創新資源應用效率的提升[13],助力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產業結構升級推動著要素優化[14],提升地區經濟實力,吸引高技術人才的集聚,政府為進一步推動地區經濟增長而頒布相關政策帶來創新人員的集聚,創新人員的流入優化地區的勞動力結構,提升生產效率,推動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15]。同時,創新人才的引進帶來先進的知識、技術、管理經驗等,減少資源的浪費,推動地區環境的進一步改善[16],助力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可以發現,文獻主要是從某一典型地域或省份分析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且少有文獻分析創新人員集聚在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調節作用,鑒于此,本文利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固定效應模型,研究產業結構優化、創新人員集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并且考慮到不同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省(市)規模等異質性,區分東中西部地區、省(市)規模以及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分析產業結構的變動如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探討了創新人員集聚是否會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調節效應,對既有研究進一步完善,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的設定
為了檢驗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以產業結構升級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采用2001—2020 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深入分析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效應。本文在構建模型之前,先運用Stata 16.0 統計軟件進行模型選擇,本文進行了Hausman 檢驗,檢驗結果顯示P 值為0.000,小于0.1,拒絕原假設,由此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構建基礎計量模型,如公式(1)所示:
式(1)中,ehq 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iu 為產業結構升級指標;X 為控制變量,包括失業率(ue)、固定資本(fc)、進出口總額(ei)、城鎮化水平(ur);δi,t為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模型的隨機擾動項,下標t表示時間單元,i 為省份單元,βi為待估計的參數。
為進一步探究創新人員集聚的調節作用,將創新人員集聚(rdp)與產業結構升級的交互項納入模型,如公式(2)所示。
(二)變量選取與衡量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借鑒王忠輝等(2022)[17]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測算方法,一級指標分別選取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共享發展,二級指標分別為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區域協調、產業協調、污染排放、發展成果、公共服務,具體的指標測算如表1 所示。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綜合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
主成分分析的具體步驟如下:
(1)KMO 檢驗和Bartlett 檢驗。由表2 可知,KMO=0.784,大于0.5,同時,在巴特利球狀檢驗中,P 值為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拒絕原假設,表明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較強,因此所選取的樣本數據和評價指標通過了檢驗,可以進行主成分分析。

表2 KMO 檢驗和Bartlett 檢驗
(2)提取主成分確定公共因子。特征值可以衡量因子是否具備足夠的影響力,根據表3 中輸出數據現實特征超過1 的主成分因子有兩個,其累計貢獻率為74.901%。

表3 總方差解釋
(3)計算綜合得分。首先,將兩個主成分中每個指標對應的系數與所對應的貢獻率相乘;其次,將乘積除以所提取的兩個主成分的貢獻率之和;最后,得出每個指標的綜合得分。
2.解釋變量。經濟結構服務化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特征,本文借鑒任曉燕和楊水利(2020)[11]的度量方法,將第三產業的增加值與第二產業的增加值的比值作為產業結構升級(iu)的衡量指標。
3.調節變量。創新人員集聚(rdp):創新人員集聚有利于人才結構優化、相關區域創新能力的提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人才基礎。本文借鑒劉和東和劉繁繁(2021)[18]的方法,采用該省高新技術產業研發人員全時當量與全國的比重來衡量。
4.控制變量。本文加入以下控制變量:(1)失業率(ue),使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來衡量失業率;(2)固定資本(fc);(3)進出口總額(ei),使用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貨物進出口總額衡量進出口總額;(4)城鎮化水平(ur),采用各地區城鎮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各省份的城鎮化水平。
四、計量結果及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及分析
表4 列(1)僅研究了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顯示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為0.594,且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產業結構升級每提升1%,平均每年能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0.594%,這主要是由于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全要素生產率獲得了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進一步增強,部門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社會生產水平提升,推動經濟高質量的發展。在列(2)~列(5)中逐步加入了其他控制變量后,產業結構升級的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上述計量模型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了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表明產業結構升級正向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分別更換解釋變量衡量指標、調整樣本時期、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1.更換解釋變量的衡量指標。本文將產業結構升級指標替換成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三產業增加值相加之后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回歸結果如表5 列(1)所示,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結果穩健。
2.調整樣本時期。本文對2011—2015 年以及2016—2020 年兩個時間段進行回歸分析。2011—2015 年的回歸結果如表5 列(2)所示,2016—2020年的回歸結果如表5 列(3)所示,結果顯示兩個時間段的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表5 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
3.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廣義矩估計(GMM)方法,選取產業結構升級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5 列(4)所示。將表5 列(4)結果與基準結果相比較發現,解釋變量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變動較小,結果穩健。
(三)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我國東部、中部、西部的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發展水平有著較大的區別,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可能因區域差異而有所不同,因此,本文進一步根據地區、省份規模、省份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異質性分析,回歸結果如表6 的Panel A所示。由表6 的Panel A 回歸結果可知,產業結構升級對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均為顯著正向影響,但是不同地區的影響程度和顯著性水平有所不同,對東部地區的正向影響最大,顯著性水平是最高的,而對西部地區的影響最小,西部地區的顯著性水平也是最低的。這可能是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比較迅速,產業結構升級更快速,所帶來的“結構紅利”也更大,所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更大。

表6 異質性回歸結果
本文考慮到不同省份規模的大小也會影響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借鑒周少甫和陳亞輝(2022)[7]的方法,將所研究的省份按照城市年末總人口數的中位數進行區分,城市年末總人口數高于中位數則劃分為大規模省份,否則為小規模省份,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 的Panel B 前兩列所示。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產業結構升級對大規模省份和小規模省份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均發揮著顯著的積極影響。
另外,由于各個省份發展階段不同,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也會有不同,因此本文將所研究的省份根據其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均值進行劃分,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高于均值的省份劃分為高水平地區,否則為低水平地區,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 的Panel B 后兩列所示。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產業結構升級顯著促進了高水平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但對低水平地區的作用可能并不明顯。
(四)調節效應分析
調節效應的檢驗結果如表7 所示。模型(1)檢驗了產業結構升級、創新人員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模型(2)檢驗了創新人員集聚是否會對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高質量影響發揮調節作用,結果顯示交互項的系數為正,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在產業結構升級正向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創新人員集聚發揮著顯著的調節作用,高技術人才的集聚有利于進一步推動經濟高質量的發展。

表7 調節效應回歸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2011—2020 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利用《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實證考察了產業結構升級、創新人員集聚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以及在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創新人員集聚是否發揮著調節作用,并進一步分析了不同區域的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第一,從各省份來看,產業結構升級有助于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二,創新人員集聚顯著正向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技術人才的集聚為地區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知識,有利于經濟高質量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并且,創新人員集聚發揮著正向調節作用,創新人員集聚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所帶來的經濟高質量水平提升;由于產業結構升級,地區經濟增長加速,吸引著人才的集聚,高技術人才匯集推動生產效率提升,降低資源浪費率,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三,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人口規模、省份位置的不同,產業結構變動引起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動趨勢不同。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顯著推動經濟高質量水平的提升,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正向影響最小,中部地區的影響位于中間地位。第四,從省份規模和發展水平來看,大規模省份和小規模省份的產業升級均顯著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但是,不同發展水平地區的產業結構變動所引起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動趨勢有差異,高水平地區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推動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在低水平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并不一定引起經濟發展水平的正向變動。
本文根據上述實證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對策:第一,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通過產業結構的升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第二,地區要重視高技術人才引進,政府積極發布住房補貼、研發補貼等相關政策吸引創新人員的流入,匯聚創新人才,為地區經濟增長奠定人才基礎,帶來經濟高質量的進一步發展。第三,不論是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都可以通過產業結構的升級來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通過產業結構的升級來推動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推動地區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第四,在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的地區,可以通過產業結構的優化有效地帶動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在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可以考慮轉換產業升級方式來更好地推動該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