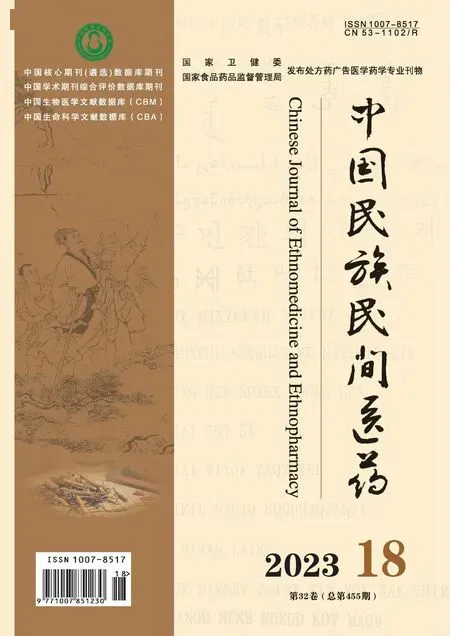經方“和法”治療惡性淋巴瘤
白 潔 孫劍聲 劉 寧 孔祥圖 于 慧 陳曉麗 倪海雯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
漢代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被譽為“中醫四大經典之一”,其所開創的辨證論治、六經辨證、治療八法等理論,在中醫藥的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尤其是其所載方劑“藥少而精,出神入化,起死回生,效如桴鼓”,被譽為“經方”。現代醫家認為,經方不僅僅是一個個孤立的經典名方,更是一種以仲景學說為指導的醫學體系[1]。中醫治病講求理法方藥,其中“法”即治療法則,是治病的關鍵,對于“法”的理解,正如古語所云“皆無非為病求去路也”。基于《內經》“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2]491,“和法”應為治療疾病的基本大法。所謂 “和法”,即和解法,對于病位在半表半里,或氣血陰陽虛實不和,臟腑功能失調者,應用“和法”,可使病邪從半表半里而出,以達氣血陰陽臟腑調和。
淋巴瘤是常見的血液系統腫瘤,其起源于淋巴結和淋巴組織。臨床常見癥狀為淋巴組織無痛性、進行性增生,尤以淺表淋巴結腫大為特點,常伴有肝脾腫大,或貧血、發熱等。根據組織病理學改變,一般分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兩類。目前,惡性淋巴瘤的發病率逐年上升,其具有惡性程度高、易于復發等特點,是現代醫學難以攻克的難題。在中國古代,雖未明確提出“淋巴瘤”這一概念,但對“石疽”“惡核”“痰核”“陰疽”“失榮”等與淋巴瘤病因病機、臨床癥狀類似的疾病的治療有十分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推敲和借鑒。其中,仲景所創經方蘊含的“和法”就對臨床惡性淋巴瘤的辨證用藥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目前,淋巴瘤的治療手段主要采用分子靶向藥聯合化療,隨著新藥的使用,患者生存期得到了明顯的延長,但是治療相關的并發癥及患者全身合并癥是影響足量規范治療的重要因素,同時,治療藥物相關的并發癥,如胃腸道并發癥、化療藥物導致的腸道粘膜損傷、菌群失調等均是目前新藥聯合化療時影響患者治療及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倪海雯主任以經方理論指導臨床復雜、重癥、疑難等疾病的辨治,執簡馭繁,以經方之法緊扣核心病機要素,以經方之核心用藥合方治療復雜病癥,師古不泥古,現簡述仲景“和法”在惡性淋巴瘤中的應用如下。
1 和解表里之小柴胡湯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曰:“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嘿嘿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3]37《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曰:“血弱氣盡,腠理開……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嘿嘿不欲飲食。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3]38小柴胡湯是治療少陽證的主方,少陽在半表半里,涉及足少陽膽經、手少陽三焦經,有出入表里、陰陽樞機的作用。《靈樞·經脈》:“膽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眥……下耳后……下頸,合缺盆,從缺盆下腋……三焦手少陽之脈……其之者,從膻中上缺盆,上項,系耳后直上……從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2]38從少陽經的經絡循行來看,其主要經過耳前、耳后、頸部、鎖骨上窩、腋下、腹股溝等部位,與現代醫學中淺表淋巴組織的分布大致相同。在臨證中發現惡性淋巴瘤多由于素體虛弱,釀生痰、熱、瘀等病理產物,積蓄日久則發病。從少陽經所主臟腑的生理病理特性來看,惡性淋巴瘤的致病因素痰、熱、瘀等的產生于手少陽三焦經密切相關,三焦為元氣之別使,水谷之道路也,若三焦氣化失調,則會引起水液代謝障礙,氣機失調,痰飲、水濕、瘀血內生。從少陽病的疾病特征來看,淋巴瘤初起發病,病邪尚未入里,機體尚存一絲正氣,臨床可見“往來寒熱”等正邪交爭之象,治療上若單純是使用攻邪之法,非但不能驅逐病邪,還會損傷正氣,使病邪由表及里或由陽及陰,造成疾病進展,故應使用和解少陽之法,方可奏效。莊娟娜等[4]認為 “休作有時”之休作廣義上包括各種癥狀之休作,屬少陽樞機不利所致,故使用小柴胡湯治療惡性淋巴瘤復發或化療后的反復性藥物不良反應患者,療效甚好。丘明和教授[5]認為少陽樞機不利為淋巴瘤的核心病機,貫穿淋巴瘤發生發展的全過程。李達[6]自擬小柴胡湯化裁的調和肝脾方,應用于造血干細胞移植過程,以求疏肝和解,健脾和胃。甘欣錦[7]認為小柴胡湯對于免疫抑制免疫抑制狀態顯示出明顯的優越性,對經放化療治療后的惡性淋巴瘤患者有提高自身免疫功能、殺傷或抑制微小殘留病灶、預防疾病復發等的作用。現代藥理研究[8]發現小柴胡湯有調節免疫、抗炎、調節內分泌、抗肝纖維化、抗腫瘤等作用。倪海雯主任在臨證中常使用小柴胡湯化裁治療淋巴瘤伴見口苦、口干不欲飲,心煩,胃脹,納差,苔黃膩,脈弦數等癥狀者。因其少陽樞機不利,少陽郁火,或上擾心神,或橫逆犯胃,方用小柴胡湯加減,其中柴胡疏散少陽邪氣,黃芩清泄少陽之熱,半夏、生姜、大棗、太子參、麩炒山藥、麩炒白術等固護脾胃,加以白花蛇舌草等抗癌藥物祛癌毒之邪。諸藥合用,和解少陽,以祛半表半里之邪。
2 寒熱并調之半夏瀉心湯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曰:“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3]56病機為小柴胡湯證誤用攻下,損傷脾胃陽氣,少陽邪熱趁虛而入,以致寒熱互結,遂成痞證。《金匱要略》補充曰“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9],里虛胃寒故心下痞,寒飲郁而化熱上泛則嘔,熱激飲于腸則腸鳴,指明其病機為脾胃升降失常,而成上熱下寒之證。半夏瀉心湯有保護胃黏膜、抗腸道腫瘤、抗HP感染、調節腸道菌群等現代藥理作用[10-11]。花寶金[12]認為腫瘤的發生多為寒熱虛實夾雜,尤其是放化療等治法極易損傷人體正氣,而出現口干渴、咽喉不利、唾膿痰、心煩、惡心嘔吐等上熱癥狀和心下痞滿、腹痛、腸鳴泄瀉、食納差等下寒癥狀并見,故在臨床治療上常使用半夏瀉心湯加減化裁,以和解表里,清上溫下,收效甚捷。徐瑞榮[13]認為半夏瀉心湯的病機關鍵在于中氣虛弱,濕熱阻胃,寒熱錯雜,升降失調,氣機逆亂,臨床上惡性血液疾病的發病或化療治療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寒熱紊亂的胃腸消化道癥狀,故常使用半夏瀉心湯平調寒熱陰陽。麻柔[14]常使用半夏瀉心湯治療化療后出現嘔滿、不欲食、苔膩或大便稀瀉等中焦濕熱癥狀兼有虛象者。倪海雯主任在臨床中,對于淋巴瘤癥見上腹部不適,口干口苦等上焦胃熱之象,而又兼見有稀便,納差等中焦虛寒之癥,常使用半夏瀉心湯加減,其中干姜、半夏配黃芩、黃連辛開苦降,寒熱并調,佐以大棗、生山藥、生薏苡仁等味甘之品,調和脾胃扶助正氣。
3 調和肝脾之四逆散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曰:“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3]99該方常用于治療出現四肢厥逆,而無明顯寒證或熱證者,然后世將其拓展為疏肝調脾之基本方。肝主疏泄,能調暢情志,促進脾氣升清與運化,若肝失條達則脾土壅滯。脾主健運也有助于肝氣條達。淋巴瘤為惡性腫瘤,患者多因情志不舒,肝氣郁結,肝失條達,進而木克脾土;或因素體中焦虛弱、憂慮傷脾,脾失健運,氣機壅滯,導致肝失條達,從而形成肝脾不調證。郎立新[15]通過觀察益氣解毒調和肝脾法治療惡性血液病伴抑郁狀態療效及對T淋巴細胞亞群水平的影響,得出結論四逆散加減治療惡性血液病伴抑郁狀態療效顯著,且不良反應小,安全性高,還可顯著提高血液病患者的免疫功能。四逆散主要有催眠、抗抑郁、調節胃腸功能、保肝等藥理作用[16]。臨床上,倪海雯主任靈活使用四逆散有效改善淋巴瘤患者因情緒焦慮或抑郁導致的胃腸功能紊亂、失眠、經期不調,或化療導致肝功能損傷等。方中柴胡解郁行氣;調暢氣機,枳實理氣解郁,破結泄熱;白芍養血斂陰柔肝。其中腹瀉重者,加用白術、茯苓;失眠重者加用茯苓、夜交藤養心安神;月經失調者加用益母草等。
4 調和營衛之桂枝湯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言:“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干嘔者,桂枝湯主之。”[3]9《傷寒來蘇集》中將桂枝湯譽為“仲景群方之冠,乃滋陰和陽、調和營衛、解肌發汗之總方也”。營衛概念首見于《素問·痹論》云:“榮(營)者,水谷之精氣也,和調于五臟,灑陳于六腑,乃能入于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衛者,水谷之悍氣也,其氣剽疾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于盲膜,散于胸腹”[2]365。《靈樞》曰“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為血”[2]162,由此可見,營氣是血液的重要組成部分,故常以“營血”相稱。營血屬陰,又稱之為營陰。營陰與衛陽密切聯系,共同維護機體平衡,若營衛失和,則會出現自汗、易受外邪、或晝不精,夜不暝等癥狀。徐奔[17]使用桂枝湯加減以改善患者貧血、自汗、惡風等癥狀,療效顯著。蘇鳳哲[18]使用桂枝湯治療血液病合并外感者,因其陰血已傷,不可過用發汗,進一步耗傷氣血,需調和營衛,扶正驅邪,以求疾病向愈。倪海雯主任認為淋巴瘤放化療后,多出現骨髓抑制、機體免疫力低下,表現出營血虛弱、衛氣不固之象,以營衛失和為基本病機,故使用桂枝湯加減,以平和之藥調和營衛,調整陰陽,增強人體抗病能力。方中桂枝、姜、棗、甘草等健脾開胃、顧護后天之本,使正氣充盈,邪無所留。正如章虛谷所說“此方立法,從脾胃以達榮衛,周行一身,融表里,調陰陽,和氣血”,“故無論外感、內傷,皆可取法以治之”[14]。
5 調和虛實之烏梅丸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言“蛔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3]104,其由烏梅、細辛、干姜、炮附子、蜀椒、黃連、黃柏、當歸、人參組成,其組方酸辛苦并用、寒熱共調、扶正祛邪并舉,起初在仲景原文中主要用于蛔厥證,但后世醫家對烏梅丸的理解不斷加深,從而擴大了烏梅丸的應用范圍。烏梅丸是厥陰病的主方,《傷寒論》曰:“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3]102邪在厥陰,厥陰內存相火,郁極而發則出現熱證,饑不欲食表明其存在中焦脾胃虛寒,水谷運化失職。《醫宗金鑒》曰:“厥陰者,陰盡陽生之臟,與少陽表里者也。邪主其經,從陰化寒,從陽化熱,故其為病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也。”[19]厥陰病篇位于六經之末,全篇死癥居于六經之首,病至厥陰則外感、內傷已至最末期,元氣衰亡、氣血耗傷殆盡、生死頃刻[20]。王萍等[21]認為惡性腫瘤中后期常出現寒熱錯雜的表現,且厥陰風動挾痰瘀毒流竄是惡性腫瘤轉移的病機關鍵。研究[22]發現烏梅丸具有抗炎、調節免疫、促進胃腸功能恢復、調節腸道菌群、抑制細胞凋亡、修復黏膜屏障和抗氧化損傷等現代藥理作用。倪海雯主任在臨床運用中,使用烏梅丸加減,治療中晚期淋巴瘤患者出現腹痛腹瀉癥狀,或由于化療藥物損傷人體正氣,或抗生素使用導致腸道失調,均有較好療效。方中烏梅味酸入肝,斂肝陰,緩肝以防克脾,同時能收斂止瀉;黃連、黃柏苦寒,清泄肝火;桂枝,細辛散在里之寒氣;炮附子補陽;太子參、麩炒白術、麩炒山藥等甘淡之品,益氣健脾;白芍配伍炙甘草以達緩急止痛之效。
6 案例舉隅
高某,男,82歲,2020年4月發現左側頸部腫痛,伴脹痛,無畏寒發熱,無胸悶氣喘,未予重視,后腫塊逐漸增大,出現氣喘不適,遂于2020年5月至鼓樓醫院行頸部淋巴結穿刺、病理示: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生發中心起源。PET-CT示:(雙側頸部、雙側鎖骨區、雙側腋窩、雙側胸壁下、雙側胸骨旁、右肺門及縱隔內)多發腫大淋巴結,累及左側鎖骨,葡萄糖代謝顯著增高;右側第一胸肋關節葡萄糖代謝增高,符合淋巴瘤表現。明確診斷為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生發中心外,Ⅳ期B組,IPI積分4分,高危組)。分別于2020年6月19日、8月14日和10月15日至鼓樓醫院行miniR-CDOP方案三療程。患者難以耐受化療,遂于我院尋求中醫藥治療。
首診(2020年11月24日):患者神疲乏力,面色少華,自汗,胃脘脹痛,納差,口干口苦,大便不成形,無腹痛,無惡心嘔吐,無惡寒發熱,舌紅,苔微黃稍膩,脈細弱。四診合參,辨病為惡核,辨證屬寒熱錯雜證。以健脾和胃,平調寒熱為法。方以半夏瀉心湯合參苓白術散加減:法半夏12 g,干姜9 g,黃芩9 g,黃連3 g,大棗6 g,太子參15 g,麩炒白術20 g,麩炒山藥20 g,生薏苡仁15 g,重樓6 g,白花蛇舌草20 g,甘草6 g。7劑,水煎服,早晚各1次。
二診(2020年12月1日):患者精神較前好轉,口干口苦、胃脹減輕,便稀,日兩次,胃口稍好轉,乏力自汗同前。予首診方加茯苓15 g,澤瀉12 g,仙鶴草20 g,黃芪12 g,防風9 g,白扁豆15 g,陳皮9 g,蘇梗6 g,刀豆殼9 g。7劑,水煎服,早晚各1次。
三診(2020年12月12日):患者大便恢復正常,乏力、胃納明顯好轉,自汗減輕。予二診方繼服,7劑,水煎服,早晚各1次。
后隨診1年余,患者訴癥狀緩解,體力恢復。
按:患者確診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Ⅳ期),行三療程化療后,機體不耐受。患者高齡,素體本虛,加之癌毒侵襲,藥毒所傷,出現乏力,稀便,納差等中焦虛寒之象,及胃脘脹痛,口干口苦等上焦胃熱之象,辨證屬寒熱夾雜證,治以扶正祛邪,平調寒熱,方用參苓白術散及半夏瀉心湯加減,其中干姜、半夏配黃芩、黃連辛開苦降,寒熱并調,佐以大棗、生山藥、生薏苡仁等味甘之品,調和脾胃,扶助正氣,輔以用白花蛇舌草等抗癌藥物祛除癌毒。二診,患者乏力、自汗同前,便稀,加予茯苓、澤瀉、白扁豆健脾化濕,陳皮、蘇梗、刀豆殼醒脾和胃。患者高齡,基礎疾病多,加之化療后藥毒所傷,病機愈加復雜,非單純補益或攻伐能奏效,需標本兼顧,寒熱并調。倪海雯主任認為淋巴瘤的中醫病機主責之于臟腑虛損,痰濁瘀血等邪毒內停,膠結盤踞,變生癌毒。多因復合是淋巴瘤病機特點。治療上主張復法組方,以和法為要,顧護中焦為主,調和氣血、寒熱、虛實,以平為期,從而達到治療目的。
7 結語
淋巴瘤的治療目前以放化療及靶向用藥為主,極大地改善了本病的預后,延長了總體生存。復發、耐藥是目前臨床面臨的主要挑戰。老年群體治療不耐受及合并癥是患者求諸中醫治療的主要原因,也是發揮中醫藥優勢的關鍵所在。患者免疫化療后藥物所致的副作用如感染、胃腸道并發癥、腫瘤所帶來的發熱、盜汗、疲乏等,病機復雜,癥狀多變,寒熱錯雜,虛實并見,以經方和法指導疑難復雜病治療甚為合拍,我們希冀從仲景經方中尋找亮點,從而更好地發揮中醫藥增效減毒的優勢,為中西醫結合治療淋巴瘤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