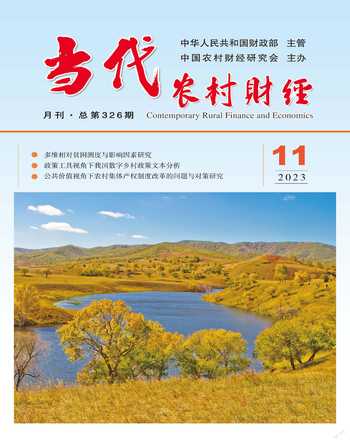多維相對貧困測度與影響因素研究
黃馨怡 許敏蘭 陳明蘭
摘要: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集“大山區、大農村、少數民族聚居地”于一體,擺脫絕對貧困后,相對貧困治理后勁仍有所不足。本文構建包含經濟、可行能力、社會保障、政策、內生動力在內的多維相對貧困識別體系,運用A-F法對多維相對貧困進行識別、測度和分解。研究發現,區域內30.90%的家庭在2個維度上存在貧困,家庭在內生動力與政策維度的相對剝奪感最高。在此基礎上,通過二元Logistic模型進一步對農戶家庭的致貧因素進行研究。最后,基于本文實證研究結果,為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相對貧困有效治理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湘鄂渝黔 多維相對貧困 A-F方法 二元Logistic模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特色農業減貧的長效機制、效應評價及對策研究”(20BJY169);2022年國家級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特色農業緩解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效應評價及對策研究——以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為例”(202210554005);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XSP19YBZ067)。
一、引言
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相對貧困的治理將成為后扶貧階段的重要任務。較絕對貧困而言,相對貧困的致貧因素更為復雜,貧困維度也由單一收入維度延伸至多維。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集“大山區、大農村、少數民族聚居地”為一體,在脫離絕對貧困后,仍然是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洼地”,部分“脫貧摘帽”農戶生計水平偏低,面臨較高的返貧風險,完善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多維相對貧困識別體系、測度多維相對貧困程度并分解主要致貧維度,有針對性地治理相對貧困對于相對貧困的整體治理有著重要意義。
目前,學界對于相對貧困的概念尚未形成統一的界定,但相對貧困的內涵已從收入貧困進一步延伸到能力貧困(Sen,1997)、權利貧困(UNDP,1997)、相對剝奪(Townsend,1979)、社會排斥(李棉管等,2020)、知識貧困(王太明等,2021)等,貧困視角從單一收入維度轉向多維度已成為主流趨勢(劉海霞,2023),但未來階段對相對貧困的理解仍然要以絕對貧困作為內核(林閩鋼,2020)。學界關于相對貧困豐富的研究成果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但現有研究在相對貧困測度方面仍主要聚焦于以收入為主的經濟維度,對相對貧困的多維測度有所忽視。
因此,本文基于對相對貧困內涵的理解和研究區域現狀,引入包括收入在內的多維剝奪指標,構建多維相對貧困識別體系,對研究區域多維相對貧困現狀進行測度,并進一步分析其影響因素,對鞏固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二、多維相對貧困研究設計

(一)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深居武陵山腹地,是典型的跨行政區的貧困地帶,近年來依托扶貧政策和地區資源稟賦,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自脫離絕對貧困以來,脫貧戶減少了部分來自政府的穩定補貼與扶持,相對貧困治理后勁有所不足。長期以來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導致其早期開發不足,經濟發展不充分,產業結構傳統且較為單一,基礎設施普及率低,整體發展水平較低等問題仍然存在。
本文選用2020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以下簡稱CFPS)數據及課題組實地調研數據,使用stata17對湘鄂渝黔四省交界處區域樣本進行有效性篩選,最終得出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共890個有效樣本,其中湘西地區213個、鄂西南地區237個、渝東南地區210個,黔東地區230個。
(二)測度模型設定與指標選取
1.模型設定
A-F方法通過雙重臨界值來識別個體(家庭)在各維度以及總體上的相對貧困狀況(Alkire S, Foster J.,2011),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所采納,成為目前測量和評估多維貧困的主流方法。本文采用A-F方法對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進行多維相對貧困測度與分解,具體步驟如下:
(1)單維度相對剝奪識別。以樣本區人口總量和相對貧困總維度個數設定矩陣。zj表示維度j被剝奪的臨界值,若xij≦zj,令gij=1,表示樣本i在維度j上被剝奪;反之,令gij=0。
(2)多維度相對剝奪識別。令各維度權重為wj,構建矩陣G={wjgij},并計算相對貧困剝奪總分,若≥k,則認為樣本i屬于多維相對貧困;反之,則不屬于。


2.指標選取
本文結合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實際情況,參考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MPI指標體系、張承等(2021)、董艷敏等(2023)等選取的多維貧困指標,基于對相對貧困的內涵的理解,從收入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視角出發構建多維相對貧困識別體系。其中,收入貧困由經濟維度體現。收入是經濟維度的主要指標,本文借鑒方迎風等(2021)提出的平均收入的60%為臨界值。就業是緩解收入貧困的重要措施,故將就業也引入經濟維度。可行能力與內生動力分別從客觀和主觀視角來衡量能力貧困。最高學歷與健康狀況反映個體改善生活的現實能力,個體改善生活的主觀意愿表現為發展意愿與生活滿意度。權利貧困主要由社會保障與政策維度反映。醫療、教育、養老與住房保障是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政府在我國貧困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結合CFPS數據的可得性與穩定性,本文主要選取政策滿意度與產業幫扶作為衡量指標。
同時,本文參考UNDP全球多維貧困指數方法,采用等權重法進行賦權,具體維度與維度指標描述性解釋及權重如表1所示。
三、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多維相對貧困狀況測度
(一)單維相對貧困測度
結果顯示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家庭樣本在五個維度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對貧困,這反映出研究區整體發展相對落后。其中產業幫扶、住房保障、生活滿意度、教育保障指標與政策、內生動力維度的相對貧困發生率最高,究其原因,仍然與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山地廣布,貧困歷史悠久,貧困問題復雜多樣有較大關聯。由于地區對外交通不便,基礎設施匱乏,政策支持力度有限,在住房和教育保障問題上存在諸多問題,產業發展也以農業為主且大多數農戶僅從事農業種植、采摘等基礎前端性工作,農業增收效應有限,生活總體滿意度不高。此外,勞動者協會如農村經濟合作社效能不高,產業扶持力度不足的問題也進一步制約著湘鄂渝黔省際交界地區相對貧困治理的進程。
(二)多維相對貧困測度
剝奪閾值k的設定在多維貧困識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UNDP發布的多維貧困指數設定的k=1/3,但由于本文維度數量與MPI中不同,同時為了更好觀察在各剝奪閾值下研究區域多維相對貧困情況,故采用變動的剝奪閾值k,以期選出適合研究區域的多維相對貧困剝奪閾值。
貧困發生率主要衡量多維相對貧困廣度。由測度結果可知,隨著k值的變化,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家庭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存在明顯變化。當k值從0.1增加到0.4時,多維相對貧困發生率從99.55%下降至30.90%,大幅下降但總體數值較高,表明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約2/3的家庭承受著2個維度及以下的貧困;當k值從0.4增加到0.8時,多維貧困發生率從30.90%下降至0.11%,變化幅度趨小且數值較低,多維相對貧困程度顯著降低,1/3家庭受到了2個維度以上的貧困;當k=0.9時,多維相對貧困發生率為0,說明所選樣本中沒有同時存在4個維度以上的貧困。測度結果符合我國已脫離絕對貧困的基本國情,同時也體現出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發展較為落后,多維相對貧困問題較為顯著。
平均被剝奪程度反映多維相對貧困深度。樣本家庭的平均被剝奪程度隨著臨界值k的增加而增加,從k=0.1時的32.10%增加至k=0.8時的85.00%。這一現象表明,隨著多維相對貧困剝奪閾值上升,貧困戶數不斷減少,但多維相對貧困深度不斷增加。當k=0.4時,相對貧困家庭平均被剝奪程度高于46.87%,此類家庭存在著“緩貧難,返貧易”的問題,應成為重點關注對象并納入貧困檢測體系中。隨著剝奪閾值k的增加,相對貧困準入門檻提高,地區多維相對貧困程度相應降低,多維相對貧困指數呈下降趨勢。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多維相對貧困剝奪閾值k=0.4為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多維相對貧困重要測度節點,當k=0.4時,研究區域內30.90%的家庭在2個及以上維度存在貧困,多維相對貧困指數為0.145,符合本文對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多維相對貧困情況的預期,綜上所述,本文將k=0.4設定為多維相對貧困剝奪閾值。
(三)多維相對貧困維度貢獻率分解
由分解結果可知,不同維度的貢獻率差異較大。k=0.4時,貢獻率從大到小依次是內生動力、政策、社會保障、經濟、可行能力。其中,內生動力與政策貢獻率分別為27.46%、25.29%,維度貢獻率最高,均超過20%,可能源于研究區域貧困人口思想仍較為落后,對輸血式扶貧的依賴性較高,缺乏開闊的視野與積極的自主意識,且區域內扶貧政策缺乏可持續性,在脫離絕對貧困后過渡到相對貧困有效治理方面存在脫節之處。
社會保障、經濟維度的貢獻率分別為19.16%、15.44%,均超過15%,現階段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在社會保障方面仍存在公共服務性基礎設施不完善,社會保險覆蓋率較低的問題。經濟維度貢獻率較高反映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較大,家庭勞動力就業不穩定等問題。可行能力的貢獻率相對較低,僅為12.65%,可能由于大眾對于教育和健康重視程度不斷上升及國家精準扶貧期間對基礎教育、醫療設施的初步普及降低了相對貧困家庭在這個維度上陷入貧困的概率。
隨著K值的上升,經濟與可行能力維度貢獻率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可行能力維度的貢獻率出現了將近15%的上升,而社會保障、政策、內生動力維度的貢獻率總體上則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社會保障維度貢獻率降至20%以下;內生動力維度和政策維度貢獻率仍高于20%。即對于貧困程度更深的家庭而言,可行能力、內生動力、政策支持不足是導致家庭陷入多維相對貧困的深層原因。深度多維相對貧困家庭對現有生活現狀不滿但因缺乏發展能力和發展條件,致使發展動力不足,家庭多維相對貧困現狀得不到改善,享受較好的教育、醫療等服務的權利被限制,進一步導致發展能力與動力不足,容易深陷貧困的惡性循環,亟需政府部門政策支持的介入。
(四)地區多維相對貧困分解
本文在k=0.4下對區域的多維相對貧困狀況進行分解。四地平均被剝奪程度相似,均高于45%,多維相對貧困程度深,返貧風險大。同時,多維相對貧困發生率和多維貧困指數均呈現出渝東南地區最高,鄂西南地區、湘西地區次之,黔東地區最低的情況。
本文進一步在k=0.4時探究各維度對四地多維相對貧困的貢獻率。政策維度對四地貢獻率均較高,超過20%,表明現階段研究區整體均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可持續性不強、政策落實到農戶家庭過程不暢等問題。此外,對四地的分解結果進行分析,情況如下:
渝東南地區家庭內生動力維度貢獻率高,家庭發展自主性不足問題相對較為嚴重。渝東南地區各縣域經濟不發達,整體受教育程度與公共基礎設施與重慶市平均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且較少受到重慶市旅游業發展的帶動,區域內人口思想落后,對輸血式扶貧的依賴性仍然較高,導致內生動力維度致貧率居高不下,多維相對貧困指數高達0.263。鄂西南地區內生動力及社會保障維度貢獻率較高。近年來,鄂西南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較為迅速,相對貧困狀況有所好轉,但基礎設施滯后的問題仍然存在,民生保障不足,醫療教育等領域發展落后,對地區內家庭發展內生動力的激發有限,多維相對貧困指數為0.149,返貧風險較高。湘西地區社會保障和可行能力維度致貧率較高。湘西地區依托當地資源稟賦,大力發展八大特色農業產業及文旅產業,經濟發展總體較為平穩,但在財政投入政策銜接方面存在效率性不足的問題,公共服務設施供給不平衡、不充分,公共衛生服務能力不足,區域內家庭居民健康水平有待提升,多維相對貧困指數為0.098。黔東地區社會保障及經濟維度致貧率較高。黔東地區多年來基礎設施與基礎保障薄弱,產業的增收效益有限,但隨著“縣縣通”高速及鐵路的開通極大的改善了交通區位條件,依托“梵凈山”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品牌發展的產業鏈也給當地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多維貧困發生率為0.077。
四、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多維相對貧困的影響因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表現出了較為顯著的多維貧困特征,經濟、可行能力、社會保障、政策、內生動力是影響研究區域多維貧困狀況的主要維度,然而,戶主、家庭與外部因素是否也影響農戶多維相對貧困暫無定論。因此,本文引入戶主因素、家庭因素與外部因素對研究區域農戶多維貧困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由于“是否為多維相對貧困”是一個二分變量,本文借鑒左宇曉(2022)的研究方法,選取二元Logistic模型進行分析。將上述變量引入Stata17,相關變量解釋與輸出結果如表2所示。回歸結果顯示Prob>chi2=0.0000,回歸模型顯著。
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戶主因素方面,健康狀況及教育程度與被解釋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戶主的健康狀況越好、教育程度越高,其勞動能力和學習能力也隨之增強,對新事物、新理念的接受與實踐速度也越快,能夠更好地掌握各類技能,家庭陷入多維貧困狀況的可能性就越低。戶主因素中的年齡與婚姻狀況以及家庭因素的顯著性均較低,與研究區域家庭多維相對貧困的關聯度較低。外界因素中,政治參與與社會參與達到顯著水平,即研究區域家庭政治參與及社會參與程度越高,越能夠理解與支持當地扶貧與鄉村振興政策,并參與到其中去,緊跟政策導向,家庭更不容易陷入多維貧困,因此完善基層民主及政策落實制度,鼓勵村民之間的溝通交流與經驗借鑒也有利于改善相對貧困狀況。
五、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A-F雙臨界值法及二元Logistic模型對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多維相對貧困現狀進行了定量研究和系統性分析,得出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整體多維相對貧困情況普遍,30.90%的家庭存在2個維度及以上的貧困,但極端相對貧困現象的發生率較低。其中,內生動力與政策是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主要致貧原因,反映目前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普遍存在政策可持續性不高、家庭內生動力不足且對政策依賴性大的問題。此外,可以發現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整體多維相對貧困主要由鄂西南地區、渝東南地區貧困程度拉高。從多維相對貧困的影響因素來看,健康狀況、教育程度、政治參與及社會參與對研究區域家庭多維相對貧困程度產生顯著影響。本文依據實證檢驗結果,對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相對貧困治理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
(一)要建立與地區高度適配的多維相對貧困的識別與監測機制,循序漸進地制定扶貧補貼政策

目前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已經脫離絕對貧困,但是據上文分析發現,四地居民對于輸血式扶貧依賴性仍然較高,直接切斷對貧困戶的扶貧補貼反而會增大返貧的可能性,不利于整體性相對貧困的治理。同時,政府應根據當地情況建立更為全面的貧困識別體系,充分聯系村集體與各鄉鎮定期更新區域內家庭的檢測數據,對相對貧困人口實行動態監測,對納入相對貧困檢測體系的家庭進行定期走訪與清理。由實證結果可知,研究區域不同區劃間的致貧原因具有差異性,相對貧困的識別體系及治理戰略都應基于這種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對致貧貢獻率高的維度進行傾斜。基于本文測度結果,湘西地區、鄂西南地區、渝東南地區應更加重視權利與能力貧困,黔東地區則應對收入與權利貧困進行一定的傾斜。
(二)大力發展地區特色產業,增強相對貧困家庭可持續發展能力與內生動力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可以有效實現脫貧地區相對貧困的治理。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家庭有著豐富的地理資源與能力稟賦,各地特色農業產業發展勢頭良好,通過技能培訓、產業幫扶等手段,可以提高相對貧困家庭發展能力。同時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建立農村合作社等方式完善利益聯結機制,可使相對貧困家庭鏈式嵌入當地產業鏈各環節,激發其萌生努力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主觀意愿,并付諸于實踐,完成相對貧困戶的自我飛躍,最終實現相對貧困家庭長足發展與相對貧困地區整體發展并舉。
(三)大力完善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基礎設施,提高地區社會保障程度
基礎設施滯后是本文研究區域發展的一大短板,數據顯示研究區域內基礎設施覆蓋率均低于本省平均水平。需進一步加快地區建設,升級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的基礎設施,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具體體現為增加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基礎教育和醫療設施數量,加大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覆蓋率,提高住房保障,對老舊居民住房及危房進行監測與改造拆遷,形成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同時,交通基礎設施是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撐,基于本文研究區域多山的地形結構,應大力加強當地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促使交通基礎設施服務鄉村振興,建立農村公路“+產業”“+生態”“+文化”發展模式。
(四)各地政府應加強交流合作,形成相對貧困治理的合力
湘鄂渝黔省際交界處各市縣在地域上相鄰,地理區位條件趨同,且均面臨著相對貧困問題積累已久、貧困程度深的問題,在致貧原因中也有相似之處。各地政府在進行相對貧困治理時應采取“協調聯動、統籌發展”的發展戰略,在打破交通壁壘的基礎上,加強資源整合,提高地區間之間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大數據、知識資本等高素質要素流通效率。著力解決四地部分產業結構高度同構且水平低的問題,形成“各有所精”的發展格局,打造武陵山片區優勢產業集群。同時,利用豐富民族文化資源創建武陵山片區全域旅游國家示范區,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形成相對貧困治理合力,達到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治理效果。
參考文獻:
[1]Sen,A.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ofPoverty[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81( 2) : 285-307.
[2]Programme U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J]. New Y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6(2):430.
[3]Townsend,P.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 Living[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79.
[4]李棉管,岳經綸.相對貧困與治理的長效機制:從理論到政策[J].社會學研究,2020,35(06):67-90+243.
[5]王太明,王丹.中國共產黨治理農村絕對貧困的歷程、經驗及啟示[J].農業經濟,2021(11):84-86.
[6]劉海霞,周亞金.后脫貧時代中國相對貧困治理研究——基于馬克思相對貧困理論的視角[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1-9.
[7]林閩鋼.相對貧困的理論與政策聚焦——兼論建立我國相對貧困的治理體系[J].社會保障評論,2020,4(01):85-92.
[8]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Poverty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476-487.
[9]張承,彭新萬,陳華脈.我國多維相對貧困的識別及其驅動效應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21(11):15-29.
[10]董艷敏,嚴奉憲.風險沖擊對農村居民家庭相對貧困的影響——基于CFPS數據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23:1-13.
[11]方迎風,周少馳.多維相對貧困測度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21,36(06):21-30.
[12]左宇曉,卜津月.我國勞動力人口多維相對貧困測度及影響因素分析[J].統計理論與實踐,2022,No.518(06): 29-35.
(作者單位:湖南工商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湖南工商大學經濟貿易學院)
責任編輯: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