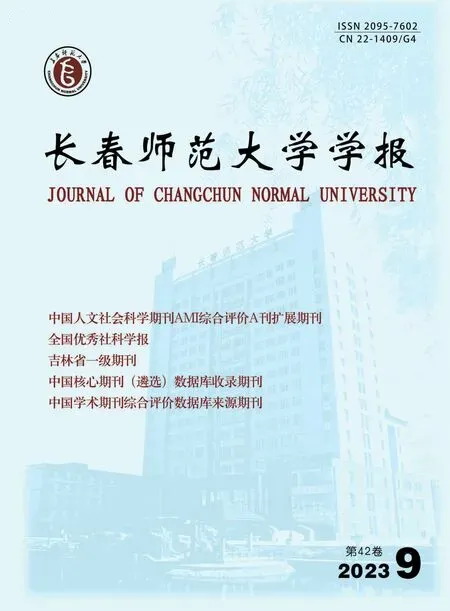《左傳》中“君子曰”非孔子、左丘明、劉歆之言考
龐光華
(五邑大學 文學院,廣東 江門 529020)
先秦人很重視格言警句對人的教育和啟發作用,有思想啟發的格言往往廣為傳頌。說這些格言的人被稱為君子,這樣的君子不是專指一人,是一個泛稱。只要他說的格言符合當時正當的價值觀,而且有哲理上的啟發性,就會被人們引述和傳頌。
《論語·憲問》:“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史記·老子列傳》:“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古之有德者稱君子,其言可堪后世效法者皆有各種文字記錄,絕非僅憑口耳相傳。《文心雕龍·諸子》曰:“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者也。”可知戰國為著書盛行的年代。
《論語·子罕》:“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莊子·人間世》曰:“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同章又曰:“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法言》與《法語》同義。此為古有《法語》書之鐵證。
《詩經·雨無正》:“如何昊天,辟言不信!”毛傳:“辟,法也。”“辟言”正是“法言”。《法語》即是記錄圣賢語言的專書。“法語”一名猶如“格言”“嘉言”。《詩經·抑》:“慎爾出話。”毛傳:“話,善言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后世之《增廣賢文》,今之名人語錄、座右銘之類,皆近似“法語”。古之《法語》書流傳甚廣,為正規的教育課程之一。《郭店楚墓竹簡》中有《語叢》四卷,正是古之《法語》中的一種。筆者在《法語考》中考證先秦以來的“法語”頗詳[1]。今細案《左傳》中的“君子曰”之言,可以推知“君子曰”之言本來記錄于各種文獻,有的屬于“法語”。
一、“君子曰”非左丘明之言
《左傳》中的“君子曰”之言是《左傳》固有之文,還是為后人所加?學者眾說紛紜,今不枚舉。筆者在研究古之《法語》(也簡稱《語》)之后,確信《左傳》中的“君子曰”不是《左傳》固有之文。細考“君子曰”之言,發現不少是格言警句加上具體的評論。其中的格言或定論性語句正類似古代的《法語》。《禮記·中庸》:“是故君子……言而世為天下則。”古時《法語》之言均被當作君子之言,《左傳》引述來批評史實。
我國自古以謙遜為美德。《論語》中孔子自稱為“丘”,沒有別的自稱。《左傳》的作者哪有自稱為君子的道理?明是引述圣賢語錄,統稱為“君子曰”。《國語·周語中》:“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可知把“君子曰”之言編入《左傳》的人不會自稱為君子。《左傳》之例,凡稱“書曰”皆指孔子《春秋》;凡稱“禮曰”皆指《禮經》或《禮志》中之言;凡稱“君子曰”皆泛引君子的評論,非專指一人。“君子曰”無一為左丘明自道。《左傳》中還引有許多《詩經》《書經》中的成言,還涉及《周書》《周易》《周詩》《軍志》等。儒家信守“述而不作”之訓,故慣于引古人之言來表意。《左傳》引“君子曰”來作歷史評論,是完全正常的。
古人慣于引成言來達意,再加上自己的按語,其體例如:
《韓非子·難三》:“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老子語錄“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為成言,“其子產之謂矣”是韓非子之言。
《國語·周語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襄公稱“人有言曰”,即是《左傳》所錄春秋時人慣說的“古人有言曰”。“兵在其頸”為法語。“其郤至之謂乎”為襄公語①。
《莊子·秋水》:“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其中“聞道百,以為莫己若”為野語,不確定指某一個人說的,非河伯自己之言。
《左傳·宣公十六年》:“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引述“諺曰”之言的人引用俗諺,再加自己的按語,不知道“諺”的作者是誰。
《論語·學而》:“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其斯之謂與”以前引《詩經》中的成言,并非子貢語錄。
《禮記·喪服四制》:“《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也是其例。
《呂氏春秋·行論》曰:“《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古人凡稱“其此之謂乎”之類話之前的語錄皆為前人格言或成語。古書中例證多如恒河沙數。
《中論·法象》:“《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
《孟子·滕文公上》:“《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
《孟子·萬章上》:“《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同篇:“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孟子·公孫丑上》:“《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在《荀子》中,此類句式多達近百例,一覽即知。《左傳》“君子曰”中凡是格言或評論性語句,皆為“法語”。“其□□之謂乎”為插入“君子曰”之言的編者的案語。故“君子曰”所引之言,不可能是左丘明自己的語言。
《左傳·隱公元年》:“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此雖非格言,但為評論性嘉句,不可能是左丘明自己的話。
《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其是之謂乎”為引述者之言。這里的“君子曰”在《商頌》之前,左丘明怎么可能將自己的話放在《詩經》的前面?太不合情理。
《左傳·隱公五年》:“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大義滅親”是當時的成語)。其是之謂乎(此為左氏語)。”
我們據上引之《國語》《韓非子》《論語》《呂氏春秋》《莊子》《荀子》《孟子》《禮記》,可知“其是之謂乎”是當時習語,絕非所引古人成言。“其是之謂乎”之前的話才是古人格言。尹灣出土的竹簡《神烏賦》:“曾子曰‘烏之將死,其唯哀’。此之謂也。”亦是明例。《左傳·隱公五年》:“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這是“法語”,沒有引述者自己之語言。
《左傳·隱公六年》:“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善不可失,惡不可長”明顯是格言,而且放在《尚書》的前面,不可能是左丘明自己的話。
《左傳·桓公六年》:“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鄭世子忽在說話中已經引用“君子曰:善自為謀”。可知《左傳》中“君子曰”之體例非左丘明自創,實為當時之慣例。或許有人把“君子曰”以前的話定為世子忽之言,“君子曰”之言為述者所引。但我們認為《左傳》這句話中引用的《詩》和“君子曰”都應該出自“大子”之口,由“大子”引錄,這樣判斷才符合全句的意思。這個例證十分重要,可知“君子曰”不可能是左丘明之言。
我們可以舉出類似的旁證。《國語·楚語上》:“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谷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溪。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國語》此言兩次引述“君子曰”之言,一為“君子曰:違而道”(違反君王的意愿,卻符合大道,有好的結局);一為“君子曰:從而逆”(順從君王的意愿,反而沒有好結果,沒有好報)。從全句的意思看,可以肯定這兩處“君子曰”之言是倚相在回答司馬子期的話語中所引述的,絕不可能是《國語》的作者自己加的。由此可知,春秋時期的人們已經在說話時引用君子之言。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左傳》中的“君子曰”中的君子絕對不是左丘明。另外,《左傳》中的“君子曰”之語常與《詩》《書》并稱。可知“君子曰”之言有很多可能出于專書《法語》,與《詩》《書》同例。左丘明能把自己的話置于《詩》《書》之上嗎?“君子曰”之語斷非左丘明者自己的語錄。其它“君子曰”之例皆可類推。
《左傳》還常常引述“古人之言”,多為格言警句,有較大的思想啟發作用和教育功能。例如:
1.《僖公六年》:“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古人有言曰”與“君子曰”類似。
2.《文公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馀幾’。又曰‘鹿死不擇音’。”
3.《宣公十五年》:“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4.《成公十八年》:“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國語·晉語六》作“人有言曰”,無“古”字。
5.《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逆之而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
6.《襄公二十六年》:“文子曰:……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7.《昭公七年》:“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以上所錄《左傳》中所述“古人有言曰”均是《法語》中之句,胥出《法語》[1]。春秋時人的慣例是在引用《法語》中所錄的圣哲之言時,稱之為“古人有言曰”或“人有言曰”,或稱作“君子曰”。《左傳》中人物所稱述的出現在口語中的“古人有言曰”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君子曰”。
二、“君子曰”非劉歆之言
我們現在討論另一個問題,即《左傳》中的“君子曰”的出現在什么時候?是否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晚至西漢?《左傳》中的“君子曰”至少在戰國時代已經存在,因為司馬遷的《史記》就已經有幾處引錄了《左傳》的“君子曰”,表明司馬遷讀到的《左傳》已經有“君子曰”之言。這是確鑿不易的。今考論如下。
《史記·秦本紀》言秦繆公死以三良為殉,后引“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此可比對《左傳·文公六年》:“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明是太史公引用《左傳》之文,稍有改編。因此,司馬遷已經見到了《左傳》的“君子曰”之言,斷不可能是西漢末年的劉歆偽造。
《史記·宋微子世家》:“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可比對《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司馬遷直錄《左傳》原文,對《左傳》中難解之處又改變語詞加以說明。
《史記·魯周公世家》:“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可比對《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左傳》的“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太史公概括為“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可知司馬遷讀過《左傳》此處的“君子曰”之言。
《史記·魯周公世家》又曰:“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可比對《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左傳》的“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太史公概括為“君子曰:是不終也”。二者的對應關系極為明顯。
《史記·晉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觽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可比對《左傳·桓公二年》:“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這是太史公把《左傳》中師服的話概括成“君子曰”之言,“君子”應指師服。《毛詩·椒聊》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也是把師服當作君子。
《史記·晉世家》:“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可比對《左傳·襄公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仇,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司馬遷將《左傳》的“君子謂”的評論概括為“君子曰”之言。《左傳》《史記》相應的內容高度吻合,司馬遷肯定見過“君子謂”之言。而且《左傳》此處將“君子謂”放在《商書》的前面,因此不可能是左丘明自己的言論。而且整部《史記》,凡是司馬遷引述《左傳》“君子曰”之言都沒有將這個“君子”當作《左傳》的作者左丘明,可見司馬遷也認為《左傳》“君子曰”和自己《史記》中的“太史公曰”是不同性質的。這條鐵證表明司馬遷絕不認為《左傳》中“君子曰”的君子是左丘明,更不認為那是孔子。我們在下面還會談到這個問題。
《史記·晉世家》:“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可比對《左傳·僖公九年》:“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司馬遷幾乎全錄《左傳》之文,只是把《左傳》‘荀息有焉’改為更加普通的句式為‘其荀息之謂乎’。這也表明司馬遷見到的《左傳》已經有“君子曰”,絕不可能是劉歆偽造。
《史記·趙世家》:“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可比對《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司馬遷明顯是把《左傳》中的大史董狐說成是君子,而不是把孔子說成是君子。
另可舉旁證如《論語·雍也》:“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可比對劉向編撰《列女傳》卷六《椘野辯女》條:“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列女傳》稱顏回為君子。
《左傳·昭公十三年》:“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則孔子稱子產為君子。
這些“君子曰”皆是太史公根據《左傳》錄出,或概括,或改編,或演繹。太史公也直稱君子,不稱左丘明或其他。而且司馬遷還把《左傳》中的師服之言、叔向之言都歸納為“君子曰”,把董狐稱為君子。凡此皆表明司馬遷不以《左傳》中“君子曰”的“君子”是專指左丘明。君子乃是泛稱。而且以上所比對的材料足以表明《左傳》中的“君子曰”之言絕不如宋代以來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是劉歆所混入。因為正如我們所論證的一樣,遠在劉歆之前的司馬遷所讀到的《左傳》就已經有了“君子曰”。
三、“君子曰”之言為先秦經典的文化傳統
還有一個問題,即《國語》和先秦西漢的眾多文獻中也引用了不少“君子曰”之言,這是春秋以來的文化慣例。今列舉如下:
1.《晉語一》:“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2.《晉語一》:“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3.《晉語一》:“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4.《晉語一》:“果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也。”
5.《晉語二》:“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5.《晉語二》:“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6.《晉語四》:“退三舍避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眾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
7.《晉語六》:“君子曰:勇以知禮。”
8.《晉語七》:“君子曰:能志善也。”
9.《楚語上》:“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谷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溪。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以上是《國語》所引錄的“君子曰”,其中只有一條出于《楚語》,其余皆見于《晉語》。顧頡剛《浪口村隨筆》卷之五《〈國語〉中之“君子曰”》一文有見于此,便論曰:“然則于記事之末援君子之名以論事者,其殆晉國特有之史法耶?《左傳》之文出晉史者最多,則《左傳》中之“君子曰”其即沿襲晉史之文耶?然《晉語》所載簡練殊甚,多者七字,少者二字耳,則《左傳》所載長篇大論其出于后人之增益耶?凡此問題,皆今日所當考慮者也。”[2]顧頡剛的觀察相當犀利,很值得重視。
我們還須注意的是《國語》與《左傳》中所引的“君子曰”幾乎無一雷同。如《晉語二》:“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而《左傳·僖公九年》作:“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顯然《國語》和《左傳》所引錄的“君子曰”出于不同的君子之口。《國語》中其余的“君子曰”之言皆不見于《左傳》。而且據上文所論述,司馬遷《史記》引錄的“君子曰”都是根據《左傳》,沒有一條與《國語》的“君子曰”相符合。
古書中引述的“君子曰”之言很多是曾經有專書收集,這種書在先秦叫《法語》,或簡稱為《語》。《法語》書是通名,而不是一部書的特稱;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法語》,也許同一時期也有不同的《法語》。在《左傳》和《國語》之外,有很多書都引述有“君子曰”,上文已經有所舉證,今更列舉它例如下:
1.《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
2.《韓詩外傳》卷八:“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后可使也。”
3.《晏子春秋》卷三《內篇問上》:“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4.《晏子春秋》卷五《內篇雜上》:“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于政。”同卷:“君子曰:圣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同卷:“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5.《晏子春秋》卷六《內篇雜下》:“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6.晏子春秋》卷八《外篇》:“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7.《荀子·勸學》:“君子曰:學不可以已。”
8.《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險,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
9.《韓非子·難四》:“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
10.《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11.劉向《說苑·權謀》:“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
12.劉向《列女傳》共引有“君子曰”十七處,今引四例:(1)《列女傳》卷一《有虞二妃》條:“君子曰:二妃徳純而行篤。”(2)《列女傳》卷二《秦穆公姬》條:“君子曰:慈母生孝子。”(3)《列女傳》卷四《衛宗二順》條:“君子曰:二女相譲,亦誠君子。可謂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夫世。”(4)《列女傳》卷六《椘野辯女》條:“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13.《說苑·君道》:“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訓也。”
14.《孟子·離婁》:“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巳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15.《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這個“君子曰”指的是《呂氏春秋·察傳》篇中孔子的話,“君子”指孔子。
16.《淮南子·人間》:“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此處的“君子曰”出于《老子》第六十二章,“君子”指老子。
《說文解字系傳·錯綜》:“君子曰:‘作書者其知后世之患乎’?”《資治通鑒》中也多有“君子曰”之言。可知“君子曰”是圣賢語錄的泛稱,并非專指一人。劉向《列子書錄》:“《穆王》、《湯問》二篇迂誕詼詭,非君子之言也。”《文心雕龍·征圣》:“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行’。”我們斷不能認為以上的“君子曰”之言都出自一人之口。豈得以《左傳》的“君子曰”專指左丘明耶?
在西漢前期成書的《禮記》中,我們發現大量的“君子曰”之言。今列舉于此:
1.《檀弓上》:“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2.《檀弓上》:“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3.《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4.《禮器》:“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5.《禮器》:“君子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
6.《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7.《學記》:“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
8.《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見《祭義》。
9.《祭統》:“古之君子曰:‘尸亦馂鬼神之余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古人有“君子之言”的說法。例如:
1.《左傳·昭公八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以子野為君子。
2.《禮記·檀弓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3.《禮記·緇衣》:“君子道人以言。”道與導通,訓引導。
4.《禮記·檀弓上》:“是非君子之言也。”
5.《新序》卷七《節士》稱:關龍逢“立而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念矣夫’。”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言孔子作《春秋》,孔子的褒貶皆寓于具體的人物行事之中,不空立格言。《逸周書·史記解》反思歷代各國亡國的教訓,皆就事論事,不徒托空言。《禮記·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古代的教育把抽象的道德寄托于具體的事物之中,以事明理。《文心雕龍·宗經》:“《禮》以立體,據事制范。”規則要通過具體的事例來確立。章學成《文史通義·易教上》:“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故《法語》所集的君子之言有許多是就事論事的具體的人物行事的評論,并不都是格言警句。因此,《左傳》引錄的“君子曰”之言有許多是在評論具體人物。
四、“君子曰”非孔子之言
顧頡剛《浪口村隨筆》卷之五《〈春秋〉與君子》根據《公羊傳》何休注和《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認為《左傳》和《國語》中的“君子曰”中的君子專指孔子。我們不再轉錄《公羊傳》何休注和《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上文已經對此予以批駁。我們難以同意顧頡剛的意見,再總結理由如下。
其一,《公羊傳》何休注和《春秋繁露》都是漢代的今文經學。今文經學的一大特點是神化孔子,把許多與孔子無關的言論和功績都算在孔子身上。這是不可信的。
其二,我們在上面論述過,《左傳》中鄭莊公的兒子世子忽、《國語》中楚國的左史倚相都已在自己的說話中引用“君子曰”之言②。鄭國世子忽的時代遠在孔子之前。司馬遷在《史記》中把《左傳》中的師服之言說成是“君子曰”。在《左傳》中同時出現孔子和董狐時,司馬遷稱董狐為君子,而沒有稱孔子為君子。可見,司馬遷心中的《左傳》中“君子曰”的君子不是孔子。從《史記》看,司馬遷明確認為“君子”不是專指一人。
其三,我們在上文指出過:《國語》和《左傳》中“君子曰”的君子絕不會是同一人,怎么能說就只是孔子呢?就是《左傳》中的“君子曰”的君子也是眾多的無名英雄,并非特指一人。
其四,《禮記》中凡是稱引孔子之言,皆直稱孔子,可是正如我們上文所列舉,《禮記》有比較多的“君子曰”,也因此可知孔子與“君子曰”的君子并非一人。而且《禮記·祭統》:“古之君子曰:‘尸亦馂鬼神之余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稱“古之君子曰”,豈能以“古之君子”就是孔子?
其五,《左傳》的“君子曰”已經引述了孔子《春秋》,可知“君子”不是指孔子。《左傳·成公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這里的《春秋》顯然是孔子所修的《春秋》,而不是作為各國一般史書的原始未修的《春秋》。《左傳》“君子曰”已經引用和評論到孔子的《春秋》,可見這個“君子曰”一定是在孔子《春秋》廣為流行后,才有可能作出,“君子”絕不可能是孔子。
因此,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左傳》和《國語》中的“君子曰”的“君子”斷然不會是孔子。
五、“君子曰”可能出于虞卿學派和荀子學派
從以上的論證可知,《左傳》中“君子曰”之言既不是左丘明的話,也不是孔子的話,更不可能是西漢末年劉歆的撰作,甚至不大可能是左丘明在撰《左傳》時引述他人的語言。筆者認為,所有的“君子曰”之言都是在《左傳》成書后才加進去的。“君子曰”之言極有可能是在《左傳》流傳的過程中,由《左傳》的傳人及后學添加進去的評論性話語,其時代也應該是在先秦的戰國,不可能到西漢。
“君子曰”之言既非《左傳》的作者所說,也非其所引述,而是在《左傳》流傳的過程中,儒門后學在閱讀《左傳》時所加的評論性話語,如虞卿等人便很有可能做這種事,也有可能是荀子在齊國主盟學術時所加,因為有人考察出《荀子》的思想與《左傳》中“君子曰”之言的思想頗能相通。《左傳》插入“君子曰”之言的評論家顯然非常熟悉《法語》,定是儒門中人。儒家熱衷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評論歷史時并非隨心所欲地亂說,而是引用廣為流傳的圣賢語錄和歷史評論(很多收錄在《法語》中)來與《左傳》中的人和事相映證。這些圣賢語錄和歷史評論都早已存在,《左傳》的后學只是把它們編入《左傳》中而已。他們很多時候也不知道這些“君子曰”之言到底是誰說的,所以才將之泛稱為“君子曰”。不過,能在《左傳》中增補內容的人必是相當有造詣的儒門賢達,所以筆者疑心可能是虞卿及其門人以及荀子及其門人。考《經典釋文序錄》[3],《左傳》的傳授源流十分清晰。左丘明傳儒門名士曾申,曾申傳大軍事家吳起,吳起傳子期,子期傳楚國人鐸椒,鐸椒傳虞卿(后為趙國相國),虞卿傳同郡的荀子,荀子傳給大漢丞相、北平侯張蒼,張蒼又傳給一代大儒賈誼,后又傳到賈誼之孫賈嘉。從此《左傳》在漢代一直流傳下去。可見,今本《左氏春秋》是從虞卿學派、荀子學派傳下來的。可能從曾申開始就有在《左氏春秋》中加入“君子曰”的評論,后來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吳起、子期、鐸椒都有加入“君子曰”的評論。直到虞卿學派和荀子學派,大規模地增入了“君子曰”之言。
荀子本是《左傳》的重要傳人③。劉申叔先生《群經大義相通論》中有《〈左傳〉〈荀子〉相通考》,論《左傳》與《荀子》相通之處[4]。今舉一例。《左傳·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而《荀子·勸學》:“《春秋》之微也。”足見二者相通。楊倞注就引《左傳》此文為釋。可知荀子通曉《左傳》。荀子確實與《左傳》關系密切。虞卿與荀卿在世時就已經名聲很大④,荀子是虞卿的學生,二人被公認為賢人和傳經大師,有很多門生。他們在對廣大學生講授《左傳》的過程中,可能引用已經流傳的收錄在《法語》中的格言嘉句評論歷史人物。
六、結語
古人著述本有“言公”之心,如《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的門客所著,而非出自呂不韋之手。《淮南子》乃劉安的門客所著,而非劉安親撰。然而,后世只知呂不韋、劉安,不知真正的作者是什么人⑤。正如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所言:“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為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章學誠此書論述古人言公之旨頗為詳盡。
孫星衍的《問字堂集》、余嘉錫先生的《古書通例》均闡發了先秦時的古書(尤其是諸子書)被后學增補實為慣例,乃是出于古人言公之心,并非作偽。我們只要參照諸子書成書的經過,就可以明白作為先秦的儒家的歷史教科書的《左傳》在流傳中完全可能被增補。但是,《左傳》中所有的“君子曰”之言都是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插補進了《左傳》,所以司馬遷《史記》才有可能參考利用“君子曰”之言。這點足以證明《左傳》中的“君子曰”絕不是西漢末年一代宗師劉歆所混入。
有人將《左傳》中的“君子曰”與《史記》中的“太史公曰”相提并論,以為是同性質的評論。我們則認為,二者全不相謀。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考證了作為太史令的司馬遷為什么被稱作太史公。王先生曰:“韋昭則以為外孫楊惲所稱……惟公書傳自楊惲,公於惲為外王父,夫談又其外曾祖父也,稱之為公,於理為宜。韋昭一說,最為近之也。”也即是說,《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在司馬遷筆下本來應該是太史曰或太史令曰。太史令本是一種職官,與《左傳》中的作為泛稱的君子不應混為一談。“太史公曰”之言出自司馬遷的手筆,而“君子曰”并非出自左丘明的創作。
總之,《左傳》的“君子曰”之言不可能是孔子、左丘明、劉歆之言,而是春秋戰國時代評論歷史的一種學術慣例。司馬遷讀過的《左傳》已經有“君子曰”之言。“君子”并非專指一人,而是泛稱符合儒家價值觀的賢人。“君子曰”之言是《左傳》在戰國時代的儒家傳授過程中引用和加入的評論,編入者很可能是虞卿學派和荀子學派。“君子曰”之言中的很多格言可能被收編入先秦時代的各種《法語》中。
[注 釋]
①《左傳·昭公七年》:“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亦稱“人有言曰”,無“古”字。
②倚相之名不見于《左傳》和《史記》。據《國語》,倚相與楚國的司馬子期同時,而司馬子期是楚平王之子,那么倚相就應該是孔子的晚輩而與孔子同時,有可能聽到過孔子的言論。但是整部《國語》凡是引用孔子的話皆在《魯語》,不稱孔子或君子,而稱仲尼。
③見劉向《別錄》與《經典釋文敘錄》,亦可見汪中《述學》里的《荀卿子通論》。
④《錢玄同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四卷有《辭通序》甚至說:“荀卿又叫荀況并非是因為荀子名況,而是‘卿’與‘況’古音相通,‘況’是‘卿’的假借字”。荀子的本名早已失傳。但是,我們認為荀子的名字就叫荀卿。《史記·夏本紀》的《正義》引《荀子》名為《孫卿子》,《史記·項羽本紀》的《索隱》引為《孫卿子》,《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隋書·經籍志》:“《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都明確記為《孫卿子》。《荀子·儒效》:“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于人之國。”《毛詩正義·傳述人》:“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晉書·地理志上》:“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皆稱孫卿子。古書中其他類例甚多。按照古人的慣例,凡稱“子”者,“子”前面的稱呼應該是其人的姓或姓名,如韓非子、孫武子、尉繚子,其中的韓非、孫武、尉繚都是人名,并非尊稱。因此,既然《荀子》又有《荀卿子》或《孫卿子》這樣的名稱,那么荀卿或孫卿就應該是人名,而不是尊稱。更考古書,在漢代以前,古人確實有以“卿”為名或為字的。除荀卿、虞卿之外,《漢書·儒林傳》有貫長卿;司馬相如字長卿;《史記·殷本紀》:“湯崩”。《集解》:“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索隱》:“長卿,諸本多作劫姓。按:《風俗通》有御氏,為漢司空史,其名長卿,明劫非也”。《史記·呂太后本紀》:“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集解》引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隋書·經籍志》:“《雜字指》一卷,后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急就篇》:“周千秋,趙孺卿”。
⑤《淮南子》是淮南八公所撰。《呂氏春秋》多為荀子學派的學者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