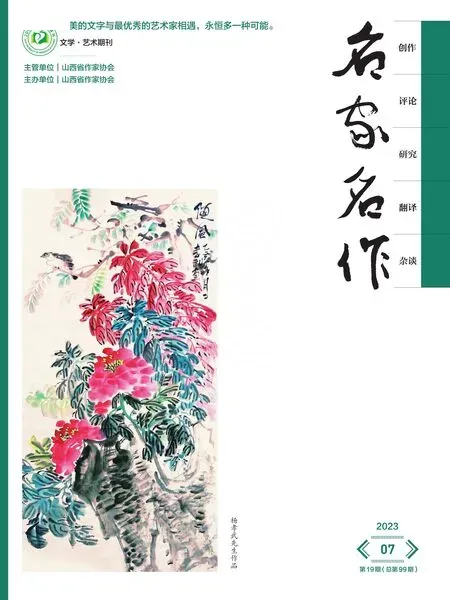論《局外人》中的肉體感官敘事
——基于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的進一步討論
陸 柔
在讀者看來,《局外人》這部小說蘊藏著多個主題,如死亡、宇宙自然、宗教、道德、懺悔、媒介、法律、正義、承諾等。它篇幅雖短小,含意卻廣泛,其廣泛意義總是能吸引來眾多不同角度的批評意見,這正是這部小說能在時間長河中保留其并不十分閃耀而獨特的價值的原因之一。在這琳瑯滿目的主題之中,如果我們愿意采取一種原始且直觀的視角,再次標記出自然與人類社會之間那條古老的界限,就不難發現宇宙自然這一主題幾乎徹底被劃分到了死亡、愛、宗教、道德、正義、承諾等與社會性人類密切相關的另一邊。宇宙自然和其作用于人身而產生的肉體感覺,這二者與人類社會的普遍情感、傳統制度與習慣法則之間形成了隱約的對立,給處于界限兩邊的人造成了一種“無法容忍的語義空虛”①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作者引述齊馬《社會批評概論》時關注到齊馬對預審法官和默爾索之間的一種模糊的“無法容忍的語義空虛”的闡釋性分析。。就《局外人》這部作品來說,正因肉體感官敘事話語在小說中的推動情節和塑造人物方面的作用,而向讀者呈現了解析文本構建和介入人物內心的一條“蹊徑”。因而,把握這部作品中的肉體感官敘事話語對我們理解《局外人》非常重要。
一、肉體感官的獨立性
針對小說《局外人》的語言表現,朱國華先生在《〈局外人〉的幾種讀法》中特別提到了這部作品的兩種敘事風格:一種是淡漠的、流水賬式的廣為人知的敘事風格;另一種是不時出現的抒情風格,這種不常見的抒情風格往往與默爾索的肉體感官密不可分。較為典型的是幾次重要場合中加繆對默爾索敏銳覺察到的或回憶的現象及情境的描寫,如在母親葬禮上的感受:
濫施淫威的太陽……叫人無法忍受。
車頂上車夫的熟皮帽子……置身其中,我不禁暈頭轉向。所有這一切……使得我頭昏眼花。
還有在海灘槍殺阿拉伯人前默爾索的感受:
刀刃閃閃發光……我只覺得太陽像鐃鈸一樣壓在我頭上,那把刀閃亮的鋒芒總是隱隱約約威逼著我……此時此刻,天旋地轉……我覺得天門大開,天火傾瀉而下……
又如庭審時默爾索在律師發言時的感官性回憶:
那生活已經不屬于我了,但我從那里卻曾得到過我最可憐、最難以忘懷的快樂,如夏天的氣味、我所熱愛的街區、傍晚時的天空、瑪麗的笑聲與裙子……
可以看到,這些抒情片段包含了鋪陳、比喻、鮮艷的色彩與對比,這些詩意的言辭描繪的對象是一個個自然意象。太陽、大海、沙子等自然物被抒情的語言賦予了人格化的力量,造成“嚴酷”“逼射”“威逼”等感受。其中,每種自然物象幾乎都是獨立陳述的,柏油路面、車夫的帽子、藍天白云、人們穿的衣服等意象具有空間上的某種關聯,但這種關聯被加繆有意隱去,而默爾索對一件又一件自然物的獨立感覺被單獨呈現。隨著敘述者的敘述,肉體感官逐漸變成大量獨立的圖像①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原文:“肉體感覺一開始會被注意到,但后來會變成大量獨立的圖像。”,這一點體現得更為明顯的大概在于默爾索對街道上行人的觀察,視覺感官圖像匯聚成了零碎的跳躍的描述性語言。當然,從宏觀來看,加繆為肉體感官采用的這種抒情語言在小說語言風格中也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二、肉體感官敘事話語效果
加繆用抒情與修辭的方式來描寫默爾索視角的宇宙自然和肉體感官,這讓讀者在閱讀他的這部早期作品時感覺耳目一新。但同時一些批評家也認為,“這些抒情和修辭的段落在美學上不盡人意”②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作者在這里引用了 King,A. 的觀點。。這些批評家認為,在這些語段中,“作者的聲音侵入得過于明顯,倒退到了闡釋的層面”③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作者在這里引用了 King,A. 的觀點。,即加繆在關鍵時刻用自己的聲音代替了默爾索的聲音。朱國華先生在文中引用這個觀點是為了補充他對《局外人》語言風格的判斷,但我們結合文本來看,所謂的“關鍵時刻”不正是自然力量對人產生影響和人類肉體感官開始強烈覺知的時刻嗎?我們可以說,加繆為了描寫肉體感覺充沛的這些“關鍵時刻”,采用了抒情與修辭的方式,但這些抒情與修辭的語段由于作者的明顯介入而導致“美學上的不如意”。對于批評家們的聲音,加繆作出了辯解,他聲稱這是自然和日常的④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作者在這里引用了 King,A. 的觀點。。為什么加繆會這么認為?這還與加繆本人的性格和寫作個性有關。
當然,在加繆描寫肉體感官的語段中,除了抒情和修辭與主人公的不完全貼合帶來的“作者入侵”之外,還存在著一種積極作用,即它能夠幫助加繆使用一組(描寫肉體感官和宇宙自然的)詞句來同時達到推進敘事和交代敘事心理原因的雙重目的,從而更加經濟地使用語言⑤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作者在這里引述舍弗 (P.Schofer) 所引用的一位研究者的觀點,該觀點認為加繆采用充滿隱喻的表達方式,其旨在經濟地使用語言來達到雙重目的。。
這里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宇宙自然與人類社會在《局外人》中的割裂也造成了人類社會中統治階級的語言與個人肉體感官語言的對立。也就是說,描寫默爾索肉體感官的語言,在文本中絕無可能成為官方權威的語言。相比于第一部相對純粹自然的肉體感官語言,小說第二部對肉體感官的描寫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嘲諷的態度和默爾索語言的浮夸不驚,因此也可以說,第二部肉體感官語言功能較第一部更為豐富。這就涉及小說的結構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節討論。
三、肉體感官、小說結構與人物個性
我們可以明確的是,小說第六章的殺人案件具有切割小說的關鍵作用。愛麗絲·卡普蘭就曾說過“海邊殺人案將故事恰好分成嚴格對稱的兩部分”,這使得這部小說具有故事的對稱性⑥愛麗絲 ·卡普蘭:《尋找〈局外人〉:加繆與一部文學經典的命運》,琴崗譯,新星出版社,2020,引言第3 頁。。我們無法忽略肉體感官在第一部第六章中的篇幅與作用,進而可嘗試發問:第六章殺人案對于小說結構具有關鍵作用,是否也意味著肉體感官對于敘事框架和人物命運同樣具有關鍵作用呢?或許這正是加繆意在強調卻始終隱晦不清的地方,換言之,肉體感官極有可能是故事情節推進和人物命運發生劇變的根本原因。
在小說結構層面,已經有一部分批評家指出這場海灘殺人案的非預謀性,認為默爾索槍殺阿拉伯人完全是受自然環境(太陽、大海)的影響,在此筆者持同樣的觀點。值得一說的是,在第一部中,肉體感官與例行事務的矛盾持續著隱性存在的狀態。加繆用他淡漠的語言最先向讀者展示了例行事務中的默爾索,其后,母親的葬禮與海灘槍殺案作為突出事件,可視為日常生活和例行事務的兩次中斷,每一次例行事務的中斷都不自覺地促進著肉體感官的強化。而默爾索一直以來煩惱的原因也是自己的肉體感官與社會倫理、宗教、道德發生了沖突。到了第二部,不僅默爾索的肉體感官被迫獨立于以檢察官為代表的法庭力量所精心構陷的閉包敘事,甚至他在第一部由于遵從自身實存感而在日常生活中無憂無慮的外在表現也成了這場構陷的主要內容。此外,在第一部中默爾索的肉體感官雖受壓抑,但這股壓抑的力量來自社會普遍道德原則,默爾索仍能在這些條條框框中找到喘息的縫隙,也因此海灘殺人案才成為可能。但在第二部里,入獄是法庭力量集中起社會集體憤怒對默爾索的肉體感官渠道的直接阻絕,壓抑更加直接可感。肉體感官將默爾索從例行事務推向監獄,再把罪行從可饒恕升級至不可饒恕的等級,不可不謂是故事情節的重要推手。
在人物個性層面,正如麥卡錫所說,默爾索并非一個完全消極的存在物,冷漠的言談舉止不過是他的生存策略,是假象,真實的情況反而是通過抒情風格在某些特定時刻爆發出來的,這也與加繆本人的解釋遙相呼應⑦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作者在這里引用了麥卡錫的觀點。。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默爾索不注重倫理道德——對于這樣一個注重實存感受的人來說,掌握在此世界的基本生存策略以獲得一定的生存空間已完全足夠,在他看來,宗教、正義、愛情等都是生存過程中社會強加的繁縟枷鎖,沒有必要關注和踐行。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實踐并不能代表默爾索這個個體,默爾索這個人藏在自己的肉體感官里,活在當下的實存感受中。也正是借由加繆對默爾索肉體感官的描寫,我們才能發現主人公是如此聰穎過人和具有敏銳的洞察力。由于對肉體感官的注重,周遭生活中的大部分人和事對默爾索而言都失去了吸引力,乃至趨向于無意義,這時一種存在主義的虛無在他身上便得到了顯示。
四、實存感死活間的荒謬
不過存在主義并不是此文的重點,本文的重點在于,跳出薩特、海德格爾等人分析他者對主體建構產生作用的觀點而將視線聚焦到“他者”最初的概念上,即相對于“自我”的、一切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人、事、物)。我們不妨將使我們肉體感官活躍起來的重要對象——宇宙自然,暫且淺顯地視為“他者”,如此一來我們將獲得一個新的發現:加繆《局外人》所展現的社會與韓炳哲在《愛欲之死》①韓炳哲:《愛欲之死》,宋娀譯,中信出版社,2019。本文所引韓炳哲觀點均源自此書。中談論的社會,此二者的共性還能夠從宇宙自然這一“他者”的方面來理解。以默爾索為例,筆者之所以認為默爾索是一位在荒誕世界里保持真誠的人,是由于他對實存感的“真誠”(或者純粹)從根本上體現了他對宇宙自然這一存在經驗的認同。韓炳哲所談的純粹之愛包含了由愛驅動的性欲,而默爾索的真誠純粹則包含了他的肉體感官欲。這種實存真誠的最基本條件也同純粹之愛的基本條件一致,即要求一個人有勇氣消除自我,以便能夠發現“他者”的存在。默爾索對實存感的堅定與執著也正照應了巴塔耶論色情的那句驚世駭俗的話②巴塔耶:“所謂色情,可以說是對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默爾索的實存感受和肉體感官也是一種對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將宇宙自然作為“他者”來理解《局外人》不是沒有原因的,產生實存感的前提是自然強烈的“威逼”力量,也是本文第一節提到的被加繆人格化的自然力量。在《局外人》的社會里,宇宙自然與人類社會總是不對稱的、相互獨立的,這與愛欲的前提是他者的非對稱性和外部性相契合。此外,“我們時刻把所有事物拿來比較、歸類、標準化,為‘異類’尋找‘同類’,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體驗‘他者’的機會”,這正是默爾索以外的其他人對周遭自然沒有關注更無體驗而導致的實存感受的缺乏,為傳統道德習慣、禮儀所縛,而法庭力量要將默爾索這個“異類”標準化的一個荒誕社會的生動寫照。實存感消亡者活于現實世界對“自我”的規定和馴化中,而實存感未亡者將被從所謂“自我”的世界拉扯出去,轉移到“他者”世界,這就是實存感的死活能對《局外人》中社會的荒謬性產生影響的原因。
五、結語
我們必須承認,局外人的第一人稱敘事不是那么可靠,這一點不少學者專門提出過質疑③如西蒙 ·李 (S.Lea),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這一關于敘事統一性的悖論或疑問直至目前還沒有得到一個權威的定論。那么包含于第一人稱敘事的肉體感官敘事部分,這種沖動的、直接的、帶有阿爾及爾粗糲的風情的感官陳述,如果放到可靠性判斷的天平上,我們又該如何對待呢?其中有沒有敘述者對讀者有意的誘導利用(即為同情而同情④參見朱國華《〈局外人〉的幾種讀法》,作者引述了美國學者布蕾 (G.Bree) 的假設讀者視角理論,討論了敘述者對讀者的誘導利用的問題。)呢?再進一步說,相比于口語化的復合過去時給讀者帶來的默爾索的對話直接性的幻覺(當然這很可能是加繆的預期效果),默爾索的肉體感官書寫到底能不能讓讀者產生完全的同情心?這種肉體感官描寫相對于小說其他部分淡漠的敘事話語是更純粹還是更復雜了?這些問題我們目前都還很難評判,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