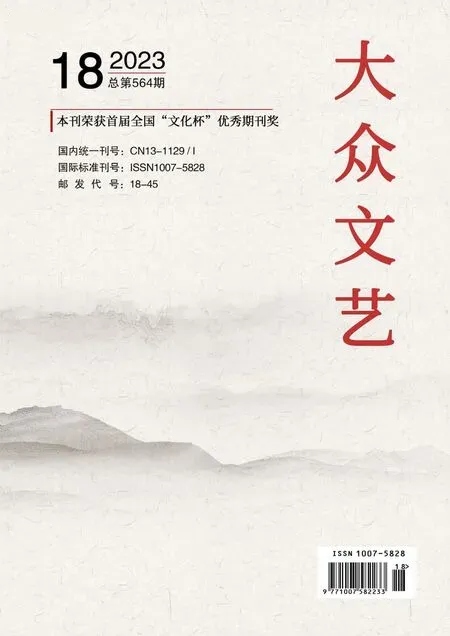新時代主旋律電影人民性的藝術書寫
張毓喆
(山東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山東濟南 250000)
人民性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最鮮明的核心思想和品格特征,始終貫徹于新中國的發展脈絡中,指引著人們的思想與實踐活動,并為文藝作品的創作提供理論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指出“人民是文藝之母。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1]這彰顯出“人民性”在社會主義文藝中的重要性,也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新時代主旋律電影之所以能被觀眾接受、被市場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其深蘊“人民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扎根現實生活,彰顯求真向善的積極立場,既有現實思考又有美學特色,實現了文藝創作的時代使命和社會價值。
一、內容主旨:家國情懷與集體記憶的影像呈現
新時代主旋律電影以鮮活的主旨內容呈現時代表征,凝練人民的利益訴求,依靠歷史框架中的家國情懷和集體記憶滿足人民的情感需求,透過影像的方式構建家國認同感。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國兩相依。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一的家國情懷是主體對共同體的認同,并促使其發展的思想和理念。家國同構這種社會構形是家國情懷的關鍵,強調家庭和國家的結合、個體發展與祖國發展的聯結。新時代主旋律電影準確把握時代脈搏,書寫著賡續傳承的家國情懷。電影《長津湖》以抗美援朝戰爭為背景,展現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饑寒交迫條件下的頑強抗戰精神,楊家兄弟三人相繼投身戰場,這既體現著小家內部的抗戰精神傳承,也彰顯出“舍家為國”的家國大義。延續前作的《長津湖之水門橋》更加濃墨重彩地表達愛國主義情感,雷公、平河、余從戎、伍千里的犧牲均顯示出自我精神與祖國精神的融合,自我力量對民族力量的貢獻,滿足了觀眾對中國人民志愿軍理想形象的認同,使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熱淚盈眶、熱血沸騰,在電影所塑造的歷史情境中形成了對抗美援朝戰爭的認知,激發起觀眾的家國情懷。
人民作為現實的主體,對社會變遷和人生百味有著最為直接的感受。新時代主旋律電影在故事的講述中喚醒人民的集體記憶,以集體記憶凝聚身份認同。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認為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它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群體都有其對應的社會記憶。[2]在新時代的傳播語境下,集體記憶通過電影這種媒介形式再現,以強調或抹除細節來重新塑造集體記憶。例如《我和我的祖國》上映時間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的時間節點,電影選取了七十年中七個經典的重大事件,使不同時代、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觀眾都能找到所熟知的個人記憶,因而也更像是一部祖國奮斗史,帶領觀眾重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奮斗故事。盡管記憶可能是模糊且不連貫的,但通過電影再現、重構等敘事手段,觀眾的集體記憶與影像得以對應,使得記憶更加穩固。如果說《我和我的祖國》是以重塑的方式喚醒集體記憶,那根據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真實事件改編的《中國醫生》《穿過寒冬擁抱你》則讓觀眾看到了新時代主旋律電影對集體記憶的正書寫。2019年冬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白衣逆行者勇敢無畏沖鋒在前,不顧自身安危守護人民生命安全,人民群眾原本平靜的生活狀態發生了改變,所有人以各種方式感同身受,甚至參與其中。抗疫這個話題作為當代人民共同經歷的一段集體記憶,觀眾更易將自身代入其中,影片也正是通過這段全民記憶碰撞出全民情感,讓觀眾看到集體記憶的鑄成過程,在后疫情時代有所反思。
二、價值選擇:多元題材和平民視角的話語表達
新時代主旋律電影并非對特定題材或風格的限制與規定,而是一種普遍的砥礪性的表征,是“與時代同步伐、與人民同呼吸”的親民性的價值選擇與價值表達。[3]新時代主旋律電影在題材選擇方面呈現出開元包容的特點,既有對革命歷史題材、重大歷史事件的書寫,也有對于現實民生的深刻挖掘,是對時代歷程的藝術回望,也是對現實生活的深刻描摹。
黨的十八大以來,主旋律電影與現實主義愈發貼近,這些影片聚焦社會的發展,關注人民生活,影片中所討論的話題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也正是當下人民最為關切的社會議題。文牧野導演2018年的作品《我不是藥神》雖是小成本制作,卻收獲高票房和好口碑,也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影片將鏡頭對準買不起天價藥的白血病患者和為他們代購仿制藥的群體,聚焦中國人民幾十年來持續關切的“看病貴、看病難”的社會問題,法與情、錢與命的博弈點燃了輿論風暴。在影片播出后,立法機關對輿情進行回應并作出重要舉措,新版《藥品管理法》規定“進口國內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藥不再按假藥論處”,影片中所提及的治療白血病的特效藥也被列入國家醫保范疇。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從治標、治根到治本,保障了人民安居樂業和社會安定秩序。與此相關的影片《掃黑·決戰》站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三周年收官節點,融重大的社會真實事件于劇情之中,例如孫小果案、操場埋尸案、李氏兄弟案,真實還原并披露斗爭中鏟除黑惡勢力及其背后保護傘的細節和過程,讓人民在凝練的藝術作品中感受到黨和國家掃黑除惡的決心,守住了人民的心。再如2022年的《人生大事》關注到中國人較之避諱談及的死亡和殯葬話題,以溫情的方式讓觀眾“淚中帶笑”地體悟生命哲學,滿足了觀眾對民間殯葬業的好奇心理,也反映出殯葬工作者在社會中備受偏見的現狀。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浸染中,新時代主旋律電影不斷擴大創作疆域,呈現出數量與質量齊升的現象,以高票房和好口碑彰顯其不斷進化的“姿態”。[4]
縱觀新時代以來幾部被廣泛認可的主旋律電影,在藝術主體的選擇和塑造方面都呈現出平民化和多樣化的特點,譜寫了一首首傳奇性的平民史詩。新時代主旋律電影避免了傳統的高大全精英敘事的方式,并非通過塑造英雄楷模來進行敘事,而是將目光放在了平凡小人物身上,采用以小見大、以微觀知宏觀的方式,以飽滿的人民性講述他們的平凡故事,這些故事貼近受眾的生活環境和成長經驗,符合受眾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特征,以受眾本位的路徑實現了有效傳播。2019年國慶檔《中國機長》改編于真人真事,影片沒有將機長這一英雄形象臉譜化,而是還原到普通人形象上,淡化了英雄主義色彩,著重表現機長的日常生活和機組人員面臨突發災難時的職業操守和職業精神,接近了觀眾們的平民意識,使機長這一角色更加“接地氣”。2020年國慶檔《我和我的家鄉》也采用平民視角,五個故事單元的主角都是與觀眾一樣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但通過人與人、人與家鄉的聯結傳達出了不普通的情感力量。出租車司機張北京、農民發明家黃大寶、鄉村教師范老師等,都是與時代發展貼近的普通人,電影中“我”的形象或許也是銀幕前的“我”,是每一個平凡的普通人,也是每一個愛崗敬業、無私奉獻、舍小家為大家的平民英雄。
新時代主旋律電影對人民主體的表現范圍愈加擴大,它將鏡頭聚焦于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人物,藝術化展現社會多元場域的生活細節。教師、警察、醫生、學生、司機、農民工、媒體人、鄉村書記、殯葬師等各種形象都被搬上銀幕,中國當下社會中人民所面臨的生活、工作、感情難題得以有質感地呈現。拉康的“鏡像理論”描述了“自我”如何在與另一個完整對象的不斷認同中實現構建,對于觀眾而言,銀幕是嬰兒鏡像階段的延伸,在觀影時他們會將自身形象代入電影角色,從中找到自己關于某些事物的親身體驗,使潛藏在內心的無意識得到升華,從而完成自我的構建,實現對電影主體角色的鏡像認同,這在人民性立場之上,越發的完美貼合。
三、營銷宣發:多渠道宣傳和情緒營銷的雙重發力
新媒體時代下,信息傳播邊界的消解加速信息的擴散速度,電影的傳播路徑也發生轉向。以抖音、快手、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成為新時代主旋律電影傳播的重要手段。新媒體平臺擁有并可以凝聚強大的用戶流量,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可以與電影形成聯動,在碎片化時間的片段觀看可促成觀眾走入影院觀看完整電影的行為。微博則通過話題的發布、意見領袖的引導形成輿論場域,提升主旋律電影傳播的熱度。麥克盧漢曾說:“媒介構成了我們的環境,并維持著這種環境的存在”。[5]新媒體高參與性、強互動性的特點使得人人都成為傳播者,個體的傳播力量不斷積聚,在二次傳播中打造電影口碑。同時,新媒體也為主旋律電影面向觀眾提供了平臺,不少電影開設專門的抖音、微博賬號,發布與影片相關的視頻、話題和營銷活動,實現了與用戶的有效對話,眾多觀眾對影片精彩片段、主題曲、重要角色等內容重新“編碼”,使得更多細節和內容有機結合,讓主旋律電影通過再生產得到延伸。
新時代主旋律電影以敏銳的目光和細膩的情感洞察社會百態和人民生活,通過情緒營銷巧妙宣傳,實現對觀眾的情感療愈與心理按摩。情緒營銷的核心在于情感共振,它利用普世情感將影片中的某一情緒價值放大,從而調動觀眾的觀影熱情和傳播熱情,拉動票房和口碑雙雙增長。國產電影票房Top3《長津湖》《戰狼2》《你好,李煥英》均利用情緒營銷取得不錯的票房。《長津湖》在映后話題和熱度持續不斷,影片通過抖音、微博等平臺進行宣傳,真實場景的高度還原與制作給觀眾帶來視覺體驗的同時也激活了觀眾潛意識里的愛國情懷。影片中志愿軍在冰天雪地惡劣天氣下吃凍土豆的情節引發網友們集體憶苦思甜,不少網友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平臺曬出自己吃凍土豆的感受和體會,感慨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更有觀眾感慨“影片沒有彩蛋,但走出電影院看到外面燈火通明、高樓聳立,這就是最好的彩蛋。”《戰狼2》中多處讓觀眾熱血沸騰的動作戲以及“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口號,都是對觀眾情緒的引導,點燃了觀眾的民族自豪感。2021年《你好,李煥英》在春節合家歡的節點上映,通過海報、春晚小品、線上與線下共同進行宣傳,以溫情的方式觸及觀眾心底最柔軟細膩的位置,經典臺詞“我的女兒,只要她健康快樂就行了”“媽媽曾經也是個花季少女”引發觀眾對于母愛和親情的思考和審視,為當下的代際溝通提供了話題,使得觀眾從情感喚醒到話題思考,再到做出實際行動。2022年國慶檔頭部影片《萬里歸途》也利用情緒營銷,在抖音短視頻平臺發布多條短視頻進行密集宣傳,宗大偉舉起外交護照、白婳在飛機上抱著丈夫的骨灰盒極度克制眼淚的視頻,點贊量都到達200w,讓觀眾有“祖國在身后”的牢牢安全感和歸屬感,提升了觀影期待。電影作為一種“被凝視”的藝術,觀眾在觀看時從來不會置身事外,他們的心理情緒會跟隨影片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情緒而跌宕起伏。從卡茨的“使用與滿足”研究視角來看,受眾成員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其媒介接觸活動是基于特定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對于觀眾而言,生活在節奏加快的現代社會,面臨著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壓力,易產生焦慮、抑郁、激進、反叛等心理,需要得到情緒療愈與心理按摩,走進影院觀看電影這一行為基于他們以上這些特定的個人“需求”,半公開的影院環境暫時切斷了與真實空間的聯系,讓觀眾自主打開眼淚或笑聲的閘門,獲得沉浸式觀影體驗,從而使內心情緒得到舒緩宣泄,使思想壓力得到紓解釋放,讓他們的“需求”得到了“滿足”,在高壓的生活環境中感受到主旋律電影所蘊含的時代溫度。
結語
主旋律電影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產物,肩負著主流意識形態構建、傳播國家核心價值觀、彰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任務。進入新時代后,主旋律電影磅礴發展,成績斐然,但在其迎來創作熱潮和巔峰發展的時刻仍需保持冷靜思考。若要實現新時代主旋律電影的可持續發展,在未來的創作中應始終堅持“人民性”,做到讓人民創造故事、讓人民成為主角、講故事給人民聽、將人民故事講動聽,努力縫合主流意識形態與人民之間的心理罅隙。另外,在全球化語境下,主旋律電影如何被更大范圍的受眾認可和接納,如何在國際市場上獲得一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如何彰顯具有普世意義的思想價值觀念,如何在新時代永葆活力、葳蕤蓬勃,這仍值得電影創作者不斷去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