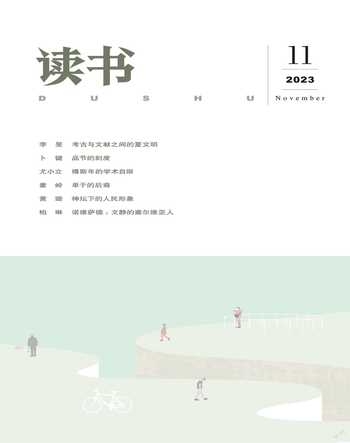卡夫卡的先驅者
許志強
一
博爾赫斯一九五一年寫過一篇短文,題為《卡夫卡及其先驅者》(王永年譯)。文中提出一個讀者感興趣的問題:卡夫卡的風格獨特,但是否真的像我們認為的那樣橫空出世?博爾赫斯說,其實卡夫卡那種聲音(或語法)在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都能找到先例,他舉了五個例子加以說明。
第一個是芝諾的“兩分法”悖論,即一個人從起點走到終點,要先走完路程的二分之一,再走完剩下的總路程的二分之一,再走完剩下的二分之一,如此循環下去,永遠走不到終點。博爾赫斯認為,這個問題的形式和《城堡》的一模一樣。芝諾的“兩分法”悖論,還有“飛矢不動”“阿基里斯與龜”等悖論,它們就是“文學中最初的卡夫卡的人物”。
第二個例子是韓愈的《獲麟解》,博爾赫斯從《中國文學精選集》中讀到它的一段西語譯文。相應的原文如下:“麟之為靈,昭昭也。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 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 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博爾赫斯認為這段文章的調子和卡夫卡的很像。
第三個例子是克爾凱郭爾。不是說他和卡夫卡在思想上相似,而是這兩個人的宗教寓言都采用了當代資產階級題材。例如,某偽幣制造者被迫在嚴密監視下檢查英格蘭銀行的鈔票。這個罪犯就是克爾凱郭爾自身的寫照,上帝不信任克爾凱郭爾,委派給他的任務恰恰是讓他習慣于罪惡。再如,丹麥教區神父關于北極探險的說法,聲稱此類探險有益于靈魂健康。但是去北極很難,甚至不可能,并非人人皆可從事此類探險,因此任何形式的旅行(包括郊游)最終都可被視為北極探險。
第四個例子是勃朗寧的長詩《疑慮》。詩中說,某君有一位名人朋友,但從未謀面,更未得到某君幫助。朋友只是私下傳頌其高尚行為,傳閱其親筆書信。有人對這位名人的行為產生懷疑,筆跡鑒定專家證實那些書信均系偽造,某君最終問道:“難道這位朋友是上帝?”
第五個例子是博爾赫斯摘抄的兩篇故事。一是出自布瓦洛的作品,說有人收集了許多地球儀、地圖、火車時刻表、行李箱,但直至老死都未能走出自己的家鄉小城;另一個故事是鄧薩尼勛爵的短篇小說《卡爾凱松納》,寫一支英勇的軍隊從城堡出發,翻山越嶺,穿越沙漠,征服了許多國度,見識過奇獸怪物,雖然曾望見過卡爾凱松納,卻從未能夠抵達那個地方。博爾赫斯解釋說,這兩個故事剛好相反,“前一個是從未走出小城,后一個是永遠沒有到達”。
博爾赫斯的講解都是點到即止,限于轉述,讓讀者自己去意會。為什么說《獲麟解》的調子像卡夫卡?大概是指那種“既非……又非”的排除法的陳述是卡夫卡特有的句式。韓愈和克爾凱郭爾的文獻都是從二手資料中獲取,如果不具有相當的敏感,則難有此類發現。文章最后歸納說:“如果我沒有搞錯,我舉的那些駁雜的例子同卡夫卡有相似之處;如果我沒有搞錯,它們之間并不相似。”這是典型的博爾赫斯話術,第二個陳述否定第一個陳述,而兩個陳述又都是正確的。一本正經的佯謬語氣,有點像是在開玩笑。這句話其實是想要指出,說“似”還不夠,有必要談一下“不似”。勃朗寧的長詩和卡夫卡作品相似嗎?應該是不像的,只是某種特質的相似而已。博爾赫斯說,卡夫卡的作品讓我們覺察到那種特質,如果他沒有寫出來,那種特質或許就不存在;現在我們讀勃朗寧和過去讀勃朗寧已經有所不同,我們偏離了當初的閱讀感受;是卡夫卡讓我們產生這種偏離,意識到勃朗寧詩中預示的卡夫卡邏輯。而這種“不似之似”的意義是更重要的。
《卡夫卡及其先驅者》一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文章,例子都是信手拈來,重在感受而非論證。卡夫卡對中國書籍的閱讀,在各類傳記和專題研究中都有涉及,博爾赫斯的文章沒有引用相關文獻,而是表達其即興的一得之見。韓愈的《獲麟解》對卡夫卡有過影響嗎?文中沒有提供證據。除了第一個例子有人講過,后四個都是博爾赫斯發現的,其凝練的轉述是在強調,此中存在著所謂的“家族相似性”。文中舉述的例子,可分成三組。芝諾的悖論和韓愈的文章是一組,提煉的是無限可分的概念。克爾凱郭爾和勃朗寧是一組,有關上帝的假設暗示了否定神學的觀念。布瓦洛和鄧薩尼勛爵是一組,那些故事包含迷宮的主題,將命運和迷宮的概念聯系起來(想必博爾赫斯本人對此興味盎然)。卡夫卡式的懷疑主義,他的有關無限小、不可抵達、存在的荒謬和殘酷的玩笑等主題,在這三組例子中反映出來。可以說,它們都體現了卡夫卡特有的思維和風格。
第二組的神學味道最濃。“用當代資產階級題材創作宗教寓言”,這是否算是克爾凱郭爾的特點姑且不論,用來描述卡夫卡則是精當的。現代資產階級題材,總的說來其性質是極為世俗的,用這種題材創作宗教寓言,與班揚的《天路歷程》等傳統宗教寓言就不同了,后者缺乏的是卡夫卡作品對社會體制(資產階級法權體系)的描繪和揭示。卡夫卡小說的一個特質,是用世俗性的描寫圖解形而上學。或者說,他在世俗性的題材中嵌入形而上視角,在形而上的終極探討中注入世俗性的基調。世俗性層面和形而上層面的雙向融合,造成其作品特有的張力,呈現神秘的寓言性和怪誕的喜劇性。按照庫切的說法,卡夫卡作品中的悲劇和玩笑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像《城堡》《訴訟》等篇,搞不清作者是嚴肅的還是搞笑的。這種敘述的含混性,恐怕是雙向融合帶來的一個必然結果,一定程度上還帶有某種消遣性質。我們知道,喜劇的消遣意味在班揚的作品中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真理屬于信仰的范疇,斷不至于讓人用含混的敘述和玩笑來解釋。
博爾赫斯的小說便是在這個意義上延續了卡夫卡傳統。它們不是通常所謂的宗教小說,也不是古代和中世紀神話的回光返照,而是當代懷疑主義和自我境況的寫照。這種“陰森的神話”不會促進人的信仰,倒是以形而上的象征和自然主義的細節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混亂狀況,具有新穎的藝術表現力。可以說,《卡夫卡及其先驅者》一文表達了博爾赫斯對卡夫卡的認識,也隱微地表達了卡夫卡之于他自身的意義。不過,博爾赫斯講的克爾凱郭爾和勃朗寧,其格調究竟是更像卡夫卡還是更像博爾赫斯本人,還是值得商榷的。卡夫卡的作品中并無圣徒或上帝是罪犯的寓言,而在博爾赫斯小說中此類寓言頗為多見。
二
對卡夫卡的先驅者進行探究,博爾赫斯的做法并非首創。本雅明作于一九三四年的文章《弗蘭茨·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紀念》,開篇就在談這個問題。他轉述了一個出處不詳的俄國故事,有關權臣波將金和下屬官僚之間的一段軼事,講得怪誕滑稽,不可思議。文章指出,“這個故事像一個先驅,比卡夫卡的作品早問世二百年”;“籠罩這個故事的謎就是卡夫卡”;“總理大臣的辦公廳、文件柜和那些散發著霉氣、雜亂不堪、陰暗的房間,就是卡夫卡的世界”;“那個把一切都看得輕而易舉、最后落得兩手空空的急性子人蘇瓦爾金,就是卡夫卡作品中的K.”;“而那位置身于一間偏僻的不準他人入內的房間、處于似睡非睡的蒙眬狀態的波將金,就是此類當權者的祖先:在卡夫卡筆下,他們是作為閣樓上的法官、城堡里的書記官出現的,他們盡管身居要職,但卻是些已經沒落或者確切地說是正在沒落的人”。卡夫卡的小說幾乎成了波將金軼事的翻版。波將金的故事沒有底本,難做比較。從本雅明的轉述來看,說它是“先例”也無可置疑。考慮到這則軼事的東歐背景(舊俄官僚世界),我們似乎能夠窺見政治文化的親緣關系之于兩者的意義。本雅明講的這個例子有啟發性,對博爾赫斯的文章也是必要的補充。
本雅明的評論文章,方法和博爾赫斯的沒有不同,都是運用一種機智的相面術,矚目于對象的辭氣、印記、姿態等做綜觀考察,而其闡釋則要深入得多,精彩的見解不少,頗能體現本雅明的特色。除了這篇紀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的文章,還有另一篇題為《卡夫卡》的短文,觀點都值得重視。讀者感興趣,可參看漢娜·阿倫特編輯的《啟迪: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
回到博爾赫斯的話題。從文學史的角度挖掘卡夫卡和前輩作家的聯系,還可以勾勒幾處有關聯的線索,比如狄更斯的《荒涼山莊》。其對卡夫卡的創作有影響,這一點英語研究文獻中已有論述。狄更斯描寫法庭和律師,其核心部分即英國古老的“大法官庭”,已把《城堡》和《訴訟》的中心意象刻畫出來了。狄更斯漫畫化的寫實筆觸——法官和律師的顢頇、詭辯、拖延,權力機構籠罩在迷霧和黑暗之中,等等——賦予“大法官庭”某種怪誕的寓言性,這一點和卡夫卡作品的關聯是不言而喻的。說到《訴訟》等篇的“陰森的神話和荒誕的制度”,有什么能比《荒涼山莊》的描寫更具相似性的呢?
除此以外,我還要講一個細節,即《訴訟》(章國鋒譯)第六章中的一個插曲。這一章講的是K. 的叔父帶著K. 去拜訪一位熟悉的律師,律師臥病在床,家中只有一名女仆照料他。他們在黑咕隆咚的臥室里談論K. 的案子,律師蓋著被子侃侃而談,顯示對這個案子的進展頗為知情,這讓K. 有點吃驚:躺在黑屋子里的律師怎么還會跟司法界有來往呢?律師說:“現在由于我病了,遇到了一些困難,但盡管這樣,還是有不少在法院工作的朋友來看我,我可以從他們嘴里了解很多情況,也許比身體健康、成天待在法院里的人知道得還要多。比如,現在有一位好朋友就在這兒。” 律師說完便朝屋里一個黑暗的角落指了指。小說接著寫道:“‘在哪兒?K. 吃了一驚,有些唐突地問。他半信半疑地朝周圍看了看。小蠟燭的光根本就照不到對面的墻,那個黑暗的角落里的確隱隱約約有什么東西動了一下。叔父把蠟燭舉過頭,借著燭光,他們看到一位年事已高的先生坐在屋角的一張小桌旁。他大概連氣也不敢喘,以至于待了那么久居然沒被人發現。”
《荒涼山莊》(黃邦杰、陳少衡、張自謀譯)第二十二章,講法律文具店店主斯納斯比先生去拜訪圖金霍恩先生,向后者密報情況:“快說完時,他忽然嚇了一大跳,而且立刻把話打住——‘哎呀,先生,我不知道這里還有一位客人!”小說接著寫道:“斯納斯比先生真的吃了一驚,因為他看見離他們桌子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站在他和圖金霍恩先生之間。這個人一手拿帽子,一手拿手杖,很注意地在聽他說話。斯納斯比先生記得,他進來的時候,沒有看見這個人,而后來也沒看見有人從門口或從哪一扇窗戶進來。屋子里倒是有一個衣櫥,但是他沒有聽見衣櫥打開時鉸鏈發出的那種嘰嘎嘰嘎聲,也沒有聽見有人走路時踩著地板的聲音。”這個細節和卡夫卡的細節有著相同的敘述原理:私密談話中突然發現有陌生人在場,簡直是神出鬼沒,讓人感到有點驚悚也有點滑稽。狄更斯喜歡在小說中加入偵探懸疑的氣氛,而且擅長搞笑,卡夫卡把這一招學來了。
應該指出,這種滑稽驚悚的敘述在狄更斯小說中是局部的處理,而在卡夫卡的小說中則貫穿全篇,構成某種方法論的意義。《訴訟》運用狄更斯的滑稽驚悚敘述,至少有如下四處:K. 參加法庭預審會議、K. 拜訪畫家的寓所、K. 和叔父拜訪律師、K. 在大教堂被神父點名,而這四個情節都是小說的關鍵。卡夫卡把狄更斯的玩笑提煉為一種怪誕的夢態敘述,使之寓言化和風格化,這是其方法論的意義。《訴訟》中還有其他一些細節是從《荒涼山莊》中移植而來的,像“樓梯和孩子”的場景描寫等,如出一轍。卡夫卡對狄更斯的模仿應該比我們想象的還要頻繁而深入。
三
相比狄更斯作品,班揚的《天路歷程》和卡夫卡作品的關聯不大有人講起,這里也細致對比一下。
《訴訟》第九章中,神父對K. 講了一個故事,說一個鄉下人終其一生都進不了法的大門。這個故事也被作者拿出來用作單篇微型小說,題為《在法的門前》,是讀者比較熟悉的一篇作品。可以斷言,《在法的門前》中給鄉下人準備的那扇門,是從《天路歷程》中挪移過來的。《天路歷程》(西海譯)中譯本第32 頁,宣道師指點“基督徒”走正道,有這樣一個細節:“于是宣道師對他說,你的罪很重,就因為你有罪,所以你做了兩件壞事,你舍棄那條好路而走上被禁止走的路,不過在小門那邊的人還是會接待你的。”第34 頁上寫道: “ ‘基督徒說:宣道師教我到這里來敲門,我就真的照辦了,他還說,你,先生,會告訴我該怎么辦。‘好心說:門是向你開著的,誰也不能把它關起來。”
《在法的門前》的結尾,鄉下人對看門人提出疑問——“‘所有人都想到達法,鄉下人說,‘但這么多年,除了我之外,卻沒有一個人求見法,這是為什么呢?”看門人回答說:“誰也不能得到走進這道門的允許,因為這道門是專為你而開的。現在我要去把它關上了。”
我們看到,一扇門是永遠開著的,一扇門是開著但最終要關上,兩者性質自然是不同。但仔細體會也有共同點,即它們都是為主人公“專設”的門。所謂“專設”也就意味著不同尋常,包含某種特別的許可,也帶有不能違抗的禁令色彩。
《天路歷程》中的“基督徒”被告知,必須通過一道專設的小門,不從小門進入是不允許的,從其他途徑進去,例如,翻墻進去,就是不合法的。而且,那道門并非對所有人都敞開,那些無知的人、意志薄弱的人,就沒有資格進入。這就把特設的“許可”和“禁令”講得很清楚了。《在法的門前》中的“鄉下人”被告知,這扇門專為他而設,而他既然是死到臨頭了,也就沒必要進去了,因此要把門給關上。換句話說,他本來也許是可以進去的,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他只覺得納悶,為什么別人都不來,只有他一個人等在門口。殊不知這道門是專為他而設的,而“專設”的意義卻變得荒謬,“鄉下人”在徒勞的等待中耗盡了一生。這真是一個荒謬而殘酷的寓言。
有關“門”的寓言,那種鄭重其事、神秘莫測、帶有焦慮的語氣,把卡夫卡和班揚的創作聯系起來。不妨假設,卡夫卡曾矚目于班揚的寓言,并且把《天路歷程》中那扇門挪移到他的作品里。他對“門”的思考是基于班揚的描繪:門內和門外、許可和禁令、接納和拒絕等。這種二元區分是神秘而露骨的,把“門”的閾限性及其空間的象征性標記了出來。《在法的門前》塑造的正是這樣一個閾限性的空間,它把前景和背景的神秘關聯有效地突顯出來。
“門是專設的”這個概念很重要。缺少這個概念,卡夫卡和班揚的聯系恐怕就不會那么別有意味了。門代表空間的內外之分,這只是普通的象征。“專設”則給空間的象征性涂上一層威權的玄秘色彩。要言之,此處描述了一個針對個體的超驗性存在,個體無權認識這個超驗的存在,至多是通過其代理人接受指令,而代理人只是指令的傳達者,代表著真理體系的最低等級,把守著神秘的入口,對個體擁有權力,而個體則處于被動狀態,只能是被告知,被揀選,被注入焦慮的情緒,個體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和一種抽象的絕對指令打交道,這便是“專設”一詞的附加意義。卡夫卡的兩部長篇小說,《城堡》《訴訟》,均包含上述寓意,即關于威權和個體的存在論意義的詮釋。就此而言,《在法的門前》這篇千字文具有發軔之作的性質。它有形而上的象征,有自然主義的細節,也許稱得上是卡夫卡的“陰森的神話”的一塊基石,需要給予特別的重視。
應該指出,卡夫卡對“專設”一詞的演繹,顯示某種荒謬、殘酷的玩笑意味,因而流露出存在主義的基調,而在班揚的作品中并無此種意味。《天路歷程》是純粹的基督教作品,講的是選民、天啟、罪孽等概念,“專設”一詞的象征性是在傳達這些概念。存在主義的描述和基督教的描述有著不同的取向,兩者不可混為一談。
此外,“門的寓言”在班揚的書中只是朝圣者親歷的諸多寓言中的一個,似無特別的意義要讓人單獨予以重視。是卡夫卡的作品讓我們回顧這則寓言,讓我們偏離閱讀的重心,對它刮目相看。用博爾赫斯的話說,卡夫卡讓我們產生了這種偏離,認識到其中的相似,或者說是“不似之似”,從而看到班揚的作品是如何預示了卡夫卡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