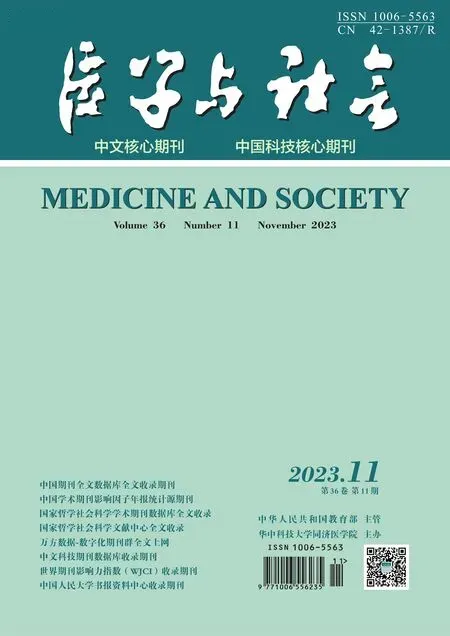成都市三級綜合醫院醫療服務質量與績效評價
伍利香,田明政,王 濼,吳 妮,周曉媛
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衛生學院,四川大學華西第四醫院,四川成都,610041
醫療質量直接關系到人民的健康權益,提升醫療質量、滿足群眾健康需求是當前醫療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與要求[1]。國內外研究發現,按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iagnosis related group,DRG)付費會對醫院行為方式和運營管理等方面產生影響,進一步影響醫療服務的質量;合理實行DRG付費可以有效調節醫療行為,激發醫療機構提高醫療質量的內生動力[2-4]。DRG是一種根據主要疾病診斷、治療方式、合并癥與并發癥、年齡、性別等因素,將患者分為若干診斷組的病例組合方案和管理工具[5];國家醫療保障疾病診斷相關分組(China healthcare security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CHS-DRG)是國家醫保局在綜合考慮我國國情和國內各DRG分組版本基礎上制定的用于我國開展DRG付費工作的統一分組標準[6]。2020年6月,國家醫療保障局印發《關于醫療保障疾病診斷相關分組(CHS-DRG)細分組方案(1.0版)的通知》,指導各試點城市規范DRG分組和試點工作。
國家政策引導下,近年來各城市紛紛進行DRG試點。但對于DRG支付方式下醫院醫療質量呈現何種狀況,同級醫院間是否存在質量差距,哪些因素可能造成差距等問題仍然沒有答案。不少學者嘗試采用DRG分組結果及相關指標對醫院進行評價,如楊雅蘭等采用DRG指標對四川省的三級醫院進行了質量評價[7];成月佳、劉衛剛等利用DRG指標分別對康復外科的管理效果和骨科的醫療質量進行了評價[8-9]。基于DRG指標開展醫療服務質量與績效評價,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評價的可靠性與科學性,有助于醫療質量的持續提升。但這些評價指標大多數不是采用CHS-DRG分組器進行分組,對DRG實際付費和醫院管理的指導意義有限。就國內而言,分組器就存在BJ-DRG、CN-DRG等幾個版本,各版本之間的分組存在差異。
近年來,部分學者開始使用CHS-DRG分組器進行數據測算,如李會玲等基于CHS-DRG對哈爾濱市醫療機構進行了服務績效評價[10],但該研究僅對既往數據進行探索性研究和回顧性分析,未使用實際付費數據進行評價。何瑜璇進一步使用了CHS-DRG付費數據對醫院實際運行狀況進行了分析,但數據僅包含北京市東城區5家定點醫療機構,評價范圍較小[11]。盡管我國醫療質量評價相關研究逐漸增加,但主要局限于針對某個科室、個別醫院進行評價,評價對象數量較少,權威性和指導性相對較弱。同時國內外關于CHS-DRG付費數據進行醫院綜合評價的研究相對缺失,尤其是利用大數據對同級醫院進行實證性評價方面尚不多見,亟需對該方面研究進行補充和完善。
本文借助2021年四川省醫療保障局對省本級醫保實行CHS-DRG付費的契機,利用CHS-DRG實際付費后的真實數據,基于熵權TOPSIS和RSR相結合的方法,選擇西部地區醫療資源聚集且實行了CHS-DRG付費的成都市45家三級綜合醫院進行醫療服務質量評價和比較,旨在探索同級醫院間存在質量差距的原因,為提高西部地區三級醫院服務質量,提高醫保基金利用效率和完善CHS-DRG付費制度提供建議。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于四川省醫保事務管理中心,通過調取四川省醫保綜合服務平臺及DRGs基金結算系統2021年全年CHS-DRG實際付費數據,選取成都市實施CHS-DRG付費的45家三級綜合醫療機構數據進行分析。45家醫院覆蓋成都市各個區縣,對其進行分析可以概括和評價整個成都市三級綜合醫院的總體質量。
1.2 評價指標
通過參考國家醫療保障局2019年發布的《國家醫療保障疾病診斷相關分組(CHS-DRG)分組與付費技術規范》及查閱文獻中DRG考核監管指標[7,12],結合四川省病案首頁提供的數據和管理情況,選出13個評價指標對成都市三級綜合醫院進行醫療質量和績效綜合評價,包括醫療服務能力指標:住院服務量(X1)、DRG組數(X2)、三級手術占比(X3)、四級手術占比(X4)、CMI值(X5);費用控制指標:實際補償比(X6)、藥占比(X7)、住院次均費用(X8)、自費項目費用占比(X9);醫療質量指標:30天再住院率(X10)、住院天數(X11);醫療效率指標:時間消耗指數(X12)、費用消耗指數(X13)。
1.3 研究方法
TOPSIS法,又稱理想解法,是有限方案多目標決策分析中的一種有效評價方法[13]。RSR 法指在一個n 乘以m的矩陣中,通過對指標進行編秩,獲得無量綱統計量RSR,以 RSR值對評價對象的優劣進行排序,廣泛應用于醫療衛生領域的多指標綜合評價[13]。本文通過熵權法對評價指標賦予權重,然后結合熵權TOPSIS 法與RSR法對指標進行綜合評價。
1.3.1 熵權TOPSIS法。 收集原始數據,并對指標同趨勢化處理:即將所有評價指標都轉化為高優指標,X7-X10為低優指標,采用公式Xi=(Xmax-Xi)進行轉換;X11-X13為中間指標,采用Xi=1-(|Xi-Xbest|)/(|Xi-Xbest|)進行正向化處理。

計算歐式距離D+和D-以及相對接近程度CI值,公式如下:
1.3.2 RSR法。計算秩和比,構建n行m列的指標矩陣,研究RSR分布。計算回歸方程為RSR = a + b Probit。依據RSR值對結果進行分檔。
1.4 統計學方法
利用Excel 2017錄入和建立數據庫,使用SPSS 25.0對數據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對回歸方程:Y=a+bX進行顯著性檢驗(F檢驗,)P<0.05認為回歸系數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熵權TOPSIS結果
2.1.1 原始數據及熵值賦權后的結果。由原始數據可知,各指標間存在量綱差異,需對數據標準化處理,見表1。結合熵權法對同趨勢化和歸一化后的指標賦予權重,結果可見藥占比、住院次均費用、30天再住院率和時間消耗指數權重最大(0.082),住院服務量權重最小(0.065)。總的來看,熵值賦予各指標的權重差別不大,表明本研究指標選取較為均衡,結果見表2。

表1 評價指標原始數據

表2 醫療質量評價指標的信息熵、 效用值和權重
2.1.2 三級綜合醫院CI值及其排序結果
由表3可知,2021年四川省本級醫保采用CHS-DRG付費方式下,成都市45家三級綜合醫院間服務質量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CI值排名前三的醫院為A16(0.621)、A1(0.621)、A10(0.604),排名后三位是A5(0.408)、A21(0.407)、A39(0.391)。

表3 2021年各三級綜合醫院CI值及排序
2.2 RSR綜合評價結果
利用Probit和RSR值擬合回歸方程:RSR=0.949+0.289Probit(F=923.605,P<0.001),方程具有統計學意義,擬合優度R2值=0.961,表明模型擬合較好。結合最佳分檔原則,根據RSR臨界值把45家三級綜合醫院服務水平分為3檔。第1檔RSR 臨界值<0.156,包括A45、A14、A42等7家醫院(15.6%);第2檔RSR臨界值介于[0.178, 0.822),包括A40、A23等30家醫院(66.7%);第3檔RSR臨界值≥0.844,包括A1、A16、A10等8家醫院(17.7%)。分檔結果見表4。

表4 RSR分檔結果
3 討論
3.1 熵權TOPSIS法和RSR法結合CHS-DRG付費指標可以較好地評價醫療質量
指標選取是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要更加關注和強調指標的客觀性、 科學性和可比性等[14]。胡松年等在研究中指出我國醫療質量評價指標廣泛存在指標單一、表述和定義不規范、指標來源渠道不夠權威、數據準確性不高等問題[1]。為避免出現上述問題,本研究首次采用四川省醫保局CHS-DRG結算數據,指標來源渠道可信、數據準確性高,且選取能反映服務質量與績效的服務能力、費用控制、醫療質量、醫療效率4類13項指標,指標類型豐富、定義明確。
結合熵權TOPSIS和RSR法既可以利用TOPSIS法充分使用數據信息的優勢,又可以根據RSR值對服務質量及其差異性進行比較排序,結果更加科學、可靠[15]。同一地區的醫療機構所面臨的環境及政策基本相同,對同地區同級別醫療機構采用相同的DRG指標進行橫向比較,可以促進醫療服務質量評估和醫療績效考評工作的完善,具有科學的指導意義和可操作性。同時通過質量評價可以在同級醫院間形成良好的競爭氛圍,使各醫院找準定位,明確自身在支付方式改革下提供醫療服務的優勢與不足,為刺激醫療機構持續改善醫療質量提供外在動力。
3.2 費用控制和醫療效率是影響三級綜合醫院醫療服務質量的主要因素
從熵值權重來看,藥占比、住院次均費用、30天再住院率和時間消耗指數權重最大(0.082),表明這4個二級指標是影響成都市三級綜合醫院醫療服務質量評價結果的主要影響因素;而住院服務量權重最小(0.065),對評價結果的影響稍弱。由此可以看出,CHS-DRG支付下,醫院的發展方式應從粗放式的規模擴張轉向內涵式的提質增效,在保證收治能力的前提下更加關注醫療質量和效率[16]。減少不合理用藥和不必要檢查,合理控制住院次均費用和時間消耗等是醫院提升質量和績效水平的必經之路。
國務院辦公廳2021年發布的《關于推動公立醫院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指出,要發揮公立醫院尤其是三級公立醫院在城市醫療集團中的牽頭作用。因此三級公立醫院要順應醫保支付改革的必然趨勢,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加強臨床專科建設、推進醫學技術和醫療服務模式創新;在滿足DRG合理控費的基礎上提高同級醫院間服務同質化水平,推進三級綜合醫院服務效率和服務能力的提升,實現內涵式發展。
3.3 成都市各三級綜合醫療機構之間醫療服務質量存在差異
TOPSIS法中排名最好的A1和A16醫院,CI值為0.621;排名最差的A39醫院,CI值為0.391。RSR分檔結果顯示,處于2、3檔水平的有38家(84.4%),表明45家三級綜合醫院大部分質量較好。其中質量最優的醫院A1和質量最低的A39 RSR差值達到0.967,說明盡管同為三級綜合醫院,但各醫院間醫療服務質量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這與楊雅蘭等研究結果一致[7]。分析其原因,可能與醫院管理水平差異有關[17]。質量最優的A1醫院從上世紀90年代緊扣“管理創新”主題不斷提升內部管理水平,包括強化管理人才培養、設置專科助理、優化醫院流程等,各科室均得到綜合可持續的發展,醫院綜合排名從全國第60-70名上升至第2名[18]。而A39醫院建院時間較短且地處郊區,與A1相比專業技術人員缺乏,高水平的專家教授稀缺;專科能力不強,學科建設和醫療技術相對落后,醫院不重視內部管理,從而導致該醫院醫療質量評價結果靠后。
因此,建議質量較低的醫院加快轉變傳統的管理模式,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健全醫院人力資源管理、醫療質量安全管理、科研管理等制度,建立新的績效考核體系和分配機制,提高管理效率和能力[19]。積極向排名靠前的醫院學習,通過專科共建、業務指導、科研協作等方式,學習優秀管理經驗,激活自身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