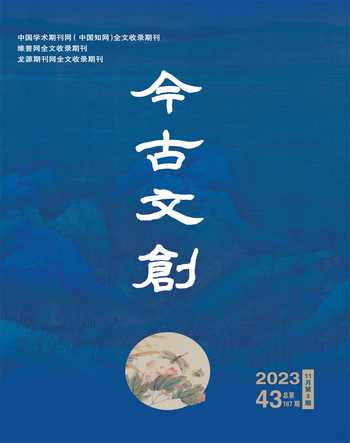馬金蓮小說中敘述聲音類型分析
朱佳苗
【摘要】馬金蓮是寧夏著名的女作家,她的小說常以西海固鄉村的底層女性為小說主角,真實展現她們的日常活動以及心理活動。以往對于馬金蓮的研究,多集中于對其小說中的貧困敘事、底層書寫的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多為性別批評、社會學批評。本文從女性主義敘事學視角出發,對其小說中的敘述聲音類型和敘述音強兩個方面展開分析,從中探討馬金蓮對女性命運的關注。
【關鍵詞】馬金蓮;女性主義敘事學;敘事聲音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3-003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3.010
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女性主義敘事學是由美國學者蘇珊·S·蘭瑟和羅賓·沃霍爾共同創立的一門文學研究方法,她們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與結構主義敘事學相結合,使之成為后經典敘事學的重要分支之一。21世紀初,中國學者便開始了女性主義敘事學相關理論著作的譯介工作,并將其廣泛應用于文學批評實踐過程當中。盡管女性主義敘事學進入中國的時間較短,但也發揮著巨大作用。
“聲音”這個概念在女性主義敘事學中相當重要,“它指敘事中的講述者,以區別于敘事中的作者和非敘事性人物。”[1]“在各種情況下,敘述聲音都是激烈對抗、沖突與挑戰的焦點場”[1],蘭瑟認為對“聲音”的爭奪,就是對話語權的爭奪。女性主義敘事學將敘事聲音的研究聚焦于女性作家、女性角色之中,這一行為體現出的是對傳統男性敘述聲音反抗與解構的堅決態度。蘭瑟在書中主要研究了三類敘事模式:作者型敘述聲音、個人型敘述聲音以及集體型敘述聲音。作者型敘述聲音指一種“異故事的、集體的并具有潛在自我支撐意義的敘事狀態”[1],在這種敘述模式下,作者不會參與到虛構的文本當中,是獨立于文本之外的存在。此時,作者僅僅是書中人物言辭和行動的表述者,但同時也有著全知全能的視點,具有權威性。個人型敘述聲音是指“有意講述自己故事的敘述者”[1],類似于第一人稱敘述,即由“我”自述以“我”為中心而展開的故事。個人型敘述的權威低于作者型敘事,但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性和文本的自傳色彩。集體型敘述指一系列行為,“或者表達了一種群體的共同聲音,或者表達了各種聲音的集合”[1],因為對于集體敘述聲音的研究仍未形成一套專門的敘事學術語,所以在本文中未曾涉及此部分內容。
馬金蓮是寧夏20世紀80年代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小說總是有著獨特女性敘述視角,她總是不厭其煩地描繪著西海固女性形象。這些女性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天真無邪的女童形象、勤勞隱忍的鄉村婦女形象和“進城”后的知識女性形象。馬金蓮的創作多以個人型敘述和作家型敘述對應著她的兩種視角的選擇——幼年女童視角和成年女性視角。首先,她總是采取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來對童年時光進行回憶,對女童形象進行塑造的同時融入了自身幼時的真實經歷和真切感悟,使這種書寫具有了自傳色彩,再加上第一人稱帶來的親歷性,使這一視角具有了個人型敘述模式的特征。其次,馬金蓮有許多以第三人稱視點塑造的成年女性形象,在這類形象當中,又分為鄉村底層婦女形象和城市知識女性形象。此時敘述者不參與到故事當中,對應著蘭瑟所說的作者型敘述聲音。
一、馬金蓮小說中的敘述聲音
蘭瑟認為個人型敘述模式中,“講故事的‘我’也是故事的主角,是該主角以往的自我。”[1]雖然個人型敘述模式不單純指第一人稱視角,但是馬金蓮在有關童年敘述的小說中常以第一人稱展開回憶,而這種回憶就是她的童年過往。生活在西海固這片貧瘠的土地上,貧困自然成了大多數西海固作家的表現對象,馬金蓮也不例外,但是正是自由散漫的童年生活塑造了她獨特的女童視角,在表現苦難的同時,也對苦難進行了消解。以女童視角書寫自己熟悉的童年故事,是對童年生活的回望和思考。
(一)馬金蓮小說中的個人型敘述聲音——女童視角
馬金蓮的多篇小說中都可以劃分為個人型敘述聲音的類型,但是最為集中地體現在她對女童視角的運用上。她以女童的視點觀察著身邊的女性,充斥著饑餓困苦的整個童年中,這些女性始終影響著“我”。在《永遠的農事》中,“我”和姐姐從五六歲開始就被母親教著種地、做飯,培養將來作為媳婦的本事,原本性格蠻橫的姐姐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得溫柔。《賽麥的院子》中,賽麥的母親因為沒有生出兒子不被人看作是女人,兒子終于出生后,卻不幸染上重病,為了給兒子治病欠下大筆債務,兒子卻沒能留住。《柳葉梢》中,父母外出耕作,留下梅梅照顧更為年幼的妹妹,家里沒有糧食,只能靠喝著涼水充饑。
盡管成長的過程伴隨著饑餓、貧困與責罵,但是苦難只是作為背景而存在,馬金蓮對童年故事的書寫總是覆蓋著一層明快的回憶濾鏡。“馬金蓮小說以其不帶批判的天真女童視角書寫苦難與性別歧視,雖然弱化了苦難敘事的社會批判功能,但更能將讀者的思考引向文化內部。”[2]女童視角消解了傳統父權在物質、精神上對人的影響和束縛,以童年的無憂無慮和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完成了對生活的詩意化改寫。在《父親的雪》中,生父離世,母親改嫁,“我”和哥哥寄住在二爹家。在一次去看望母親的返程上,“我”倔強地獨身走在雪夜里,卻不知道后爸在后面默默守候,甚至因此落下了病根。《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中,“我”和姐姐無憂無慮地唱著童謠,觀看奶奶臥漿水,一壇漿水酸菜不僅連接了爺爺和二爺兩個大家庭之間斬不斷的親情,也構筑了生活中最容易獲取和感受的幸福。
作者站在文本背后以追溯的目光去回憶童年時,不僅真實地再現了苦難,更完成了對苦難的消解。因為與童年隔著相當長的時間距離,所以馬金蓮在抒寫童年回憶時總是模糊不清的。但也正是因為這種時間間隔,她得以以審視的、批判的目光去看待童年里的人和事。敘述者作為成年人的思考模式隱藏在天真爛漫的兒童視角之中,在對苦難進行消解的同時,透徹地解析了母親悲慘命運的根源,預測了姐姐以及“我”自己終將走上母親走過的道路,“終有一天,風刀子毒陽光,會把我們變成母親一樣的女人。”[3]正是在兒童和成人的雙重目光下,馬金蓮完成了對生活在西海固鄉村的女性命運的關切和預測。
馬金蓮以成年女性視角進行敘述的小說大多屬于作者型敘述聲音的范疇。文本是虛構性話語構成的,和現實生活有著一定的距離,馬金蓮作為小說的寫作主體,選擇了故事當中的成年女性作為敘述主體。盡管小說中主人公的經歷與作者重合,體現著作者思想意志,但仍然是虛構的人物,敘述者并不存在與小說虛構的文本當中,而是站在文本之外的視點對故事展開敘述,不能將書中主人公同作者等同起來,這也就是作者型敘述聲音權威性的由來。
(二)馬金蓮小說中的作者型敘述聲音——成年女性視角
1.鄉村底層女性視角
馬金蓮以扇子灣為原型構建起的西海固鄉村世界,是她對鄉村農耕日常、貧瘠生活環境進行如實的描繪。“她的敘述沒多少技巧上故弄玄虛的痕跡,而是得益于她堅實的生活實踐與扎實的情感體驗。”[4]她總是將自己所經歷過的西海固農村媳婦的生動體驗全部融入小說創作,對于鄉村底層女性形象的描繪貫穿著馬金蓮文學創作過程始終。
馬金蓮在平淡的敘述節奏中,訴說式地呈現西海固鄉村底層女性生活的不易與艱辛,她對鄉村生活展開全知全面的細致刻畫,農耕農忙、家庭瑣事、妯娌矛盾是小說構成小說的全部內容,并以主人公的心理活動為主線而串聯起來。正是出自對自我熟悉生活的刻寫、對自我經歷體驗的描摹。這些西海固鄉村底層女性是如同作者那樣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女性的縮影,體現著這一群體女性意識的自我覺醒。
馬金蓮前期作品多回憶童年時光以及抒寫西海固鄉村家庭瑣事,近年來,她塑造了許多知識女性形象,這種轉變的發生是伴隨著馬金蓮從鄉村到城市的位置轉移而發生的。與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使馬金蓮寫作的角度與之前有了較大區別,她所塑造的女性也不僅僅局限于鄉村底層女性,城市知識女性形象也成了她使用作者型敘述聲音所描繪了女性形象的一大類別。
2.城市知識女性視角
對城市知識女性形象的塑造大多沿用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其主題仍然是表現和關注西海固女性的生活。我們不難發現,馬金蓮筆下的知識女性仍然是屬于西海固鄉村的,她們是從鄉村走向城市的。盡管身處城市,習慣于繁忙的都市生活,她們精神內核仍然是堅韌且強大的。在這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貧困敘述的主題不再,這些走進城市的知識女性往往是有著一份行政單位的體面工作,不用再為了基本的生活開支而奔波,因此馬金蓮書寫的主題上升到了展現和關注現代女性精神狀態的高度。
《化骨綿掌》中,蘇昔收到了同學聚魂的邀請,她精心打扮準備赴宴,卻被丈夫一直質疑詰問,因此選擇了離婚。《良家婦女》中,在醫院照顧女兒的蘇于漸漸被三床的男人所吸引,理智控制著她的情感,在男人對二床的女人獻殷勤時卻忍不住吃醋,最終還是理智占了上風。《午后來訪的女孩》中,外甥女致電蘇亦要來拜訪,卻在陰差陽錯之間招待了另一位陌生的女孩。時尚前衛的陌生女孩和傳統保守的蘇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馬金蓮通過對女性現代生活片段的展示,以一種“以我觀她”式的自省對現代社會下知識女性的精神狀態生存狀態進行了反思。她所塑造的這些蘇姓女子,都是以她們的心理意識流動組織故事脈絡。鄉村底層女性系列中的女性只是默默呈現生活的艱辛、內心的憂愁,城市知識女性對男性父權的反抗則變得堅決,她們追求幸福的意愿也變得強烈,但仍然是對“男性權力中心”溫和而含蓄批判。馬金蓮把女性的苦難、掙扎于反抗直白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以此來探尋男權社會下普通女性的生存道路。
“音強”是語言學的重要概念,將這一概念引入到敘事學中,“音強”便與作家的敘述權力具有了緊密聯系,在女性主義敘事學中表現為女作家的敘述權力。馬金蓮作為眾多女作家的之一,她的創作過程也代表著她的敘述權力的提升過程。
二、馬金蓮小說中的敘述與“音強”
(一)“音強”與敘述中的“音強”
“音強”是語音的四要素之一,“是用來量度聲音強弱,聲音大還是小、響還是輕。‘音強'更多地用于聲學(偶爾用于聽感)”[5],討論語音的聲學性質時音強的因素不可或缺,但不起主導作用。敘述中的“音強”可以理解為作家敘述聲音的強弱,敘述聲音的強弱又彰顯著作家權力的強弱。敘述學中的音強與女性作家身份焦慮密切相關,女性作家因其長久以來所處的社會環境,一直在為她們被剝奪的權力做斗爭,其中也包括寫作的權力。而“作者身份的焦慮”是桑德拉·吉爾伯特與蘇珊古芭在《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一書中,提出的理論。女性的這種焦慮來自復雜的,從根源上來看是女性對權威的恐懼。“在女性藝術家而言,這種權威似乎從定義上看就是不適合于她的性別的。由于作者身份的焦慮是由社會對女性的生物屬性所施加的影響造成的。”[6]
(二)馬金蓮小說中的敘述“音強”
20世紀二三十年,以丁玲、蕭紅等為代表的女性文學熱潮標志著女性作家身份開始獲得國人的普遍接受,女作家的敘述權力擴大,女性作家身份的焦慮也逐漸減弱。但這種焦慮至今仍對不少女作家產生著負面影響。馬金蓮沒有對傳統父權社會辛辣的嘲諷,也沒有激烈的抗議,而是低聲的訴說,“低訴式”的創作方式正是敘述“音強”低弱的表現,這也是她小說的一大特色。
馬金蓮的小說往往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從女孩、少女到鄉村女性再到后來的知識女性,這些女性角色無一不體現著馬金蓮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個人體悟。女童視角以及鄉村底層婦女視角下女性角色地位的低微,實際上代表著敘述者對自己所擁有的權力的焦慮。小說中有姓有名女性角色卻只有主人公一個,女性普遍存在著一種的無名狀態,她們被稱為“母親”、某某女人,某某媳婦。書中的女性角色作為一種符號而呈現,象征著女性低下的從屬地位。馬金蓮筆下的這些女性人物形象社會地位低下,她們只有在作為男人的妻子或者孩子的母親時才有意義。敘述者在進行敘述行為時的權力也是低微的,敘述音強也是微弱的。敘述者總是采取一種溫情的態度來完成對女性艱難生存狀態的展現,訴說式地呈現女性的心靈創傷。馬金蓮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態,以此作為對傳統父權制社會的泣訴與反抗。但這種刻意放低自己的姿態,仍是對《閣樓上的瘋女人》之前以及后來的女性作家身份焦慮的延續。
與小說中女性的無名狀態相反的是,書中的男性角色一般都有名有姓。但男性始終處于一個缺失的地位,對于男性角色的描寫也沒有像女性那樣細致和豐富,可以說馬金蓮的大部分小說都描繪的是一幅生動的女性人物群像。這其實是女性作家身份焦慮的一種表現,小說中的男性幾乎全部都是父權制社會下傳統男性的典型形象,原生家庭中父親的缺席(《賽麥的院子》中賽麥的父親馬三山常年游走在外),婚姻生活中丈夫的缺席(《馬蘭花開》中馬蘭的丈夫李爾薩經常在外務工)。馬金蓮筆下的男性角色的缺失或模糊不清,是女性在物質上、思想上擺脫男性束縛的符號化表現。正是在男性缺位的狀態下,生出了女性獨立的性格,進一步催生了她們獨立意識的覺醒。
總體來說,馬金蓮的小說發展史體現出她作為女作家敘述權力的逐步提高,但這種提高是在她前后期作品的對比下產生的。因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生活習慣的限制,這種提高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在創作方式上體現為“低訴式”寫作。
三、結語
馬金蓮作為寧夏較為出名的女作家之一,同時也在“80后”作家中有著代表意義。在個人型敘述聲音模式中,她時常以女童稚嫩無邪的目光去觀察周圍世界,在作者型敘述聲音模式中體現為以成年女性的視角去“觀測”周遭一切。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看與被看”的權力始終存在著,盡管敘述者把自己放在一個較低的社會位置上,而這種看與被看的權力實際上就是女性的敘述權力。馬金蓮長久以來寫作過程可以說代表著女性作家敘述聲音的“音強”逐漸放大的過程,她以自己的方式對傳統父權社會提出了抗議,書寫了自己獨特的女性特質。在表層的文字之下隱藏著她對新世紀下女性命運、出路的獨特思考,體現出的是對女性終極的人文關懷。
參考文獻:
[1](美)蘇珊·S·蘭瑟.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M].黃必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4-22.
[2]韓春萍.馬金蓮小說中的女童視角及其文化意義探析[J].民族文化研究,2016,8(34).
[3]馬金蓮.1987奶奶的漿水和酸菜[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6:59.
[4]買莉.作為一種現象的西海固文學——兼論石舒清和馬金蓮的小說創作[J].回族研究,2021,2(01).
[5]朱曉農.語音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41.
[6]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M].楊莉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