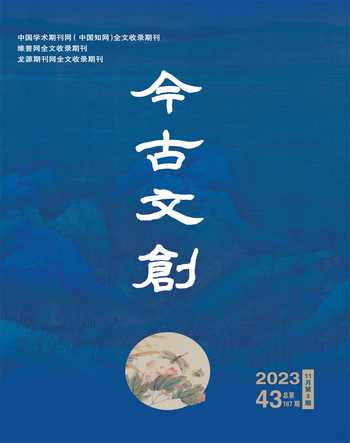感悟自然與敬畏生命
【摘要】葉梅的散文集《福道》具有豐富的生態內涵。葉梅通過對城市生態和河流生態的書寫,批判不合理的人類行為對自然生態造成的嚴重破壞,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喚起大眾的生態意識;她通過對萬物相克相依、敬畏生命的書寫,傳達建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理想;她還通過詩意的文字和藝術的插畫這一圖文并茂的形式,達至詩畫一體的境界,建構出感悟自然、敬畏自然、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生態之美。
【關鍵詞】《福道》;生態批判;生態理想;生態之美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3-004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3.013
基金項目:中南民族大學2023年博士研究生學術創新基金項目“女性觀照、生態書寫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新時代葉梅創作論”(3212023bscxjj20)。
新時代以來,葉梅一直專注于生態文學創作,在受聘擔任生態環境特邀觀察員的切實行動中,進行了貼近大地的生態書寫。《福道》是葉梅新近出版的一本生態散文集,全書由31篇散文組成,以詩意的筆觸寫出了葉梅近年來對生態的觀察和思考,有著豐富的生態內涵。她的散文并不是為生態而生態的寫作,也不是學習生態文學理論之后的實踐,而是她在切實的生態觀察、生態保護中真實感受的自然抒發,是她多年來行走在祖國大地上的所見、所聞、所思的真誠表達,藝術精湛、感染力強。
一、痛徹心扉的生態批判
生態批判是生態散文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同于郭雪波圍繞科爾沁沙地展開人與動物的沖突,也不同于葉廣芩圍繞秦嶺腹地批判人對動物的戕害,葉梅將視野放在全國的生態破壞和生態危機之上,以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感受去書寫該地的生態情況。在《福道》中,葉梅尤為關注城市生態和河流生態,批判不合理的經濟發展等人類行為對城市生態和河流生態造成的嚴重破壞。
一般來說,作家或學者在談到生態時,往往都會把目光轉向草原、山地、村莊等地理空間,而葉梅卻另辟蹊徑,關注城市的生態。實際上,當代人更多地生活在城市,城市生態關乎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但人們總是向往山清水秀、落英繽紛的桃花源之地,卻忽略了身邊的城市生態。葉梅聚焦于城市生態,彌補了生態文學對城市生態關注不夠的不足,這正是葉梅生態批判的獨特之處。葉梅生活在北京,她對自己生活的這個城市的生態有著切身體驗,也希望城市的生態變得更適宜萬物的生長。她毫不避諱地批判她家附近那條發黑發臭的蓮花河,提出如何向子孫后代交代的質疑;也痛徹心扉地批判北京兇猛的霧霾,霧霾給城市里的人帶來諸多生活的不便和糟糕的心情,更重要的是,霧霾是一種大氣污染狀態,是生態危機的表征。通過寫城市里的生態危機,葉梅傳遞出深深的生態憂患,試圖用自己的文字為當代城市人敲響生態警鐘。
葉梅也非常關注祖國各地河流的生態。河流是孕育人類文明的搖籃,葉梅對河流有著天然的親近之感。葉梅出生和成長在三峽岸邊,從小就在山水之間感受自然萬物,三峽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她的童年伙伴,成年后她又在鄂西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草木、山水已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流淌在她的血液中。之后,她從三峽走向全國各地,也格外關注各地的河流,同時念念不忘哺育自己的長江三峽。河流似乎融入葉梅的血液之中,隨著她的生命一起律動。福州的“福道”在成為“福道”之前,也是臭味沖天、被嚴重污染的流域。葉梅感嘆,“若那河能發出聲音,一定會是哀號不已”[1],實際上,那臭味、那渾濁之水就是河流哀號的表現。
葉梅同樣關注到河流可能帶給人類的災害,她回望1998年長江特大洪水造成的嚴重災難,并從中悟出“要珍惜家園,保護山河”的道理。生態意識的覺醒往往要在經歷過生態災難之后,唯有痛苦和失去才讓人類刻骨銘心。這其實也是葉梅對人類文明的一種批判,人類文明似乎總是走上一條先破壞再保護的路,等人類醒悟過來時,很多生態已無法恢復。
當然,葉梅并沒有因為進行生態批判就忽略人們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取得的成果。福州成為真正的“有福之州”,得益于人們對河流的治理;長江特大洪水之后,簰洲灣的人們不斷探索發展新途徑,借助科技力量發展生態農業。葉梅將昔日的污染和今日取得的生態文明建設成果進行對比,更顯示出生態保護和修復的重要性。而大自然也足夠仁慈,給予了人類足夠的生存空間和改過自新的機會。
生態批判并不是葉梅的最終目的,通過生態批判,葉梅擬喚起大眾的生態意識。首先要從觀念和意識上改變人定勝天、征服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讓人們意識到生態的重要性,這樣,隨之而來的生態行為和實踐才更有意義。
二、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存的生態理想
除生態批判外,葉梅還將自己的生態理想寄托在一篇篇優美的散文之中,其生態理想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生物之間相克相依,人保持著對生命的敬畏與熱愛,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存。這一生態理想既是葉梅理想中的世界,也是她在祖國大地上探尋到的生態現實的概括。
葉梅充分認識到生物之間相克相依的關系。正如萊切爾·卡遜所說:“地球上生命的歷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2]大自然是一張龐大的生命之網,任何生命都是這張網的有機組成部分,部分與部分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這張網沒有絕對的中心。“生命之網”的觀念是生態整體觀的一種表達,破除了人類中心主義。在葉梅筆下,青海湖的湟魚、鳥兒和人就構成了這樣一張生命之網。“鳥兒多的時候魚兒多,鳥兒少了魚兒也會少,魚鳥共生,相克相依”[3],魚和鳥兒本身就達到一種生態平衡。然而,由于人類的過度捕撈,魚兒越來越少,人類一度破壞了這種生態平衡,幸而,人們意識到問題所在,加大了對魚兒的保護。現在,人和魚兒、鳥兒和青海湖和諧共存。若以人類為中心,勢必會造成對自然的破壞;若不以人類為中心,而以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為價值追求,則能有效地保護自然、保護生態。
葉梅還保持著對天地萬物的敬畏,這天地萬物包含有生命的動植物、微生物等,以及無生命特征的天空、石頭等物,葉梅將這些看似無生命特征的物體神化或人化,它們也成為生命之物。
一方面,葉梅對動植物有著敬畏、尊重、熱愛之心,為生命的可貴、可敬而禮贊。在葉梅筆下,一切生命都充滿靈性。《魚在高原》對青海湖的湟魚進行了高度的禮贊,獻出了作者最誠摯的敬意。作者驚嘆于湟魚洄游這一大自然的奇觀,贊美湟魚的血氣方剛、勇往直前、不畏犧牲,贊美湟魚為繁衍付出的生命代價,贊美它們生命的高貴。青海湖的魚是自然萬物的一種,也是自然萬物蓬勃生命的代表,對湟魚的禮贊也即是對自然萬物的禮贊。
另一方面,葉梅對天地、山水等物體也懷有基本的尊重乃至敬畏。所謂萬物有靈,這里的萬物,其實是包含自然的一切物體的。三朵是玉龍雪山的名字,人們愿意給一座山取一個可愛的名字,顯出人們對山的親昵,這種命名方式與科學家不同,更多地帶有人們的情感而少了幾分科學性。人們將玉龍雪山稱為“三朵”,實則是人們從內心深處承認了山的人格化乃至神格化。三朵就是這樣一座山,千百年來屹立于麗江,人們創造了無數的神話和傳說訴說三朵的偉岸、傲然與神圣。而在葉梅看來,對待三朵最好的方式,就是減少踏在它身上的腳印。對于雪山等崇高之物而言,征服雪山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表現,人類能做的就是不打擾,這種“無為”恰是一種“有為”,是對雪山的崇高敬意。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生態文學主要致力于生態批判的話,那么葉梅新時代的生態書寫則關注人類的生態責任,書寫中國多年來進行的生態文明建設,表述作者的生態理想,而且這一理想正在一步步變成現實。葉梅“以平實書寫呈現人與自然的關系、考量人在生態中的位置,以樸素筆法還原萬物應有的狀態,講述人與自然之間率真的故事”[4],同時“充溢著一種自然的機趣,情感深沉而濃釅,文字真率而清爽,行文中流淌著對天地的感悟,躍動著自然的力量”[5]。
難能可貴的是,在構建生態理想時,葉梅并沒有忽略人的作用。一些生態作家傾向于書寫人與自然的對立和沖突,卻忽略了人在保護生態中發揮的積極作用。人也是自然萬物中的一種,葉梅注意到每一個為生態保護做出貢獻的平凡之人,表達了對這些人的歌頌和感激之情。人類應該與其他自然萬物一起,為構建人與自然萬物生命共同體而奮斗。
三、圖文并茂的生態之美
《福道》圖文并茂,不僅通過詩意的文字描繪了一幅幅生態場景,還通過一幅幅插畫凸顯了生命之美、溫馨之情。作品中的插畫常常被人忽略,但實際上,它們“參與了正文本意義的生成,是文本構成的一部分,造就了文本圖文并茂的特征,使作品更加充滿一些感性的燦爛”[6],這些插圖不僅有助于闡釋正文,還與正文構成互文關系,以視覺化的方式增加讀者對作品的感受和理解。
一方面,葉梅通過詩意的文字繪就一幅幅生態場景。葉梅行走祖國大地進行生態觀察,她認為將生態觀察轉化成生態書寫有三個步驟:“動心動情”“反復認識”和“美的文字”[7]。葉梅以“動心動情”和“反復認識”進行生態觀察,以“美的文字”進行生態散文寫作,她切實踐行著自己的生態文學創作理念。
所謂“動心動情”,就是對所觀察的自然環境有感情。在《聽茶》中,葉梅不寫品茶而寫“聽茶”,所謂“聽茶”,實際上是讓茶樹聽到人們唱采茶調的聲音。采茶人在采茶時一般都會唱采茶調,常見的采茶調,既表達了人們豐收的喜悅,也代表了采茶人對茶葉的撫慰,后者常常為人所忽略。葉梅認為采茶人的心情會影響茶品,這是萬物有靈、互滲律等觀念的體現。正是將茶樹看成和人一樣平等的生命,才有人、茶的合一。葉梅進一步由聽茶聯系到人對待自然的態度,“人類對大自然的探求從來沒有停歇,但敬畏之心斷然不可無,只有謙恭地聆聽它們發出的聲音,讀懂它們的表情,才能求得彼此的和諧”[8]。品茶已經被貼上高雅、閑適、小資情調等標簽,甚至遠離了采茶人的日常生活,而葉梅能夠關注到采茶人與茶樹和茶葉之間的互動交流,并將其提升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這源于她對自然的強烈敬畏、尊重、熱愛之情。所謂“反復認識”,強調對書寫對象要深刻了解。她以行走大地的方式觀察各地的自然生態。行走大地并進行文學創作具有悠久的傳統,活躍于當代文壇的眾多作家都是如此,如阿來、吉狄馬加等,他們或行走在故鄉的土地上,或由故鄉出發走向全球。葉梅顯然也是其中一員。在她看來,認識一個地方至少要去三遍,第一篇感覺自己對這個地方足夠熟悉,而第二遍卻又感覺一無所知,待到第三遍時,對這個地方的認識又不一樣。
葉梅始終對不同地方保持著探求的欲望,并通過行走、交流、閱讀等多種方式反復認識這個地方,讓陌生的“空間”變成熟悉的“地方”。正因為此,她才能發現許多被忽略的大自然的美麗與魅力。葉梅最終將強烈的情感和深刻的了解化為優美的文字,她的生態散文引經據典、文字清新、語言詩意、細節生動、思想深刻,這些共同構成她筆下文字美的特質,其散文具有詩化的語言和意境,而這詩化的語言和意境又源于萬物和諧共生的現實。
除詩意的文字外,《福道》還配以12幅插畫,這些插畫都是生態主題,可稱之為“生態插畫”,它們分別是《邊緣》《生命》《大海》《傾聽》《猛獸》《懸崖》《雪原》《大河》《望鄉》《源頭》《共度》《秘境》。這些插畫是《福道》的“副文本”,“‘副文本’是相對于‘正文本’而言的,是指正文本周邊的一些輔助性的文本因素。主要包括標題(含副標題等)、筆名、序跋、扉頁或題下題詞(獻辭、自題語、引語等)、圖像(封面畫、插圖、照片等)、注釋、附錄、書刊廣告、版權頁等”[9]。圖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副文本,與文字構成相輔相成的關系。這些插畫都通過黑白兩種顏色、線條組成畫面,但黑白兩色和簡單的線條卻蘊含著豐富的色彩、意義和生命力。如《邊緣》一畫,左下角是一只大象,大象的留白處又呈現出駱駝和鼴鼠的形狀,大象上方飛著小鳥,大象前面是河流、山巒,右上角游著一條條魚。大象的“邊緣”構成了其他動物,魚的“邊緣”構成了水,小鳥的“邊緣”構成了天空,自然萬物就是這樣相互依存,相互成就。而“邊緣”和“中心”是相對的,所謂的“邊緣”,也可以是“中心”。
再如《懸崖》一畫,在懸崖邊,走在最前面的麋鹿,接著是豹子,再是鱷魚,再是猴子,最后是烏龜,天空中的鳥兒也在懸崖邊盤旋。這幅畫具有強烈的批判意味和憂患意識,這些動物靠近懸崖,或許就是瀕臨滅亡的象征,無論是珍稀動物還是日常可見之物,如果人類不加以保護,他們都可能會跌入懸崖、走向滅亡。這些生態插畫增加了人們對生態危機、生態理想等更直觀的感受,帶給讀者強烈的視覺沖擊,令其在品讀文字之余“目睹”到生態畫面。詩的文字與藝術的插畫的結合,才構成完整的生態文本,《福道》雖然“并非寫山河生態的全貌,但文章都導向了生態美這一主題”[10],體現出感悟自然、敬畏自然、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生態之美。
總之,葉梅的《福道》具有豐富而獨特的生態內涵。新時代以來,葉梅從小說創作轉向散文創作,“從原來感性的生態寫作,變成了理性而專業的生態寫作;筆調從原來描寫生態被破壞、被污染的沉重和嚴肅,轉變為對當下綠水青山的欣喜和歌頌”[11]。但不變的是,她“繼續堅持著她的關愛自然,關注生態的信念和熱情”“以人文地理考察為經,以動物植物生態觀察為緯,通過自己的文字,尋找和弘揚著真善美”[12]。在《福道》中,葉梅批判不合理的人類行為對自然生態造成的嚴重破壞,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建構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理想,建構出感悟自然、敬畏自然、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生態之美。
參考文獻:
[1][3][8]葉梅.福道[M].重慶:重慶出版社,2021:27,8, 271.
[2](美)萊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M].呂瑞蘭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6.
[4]北喬.以節制性書寫豐富生態文學的倫理敘事:讀散文集《福道》有感[J].中國民族,2022,(05):74.
[5]張健.自然的機趣,生命的尊嚴——葉梅散文閱讀印象[J].長江叢刊,2018,(07):14.
[6][9]金宏宇等.文本周邊:中國現代文學副文本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10,4.
[7]李景平.以文學的方式為世界點染綠色——中國散文學會會長葉梅訪談錄[J].中國生態文明,2022,(03):88-89.
[10]李傳鋒.對自然的敬畏 對生命的禮贊——讀葉梅生態散文集《福道》[N].中國民族報,2021-11-19.
[11]楊彬.文學的基層力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237-238.
[12]興安.生態理想與美學的深度思考——葉梅及其近期散文寫作[N].新民晚報,2023-03-15.
作者簡介:
艾樂,女,江西撫州人,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21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少數民族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