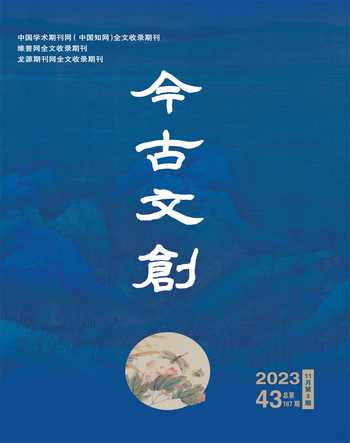張載哲學的生態智慧思想初探
李坤昊 馬鈺馨 王喆
【摘要】張載作為宋明理學時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以“與天為一”作為生態倫理的終極目標,通過“民胞物
與”的生態倫理觀念,詮釋“乾坤父母”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倫理思想。其思想以“氣一元”為認知基
礎,闡釋人德與天德同源一體,將道德領域從人與人拓展至人與自然,體現出萬物共生和諧相與的生態倫理
智慧。當今時代,環境問題日益嚴峻,深度探究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的寶貴資源,有利于人們樹立良好的生態
道德理念,培養正確的生態道德意識,最終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道德責任。對于生態倫理中國化,建設有中
國特色的生態保護之路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張載;與天為一;民胞物與;乾坤父母;生態倫理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3-0081-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3.026
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人類對于自然資源一味索取,只顧眼前利益,忽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人類生存環境持續亮起紅燈,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在借鑒儒釋道三家的天人關系思想的基礎之上,又提出了“民胞物與”“乾坤父母”等新的理論,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生態倫理觀。回看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其中的生態智慧極具遠見性,對于探尋當代生態問題的解決之法,進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生態倫理學在20 世紀40 年代,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了,生態倫理是將自然環境融入人類的道德關懷體系當中,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倫理關系。在中國思想史中,生態倫理思想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隨著人們對自然界的不斷探索,生態倫理思想也不斷發展。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吸收了先哲們的智慧思考,他作為宋代儒學思想家,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生態智慧。張載生態倫理思想的誕生,與北宋時期的社會背景息息相關。第一,當時國家面臨內憂外患。在連年征戰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百姓流離失所。第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造船業、陶瓷業、紡織業較前朝相比,有了很大發展。人們認識自然、把握自然規律并加以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進一步提高。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引發了先哲們對于天人關系、自然與人的思考。
一、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原則
生態倫理原則是指在生態環境中調節人與自然利益關系的根本性指導原則,是在生態關系中應當普遍遵循的準則。天人關系是中國先哲們一直探索的理論核心問題。首先,“和”的觀念誕生很早。最初,其含義局限于音樂之和,而在先秦時期,《國語》中記載,史伯對鄭桓公說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意為實現了和諧,萬物方能生長發育。史伯將“和”進行了理論提升,成了天地萬物生長發育的法則。其次,“天”在不同的情境下被賦予不同的含義。當把人格意志賦予“天”時,天則變為人神,能夠主宰天地萬物;當把“天”置于萬物時,天則變為使人類充滿好奇,充滿迷思的自然界;當把“天”看作是一種抽象的生存準則時,天則變為自然界萬物生長發展的規律。“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形成早期,指的是人與神的合二為一,為封建統治提供身份上的合理性,而后期,則主要是指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張載是宋代理學中宣揚天人合一思想最鮮明的代表。首先,張載認為佛教將天降低至與人齊平,是一種錯誤的觀念。他從《中庸》“誠”“明”兩概念出發,認為“誠”有兩層含義,一即是自然規律,無法改變的;二是圣人的道德境界,是普通人難以達到的。而“明”則是對于“誠”的看法和認知。佛教貶低現實生活的意義,否定了現實世界的存在性,自然不能稱之為“明”。其次,張載在如何認識萬物本源的問題上,提出了“太虛”之氣的概念。“太虛無形,氣之本體”[1]7,“氣”是人與自然萬物的始基,自此,人與自然萬物之間情感相通,能平等的關懷自然萬物。他認為,人與自然界萬物都是由“太虛”之氣演化而來,同時也將道德之心給予人和萬物,這便是“天人合一”的理論起點。張載認為的“天”包含著兩個概念,一是有形有象的自然界萬物;二即是“誠”,代表著宇宙萬物運行規律。由于人與人之間所稟的“氣”不同,所以人有了善惡之分,張載認為“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1]330。人運用“明”的方法,人可以修養自身,達到圣人的境界。人在追求善德的過程中,領悟“天地之性”,最終實現了“天人合一”。最后,天人關系回歸于社會中,天道與人道相統一。古代思想家為了鞏固封建君主的統治,利用人們對上天的敬畏,將人道視為天道在社會中的體現,是絕對權威和不可動搖的,賦予了儒家思想中綱常名教的存在合理性。張載認為天道將人分為三六九等,吉兇之分,社會的秩序是既定的,我們只需遵循天道。統治者是上天既定,人們都應安分守己,恪守人道。
“天人合一”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模板,在實踐中,如何實現這一生態理想?張載提出了“體天下之物”的倫理規范,在論述天人和諧之道時他說道:“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1]24 如何實現“體天下物”呢?“大其心”才能體天下物。“大其心”就是將心的內在道德情感闡揚光大,不囿于人的道德行為與道德情感。所謂“大其心”,張載認為,人之心天生具有的思維認識功能,但并不是對客觀事物的表面認識,這種“物交之識”是有失偏頗的認識,沒有產生真正的心物連系,讓心與物之間存在隔閡。正確的認識方式是讓心與外物實現主客體的統一,實現“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讓心能體悟萬物之德、天地之德,將心與物之間的隔閡移除。這樣,無所謂內與外、物與我了。但是,張載也認識到這樣的境界并非是所有人都能達到的,因此他提出“不以見聞梏其心”,不要被世俗物心所蔽,要通過“體物”這一方式,感受心與物之間的感應關系,才能達到與萬物為一這一境界。
張載的“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原則將人與自然萬物置于一個共同區域下,重新界定了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首先,人具有改造自然的主體性能力,但同時也要順應自然規律。人對待天地萬物,要追求善德,關懷世間萬物,實現至善。人類對于自然萬物道德行為最終要轉化為一種自律性的道德準則,自覺的遵循自然規律,界定人類自身道德行為的善惡,最終實現“天人合一”。
二、乾坤父母的生態倫理情感
生態倫理情感是指,人們在生態環境的實踐中,由于個人的主觀性經驗對一些生態行為和生態倫理關系產生喜惡的心理活動,是一種在倫理方面對生態關系的主觀的態度。“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原則具有理論性和實踐性,但卻難以同百姓產生共鳴。情感具有一種“感通性”,能夠為生態倫理提供一種柔性支撐,更能讓人們產生感情動力。儒家將人類對自然界的情感具象化,繼而演化為君子的準則“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2]28 君子對于動物,要懷有惻隱之心,這是對萬物”善“的源泉。這種感通性給予了傳統儒家以生態情感智慧,將人類與自然萬物的情感相聯結。
張載在其《西銘》中提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1]62 張載認為,乾坤就是萬物的父母,乾為父,坤為母。乾坤出自《周易》,是乾卦和坤卦的前兩字,代表天與地,乾坤即指天地,也就是人們生活在其中的自然界。張載認為,人類在天地之間生活,所得萬物都是天地的饋贈,就像是父母對待年幼的稚子。作為子女,人類要對“乾坤”有著深切的尊敬和感恩。若沒有天地的供養,人類將無法生存。張載用“渾然中處”說明了人與自然是無法分割的一個整體,人類不可能超脫于萬物而存在。而“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則說明了人與自然最原初的關系,氣”是填塞于天地之間的物質,而“我”則是由這團凝聚的“氣”產生而來。“天地之帥”即為天性也稱天德,是萬物生命價值所在,乾坤也就成為自然萬物的價值根源。自此人的身體發膚、氣質秉性都來源于此,乾坤賦予了人生存之根本,又是造化萬物之德的源泉,由此意義上,乾坤即為父母。
張載通過“天性、乾坤、陰陽也”[1]63 闡明了乾坤對于人的道德教化功能。“性”在張載的理論體系中,既可指人性,又可指天性。他這樣解釋“性”:“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1]225“性”囊括了太虛與氣。天地之性是誕化萬物價值的源泉,也就自然賦予了萬物以天德。自此,在倫理意義上,人之成為人的德行,自是來源于乾坤。張載稱“乾坤父母”,來表達了對自然萬物的尊敬與感恩,把萬物與人歸并到同一個道德情感網脈之中,人對自然萬物,就應像對自己的父母、同胞一樣,善待萬物就變成了人之善德,形成了一種對自然萬物的生態倫理情感。
三、民胞物與是生態倫理信仰
生態倫理信仰是指,生態倫理主體在自身的世界觀的視域下,以某種信念為引導,對于生態環境的終極目標的追求,以自律的方式規范主體行為,是對生態理想的進一步升華。張載在《西銘》開篇就地提出了“民胞物與”的生態倫理觀,他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1]62 后人將其總結為“民胞物與”,在張載看來,天地是我們的父母,世間萬物都是我們的兄弟,萬物都是我們的同伴,我們都是由“氣”化生而來,同源一體。自然的,人與萬物都有著密切的倫理關系和廣泛于自然界的道德責任。首先,張載肯定了人與宇宙萬物的同源性。在張載看來,自然中人與萬物的關系樸素簡單,既萬物都為“氣”凝聚而生,那人也就不同于西方傳統“人類中心說”的觀點,人不再具有至上性,與萬物應該相互依存、相互扶植。自然對于人類來說,是一個價值寶庫,為人們提供生存所用的價值資源張載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運用人類的主觀情感和生活經驗,讓自然萬物成為人類的儕輩,向自然索取資源時,要像朋友交往時一樣,遵循基本的交往道德準則,尊重自然萬物的價值與尊嚴。
其次,對自然的尊重與愛護,對萬物價值的認同和肯定,并不會降低人的主體性價值與尊嚴。自然之所以充滿生生不息的活力,正是由于每一個生命體的存在,缺一不可。自然和人都具有道德屬性,張載通過經驗分析,認為天道賦予自然以價值。在《張子語錄》中說道:“虛者,仁之原。”[1]225 說明了自然價值具有生命意義和道德意義的。在“氣”的不斷演化發展中,自然也在不斷創造萬物,不斷涌現新的事物,這是自然的生命價值。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天地萬物運動周而復始,并不是人類強加于自然,而是自然中“誠”的屬性,是天道的超越性的道德價值。人類的道德關懷應當將自然價值包含容納,實現人類道德的“至善”境界。
最后,張載“民胞物與”思想體現傳統儒家的“仁愛”思想。“仁愛”是儒家傳統思想中的重要范疇,孔子將“仁”作為君子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將“愛人”作為社會道德原則。孟子則將仁愛擴大化,從仁民到愛物,但孟子的“仁愛”仍是具有差異性的。直到漢代,董仲舒言:“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末不愛,不愛,奚足以為仁。”[3]就是說,如果僅僅愛民的君主不能稱之為“仁”,君主要愛天地萬物、鳥獸飛禽才能是“仁”的君主。可見,傳統儒家思想就具有了樸素的生態道德意識。張載言:“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1]113 天地之德促進萬物生長,天地非人,不具有人之心,而人具有天地之德給予的“性”,即人性。正是由于此,人能體會到天地萬物中蘊含的天地之德。
張載生態倫理思想是一個系統推進的成熟思想體系,“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意識奠定了其生態思想的基礎,沒有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意識作為支撐,何來人與自然萬物的情感聯結與依存關系?將“天人合一”作為生態倫理思想的根基,人才能體會到“乾坤父母”“民胞物與”的情感,才能待天地如父母,視萬物為儕輩。通過培養“乾坤父母”的生態倫理情感,佇立起“民胞物與”的生態倫理信仰。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豐富了宋代理學的倫理觀,將人與萬物、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倫理體系中,至此,提出了“體天下萬物”的倫理實踐途徑,就是要將天地萬物以倫理化,讓人與自然實現和諧統一。
四、“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的生態啟示
生態危機是當今我國面臨的重大時代問題,生態文明建設亟須提上日程,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重中之重。自然資源的匱乏和人類欲望的無限膨脹是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矛盾,生態問題的解決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生活質量。人類過度消費資源是對自然的一種侵犯,是倫理視域下的不道德行為,也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不平衡的后果。張載提出“天人合一”生態倫理原則肯定了人與自然相依相存,為保護生態環境提供了理論支持。在新的歷史時期,應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歷史底蘊思想與本土化理論支撐。張載作為“天人合一”生態倫理思想第一人,為古代生態倫理智慧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自然萬物同根共源的主張可以規范生態道德行為、培養生態道德意識,喚醒社會生態道德良知;人們樹立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發展、保護自然生命的生態理念;“天人合一”的生態道德原則體現出人類應承擔的生態道德責任,與萬物和諧共處的生態理念;“乾坤父母”的生態倫理情感和“民胞物與”的生態倫理信仰讓保護環境的必要性多了一層生命意義上的切實關懷,實現人類生態命運共同體。
(一)規范人類生態道德行為,推進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誕生,將自然推到人類的對立面,人類的生存危機變為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博弈。在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人們將對自然的敬畏之心逐漸轉變為了對自然的征服欲望,現代人類生存危機根源在于如何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自然資源消耗量與日俱增,可持續發展的根源動力堪憂。生態環境不斷惡化,生態問題處處顯現。以巨大的環境代價換取短期的經濟利益,導致了生態污染,加劇了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但人與自然始終是統一的整體,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5]135 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掠奪,這本身也是一種不道德的倫理行為。在張載看來,維持人類正常生活的欲望是合理的,但是過度沒有節制的生活是錯誤的。我們現在提倡的綠色生活、合理利用資源,我們能在張載的生態倫理觀中得到啟示。
張載“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思想中,“窮人欲”會泯滅人的“天地之性”,是錯誤的,主張“寡欲”的生活。對于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指導性價值,提醒人們不要被欲望脅迫前行,要樹立減少資源浪費的生態環保意識,弘揚勤儉節約的社會風氣。張載“乾坤父母”的生態情感將萬物賦予倫理關系,在他看來,將萬物變為“人”,人與萬物之間便有了道德情感,將“乾坤”比作父母,揭示了天地對于人的根本意義,人應當運用處理家庭感情、家庭責任的方法來對待天地萬物。人類應當有此覺悟,不能一味索取傷害自然,要從自然界與人類的整體利益出發,規范自身道德行為,做自然界的守護者。新時代,我們要建立健全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摒棄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我藩籬。生態道德要求我們對自然萬物有敬畏之心,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可以為現代生態道德規范提供思想啟示,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倫理情感依據,使人和自然可持續發展下去。
(二)培養生態道德意識,推進形成環境友好型社會
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繼承了傳統儒家的“仁愛”之心,愛人愛己、泛愛天地萬物,認為人人都可為親為友,要將他人視作自己的同胞兄弟。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和諧、相互依存,張載“天人合一”的倫理思想將萬物同源化,萬物皆由“氣”構成,也就是說,人與萬物本質上都是相同的“氣”,這展現的是人類對自然的神秘崇拜和渴望與自然合為一體的愿景,這種對自然的“附魅”到如今科學時代的提醒生態理念應當“返魅”,都說明人類應當對大自然尊重敬畏。張載的生態智慧中,既看到了尊重自然規律的重要性,也肯定了人主體性的主觀能動性。人類中心主義雄踞生態理念核心多年,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人與自然逐步走向對立,都表明人與自然不是主仆,人類更不是世界的核心,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應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相互依存的。
從張載開始,先哲們開始用一種人文主義的視角來關注自然界,增強了人對自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天地之性”中,揭示人類生而具有地向善的道德品質,與自然萬物和諧共處、待他人如自己同胞兄弟,都是人本體中的善。而今,人類憑借自己的高度文明,不斷侵蝕著自然界,一味掠奪終究得到“反噬”,所以,順應自然規律,尊重自然萬物的生態道德意識十分重要。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并非是強制的使人接受,而是喚醒人與生俱來的善,即對天地萬物的愛護與尊重的意識。因此,在當下社會中,我們要樹立生態保護意識,自覺地進行垃圾分類、提高環境保護意識、積極參與環境改善與治理活動,發揮公民主體的能動性,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推動形成環境友好型社會。
(三)形成生態道德責任,推進人類環境共同體建設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個問題都不再是某一國家所面臨的困境,而是佇立在全球各個國家面前的一座大山。生態環境問題具有寬泛性、普遍性、難治理性,全球治理和生態治理全球化迫在眉睫。某些西方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環境,將高污染、高排放、低收益的耗能產業投放到發展中國家,調整自身產業結構的同時,將污染的源頭嫁禍于發展中國家。這種極度的利己主義思想,缺乏對生態問題的全面理解,沒有承擔相應的生態道德責任。我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體現了我國為全世界人民著想,站在生態發展大局看問題,這就是張載“天人合一”整體性思想的現代化表達。
生態文明需要全球共建,人類必須反思以往錯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乾坤父母”的思想表明了人與自然是血肉至親,“民胞物與”則進一步強調了人的生態道德責任,自然萬物的生命都與人類息息相關,自然與人本就應是一家。這種“命運共同體”的生態理念進一步推動了生態文明全球化治理的腳步,在面臨生態問題時,各國應攜手并進、守望相助,積極承擔自身責任,不推諉,不逃避。幫扶相對落后國家的生態治理,修復生態缺口,促進人類環境共同體的概念落實。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可以在生態環境治理中發揮強大的指導和規范作用,引導現代人的治理思維模式和治理行為的改變,同時也為當代生態治理框架提供有效的理論支持。
五、結語
張載的生態倫理思想是為中國生態智慧提供了精神源泉,促進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倫理依據,對于當今的生態文明建設仍具有啟示性作用。它蘊含著樸素而又豐富的生態道德思想,在時代的變化中,仍源源不斷地提供著精神養料,喚醒人們對自然的尊重與感恩之情,將生態他律變為生態自律。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自覺地保護環境、愛護自然。張載的生態智慧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歷史依據,留下了寶貴的生態文明財富,指導我們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互惠、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張載.張載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
[2]鄧球柏.孟子通說[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3]劉湘溶,任俊華.論董仲舒的生態倫理思想[J].湖湘論壇,2004,(01):38-40+73.
[4]朱貽庭.倫理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作者簡介:
李坤昊,女,山東泰安人,寧夏大學法學院2021 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倫理學。
馬鈺馨,女,寧夏銀川人,寧夏大學法學院2021 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學。
王喆,男,寧夏銀川人,寧夏大學法學院2021 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