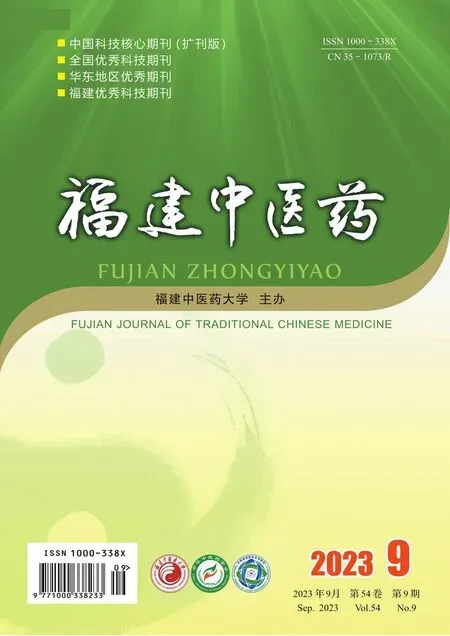中醫脾藏象與西醫脾、胰的對應更迭考
冀 蕾,游世晶,林 鈺,陶煒東,靖 媛,李毓婉,童伯瑛*
(1.福建中醫藥大學針灸學院,福建 福州 350122;2.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福建 福州 350003)
中醫藏象學說肇始于《素問·六節藏象論》,由肝、心、脾、肺、腎五大核心系統構成。脾藏象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參與飲食的消化吸收、精微物質的輸布等諸多環節,在人體生長發育的各個階段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現代醫學所言的“脾”,即Spleen,為免疫系統最大的實質器官,是造血和免疫應答的重要場所。二者雖皆名曰“脾”,但將脾藏象簡單地譯為Spleen 顯然不妥。Pancreas 為胰腺,其分泌胰液助消化、分泌胰島素助調節的兩大功能,可毫無疑問地將胰腺劃分到“消化系統”及“內分泌系統”。如此可見,脾藏象似乎更與Pancreas相吻合。
中醫學和西方醫學為兩大相互獨立的醫學理論體系,但對同一生理或病理現象的認識往往殊途同歸。近代以來,中西醫結合發展逐漸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趨勢,雙方不斷嘗試以此之視角詮釋彼之理論,找到二者千絲萬縷的聯系,以推動整個世界醫學的融合與發展,但囿于各種因素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和認知的偏差。筆者將基于脾藏象的認識發展順序,理清脾藏象與現代解剖器官的對應關系更迭史,探析脾藏象的實質臟器歸屬。
1 初識:脾藏象譯Spleen 的合理性
受近代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以解剖學為基礎的西方醫學思想和以藏象學說為核心的中醫思想開始碰撞交融,西方解剖學譯著層出不窮,其中對脾的記載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末年羅雅谷的《人身圖說》。《人身圖說》在“論脾”一章中對脾的形態、血液分布和生理功能等方面進行初步闡述,提出“其洼空之分向胃部”“其體柔軟細嫩,故易翕受肝血渣之黑液;其色較肝更黑,因其體是煉過血渣而成,其色所以黑也”[1];“留取細黑液以養其體……帶粗黑液以激動脾,使之覺餓,即欲飲食。”[2]以《人身圖說》為代表的早期西方醫學對Spleen 的認識為:緊鄰胃體,接受并過濾由肝匯入的血液,參與胃的消化功能,這與脾藏象的生理功能不謀而合。羅雅谷所傳播的西方解剖生理學知識,并不是簡單節譯的成果,而是加入了中國醫學知識的重新撰寫,是一本中國化的西方解剖學著作,基本反映了16 世紀西方解剖的概貌[3]。
二者不僅在生理功能上有相似之處,在形態大小上也基本相仿。早在《難經·四十二難》就對脾的形態數據作了最基礎的描述:“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根據秦漢度量衡折算,秦漢時期的一寸約為現代的2.31 cm[4]。《難經》所載之脾寬約6.93 cm,長約11.55 cm;成人Spleen 的寬長分別為6~8 cm、10~12 cm,與《難經》記載的數據基本吻合。從外觀來看,《補注黃帝內經素問》提出:“脾,形象馬蹄”;《中西醫匯參銅人圖說》述脾“形如豎掌”,馬蹄、豎掌等描述皆似Spleen 的外形[5]。
可以看出,在第一批中西醫結合開拓者的視角下,Spleen 的形態功能與脾藏象有相通之處,初譯為此不無道理。由于所處時代背景下中西方解剖學研究程度的不對等,文藝復興后西方通過對大量尸體的解剖使得解剖學的發展如日中天,而中醫囿于封建禮教以及“司外揣內”的診療理念,決定其并不依賴解剖知識,致使中醫典籍對脾藏象的解剖記載并不詳細精確甚至相去甚遠,直至明朝末年解剖學傳入中國后才得以逐步糾正和統一。再者,譯者中醫文化底蘊的薄弱也是一大根源,中西醫思想體系的差異導致大多數學者并未意識到藏象系統的結構是功能的結構[6],誤認為是單一的臟器,片面地將其與實質器官的形態相對應,試圖從微觀層面找到整體的功能依托,忽略了脾藏象作為整體系統的功能,造成了翻譯混淆的亂象。
2 質疑:脾藏象譯Spleen 的片面性
將Spleen 譯為脾藏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為學界的主流認識。然而,生物化學等學科的興起引發了學者的質疑和思考:Spleen 無論從解剖角度還是生理功能上,都已無法與脾藏象完全對應。一時間脾藏象的英譯歸屬眾說紛紜。
2.1 基于解剖形態的質疑 從脾藏象的解剖形態來看,《難經》所言脾實質與Spleen 大致相應,但是后世對脾的圖文描述卻大為不同。《醫方類聚》所載“脾臟圖”繪其形如鐮狀;《醫貫》論及脾有“形如刀鐮”之語;《醫林改錯》賦予了脾藏象更為具體的生理結構:“脾中有一管,體相玲瓏,名曰瓏管。”Spleen 呈橢圓形,實質區分為三大區域,紅髓、白髓及中間的邊緣區,內無管道結構,從形態來看二者并非一物。
從脾藏象的相對位置來看,《素問·太陰陽明論》有云:“脾者土也,治中央”。在五行學說理論中,脾屬土,土居中央,是人體氣機升降的樞機。Spleen 與9~11 肋相對,居胃之左,靠近人體的側胸脅肋部,與內經所言相悖。此外,《佗別傳》曾記載外科鼻祖華佗的一次剖腹手術:“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華佗對脾半腐的定位描述是“腹中”而不是“脅肋”,提示當時所見之脾并非脅肋部之Spleen。
從脾藏象的遠近關系來看,《素問·太陰陽明論》稱“脾與胃以膜相連”。解剖學觀察發現,除了Spleen 與胃相連,Pancreas 也與胃相接。在接觸面積上,Spleen 僅有脾門與胃底接觸,Pancreas 除了部分頭部,胃面的主體幾乎都通過小網膜囊與胃后壁相鄰,接觸面積更大;在連通方式上,Spleen 與胃僅通過短小半透明的胃脾韌帶相連,而覆蓋Pancreas的網膜囊附有大量的黃色脂肪,Pancreas 的連接膜在視覺上更易被發現和記錄[7]。同時,賴敏和黃春華[8]提出相合臟腑具有“遠疏近親”的方位隱喻,解剖位置越近的臟腑越容易在生理、病理角度影響彼此。以胃為中心,Pancreas 與胃的距離較Spleen 更近,符合臟腑表里配屬規律。綜上所述,站在解剖角度將脾藏象譯為Spleen 失之偏頗。
2.2 基于生理功能的質疑 脾藏體現在“象”的維度主要指消化系統。《素問》有云:“脾胃者,食廩之官,五味出焉。”谷藏曰倉,米藏曰廩,脾藏素來有“倉廩”“食廩”之稱,匯聚一身的谷食、水飲,依托“主運化”的生理功能參與人體食物與水液的代謝環節,同時發揮“脾氣散精”的作用源源不斷地將各種精微物質輸布到四肢百骸,以和調于五臟,灑陳于六腑,充養人體的形體官竅,是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享有“后天之本”的美譽。《景岳全書》提及的“脾為土臟,灌溉四傍,是以五臟中皆有脾氣,而脾胃中亦有五臟之氣”即是對“脾為后天之本”的最好詮釋,給予了脾藏象極高的評價。
脾藏還有統攝血液的作用,即“脾主統血”。《難經·四十二難》云:“(脾)主裹血,溫五臟也。”揭示了脾藏具有統攝血液的功能,能調控血液循行不離脈道。又如《沈注金匱要略·卷十六》云:“五臟六腑之血,全賴脾氣統攝。”脾主統血的功能主要是由脾氣攝血的能力來實現。只有當脾氣旺盛時,血液才能被約束于脈內,反之脾氣衰虛無力統攝,會出現各種出血癥狀[9]。
Spleen 作為一大免疫器官,是淋巴細胞的生產工廠,是機體進行免疫應答的主要場所,是人體最大的血液凈化器。Spleen 對血液的過濾凈化可以調節血量,與“脾統血”的功能相合,但“主運化”的核心功能卻未能得到充分體現,籠統地將Spleen 與脾藏象的功能對應未免有削足適履之嫌。
3 相持:脾藏象錯譯的復雜性
自《人身圖說》首次將Spleen 譯脾之后,學界就脾藏象的英譯歸屬展開激烈探討。1708 年,中西醫學者共同編寫的《欽定格林全錄》將脾納入消化系統,并首次提出“脾”應譯為“Pancreas”,開辟了探索脾藏象英譯歸屬的新局面[10],遺憾的是,該書并未提及Spleen 的相關內容。1774 年《解體新書》面世后,將Pancreas 譯為胰、Spleen 譯為脾才作為共識確定下來。同時期中醫著作也開始涉及“胰”的概念:清朝王清任所著的《醫林改錯》最早提出將“胰”劃分為獨立臟器,在《醫林改錯津門、津管、遮食、總提、瓏管、出水道記》一章中明確胰腺的名稱及相對位置,“總提俗名胰子”“此是膈膜以下,總提連貫胃、肝、大小腸之體質。”王清任雖然對臟腑的形態位置作了準確描述,但由于對功能認識存在偏差,在把Pancreas 識為脾的同時將Spleen 標為胰,這恰恰與現代解剖學相反。脾與胰、Pancreas 與Spleen出現螺旋反復的交叉錯譯現象。
4 芻議:脾藏象譯Pancreas 的適時性
脾藏象的英譯版本復雜交錯,如今多數學者持有“脾即為胰”的觀點,即脾藏象譯為Pancreas。Pancreas 為現代解剖中的“胰腺”,其形態扁長,長約10~20 cm,寬約3~5 cm,重約75~125 g。Pancreas 的中譯名稱經歷了多種多樣的變化,一定程度上歸咎于一些傳教士以為中醫不存在胰腺這個器官。Pancreas 果真未曾被中醫發現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4.1 脾藏象實為Pancreas 的生理基礎
4.1.1 中醫典籍中Pancreas 的記載 縱觀中醫千年發展歷史長河,對胰、脾的描述常混為一談,但往往都指向同一個實質器官——Pancreas。對Pancreas的描述無論言胰還是脾,形態位置都大抵相同。
以胰為線索,早在《難經》時代就已提出“散膏”一詞。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指出:“西人謂中醫不知胰,不知古人不名胰,而名散膏。”散膏為中醫對Pancreas 的最早認識;南朝《玉篇》、北宋《集韻》《廣韻》皆稱胰為“月臣”,解釋為豬的脾息肉;《本草綱目》對“月臣”作出進一步補充說明:“月臣,音夷。亦作胰”;《中華大字典》云:“膵,胰也。”根據以上記載發現,從“散膏”到“月臣”再到“膵”,都是對Pancreas 的直接描述。清末醫家張山雷更豐富了Pancreas 的概念,指出胰腺在古代有稱為脾者,并且具有分泌消化液的功能[11]。
以脾為線索,《針灸甲乙經》云:“脾俞,在十一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針灸大成》曰:“脾掩乎太倉,附脊十一椎。”晚清名醫陳珍閣提出“生于胃下,橫貼胃底,與第一腰骨相齊。”背俞穴為五臟之腧在背,十一椎高度相當于現代第一腰椎上下,脾俞穴道深處為Pancreas 攀附之處。盡管《難經》及部分著作認為脾藏象為Spleen,但是放眼整個學界該認識僅占少數,并不能代表主流認識。大多學者認為脾在形態上“形如刀鐮”,內有“瓏管”,和Pancreas 的外形吻合。可見,學界對脾藏象的位置和形態逐漸向Pancreas 靠攏,雖談之脾,實則言胰。
4.1.2 西醫學界對Pancreas 功能的探索 Pancreas的近現代研究將其帶入了大眾視野,為學界重新思考脾藏象的對應器官提供了新的方向。Pancreas在西方醫學中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公元1642 年以前,Pancreas 都未曾作為一個獨立的器官出現在教科書或者是解剖圖譜上。直至胰腺管被發現,以及胰液在大量研究證明下表現出顯著的消化作用之后,Pancreas 才作為一個獨立的器官,而非腺體樣組織,或者是腹膜的一部分被人們所認識。又過了200 年,經過實驗證明胰液具有消化作用的具體機制,Pancreas 才被列為消化系統的重要環節被人們所接受。公元1869 年,Langerhans 發現胰腺中存在胰島結構,進一步完善了胰腺的生理結構。公元1921 年,加拿大醫學家Banting 從狗的胰腺中成功提取出胰島素,使得Pancreas 的功能向內分泌系統滲透,體現了其對人體血糖水平的調控作用,賦予了Pancreas 更加豐富的功能。
現代醫學將Pancreas 分為內分泌部和外分泌部。外分泌部的腺泡分泌胰液、消化酶及各種分子,參與人體的消化吸收過程;內分泌部的胰島細胞分為A、B、D 3 種,其中胰島B 細胞分泌人體內唯一一種降血糖的激素——胰島素,使得吸收入人體的三大營養物質,尤其是作為主要供能物質的葡萄糖,廣泛進入全身各個細胞之中,參與三羧酸循環,為機體持續提供能量,這與“脾氣散精”的功能有異曲同工之妙[12]。Pancreas 被廣泛證實在消化系統和內分泌系統中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能更加準確地將脾藏象的功能全貌呈現出來。
4.2 脾藏象譯為Pancreas 的病理研究 《素問·玉機真臟論》云:“脾為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以脾藏象的生理功能為參,太過即脾實病,不及即脾虛病。脾藏象的虛實病理狀態與胰腺疾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4.2.1 脾虛視角下的糖尿病 消渴病的病機常被概括為“陰虛為本,燥熱為標”,尤以脾陰虛最為多見。脾主運化是脾藏象最重要的功能,在病理狀態下,脾失健運不能運化水液,津液無法上承,患者引水自救出現口渴多飲;不能運化水谷,使水谷精微隨小便排出體外,患者出現尿多渾濁而帶甜味;不能為胃行其津液,胃失潤澤,胃火亢旺,則消谷善饑;不能輸布谷食,四肢百骸失于精微物質濡養,則肉脫形消。不難發現,脾陰虛導致的脾失健運是消渴病“多飲、多尿、多食、消瘦”癥狀出現的根本。
《醫學衷中參西錄》云:“有時膵臟發酵,多釀甜味,由水道下陷,其人小便遂含有糖質。”張錫純用臨床大量觀察和積累在消渴病與Pancreas 之間建立起互通的橋梁。現代醫學研究認為,Pancreas的胰島B 細胞遭到破壞時,機體持續性的高糖狀態可導致各大系統代謝紊亂,發為糖尿病,臨床表現常被概括為“三多一少”,即“多飲、多食、多尿、體重減少”,與消渴病的癥狀表現基本相同。
糖尿病癥狀與消渴病相似,對于如何治療消渴,《內經》中提出了“治之以蘭,除陳氣也”的治療藥物和方法。王冰認為“蘭,謂蘭草也”,選用藿香、佩蘭等芳香、化濕、醒脾類的草藥,可有效驅逐瘀結在體內的陳朽腐敗之氣。張錫純首創的“玉液湯”納生山藥、生黃芪、生雞內金等,具有升元氣、補氣補脾之功,同時“滋膵飲”創造性地以生豬胰子為主藥治療消渴。冷玉琳等[13]也認為“脾主運化”是維持胰島功能和血糖穩態的核心環節,恢復脾的運化功能可改善糖尿病胰島功能衰竭。仝小林院士[14]通過大量的臨床經驗觀察發現,用李東垣所創的補中益氣湯治療糖尿病收效卓著。宋軍等[15]運用開郁清熱法,從脾郁化熱治療脾癉,開郁清熱方可有效升高Bcl-2 蛋白表達,抑制胰島B 細胞的凋亡過程,促進胰島素的分泌。就治法而論,從脾論治糖尿病具有很好的療效,故脾藏象的病理狀態應當是糖尿病發病的中心環節。
4.2.2 脾實視角下的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是胰酶激活導致胰腺組織自身消化引起的胰腺水腫、出血、壞死的急性炎癥,常在暴食、大量酗酒后誘發,可能帶來急性上腹痛、腹脹、發熱、嘔吐甚至低血壓、休克等危急表現,是胰腺的多發嚴重疾病。
中醫對急性胰腺炎的病名并未作出統一規定。王華楠等[16]通過剖析《靈樞·厥病第二十四篇》發現,“厥心痛,痛如以錐針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與急性胰腺炎的臨床表現基本契合,認為急性胰腺炎是脾之邪氣厥逆犯心所致的心痛病證,屬“脾心痛”范疇。《素問·痹論》曰:“脾痹者,四肢解墮,發咳嘔汁,上為大塞。”蔣里等[17]認為急性胰腺炎是由于胰腺排泄不暢,自身痹阻所致,故歸為中醫的“脾痹”范疇。《素問·刺熱篇》云:“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兩頷痛。”脾熱病出現的欲嘔、身熱、腰痛、腹滿泄等也是急性胰腺炎發作的標志性癥狀。《癥因脈治》云:“膏粱濃味,日積月累,熱聚脾中,則脾熱腫之癥作矣。”過食膏粱厚味,滋膩礙脾損傷脾胃,邪毒積滯化熱,可發為脾熱病。醫圣張仲景以為“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無論是脾心痛、脾痹還是脾熱,發病時皆為足太陰經主病的“腹滿時痛”的癥狀表現,雖未明確冠以“脾實”之名,但都可歸為“脾實”之證。從病因病機、證候表現來看,急性胰腺炎與脾藏象密切相關。
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脾實證與脾虛證往往可在現代胰腺疾病中尋找到合理的解釋和印證,從病理角度指示脾藏象的解剖基礎所指應當是現代醫學中的Pancreas。
5 小 結
基于現代解剖學對比發現,中醫之脾并非西醫之脾,二者雖同名,但在形態、功能方面無法完全匹配。本文以脾藏象對譯的實質器官認知衍進為考,種種證據皆印證了脾藏象更貼近Pancreas 的形態和功能。
近現代以來,在西方醫學的發展和影響下,中西方醫學相互借鑒融合,共同認識生命科學的本質,但認識前進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由于發現胰島素功能的時間(公元1921 年)晚于Spleen 臟器被譯為中文的時間(公元1708 年),Spleen 的譯名在其后的300 年一直沿用至今,致使現代中醫學對脾藏象的認識逐漸從解剖基礎轉向功能解讀。藏象學說始于對人體內部構造直觀觀測的經驗,但先賢在臨床實踐中發現并不能解釋所有的生理病理現象,便通過“取象比類”的方法為藏象學說注入了濃厚的哲學色彩,架構起“包羅人體萬象”的宏觀大廈。這一定位賦予了藏象學說與生俱來的抽象化、模式化特點[18],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藏象學說的臨床適用范圍,使藏象系統逐漸演變為功能的合集。現代醫學以顯微鏡下發現的細胞作為生命的起點,具有重視解剖且功能邊界清晰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決定了現代醫學致力于微觀世界的研究,新的單位、結構、系統逐漸被發現后,用來解釋藏象系統的說理工具也越來越多,藏象系統的歸屬注定是一個不斷爭論、不斷更新的命題。
脾藏象系統是以脾藏為核心,圍繞生理功能、特性及其與形、體、官、竅、志、液、味、時、經絡等各部密切聯動的一個整體系統,是人體的后天之本,為生命活動提供物質能量。限于中西醫迥異的理論框架和思維模式,筆者以中西醫臟腑理論的共同始基——解剖實體為出發點,將中西醫臟器的主干功能進行匹配,不對其后根據哲學思想延伸出的枝節進行強行總結。當脾藏象歸位于Pancreas 后,隨即出現Spleen 的對應空缺。筆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詳細論證,肝藏象的核心功能與Spleen 相合。如此,對應錯位的中西醫五臟便形成了閉環。不可否認的是,即使前人對脾藏象的研究存在誤解和差錯,但斷不可認為其對中西醫之脾的發展毫無貢獻,反而是推動脾之理論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在現代醫學發展成熟的今天,學界對脾藏象的解讀仍無定論,“脾藏象為脾和胰”“脾藏象為脾和肝”等觀點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筆者始終相信,中西醫學的正確接軌,既有助于傳承古訓,守正創新,又有助于指導相關疾病的診療。本文僅是拋磚引玉,希望能為中醫脾藏象的研究發展盡一份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