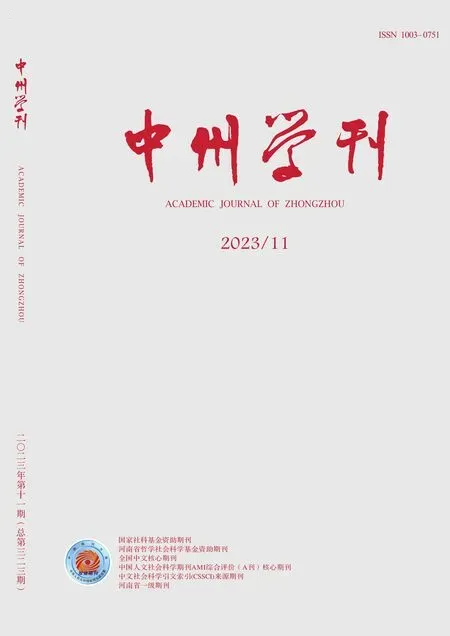道家與名家形而上學的歷史糾葛及其影響和意義
高華平
《周易·系辭上》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現代中外學者論中國哲學之形而上學,皆常以《周易》和道家(特別是《老子》)為例。黑格爾盡管對中國哲學存在偏見和誤解,認為在整體上“中國不存在純粹思辨的哲學”,但仍然認為《周易》的“太極”說和道家的《老子》的“道”論多少有一些接近于形而上學的地方。黑格爾說:“中國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范疇。古代的《易經》是論原則的書,是這類思想的基礎。”又說:“據雷繆薩說,‘道’在中文是‘道路,從一處到另一處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體、原理的意思。綜合這點在比喻的形而上的意義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進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與基礎。”[1]自魏晉玄學以來,中國學術界討論哲學的形而上學或本體論,也常以“太極”和“道”相比附。但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除了《周易》和道家的形而上學之外,還存在另一種形而上學,即名家(包括“墨辯”學者)的形而上學。《周易》和道家《老子》的形而上學,是一種以儒、道、“道法家”為代表的“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①,也是中國哲學中一種占主流地位的形而上學。名家(包括“墨辯”學者)的形而上學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純粹的形而上學。研究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無論就其內部各家各派比較,還是進行中西哲學比較,將以道家《老子》為代表的“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和以名家為代表的純粹形而上學比較,都是最好的選擇。
一、道家的形而上學:“道”

也因此,在中國哲學中,唯一一個與道家之形而上學的“道”(“天道”)相對的概念(詞),很顯然不是“太極”,而是“名”,又稱“常(恒)名”。稱“太極”為中國哲學中與“道”(“天道”)相對的本體論概念(形而上學),是儒家學者和魏晉玄學家提出的看法。“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二、道家之“道”與名家之“名”的比較
“道”即“天道”。關于“道”或“天道”的特點,學術討論實繁。1940年金岳霖先生完成的《論道》和20世紀80年代末期張立文先生的《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對此都有最全面和深入細致的分析和考察。而從形而上學的角度來看,則可以說道家《老子》的形而上學是“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而先秦名家的形而上學則是一種純粹的形而上學。老子的“道”即是“天道”,是“常(恒)道”,無形無名,先天先地,神鬼神帝,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和本根。《老子》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但這卻并非《老子》“道”或“天道”的全部。《老子》第二十一章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十四章又說:“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可見,《老子》的“道”(“天道”“常道”“恒道”)又并非絕對的抽象者,并非純粹的“理念”,故現代新儒家多稱其為“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
名家沒有專門的“道論”,甚至也沒有專門對“名”的形而上學論述,但由其相關概念、命題卻似不難看出。“墨辯”學者的《墨經》中的《經上》和《經說上》曾討論具體的“名”(形式邏輯上的“概念”)。《經上》曰:“名:達、類、私。”《經說上》曰:“名,物,達也。有實必待之名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必止于是實也。”即將“名”(概念)分為最高的類概念、一般的類概念和個別事物的概念③。但從名家最著名的“白馬非馬”等命題來看,名家對“名”的分類實如道家老子一樣,也是將“名”分為一般形式邏輯所說的“名”和形而上學的所謂“常名”(“恒名”)的。
名家的“白馬非馬”命題,學術界一般皆從形式邏輯上“白馬”概念與“馬”概念內涵外延的不同來理解。這種理解雖然正確,卻存在明顯局限,至少沒有看到道家《老子》對“名”的分類的意義,因此也就沒有看到名家之“名”的形而上學意義。實際上,名家公孫龍等人“白馬非馬”命題中,“馬”已不再是形式邏輯上的“一般的類概念”(類),甚至也不是“最高的類概念”(“達”,即物,動物),而是《老子》所說的“常名(恒名)”。“白馬非馬”,即是“名可名,非常(恒)名”。所以,“白馬非馬”命題實際上包含有三種“馬”:一是絕對抽象的不可“名”的“常(恒)名”的“馬”,二是作為形式邏輯上為“一般的類概念”甚至“最高的類概念”的“馬”,三是作為“個別事物的概念”的“白馬”。這三者之間正如柏拉圖所說三張床或三張桌子的關系。柏拉圖認為,世界上有三張床或三張桌子:一張是畫家畫的,一張是現實的,一張是概念上的床或桌子。畫家畫的床或桌子是模仿現實的床或桌子,最不可靠;其次是現實的床或桌子,既不完善也不能永久保存,所以也不可靠;最可靠的是概念的床或桌子,作為概念永久存在,是“純粹理性”或“絕對理念”[3]。對名家的“白馬非馬”命題,我們也應作如是觀,發現其中純粹形而上學的意蘊。
三、道家和名家形而上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演變與影響
中國哲學史上,先秦諸子中道家和名家的兩種形而上學產生的具體時間如何、誰先誰后,沒有文獻可征,殊難論定。然依理而論,道家“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即為其“道”(“天道”)論,“道”絕對超越而又不離“象”“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還不是黑格爾所說的“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范疇”,故其產生應早于名家作為“純粹的理性”或“絕對理念”的形而上學。但至少從老子開始,中國哲學已探索這兩種形而上學的交流和融合。《老子》第一章所謂“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將“常(恒)道”與“常(恒)名”等量齊觀,即可見其用意。
先秦時期對道家和名家的兩種形而上學進行整合的努力,一直不斷。儒家《易·系辭上》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把形而上的本體與形而下的陰陽二氣、本體論與宇宙生成論聯系起來,建構戰國儒者的形而上學。《莊子·大宗師》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這里,莊子認為“道”雖“無為無形”,“在太極之先”,“先天地生”,十分神秘,但卻“可傳”“可得”,即在形上形下之間——此可謂莊子對道家和名家兩種形而上學的整合。
當然,戰國時期系統地對道家和名家的兩種形而上學進行整合的,當數稷下黃老學者。他們以“道”為世界的本體和本源,以“法”為中介,對道家和名家的兩種形而上學進行整合,并形成了兩種整合的思路和兩個重要的學派:一個是以《管子》學派為代表的“道法家”或“法道家”,另一個是以惠施、尹文為代表的“名法”學派。
“道法家”或“法道家”對“道”的形而上學論述最大的特征,就是將“道”與“法”聯系起來,以“道生法”(《黃帝四經·經法》)的命題既確立了“道”的現實社會“法”的形上根據地位,反過來又借助現實社會“法”的權威保證了“道”的這種形上根據地位。接著,他們還進一步依《易傳》的思路,更明確地將“道”之“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精”“信”,具體化為“氣”及其屬性。《管子·內業》曰:“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谷,上為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圣人。是故民(名)氣,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淵,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由此真正完成了先秦儒家《易·系辭上》開創的將形而上的本體與形而下的元氣、本體論與宇宙生成論的結合,以更多地討論形下的社會政治哲學——在“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路上走得更遠了。
以惠施、尹文為代表的“名法”學派,在“道生法”的原則下,將“名”“法”等同,把《老子》“道可道,非常(恒)道;名可名,非常(恒)名”中的“常(恒)名”完全取消了,因而也就同時將名家原有的純粹形而上學完全取消了。《尹文子·大道上》曰:“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大道不稱,眾有必名。”又曰“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云云,以為“名”即是“法”,“法”即是“名”,“正名”即是“定法”。這就以“道法家”或“法道家”的“法哲學”取代了名家原有的純粹形而上學。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惠施、尹文為代表的名家“名法”學派已徹底拋棄了名家原有的純粹形而上學,完成一次本學派在形而上學上的自我革命。
兩漢時期中國哲學對道家和名家的兩種形而上學的整合,儒家主要沿襲著《易傳》的思路,而道家則基本繼承了稷下黃老學派的傳統。
魏晉玄學在哲學思想上整體體現為兼綜儒道、調和“名教”與“自然”的特色。但在形而上學上則主要是對先秦道家和名家的兩種形而上學進行重新整合。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貴無”派,以“無”代“道”,“以為天地萬物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列子·天瑞》引何晏《道論》云:“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王弼《論語釋疑》曰:“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老子指略例》曰:“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這樣,何、王二人雖然有時也仍然使用“道”這一概念,但卻以“負的方法”,徹底地抽空老莊“道”論中任何“可傳”“可得”和“可體”的成分,使之變成了“純無”——以名家的純粹的形而上學取代了道家的“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何晏認為“圣人無情”,嵇康主張“聲無哀樂”,都是這種形而上學思想的體現。以向秀、郭象為代表的“儒道合派”則持“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自然矣”的“獨化論”,雖表面上對當時本體論上“貴無”和“崇有”兩派,包括對先秦道家“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和名家的純粹形而上學都予以了否定,但實際則因為當時思想界普遍流行“浩浩太素,陽曜陰凝”(嵇康《太師箴》)、“元氣陶鑠,眾生稟焉”(嵇康《明膽論》)的“元氣”說,故“儒道合派”實際上只是加強了道家“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
而到了宋明理學時期,理學家借佛、道二教的心性學說,繼承了儒家原有的以《易》《庸》聯結形上、形下而整合道家和名家兩種形而上學的思路,以“天命之謂性”、性靜情動、心統性情的本體論,建構起理學“道德的形而上學”。但從本質上來說,因為理學家“道德的形而上學”所追求的最高目標乃是人的道德心性與“天道”合一,即所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故可以說理學“道德的形而上學”,乃是一種真正的“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從此以后,以“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范疇”為特征的名家的純粹形而上學就被完全淘汰,放逐出了中國哲學形而上學的領地,“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則確立了它在中國哲學中獨領風騷的歷史地位。而也正是這種“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影響和形塑了中國哲學和中國人的文化性格。
四、道家和名家形而上學的文化價值及產生的歷史根源
中國哲學史上以道家《老子》為代表的“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和以名家為代表的純粹形而上學,是兩種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形而上學。而這兩種形而上學從一開始就處于互相糾葛和交融的歷史語境之中,并最終形成了“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主導地位。可以說,以道家《老子》為代表的“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和以名家為代表的純粹形而上學,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和人類的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地位和價值。道家“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代表了中國哲學和中華民族獨特的思想文化特征,也形塑了中國哲學和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性格。名家純粹的形而上學,則顯示中國哲學和中國思想文化中也存在“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范疇”,代表了中國哲學和中國人的思想文化與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的某些共同之處,為中西哲學和文化的對話、交融、接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和結合點。
歷史地看,中國哲學之所以會形成以道家《老子》為代表的“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和以名家為代表的純粹形而上學,與中華民族在中國五千年以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中的多元互動密切相關。中國有五千年以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而根據歷史和考古學者的研究,早在仰韶文化時期,作為中華民族的主體炎帝、黃帝和東夷等大的氏族或部落群體已經基本形成,而作為后來華夏族主體的炎、黃二族原本居住在今天的陜西境內,后來黃帝族的一支“跟著中條山與太行山逐漸向東北走”,“炎帝氏族也有一部分向東遷移,他們的路途大約順渭水東下,再順黃河南岸向東”[4]。最后他們在今冀、魯、豫三省交界處這一屬于大汶口文化的區域,與東夷族相遇了——由此拉開了中華民族各族群之間互相沖突和融合的序幕。“大汶口文化的絕對年代,據碳14測定,距今6100—4600左右”;“就目前已公布的資料來看……在大汶口文化時期,有一支勢力強大居民由東向西、向南,直到今天的洛陽和信陽地區遷居”[5]。而在“大約從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中華民族早期的“民族文化區域”已基本成形,“一些考古學文化往往可以同古史傳說中的族系相照應”。
龍山文化分布于黃河下游山東和蘇北一帶,當是東夷的史前文化;黃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陜西等地分布著“中原龍山文化”,它本身又包含后崗二期文化、造律臺類型、王灣三期文化、陶寺類型和客省莊二期文化等,應是諸夏的史前文化;長江中游在屈家嶺之后是石家河文化,應當是苗蠻各族的史前文化;長江下游杭州灣一帶是良渚文化,它可能是古越人史前文化的一支。[6]
而根據筆者的最新研究,自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以來的“諸子出于王官”說,其中的所謂“王官”,在上古三代實際就是一些氏族、部落或方國(酋邦)及其首領或酋長的名字。如“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的“史官”,即是東夷族顓頊氏氏族、部落及其首領或酋長。《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敘傳》均將“史官”的源頭追溯到了顓頊氏的重、黎(重黎)二“子”。《史記·太史公自序》曰:
昔在顓頊,令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后,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這也就是說,道家哲學“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以自持”(《漢書·藝文志》)的特點,與其說是源于上古“史官”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報任安書》)的思想文化追求,還不如說它更深遠的源頭乃在于上古三代悠久的顓頊氏特別是其中重、黎(重黎)二系的歷史文化之中。
同樣,《漢書·藝文志》曰:“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而由《尚書·堯(舜)典》及《史記·五帝本紀》等文獻記載,現今可知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禮官”,是堯舜時代擔任“秩宗”的共工氏的伯夷——亦是出于共工氏氏族、部落或方國(酋邦)及其首領或酋長。而根據《國語·鄭語》“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之說,又可知伯夷屬于炎帝族,為其中共工氏一族的成員。《漢書·藝文志》在“序”“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之后,接著又“序”名家之學的特點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禮記·樂記》區別二者的特點為“樂合同,禮別異”——長于細致深入地分析事物,以求尋找其中的細微差別,即所謂“鉤析亂而已矣”(與今所謂“純粹形而上學”近似)。所以,我們似也可以仿照上文言道家實源于上古三代悠久的顓頊氏特別是其中重、黎(重黎)二系的歷史文化之論,同樣說名家與其說是源于上古三代“禮官”對“禮數”的考究,不如說它更深遠的源頭乃在于上古三代悠久的炎帝族特別是其中共工氏一系的歷史文化性格。
而根據《尚書》《史記》等文獻記載,先秦諸子中儒家、陰陽家、法家所從“出”的“司徒之官”“羲和之官”“理官”等,也與道家所源出的“史官”一樣,亦同出于東夷族的顓頊氏一系;而《漢書·藝文志》所謂“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的“清廟之守”,實際應該是“司空之官”——出于炎帝共工氏之中的“垂”(又作“倕”,即“工倕”“巧倕”)胞族或子部落④。但《史記》《山海經》等上古典籍同時又記載說,上古傳說時代的華夏炎黃二族與東夷族各氏族和部落間還存在著廣泛的婚姻和血緣關系,已走向了早期華夏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因此先秦諸子中儒家、陰陽家、法家所從“出”的“司徒之官”“羲和之官”“理官”等,也與道家所源出的“史官”一樣,亦同出于東夷族的顓頊氏一系,在思維方式上具有驚人的一致性,都顯示為一種“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而墨家和名家的思維方式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表現為一種純粹的形而上學的特征——由此也引發了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關于先秦諸子關系中是墨家源于名家還是名家源于墨家的爭論。但炎帝族共工氏由于與帝顓頊一系有著長期的婚姻和血親的交融關系,故此二族裔在思維方式和思想文化上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和互相交融。黃帝很早即“作”冠冕禮樂、推迎日、祭祀封禪(《世本·作篇》),這些亦皆被名家吸收到他們制定的禮儀制度之中;顓頊氏東夷族的最大特點是“夷俗仁”,而儒家之“禮”的根本精神亦在于“仁”,這顯然更多的應該是吸取了東夷族顓頊氏文化的養分;而由炎帝族共工氏“禮”文化演變而來的先秦諸子名家思想,又與儒家的“禮“和法家的“刑”合流為刑名禮法之學,成為戰國中后期中國學術思想的一個重要時代特點。源于東夷族的顓頊氏一系的道家“史官”和陰陽家“羲和之官”,則因其在與炎帝族共工氏的融合中深刻洞悉到各種禮儀制度的本質,而走向了對“恒名”或“天道”的追求以及對世俗社會之“名”或“禮義”的批判。老子貴“無名”,以為“名可名,非常(恒)名”,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老子》第三十八章)莊子也認為“圣人無名”(《莊子·逍遙游》);“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莊子·天道》);仁、義、禮、智,“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莊子·駢拇》)。因為“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而道家的史官及陰陽家的“羲和之官”,皆屬于東夷族顓頊氏的重、黎(重黎)之后,故其深諳陰陽消息之“天道”,以為“人道”之仁、義、禮、智,實皆源于自然之“天道”,故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向最高的“禮義”本源回歸。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似可以說,先秦諸子中以道家為代表的“境界形態的形而上學”和以名家為代表的純粹形而上學的矛盾與差別,也是上古三代炎帝族共工氏氏族或部落與東夷族顓頊氏氏族或部落在思維方式和思想文化上的差別與沖突。道家是一直強烈反對所謂“智巧”或技巧的,甚至提出要“絕圣棄智”“絕巧棄利”(《老子》第十九章)和“攦工倕之指”(《莊子·駢拇》)的主張,對源于炎帝族共工氏氏族或部落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文化特別是名家的分析智慧和墨家的技能工巧,采取一種近乎敵視的態度;而名家、墨家則對源出于東夷族顓頊氏氏族或部落的道家、儒家之將“死生存亡、窮達富貴”等社會現象皆視為“命之行也”(《論語·顏淵》《莊子·德充符》)的言行[7],予以明確的“非”之(《孔叢子·公孫龍》《墨子·非命》《墨子·非儒》)。上古傳說時代中華民族中炎黃二族與東夷族各氏族和部落的長期沖突和融合,最終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了既“道術分裂”,彼此“爭鳴”,又互相借鑒和交融的諸子百家之學;而名家、墨家的形而上學與道家、儒家及法家等不同學派之間形而上學上的歷史糾結,實際也是上古傳說時代以來中華民族各成員間文化基因的一種延續。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