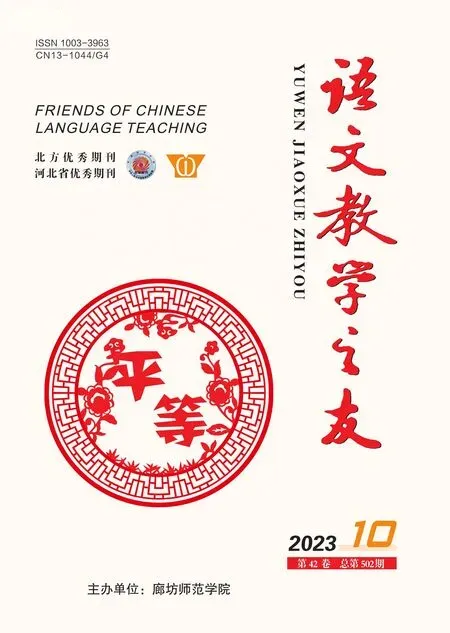基于陶潛隱逸思想創(chuàng)設(shè)《歸園田居(其一)》教學(xué)內(nèi)容
◎內(nèi)蒙古/李冬捷 于東新
當(dāng)前,部分中學(xué)關(guān)于陶淵明的詩文教學(xué)存在模式化、扁平化的問題,甚至有的還歪曲陶淵明,放大了其所謂的“消極”色彩,部分語文教師教學(xué)水平有待提升。筆者以為,陶淵明詩文教學(xué)“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要,即在課堂教學(xué)中教師要引領(lǐng)學(xué)生準(zhǔn)確而深入地理解陶淵明的思想、人格、詩藝,才能落實(shí)教育教學(xué)的目標(biāo),提高教學(xué)水平。那么,如何優(yōu)化陶淵明詩文教學(xué)的內(nèi)容?筆者以為可將“陶學(xué)”研究成果引入課堂,使之成為深入解讀陶淵明詩文的教學(xué)資源。擬以學(xué)界“陶氏隱逸思想”研究成果為抓手,嘗試創(chuàng)設(shè)陶氏詩文教學(xué)的內(nèi)容,以此提高教學(xué)質(zhì)量,落實(shí)語文學(xué)科核心素養(yǎng)的目標(biāo)。
一、陶淵明隱逸思想的內(nèi)涵
陶淵明作為古代隱逸士人的代表,他并未原封繼承傳統(tǒng)的隱逸觀念,他有自己的思考,他是“保全自我的個(gè)性獨(dú)立與精神自由,是醉心田園回歸自然的真隱”。關(guān)于其具體的隱逸思想內(nèi)涵,“陶學(xué)”界認(rèn)為主要有如下內(nèi)容:
(一)隱逸是對(duì)儒家“義”和道家“真”的實(shí)踐
陶淵明的隱逸思想不僅繼承了道家回歸自然養(yǎng)真、摒棄世俗的思想,還踐行了儒家“窮則獨(dú)善其身”的隱逸主張。他向往道家“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因而他從單純的隱居生活獲得了精神的愉悅。同時(shí)他也認(rèn)為君子的仕和隱都是對(duì)“道”的捍衛(wèi),認(rèn)為隱士是士人在“邦無道”時(shí)宣揚(yáng)“道”的重要途徑。因而儒家的“義”和道家的“真”成為陶淵明隱逸思想的基本內(nèi)容。還有學(xué)者指出:“陶淵明是融合了‘道家目的式適性之隱’和‘儒家的手段式的待時(shí)之隱’,具有陶氏的隱逸思想面貌。”可見其隱逸思想是基于儒、道兩家的合理成分,經(jīng)過陶淵明自我革新和創(chuàng)造,是他為什么要?dú)w隱、為什么堅(jiān)持躬耕的行為依據(jù)。隱逸是其踐行儒家的“義”和道家的“真”的生動(dòng)實(shí)踐,也是陶淵明捍衛(wèi)人格自由和尊嚴(yán)的路徑。
(二)躬耕是陶淵明隱逸思想的獨(dú)特內(nèi)容
“躬耕”是陶淵明隱逸思想最重要的內(nèi)容。歷史上的眾多隱者往往隱居在優(yōu)美的山水間,并不是樸素的鄉(xiāng)村田園。其生活是休閑雅致的,吟詠風(fēng)月,品詩論文,不需去田間勞作,自有傭人代耕。然而陶淵明卻和他們不同,這也是其隱逸思想最獨(dú)特的內(nèi)容。陶淵明他生活在淳樸的鄉(xiāng)村,親自下田耕耘、播種、收獲,正如他詩中所描繪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并且最讓他感到滿足的是在勞動(dòng)中獲得快樂,“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所以梁?jiǎn)⒊耪f:“陶淵明的快樂并不是來源于安逸,而完全是勤勞所得。”關(guān)于陶淵明堅(jiān)持躬耕的艱苦實(shí)踐,有學(xué)者指出:“陶淵明的農(nóng)業(yè)勞作在當(dāng)時(shí)的經(jīng)濟(jì)生活中意義并不大,其重要性是陶淵明自我內(nèi)心的一種堅(jiān)定的信念。”這種信念使陶淵明的隱逸思想迥異于眾人,獨(dú)具特色。其表面上是逍遙于田園間,追求身心自由,其實(shí)質(zhì)卻是體現(xiàn)儒家“不食嗟來之食”的硬氣,目的是捍衛(wèi)自我人格精神。
(三)隱逸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桃花源
陶淵明并不是一個(gè)利己的隱士,他關(guān)心民瘼,將自己的躬耕思想推而廣之,思考什么樣的社會(huì)模式才是理想的社會(huì)模式,他的答案就是人人躬耕,于是桃源社會(huì)圖景就在他心中形成了。所謂桃源社會(huì)模式,即“相命肆農(nóng)耕”,人人自食其力;“秋熟靡王稅”,沒有等級(jí)和剝削。這顯然是詩人長期勞作思考的智慧結(jié)晶。清人邱嘉穂對(duì)此給予肯定:“設(shè)想甚奇,直于污濁世界中另辟天地,使人神游于黃、農(nóng)之代。公蓋厭塵網(wǎng)而慕淳風(fēng),故嘗自命為無懷,葛天之民,而此記即其寄托之意。”陶淵明以淳樸、和諧的桃源社會(huì)同當(dāng)時(shí)混亂、污濁的現(xiàn)實(shí)相對(duì)比,以此來否定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不合理性。這足以說明詩人不是一個(gè)獨(dú)善其身的隱士。高建新為此解讀說:“陶淵明辭官歸隱田園并不是消極的避世,而是另一種人生積極奮進(jìn)的形式。”學(xué)界的這些研究對(duì)于學(xué)生把握陶淵明的處世態(tài)度、人格精神都是具有啟發(fā)價(jià)值的。
二、基于陶氏隱逸思想教學(xué)內(nèi)容的整合
基于陶學(xué)界對(duì)于陶淵明隱逸思想的深入研究,教師在思考如何講好陶氏詩文作品時(shí),就應(yīng)該著力講清其隱逸思想的內(nèi)涵,讓學(xué)生真正明白陶淵明是一個(gè)什么樣的隱士,進(jìn)而傳遞一種積極的精神能量。擬以《歸園田居(其一)》為例:
開頭四句: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wǎng)中,一去三十年。
這四句寫了詩人辭官的根本原因。詩人說,自己本性質(zhì)樸自然,從小就對(duì)世俗社會(huì)追逐名利的價(jià)值觀不感興趣,大自然才符合其天性追求。于是在“塵網(wǎng)”前冠以一個(gè)“誤”字,重點(diǎn)申明其志不在官場(chǎng),而是一不小心才落入其中的,因而深表悔恨。教學(xué)中,教師要帶領(lǐng)學(xué)生重點(diǎn)領(lǐng)會(huì)“俗”“韻”“性”“塵網(wǎng)”等詞的含義,以此總結(jié)陶淵明“隱逸”的內(nèi)涵,即詩人摒棄污濁的官場(chǎng),在田園中堅(jiān)貞自守,捍衛(wèi)自我人格尊嚴(yán)。莫礪鋒解讀說:“陶淵明的歸隱不是被動(dòng)遠(yuǎn)離塵世,更不是放棄,而是一種特殊形態(tài)的堅(jiān)守和斗爭(zhēng)。”可見陶淵明的歸隱是捍衛(wèi)人格的途徑。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學(xué)生可通過文下注釋了解“羈鳥”是指籠中的鳥,“池魚”是失去自由的魚。然后教師提問:“詩句采用了什么修辭手法?其思想內(nèi)涵是什么?”詩人以比喻的手法描繪了自己入仕過程中喪失自由的苦況,官場(chǎng)帶給他的是壓抑、束縛。接下來“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讓學(xué)生思考“守拙”的深層含義,以確立守拙“是穎悟后靈魂的追求,是質(zhì)性自然的堅(jiān)守”的結(jié)論。可以說,這兩句詩展現(xiàn)了詩人在擺脫世俗羈絆后,把躬耕看作是自己“守拙”的途徑,他表面上逍遙于田園間,身心自由,實(shí)際卻顯出儒家“不食嗟來之食”的硬氣,本質(zhì)是捍衛(wèi)自我人格精神。躬耕不僅解決了衣食問題,而且詩人還獲得了精神的滿足和愉悅。
有學(xué)者指出:“陶淵明的隱逸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切實(shí)自然人生,他不是給別人看的而是為了自己,因而隱逸成就了自己。”確實(shí),陶淵明與其他隱者有著明顯的不同,他將隱逸思想付諸實(shí)踐,以其整個(gè)人生來探索隱逸的真諦。戴建業(yè)說:“農(nóng)民也種田,但農(nóng)民的耕作是對(duì)命運(yùn)的被動(dòng)接受,而陶淵明的躬耕行為則是對(duì)實(shí)現(xiàn)自我生命存在方式的主動(dòng)選擇,體現(xiàn)了他對(duì)人生、生命價(jià)值的哲學(xué)思考。”作為識(shí)字的田夫,陶淵明主動(dòng)遠(yuǎn)離世俗的紛擾,自食其力,“晨出肆微勤,日入負(fù)耒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享受著隱逸所帶來的自由和愉悅。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詩人通過“草屋”“桃李”“炊煙”“雞狗”等典型的意象勾勒出一幅生機(jī)盎然的鄉(xiāng)村景象。這時(shí)可讓學(xué)生復(fù)習(xí)舊知:“這幾句詩描寫的景象是否似曾相識(shí)?”這幾句詩其實(shí)是《桃花源記》的翻版。這是陶淵明隱逸思想升華的體現(xiàn),他在躬耕之時(shí)一直思索著、探尋著,希望找到一種適合百姓生存的理想社會(huì)。鄭振鐸對(duì)此高評(píng)曰:“陶淵明不僅是一位田園詩人,更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陶淵明深感戰(zhàn)亂給民眾所帶來的痛楚,即使百姓辛勤勞作也不能求得溫飽,所以他通過虛構(gòu)的形式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富于理想主義色彩的世外桃源。足見其是擁有社會(huì)責(zé)任感的。即使遠(yuǎn)離官場(chǎng)也心系民生,以艱苦的躬耕實(shí)踐為處在水深火熱的民眾探尋合理的社會(huì)模式。這是其隱逸思想最閃光的地方。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
教師提問:“‘無塵雜’是什么意思?”師生探討的結(jié)果是:它一方面是指居所的干凈整潔,另一方面指詩人不被俗事打擾,心里沒有塵雜。“虛室”又是何意?表面是說安靜的居室,實(shí)際是指詩人心境的恬淡嫻靜。“久在樊籠里,復(fù)得返自然”,和前文“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相呼應(yīng),表達(dá)了詩人以往身在仕途,被禁錮在“塵網(wǎng)”之中,如今終于回歸了自然自由的生活,一種愉悅之情自然流出。這里,教師引領(lǐng)學(xué)生總結(jié)“自然”的含義,可聯(lián)系學(xué)界關(guān)于陶淵明“自然”哲學(xué)思想的研究成果,即陶淵明哲學(xué)思想的生命境界是“養(yǎng)真”,詩人與自然合一保持純真本性。在陶淵明看來置身于官場(chǎng),于人“與物多忤”,于己“感平生愧”,在滾滾紅塵之中必定迷失自我,只有遠(yuǎn)離官場(chǎng),斷絕世俗的“非我”,才能保全自我性命的本真,捍衛(wèi)人格的完整。可見,“陶淵明的歸隱并不是意氣用事,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其生性率真,絕不忤逆本心的人生態(tài)度是他的歸隱動(dòng)力。”所以詩人“性本愛丘山”、愛自然,自然是他捍衛(wèi)人格,保持真性的唯一路徑。而這又如何才能實(shí)現(xiàn)?那就是歸田隱逸。
總之,教師可以陶淵明隱逸思想研究為抓手,創(chuàng)設(shè)《歸園田居(其一)》的教學(xué)內(nèi)容,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這是改變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的創(chuàng)新教學(xué)模式,這是一次提高教學(xué)水平的有益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