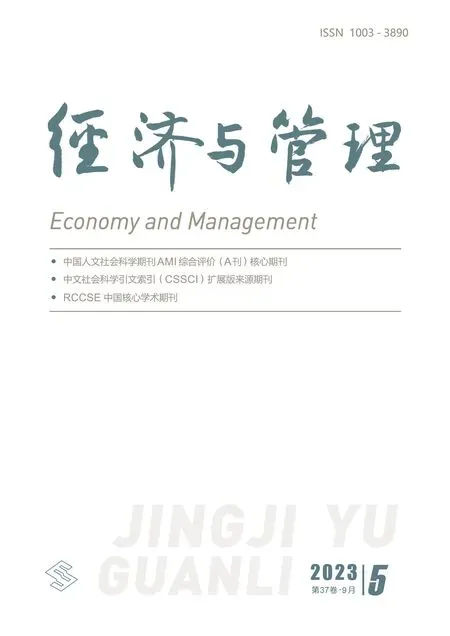醫療保險制度果真“益富”嗎
——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證據
楊 融 ,張永峰 ,路 瑤
(1.南京大學 經濟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2.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000)
醫療保險制度有利于窮人還是有益于富人,不僅攸關社會和諧穩定,還關乎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戰略的有序推進。進入21 世紀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醫療保險制度建設,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作出“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安全規范、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的戰略部署。相關數據顯示,1998 年我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為509.6 萬人,醫保基金總支出15.6 億元。到2020 年,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增長到13.6 億人,參保覆蓋率穩定在95%以上,同時醫保基金總支出達2.1 萬億元,與1998年相比增長1 345 倍。此外,作為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重要補充,商業醫療保險在中國發展迅速。2000—2013 年全國商業醫療保險總保費增長了近40 倍[1],而在2013 年后,保費收入年均增長幅度更是接近50%[2]。在社會醫療保險覆蓋率、醫保基金支出逐年提高和商業醫療保險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研究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是否實現了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目標,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何差異,不同年份醫療保險制度實施效果動態變化趨勢如何,社會醫療保險內部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再分配效應有何異同,對正確認識醫療保險制度的真實作用,優化醫療保險制度安排,解決中國醫療保險發展不平衡以及推進健康中國戰略和共同富裕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作為降低居民就醫負擔,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制度安排,對醫療保險制度實施效果的研究歷來都是學界的熱點話題。盡管醫療保險制度設計的初衷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服務可及性以推進健康平等從而縮小社會收入不平等,但已有的研究大多認為醫療保險制度并不“親貧”,反而存在明顯的“益富”效應,即醫療保險制度并非有利于窮人,而是更有益于富人。在美國、澳大利亞、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大部分都存在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現象,與窮人相比,富人更多地享受了醫療資源。但不同國家的醫療不公平程度存在差異,提供私人保險或私人醫療服務的國家醫療保險的“益富”效應更加顯著[3-4]。此外,Lee et al.[5]針對中國臺灣地區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公平的關聯性的研究發現,健康不公平40%~73%的因素在于收入水平差異。事實上,醫療保險制度不僅加大了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收入不平等,在發展中國家同樣表現出“益富”效應。Castro-Leal et al.[6]對非洲國家公共醫療受益分布的研究表明,富人在國家公共醫療補貼中受益遠大于窮人。由于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繳納的保險費和預期收益顯著不一致,因而中國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存在逆向調節作用[7]。就商業醫療保險來看,Dor et al.[8]使用美國健康和退休調查數據,在處理內生性問題后發現,商業健康保險能夠顯著提高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Banthin et al.[9]基于美國1996 年和2003 年醫療支出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擁有雇主醫療保險的群體發生醫療負擔的比例遠遠低于公共醫療保險或者無保險者。此外,與擁有公共醫療保險和沒有醫療保險的人相比,擁有私人醫療保險的人經濟負擔顯著降低[10]。
國內學者對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效果同樣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且研究結果與國外學者類似,即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并沒有起到調節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11-17]。同時,國內學者對醫療保險制度實施效果的研究還有一個特點:其研究多以某個省份為代表。如李亞青[18]基于廣東兩市的數據研究發現,高收入群體在職工醫保中的受益程度遠大于低收入群體。金雙華等[19]以陜西為樣本研究發現,總體上醫療保險制度不但沒有發揮調節收入再分配的積極作用,反過來出現了窮人補貼富人的逆向調節作用。李扶搖等[20]基于京津冀地區的研究結果表明現行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此外,王延中等[13]、金雙華等[17]分別利用2012 年和2013 年的微觀數據測算了中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效果,他們的研究表明收入更高的居民所獲得的醫保報銷額顯著高于收入更低的居民。此外,在目前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體系的保障水平有限的情況下,作為個體自發選擇的補充保險,商業健康保險在分散疾病經濟風險并緩解因病致貧中表現出的積極作用正逐步顯現[21]。盡管商業醫療保險能夠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健康人力資本,但在稀釋收入差距中,商業醫療保險更有可能促進城鎮居民對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可能性和投資份額,在農村居民中并不存在這種作用[22]。在醫療保險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中,與基本醫療保險組相比,只有多重醫療保險組能夠顯著提高農村居民家庭風險金融資產持有,商業健康保險組和補充醫療保險組在促進農村居民家庭風險金融資產持有方面沒有顯著差異[23]。這就是說,不論是社會醫療保險,還是商業醫療保險,均表現出更加有利于高收入群體的“益富”效應。
盡管國內外學者對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討,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但仍然存在改進空間。首先,既有的研究過多集中于社會醫療保險,忽視了商業醫療保險。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商業醫療保險在生活中日益普及,成為社會醫療保險的重要補充,對商業醫療保險的研究顯得越來越有必要。有鑒于此,本文同時測算了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對現有文獻進行了有益的補充。其次,大多文獻僅僅集中于某一個地區或者某一年份數據,使得其研究結論既不能客觀反映中國整體現象,又不能有效反映醫療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動態變化趨勢。事實上,中國醫療保險制度盡管起步較晚,但推進迅速,不同年份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效果可能存在巨大差異。因此,研究不同年份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可以更加深刻明晰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動態實施效果。最后,與既有文獻大多僅用基尼系數來衡量居民收入差距不同,本文同時采用受中等收入水平群體變化影響更敏感的基尼系數和對上層收入水平和底層收入水平變化相對更加敏感的泰爾指數作為收入不平等的代理變量進行了實證檢驗,從而使估計結果更加嚴謹客觀。
二、分析框架
一方面,不同收入群體在醫療保險中獲得的醫保報銷額將直接影響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事實上,隨著黨中央對低收入群體的醫療保險問題的日益重視,醫療保險政策重點逐步向低收入群體傾斜。2017 年出臺的《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提出完成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整合,有效改善了城鄉醫療保險發展不平衡的困境。2021 年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健全重特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的意見》進一步減輕了低收入群體的醫療費用負擔并有效抑制了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因此,盡管早期的研究表明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并沒有起到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正向再分配作用,但隨著醫療保險基金支出和參保人數的持續增加,社會醫療保險的受益群體開始向中等及中低和低收入居民轉變。正如李永友等[24]的研究表明,醫療保險覆蓋面的擴大和醫療服務保障能力的提高使最低收入分組成為新醫改后公共住院服務的最主要受益群體。而商業醫療保險以盈利為目的,并不具備公益性質,準入門檻相對較高,購買群體主要集中在中高及高收入群體之間。因此,相對低收入群體,中高及高收入群體在商業醫療保險中的受益程度可能更高。
另一方面,任何制度的再分配效應不論中介渠道和作用機制如何,最終均體現在對個人及家庭收入水平的影響上。也就是說,醫療保險制度通過影響不同收入群體收入水平進而間接作用于收入不平等。如果醫療保險對中等及以下收入群體的增收效應顯著大于其對中高及高收入居民,那么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有助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親貧”性質。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貨幣性收入之外,醫療保險制度同樣可以通過健康人力資本、城市融入感等非貨幣性收入影響收入差距。例如,作為最重要的人力資本,個體健康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獲得更高的貨幣性收入。潘杰等[25]利用2007—2010 年國務院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評估入戶調查數據研究發現,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可以有效提高參保居民的健康水平,尤其是對弱勢群體而言,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健康促進作用更加顯著。因而醫療保險制度實際有助于緩解由健康不平等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此外,作為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國家,中國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農業轉移人口。隨著農民工在城鎮居住、就業方面的壁壘逐漸消除,醫療保險制度對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改善作用越來越強[26]。
綜上,本文的醫療保險分配效應的分析框架如圖1 所示。

圖1 醫療保險分配效應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本文主要使用的是2017 年數據,但在測算醫療保險制度動態變化的同時使用了2013 年和2015 年數據。2017 年CHFS 涵蓋全國29 個省級行政區的355 個區縣,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借鑒王延中等[13]的設定,本文用最終年收入測算實施了醫療保險制度后的社會不平等指數,用最終年收入減去社會醫療保險報銷額后的收入測算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情形下的社會不平等指數。原因在于,如果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那么居民無法獲得社會醫療保險報銷帶來的收入。同理,本文用最終年收入減去商業醫療保險報銷額后的收入測算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的社會不平等指數。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主要有家庭收入、社會醫保報銷額、商業醫保報銷額以及主觀幸福感和醫療服務利用率。核心解釋變量為是否參加社會醫療保險和是否購買商業醫療保險。控制變量主要有個人特征控制變量、工作特征控制變量和家庭特征控制變量。其中:個人特征控制變量包括年齡、學歷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政治面貌,工作特征控制變量包括工作單位性質、工作年限、是否雇員、是否雇主、月工作天數。在以家庭為基本組成單元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家庭成員的醫保參與行為深受家庭成員的風險偏好、政治面貌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影響,居民的醫療保險決策往往家庭化。因此,本文進一步控制了樣本的家庭特征。家庭特征控制變量包括活期存款、負債規模、父親教育經歷、母親教育經歷、父親最高職務、母親最高職務。
表1 報告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本文將全體樣本按收入水平劃分為三等份,并依次定義為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從表1 可以看出:低收入群體收入均值為1.605,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均值分別為6.088 和21.604,三者之間收入差距較大。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社會醫療保險的均值分別為0.911,0.920 和0.930,大致相當;三者商業醫療保險的均值分別為0.020,0.039 和0.091,即高收入群體擁有商業醫療保險的概率顯著大于中等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

表1 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再分配效應測算
基尼系數是衡量收入差距最普遍的方法。不依賴于洛倫茲曲線的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如下:
式(1)中Δ 表示基尼平均差,且0≤Δ≤2u,u是收入均值。此外,yi是第i個個體的收入,|yj-yi|是任何一對收入樣本差的絕對值,n是樣本規模。在式(1)的基礎上可以定義基尼系數。
式(3)是不依賴洛倫茲曲線的基尼系數計算方法。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可以由未實施醫療保險制度情形下的基尼系數減去實施醫療保險制度后的基尼系數得到。
式(4)中,G表示未實施醫療保險制度情形下的基尼系數,G'表示實施醫療保險制度后的基尼系數。如果RDg>0,則醫療保險制度存在正向再分配效應,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具備“親貧”性質;相反,如果RDg<0,則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為負,存在“益富”的逆向調節作用。
由于基尼系數受中等收入水平群體變化的影響更大。有鑒于此,本文進一步測算了醫療保險制度實施前后的泰爾指數。與基尼系數不同,泰爾指數對上層收入水平和底層收入水平的變化相對更加敏感。泰爾指數的測算方法如下:
其中,yi是第i個個體的收入,ˉy是所有個體的平均收入。同理,用未實施醫療保險制度情形下的泰爾指數減去實施醫療保險制度后的泰爾指數即可得到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效果。
式(6)中,T表示未實施醫療保險制度情形下的泰爾指數,T'表示實施醫療保險制度后的泰爾指數。同理,如果RDt>0,則醫療保險制度性質為“親貧”,反之則為“益富”。
(三)模型設定
在影響機制檢驗上,本文采用簡單線性回歸。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式(7)用來檢驗醫療保險制度對居民收入和報銷額的影響。其中:inco是居民收入,ybbx是報銷額,soin代表社會醫療保險,buin表示商業醫療保險;X為控制變量,包括年齡、學歷程度、婚姻狀況、健康狀況、工作單位性質、政治面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負債規模等;ui為誤差項。
同時,在穩健性檢驗中,本文采用PSM 處理模型的樣本自選擇問題。PSM 測算出的ATT 值可以測度個體在干預狀態下的平均干預效應。在所有樣本中,每個樣本分別有參加社會醫療保險(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和未參加社會醫療保險(未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兩種狀態,每個樣本進行干預的效果如下:
假定Di=1 表示該樣本參加社會醫療保險(購買商業醫療保險),Di=0 則表示該樣本未參加社會醫療保險(未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同時Yi表示測試的結果,其等于:
如果ATT 值顯著大于0,那么可以認為參加醫療保險(購買商業醫療保險)的受益程度大于未參加醫療保險(未購買商業醫療保險)。相反,如果ATT 值顯著小于0,則未參加醫療保險(未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受益程度更大。
四、實證分析
(一)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
表2 報告了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其中:(1)列是最終收入的不平等系數,也就是實施了醫療保險制度后的收入不平等系數;(2)列是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制度情形下的收入不平等系數;(3)列是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制度情形下的收入不平等系數。

表2 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
從表2 可以看出:在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的情形下,基尼系數為0.597,比實施了醫療保險制度后的基尼系數的0.568 高5.10%;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情形下的基尼系數為0.567,低于實施了醫療保險制度后的基尼系數。即社會醫療保險實施后基尼系數有所下降,而商業醫療保險則提高了基尼系數。此外,實施了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后的泰爾指數同樣低于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的泰爾指數,但高于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的泰爾指數。因此,總體來看,社會醫療保險實際上具有正向再分配效應,起到了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的積極作用,具有“親貧”性質;但商業醫療保險則加劇了社會收入不平等,表現出逆向調節的“益富”效應。
圖2 反映了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以及實施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條件下的洛倫茲曲線。可以看出: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的洛倫茲曲線在實施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條件下洛倫茲曲線的右下方。這意味著社會醫療保險提高了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的洛倫茲曲線處于最終效果的洛倫茲曲線的上方,即商業醫療保險擴大了收入不平等。

圖2 醫療保險實施效果的洛倫茲曲線
(二)影響機制
1.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醫保報銷額的影響。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最先影響的是居民醫保報銷額,即通過影響醫保報銷額影響收入分配。因此,為了進一步理解社會醫療保險制度“親貧”性質和商業醫療保險“益富”效應的邏輯,本文檢驗了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醫保報銷的影響,檢驗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醫保報銷額的影響
從表3 可以看出:社會醫療保險對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報銷額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131,0.075 和-0.096,且其對高收入群體的邊際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社會醫療保險顯著提高了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群體的醫保報銷額,但對高收入群體的醫保報銷額并不存在顯著影響。在以商業醫療保險報銷額為被解釋變量的模型中,商業醫療保險對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報銷額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001,0.002 和0.007,其中商業醫療保險對低收入群體報銷額的邊際影響不顯著,且商業醫療保險對高收入群體報銷額的系數估計值遠大于中等收入群體。也就是說,商業醫療保險更有可能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的報銷額。因此,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親貧”性質和商業醫療保險的“益富”效應的一個形成原因在于,低收入群體在社會醫療保險中獲得的醫保報銷額遠大于高收入群體;相反,在商業醫療保險中,高收入群體獲得的醫保報銷額更多。
2.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影響。除了醫保報銷額外,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的另一個作用機制是通過影響居民收入進而影響居民收入差距。表4 為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收入的影響。

表4 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影響
表4 的估計結果表明:社會醫療保險對低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系數估計值為0.151,在1%水平下顯著,但對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系數估計值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也就是說,對低收入群體而言,參加社會醫療保險可以顯著提升其收入水平,但對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來說,參加社會醫療保險對其收入水平并不存在顯著影響。商業醫療保險對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系數估計值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對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198 和2.807,均在1%水平下顯著。即商業醫療保險對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正向影響顯著大于中等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由此表明,低收入群體在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中受益遠大于高收入群體,但高收入群體在商業醫療保險制度中的受益程度遠大于低收入群體。因此,從醫療保險制度對不同收入居民最終收入的影響來看:社會醫療保險對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顯著大于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由此縮小了居民收入差距,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再分配作用;商業醫療保險制度顯著提升了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的家庭收入,表現出明顯的“益富”效應。
(三)穩健性檢驗①
1.剔除極端值。樣本中的極端值會影響估計結果的可靠性。年齡高于80 歲的居民健康人力資本存量相對更低,超過18 歲但仍在上學的居民無法創造收入。因此,本文刪除了年齡大于80 歲的樣本和仍在上學的樣本并重新進行了檢驗。在剔除極端值后,估計結果仍然表明低收入居民在社會醫療保險中受益程度顯著大于高收入居民,而高收入居民在商業醫療保險中受益更多。
2.PSM 穩健性檢驗。由于是否參加醫療保險并非隨機行為,通常受工作單位性質、收入水平以及學歷程度等影響,因而具有明顯的自選擇問題。因此,本文進一步運用了近鄰匹配和卡尺匹配兩種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以解決基準回歸模型中的樣本自選擇問題。近鄰匹配和卡尺匹配中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ATT 值分別為3.476 和3.591,且在1%水平下顯著;而中等收入群體的ATT 為0.234,盡管大于低收入群體但小于高收入群體;近鄰匹配和卡尺匹配中高收入群體醫保報銷額的ATT 值同樣顯著大于中等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因此,PSM 檢驗同樣表明高收入群體在商業醫療保險中受益程度更高。
3.基于家庭債務的角度。債務與收入相對應。既然醫療保險能夠通過影響家庭收入進而作用于社會收入差距,那么反過來講,醫療保險應當可以緩解家庭債務進而影響社會收入差距。考慮到這一點,本文以家庭債務為被解釋變量,重新解釋了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家庭負債的邊際影響。社會醫療保險對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負債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421,-0.106,-0.069。同時,商業醫療保險對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負債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057,0.008,0.009。也就是說,社會醫療保險更有可能降低低收入群體的家庭債務,而商業醫療保險更有可能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家庭債務。這一結論從側面印證了社會醫療保險有助于緩解低收入家庭的債務陷阱,緩解社會收入不平等;而商業醫療保險可能會擴大低收入家庭的債務危機,擴大社會收入差距。
4.內生性問題。是否購買醫療保險很大程度受個人收入水平影響,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購買醫療保險的可能性也越高。也就是說,收入水平與醫療保險之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而這種反向因果關系可能導致估計結果偏誤。有鑒于此,本文借鑒周欽等[27]的設定,選取居民的風險偏好作為醫療保險的工具變量,以克服OLS 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為了檢驗工具變量的合理性,本文用Anderson LM 統計值來檢驗工具變量是否存在識別不足,用Cragg-Donald Wald F 統計值檢驗是否存在弱工具變量,用Sargan 統計值檢驗工具變量是否存在過度識別。從Anderson LM 統計值、Cragg-Donald Wald F統計值可以看出,選取居民風險偏好作為醫療保險的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識別不足和過度識別問題。同時,與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相比,社會醫療保險對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邊際影響更大;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體相比,商業醫療保險對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邊際影響更大。由此可知,在克服OLS模型中的內生性問題后,估計結果仍然表明社會醫療保險更有益于低收入群體,而商業醫療保險更有益于高收入群體。
(四)拓展性討論
1.醫療保險與醫療服務可及性。醫療服務能否有效消除不同收入群體健康不平等成為矯正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手段[24]。因此,本文借鑒李永友等[24]的設定,用“是否住院”作為醫療服務利用率的代理變量,進一步分析了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醫療服務利用的差異影響,以檢驗醫療保險是否可以通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服務利用程度從而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醫療保險對不同收入群體醫療服務可及性的影響
從表5 可以看出:社會醫療保險對低收入醫療服務利用率的系數估計值為0.040,對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醫療服務利用率的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020 和0.019,均在1%水平下顯著。也就是說,社會醫療保險對低收入群體醫療服務利用率分別是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的2.0 倍和2.1 倍。因此,就醫療資源利用程度而言,社會醫療保險顯著提高了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服務可及性,有助于改善由健康不平等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此外,商業醫療保險對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群體醫療服務利用率的系數估計值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對高收入群體醫療服務利用程度的系數估計值顯著為正。也就是說,從醫療服務利用率來看,商業醫療保險仍然體現出更加有利于高收入群體的“益富”效應。
2.城鄉差異。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另一個表現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因而考慮醫療保險制度在城鄉地區實施效果的差異十分必要。表6 報告了醫療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城鄉差異。

表6 醫療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城鄉差異
從表6 可以看出:在農村地區,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和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情形下的基尼系數為0.626 和0.596,而最終效果的基尼系數為0.595。也就是說,社會醫療保險使得農村地區的基尼系數降低了0.031,而商業醫療保險使農村地區基尼系數提高了0.001。在城鎮地區,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和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情形下的基尼系數為0.536 和0.500,同時最終效果的基尼系數為0.501,即社會醫療保險使得城鎮地區的基尼系數降低了0.035,商業醫療保險的實施則使得城鎮地區的基尼系數提高了0.001。從泰爾指數來看,農村地區最終效果的泰爾指數為0.771,與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情形下的泰爾指數一致;但在城鎮地區,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情形下的泰爾指數為0.541,而實施社會醫療保險情形下的泰爾指數為0.545。由此可見,社會醫療保險對城鎮地區收入分配的正向調節作用以及商業醫療保險對城鎮地區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作用均大于農村地區。
3.醫療保險分配效應的動態變化。為了進一步了解醫療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動態變化趨勢,本文選取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2019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分別測算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表7 報告了測算結果。

表7 醫療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動態變化
從表7 可以明顯看出:在2013 年,社會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分別使基尼系數提高了0.031 和0.044;使泰爾指數提高了0.056 和0.068。也就是說,在2013 年,不論是商業醫療保險,還是社會醫療保險均存在顯著的“益富”效應,即高收入群體在醫療保險制度中受益更多。到了2015 年,商業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仍然為負,使社會基尼系數提高了0.001;但社會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轉為正向,即未實施社會醫療保險情形下的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大于實施了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后的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由此表明,社會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在2015 年轉為正向,具有“親貧”性質,而商業醫療保險仍然表現出逆向調節的“益富”效應。在2017年,社會醫療保險的正向再分配效應開始擴大,基尼系數降低了0.029,遠大于2015 年的0.003;但商業醫療保險在2017 年仍然表現加劇收入不平等的“益富”效應。到了2019 年,社會醫療保險仍然有利于窮人,與“親貧”性質相符,使社會總體基尼系數降低了0.006。與之不同的是,2019 年實施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后的基尼系數與未實施商業醫療保險制度情形下的基尼系數一致。也就是說,商業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在2019 年或許并未導致社會差距的擴大,但其長期效果仍有待更新數據后進一步探討。
總的來說,社會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在2013年為負,2015 年轉為正向,到2017 年之后正向再分配效應進一步提升。而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在2013年、2015 年、2017 年均表現出逆向調節的“益富”效應,加劇了社會收入的不平等,而在2019 年則未表現出明顯的“益富”效應。可能的原因在于,自2013年以來,社會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報銷比例和保障范圍不斷擴大,其溢出效應逐步向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擴散,更多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開始享受到社會醫療保險的制度紅利。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低收入群體的醫療保險問題,醫療保險政策重點向低收入群體傾斜。例如,2015 年全面推開大病保險,同時保險比例提高至15%,個人負擔下降到30%以下。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 年和2016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2 年城鎮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和基金支出分別增長了39.55%和94.22%。同時,城鎮醫療保險人數的增加主要是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的增加。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不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覆蓋對象主要是城鎮未成年人和沒有工作的居民,也就是缺乏收入的群體。缺乏收入的城鎮居民大規模參與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有助于降低其就醫負擔,提高其可支配收入,進而起到調節不同收入群體收入差距的積極效果。商業醫療保險自始至終均表現出更加有利于高收入群體的“益富”效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購買商業醫療保險的群體本身就是高收入群體,中低收入群體由于并未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因而無法從商業醫療保險中受益。需要指出來的是,商業醫療保險的再分配效應盡管在2015 年和2017 年為負向,但與2013 年相比有所縮小,即商業醫療保險雖然始終存在逆向調節的“益富”效應,但這種逆向調節作用在2015 年和2017 年有所緩解。其中的原因在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居民健康意識的提高,購買商業醫療保險的群體由高收入群體逐步擴大至中等收入群體,由此中等收入群體開始享有商業醫療保險帶來的紅利,商業醫療保險的逆向調節作用也將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五、結論與建議
在穩步推進共同富裕戰略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7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測算了醫療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并檢驗了可能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發現:社會醫療保險實際上起到了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的正向再分配作用,使得社會整體基尼系數降低了大約5 個百分點。這一結論與既有的研究不同,有助于政府與社會各界正確認識我國社會醫療保險的真實作用。商業醫療保險則加劇了收入不平等,存在逆向調節的“益富”效應。影響機制在于:低收入群體在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中獲得的直接報銷和間接收入遠大于高收入群體,高收入群體在商業醫療保險中的受益程度遠高于低收入群體;社會醫療保險更有助于緩解低收入家庭的債務陷阱,商業醫療保險可能會擴大低收入家庭的債務危機。進一步研究發現:社會醫療保險更有可能提高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服務可及性,有助于改善由健康不平等引起的收入不平等,而商業醫療保險更有可能提升高收入群體的醫療服務可及性;社會醫療保險對城鎮地區收入分配的正向調節作用以及商業醫療保險對城鎮地區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作用均大于農村地區。此外,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在2013 年的再分配效應為負,到2015 年轉為正向,2017 年之后正向再分配效應進一步提升;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在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均表現出逆向調節的“益富”效應,加劇了社會收入不平等,在2019 年未表現出明顯的“益富”效應。
為了更好地發揮醫療保險制度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以促進共同富裕戰略的實現,結合本文的研究結論,有必要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持續加大社會醫療保險投入,減輕人民群眾醫療負擔,推動健康中國戰略的有效實施。盡管早期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存在逆向調節的“益富”效應,但本文的研究表明,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從2015 年開始呈現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的正向再分配作用。因此,為了有效降低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就醫負擔,推動健康中國戰略的有效實施,必須持續加大社會醫療保險的投入,進一步將社會醫療保險向低收入群體覆蓋。
其次,加大對中西部和農村地區醫療保險的支持力度,著力解決醫療保險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了地區醫療保險發展的不平衡和醫療衛生資源分布的不平衡,而醫保發展不平衡顯然制約了醫療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發揮。因此,必須加大對中西部地區醫療保險的支持力度,著力解決醫療保險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最后,完善商業醫療保險制度,豐富商業醫療保險類型。人口老齡化的快速推進加劇了醫保基金支付的負擔,醫保費用面臨缺口的壓力越來越大。而作為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重要補充,商業醫療保險可以有效彌補社會醫療保險的不足。考慮到當前的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可能擴大了收入差距,因而有必要豐富商業醫療保險類型,提供不同價位的商業保險種類,滿足不同收入層次居民的商業保險需求,為中等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購買商業醫療保險提供現實途徑。
注釋:
①限于篇幅,作者未在正文中報告穩健性檢驗結果,感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