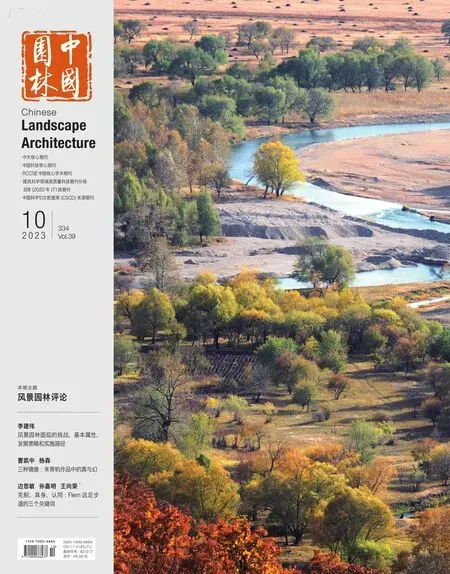克制、具身、認同:Flem遠足步道的三個關鍵詞
邊思敏 孫嘉明 王向榮
提及康策特(Jürg Conzett),我們往往會想到他享有盛譽的結構設計師身份,與此同時,與卒姆托長達7年的深度合作也是他名聲在外的一個原因。就其作品來說,在建筑方面,奧拓廣場大樓(Ottoplatz)和沃爾特學校(Volta School)充分體現出結構之于建筑形式的創造性作用;在橋梁方面,不論是枕木峽(Traversiner Tobel)的2座步行橋,還是Viamala峽谷中跨度40m的Suransuns橋,都體現了疊加于結構理性之上的、對空間體驗與現代性審美的關照。
Flem遠足步道并不是康策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本文認為,這個阿爾卑斯山腳下的步行系統具有一定的獨特性。概括來說,Flem遠足步道折射出3個關鍵詞——克制、具身(embodiment)和認同(identity)——在風景園林設計理論中,這是3個相當重要的概念。
克制,指向了人類力量介入自然環境時的基本觀念——是占有、破壞、改寫,還是共存、欣賞、轉譯?這個前置條件直接影響了規劃設計決策的制定。具身,強調人們在環境中的知覺體驗,是一個人在此地、此刻的切身感受,也是認知世界的直接方式。認同,是一種自我和群體的文化建構,亦是人們建立自身與世界之間關系的基礎。
克制、具身、認同,這三者的內在關系既非并列、也非重合,而是保持獨立又有所交叉。它們分別照應了設計的程度、體驗和更深遠的文化影響。在Flem遠足步道中,我們可以看到康策特對這3個關鍵詞的回應,而潛藏于這些回應背后的面向自然的觀念,則是觀察這個案例以外世界的一面鏡子。
1 Flem遠足步道的基本情況
步道位于瑞士東部格勞賓登州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個小鎮旁。小鎮的名字是弗利姆斯(Flims,羅曼什語Flem),這也是當地主要水系的名字,源自拉丁語“fluminae”,意為“許多溪流”。步道的全稱是“Trutg dil Flem”,羅曼什語中表示“沿弗利姆斯河的路徑”的意思。
州政府正式批建設后,在當地政府、民眾、承建商的共同努力下,Flem遠足步道于2012年夏末投入使用。它將此前分散在山間的幾段步道整合起來,向上連通至溪流的源頭,向下通往小鎮的北緣。
步道系統分為兩部分:連續的步行路線和7座步行橋。平面圖(圖1-1)中的紅線代表步行路線,藍線代表河流,這2條線時而貼近、時而稍遠,紅線橫跨藍線的位置則是沿步道設置的7座小橋①(圖1-1的7個黑色圓點)。它們形態各異,相互之間的距離也有疏有密。這些小橋如同長卷中的視覺焦點,位置的選擇和建造方式反映出畫卷展開過程中不同段落所具有的獨特地貌。

圖1 7座橋在步道中所處的位置(1-1由作者改繪自參考文獻[4];1-2中圖1為Christian Dettwiler攝,圖2為Weisse Arena AG攝,圖3為Oliver Schuh攝,圖4為Dagmar Surink攝,圖5為Christian Dettwiler攝,圖6為Christian Dettwiler攝,圖7為Oliver Schuh攝)Fig.1 Locations of the seven bridges along the trail
2 關鍵詞一:克制
2.1 技術作為幫助自然經驗呈現的工具
對于結構設計,康策特一直秉持適度的原則,他認為結構師對表現受力的執著可能更多地出于一種競爭心態——也就是通過突出結構來彰顯自身的技術高度[1]。但他同時意識到,這種動機本身已經偏離了對某個特定項目在特定情境下的關心,并可能進一步導致過激的決策反饋。
在2010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上,康策特作為瑞士的代表建筑師布置了主題為“景觀與結構”(Landscape and Structures)的展覽,以瑞士的不同路徑為線索分析了一系列人工建造物嵌入自然的案例;他還在《結構作為空間》(Structure as Space)中論述了對擋土墻的思考:“墻體的形式與輪廓——它平坦或立體,它(在自然環境中)從哪里開始、在哪里結束,這些問題與材質的選擇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2]”策展主題和自述都反映出康策特對技術與自然關系的看法,雖然最負盛名的頭銜是“橋梁工程師”,但他卻始終反對結構與技術的過度表達。依循康策特的思路,技術只是服務于如何更恰當地幫助自然經驗呈現的一種工具。
2.2 Flem遠足步道體系中的克制
2.2.1 基于行走節奏的克制
本文提及的“克制”,可以理解為一種設計中恰當的作為。但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恰當”?恰當具有一種居間性(in between)——不是純粹的不作為,或者盲目遵從最小干預原則,更不是以粗暴的方式糟蹋自然本底。“恰當”是基于特定的情境,以一種審時度勢的途徑介入景觀,同時,借助放置于自然中的人造物,達到聚焦或放大某些經驗感受的作用。也就是說,人為介入應當發揮解蔽(unconcealment)的作用,而這個過程中對“度”的把握則是最為關鍵的。
在7座步行橋中,有4座木制橋,其他3座為混凝土橋和石橋,它們在步道中呈現出ABAABAB的節奏(海拔由低到高的順序,A為木橋,B為非木材建構的橋)。從7座橋的設計形象中我們可以分辨出,4座木質小橋的“設計”成分是較少的。
為什么康策特沒有選擇把所有的橋都“好好設計”一下呢?或許這7座橋的材質選用與地貌特征之間的對應規律可以提供答案:3座非木制橋——混凝土橢圓橋(Oberste Brücke)、倒梯形窄身橋(Brücke Pilzfelsen)和石拱橋(Wasserfallbrücke)——均位于地貌險峻之處,周邊或是山谷深窄,或是地勢落差大,橋下的溪流也更加湍急;而4座木橋中,除了駐足橋(Verweilbrücke)的上游有一小段瀑布之外,其余3座所處的地勢都較為緩和。也就是說,基于行走于步道上節奏的整體性考量,康策特首先對哪里需要“發力”做出了判斷——通過木橋與非木橋穿插的節奏變換,提供時而舒緩、時而緊湊的行走體驗。
此外我們應當注意到,雖然駐足橋周邊地勢較為險峻,但康策特并沒有像處理其他幾個地勢險峻的小橋一樣使用混凝土或石材,而是仍然使用木材。除了跨度的考量外,筆者認為這個決策還與行走節奏的設想有關。在整體敘事中,駐足橋位于混凝土橢圓橋和倒梯形窄身橋之間,這兩者均為混凝土材質,形式上也更加人工化。由于駐足橋與這前后2座橋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如果也對它做過多設計,那么3座橋就無法形成高低起伏的敘事節奏。由此,駐足橋被當作一個變奏。作為結構設計師的克制、讓技術適時地消隱,這種精當的考量反而更加豐富了人們行走于阿爾卑斯山中的自然經驗。
2.2.2 基于現場判斷的克制
除了基于整體行走節奏的克制之外,這種審慎的觀念還體現在步行橋的具體設計中。
如果我們乘坐3段纜車登頂,再沿著路徑自上而下,循著水聲向下望去,就會看到一塊邊緣平滑的橢圓形板狀物“浮”在湍急的水流上,這就是混凝土橢圓橋。它的橋板一端嵌入地勢稍高的巖石,另一端則由同樣弧度的兩級臺階搭在下方的巖石上;橋身主體是一塊橢圓狀的預制混凝土,橫跨在山澗上方一個很窄的開口處(圖2-1)。

圖2-1 混凝土橢圓橋橫跨極為狹窄的巖石裂谷(Oliver Schuh攝)Fig.2-1 The elliptical concrete bridge "Oberste" crosses an extremely narrowrocky gorge
建成的混凝土橢圓橋和康策特的設計手稿(圖2-2)有明顯區別——手稿中的橋體形狀更加自然,扶手呈拱狀;而建成的橋體是規則的橢圓形混凝土板,扶手也被一并換成了僅安裝在一側的、由2根極細的金屬立柱承托的圓形實木扶手,立柱下端呈折線形,如同鹿的后腿一般優雅地站在橋面上。

圖2-2 康策特的手稿中,最初采用的是自然形態的石頭橋面[4]134Fig.2-2 Conzette's sketch of the original design featured a stone bridge deck in its natural form
康策特表示,這座橋的設想起初受到肖蒙山公園(Park des Buttes-Chaumont)的影響;而后他意識到對于他所面對的場地來說,在自然中建造“人工的自然”(artificial nature)是沒有必要的。他還提到,橢圓的形式隱喻著“Gletschermühlen”——冰川磨坊(圖2-3),這是由冰川表面或裂縫中流動的融水產生的冰中螺旋壁中空形狀,雖然由自然作用形成,卻呈現出驚人幾何性。此外,顯而易見,身體在新橋體上的運動是“平”的,那么相對應的,“平”的扶手會讓行走更加舒適②。

圖2-3 冰川磨坊(Sepp &Ursula攝)Fig.2-3 "Gletschermühlen" as known as moulin or glacial mill
康策特在郵件中對于筆者疑問的解答是頗具啟發性的——通常我們會認為,“克制”體現在當人工的、幾何的、鋼鐵的東西置入自然環境的時候;而康策特對這座小橋的設計調整則提示我們,在自然中置入“人造的偽自然”更值得警惕。看似自然的形式并非是真的自然,而看似人造的形式也不一定來自人工之手,重要的是,我們要誠實地看待形式、面對自然。
從結構角度來說,混凝土橢圓橋采用了極為簡潔的干砌法(dry-laid)——橋板和巖石之間沒有水泥黏合,2根欄桿立柱同時也作為連接構件,將橋板錨固在巖石上[3](圖3),確保積雪消融時小橋不會被雪水沖刷移位。

圖3 混凝土橢圓橋的縱剖面,欄桿立柱將橋板錨固在巖石上(引自Conzett Bronzini Gartmann AG)Fig.3 In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elliptical concrete bridge "Oberste",the railing posts anchored the bridge deck to the rock bed
除了混凝土橢圓橋,這種結構設計上的克制還體現在石拱橋中。這座橋也經歷了設計方案的調整:在已完成初稿設計(圖4-1)之后的地質勘查中,康策特發現一側的山體存在裂縫,為了避開這個位置,橋的跨度必須由11m加大到18m。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通過什么方式應對跨度增加帶來的結構問題?

圖4-1 石拱橋初版手稿[4]131Fig.4-1 The original design of the stone arch bridge "Wasserfallbrücke"
康策特本能地想到2種解決方案:是否在拱頂增加冠鉸?是否應該加大拱的弧度[4]141?顯然,在橋的頂部增加鉸點會破壞視覺上的連續性;而加大拱的弧度也會導致橋身呈現一種“凌駕”在水流之上的征服感③。在否決了這2種看起來更便捷的解決方案后,康策特選擇保持原設計中淺拱的形態,并通過巧妙的結構設計——加入起到拉結作用的鋼帶——來保證拱橋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系。
這種結構調和了大跨度所帶來的力學要求和橋體形態所需的輕盈感之間的矛盾。2條鋼帶“懸浮”在石板橋身之上,鋼帶的上方連接著扶手立柱,下方則與橋身留有一條縫隙,中間夾著與鋼帶寬度一致的若干個小圓鋼柱——它們的關系看上去就像枕木與鐵軌一樣。這些鋼柱既傳遞了鋼帶對石橋施加的力,在鋼帶與橋面之間卡出的空隙也一定程度吸收了摩擦變形。另外,由于鋼帶提供了拉力,靠近拱腳的石材就不需要像最初設計的那樣越來越厚,因而橋身看起來更加輕盈(圖4-2)。
2.3 克制從何而來
相較于對技術的炫耀,康策特顯然更關注小橋與自然的關系——人們沿途將看到怎樣的風景,穿越小橋時會有怎樣的體驗,這些體驗又如何被安置在自然之中。每座橋自身的材料、形式、結構與細部,都是為了更好地呈現行走經驗,而不是凸顯技術本身。
這種設計決策上的克制與康策特早先的教育和從業經歷有很大關聯。莫斯塔法維(Mohsen Mostafavi)認為,地圖學家伊姆霍夫(Eduard Imhof)在蘇黎世高工的繪圖教學對康策特影響重大——伊姆霍夫善于同時處理地理圖像的宏大尺度與地貌細致入微的感性表達,這種對待整體與局部、客觀與感性的調和平衡,成為影響康策特的重要原因(圖5)。“他對伊姆霍夫地圖上想象力的關注,證明了他作為工程師的能力并不局限在對某個功能人造物的技術實現上”[5]。一次采訪中康策特表示所謂結構的倫理和非倫理“最終是讓理性和感性結合起來”[6],同樣印證了他對整體與局部、理性與感性之間調和平衡的思考。

圖5 伊姆霍夫繪制的地圖(引自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Fig.5 A map drawn by Imhof
此外,與卒姆托長達7年的合作也深刻影響著康策特的工作方式。進入卒姆托事務所的動因是康策特認為“結構師的教育里缺少了某些東西”,“某些東西”,依照康策特的說法,指的是結構與項目整體、與住區和景觀之間的關系[7]。就工作習慣而言,他總是很快地進入到手工模型的制作中,先充分認識用于建造的整體環境,并與卒姆托進行大量討論來確定一種基于建筑師視角的空間策略,而對于結構本身則只有粗略的計算,并不像其他結構設計師一樣在前期就進入計算模型中。顯而易見,這種空間先行、結構后行的工作流程,決定了康策特在Flem遠足步道中優先考慮小橋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其后才是如何通過技術手段實現設想。
再從康策特的教育和工作經驗中,回到20世紀的設計思想史——克制是一種與倫理價值密切相關的品質。在20世紀初,克制是清教徒的倫理外顯,與勤奮和效率有密切關聯。克制也讓建筑設計一度走入極端的狀態,路斯那句著名的、在一定程度上被過度解讀的“裝飾即罪惡”就體現了當時的某種極端化思潮。然而,現代主義的形式語言在20世紀下半葉遭到劇烈批判,因為那些看起來克制的外觀具有抹殺場所精神的危險。在此背景下,康策特的克制是一種超越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之間對立關系的觀念:一方面,他以新的自然觀來實施克制性設計;另一方面,又用現象學來調和這種克制——這個現象學術語便可以從具身性(embodiment)的角度切入。
3 關鍵詞二:具身
3.1 從具身經驗出發的2處設計調整
在開始設計之前,康策特和一位當地居民一起進行過若干次實地踏勘,步道整體的選線以及7座小橋的具體位置,都是在這個階段逐步確定的[4]129。隨著踏勘過程的深入,康策特調整了石拱橋和倒梯形窄身橋的設計策略。遠距離想象和預判與具身經驗之間的差異,恰恰體現了康策特是如何基于具體的自然環境和身體感知迭代設計策略的。迭代的過程,也是逐漸接近他心目中設想的、希望每一位步行者親身體驗的自然之美的過程。
3.1.1 石拱橋上的風景
位于Foppa瀑布前的石拱橋是7座小橋中唯一使用天然石材的。康策特在介紹這座橋的小文——《瀑布橋:水霧籠罩》(Waterfall bridge“Mist-shrouded bridge”)開篇配有一張插圖(圖6)——這是一幅18世紀的法國銅版畫④,描繪了阿爾卑斯地區紹勒嫩山谷(Sch?llenenschlucht Valley)瀑布,以及橫跨于瀑布前著名的連通著圣哥達山道(Gotthard Pass)的“魔鬼橋”。

圖6 《魔鬼橋》[4]137Fig.6 Copperplate etching "Devil's Bridge"
在最初的設計中,康策特所描繪的石拱橋結構以及橋體與瀑布之間的關系幾乎與銅版畫一模一樣。然而在數次場地踏勘之后,他發覺最初的設計中橋與瀑布的距離過于接近了,這會帶來2個問題[4]137:一是施工難度大大增加,二是即便在中等水量的時節,人們走在橋上也會遭到大量的水霧噴濺,這不僅影響了行走體驗,也會讓小橋的形象淹沒在水霧之中。
于是,康策特決定適當拉開橋體與瀑布的距離,而這種物理位置的變化反過來豐富了瀑布、小橋和步行者之間的關系。在調整后的設計中,當人們從下游遠望時,瀑布飛流直下,前方的小橋微微拱起,淺弧線以一種抵抗重力的姿態優雅地橫跨兩岸,瀑布和小橋共同構成的畫面仿佛是《魔鬼橋》的縮影;在走近小橋的過程中,由于橋身與瀑布保持了一定距離,不會完全被水汽吞沒,小橋自身的形象也成為獨立于瀑布背景之外的觀賞對象;當人們行至橋上時,又扮演了觀眾與演員的雙重角色——他們既是這一幕戲劇的觀眾,也以身臨其中的方式參與了演出,成為此時在更遠處眺望石拱橋的觀眾眼中的“風景”(圖7)。遠、中、近的三重經驗共同構建了這個區域的自然形象。

圖7 石拱橋Wasserfallbrücke(Gaudenz Danuser攝)Fig.7 The stone arch bridge "Wasserfallbrücke"
3.1.2 倒梯形窄身橋
從遠處看倒梯形窄身橋時,會覺得像是一個趴伏在地面和水面上的實體(圖8-1)。整座橋由順河道兩岸地勢向下的臺階和橫跨水面的橋體共同構成,兩側的欄桿排布得非常細密。

圖8-1 倒梯形窄身橋Brücke Pilzfelsen(Dagmar Surink攝)Fig.8-1 The inverted trapezoidal slender bridge "Pilzfelsen"
起初的設計中欄桿只出現在橫跨水面的區域(圖8-2),而建成的橋體延長了欄桿的覆蓋范圍,連同兩側狹長的臺階一同被包裹成為一個整體空間。這個更改是出于什么考慮呢?康策特解釋說,一是安全性——在實地勘測過程中,他意識到引導踏步相當陡峭,因此設置欄桿;二是體驗性——他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僅出于滿足功能的考量,橋體的扶手是相當短的,但是延長的扶手更有助于橋體與環境的融合⑤,深入河道兩側綠地中的扶手就像邀請人們步入小橋的雙臂,將客人攬入懷中。

圖8-2 倒梯形窄身橋設計手稿,欄桿只出現在橫跨水面的區域[4]133Fig.8-2 In the original design of the inverted trapezoidal slender bridge "Pilzfelsen",handrails were only present on the portion spanning the water
當人們走近時,會發現橋身其實非常窄——康策特一反常規將扶手置于橋面上的做法,讓L形的扁鋼立柱通過一條鋼帶與橋板的側面相接,因此,橋板和豎直立柱間就留出了一段不能走上去的“空白”。這種方式把橋面寬度壓到了50cm[4]133,走在橋上的人就像被“扔”到了弗利姆斯河上,不得不在懸空的獨木橋上心驚膽戰地欣賞腳下湍急的山澗。鋼片扶手極薄的厚度還實現了最大程度的視野通透,與遠觀時密集的體量感形成巨大反差,來自未被馴化的自然的危險性和壓迫感從欄桿的空隙中蔓延而來(圖8-3)。

圖8-3 從窄身橋向下俯瞰(Oliver Schuh攝)Fig.8-3 Looking down from the inverted trapezoidal slender bridge "Pilzfelsen"
3.2 具身經驗的意義
在石拱橋和倒梯形窄身橋的現象學觀察中,我們得以了解只有通過身體在場才能獲得的空間經驗。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哲學觀把人的身體作為世界體驗的中心,認為處于世界中的身體使得可見的景象富有生命力,將生活吸入體內并保持沉于內心的感受,從而形成系統[8]。這種現實世界中的具身經驗是我們應當捍衛的,因為我們生存的世界由肉身、現象和真實的事物構成,我們用整個身體來觀看、觸摸、聆聽和度量[9],唯有通過肉身對事物進行感知,外部世界才能被認識和內化,從而形成文化性的理解——具身經驗是將世界納入自我的通道。
之于設計師,不論是結構設計師、建筑師還是風景園林師,其所建造的事物本身就體現著對世界的理解。他們將這種理解轉化為一座橋、一棟房子或者一座花園,成為將大眾引入設計者所觀察的世界一隅的通道——橋、房子和花園成為媒介,邀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以身體參與的方式走進設計者的話語之中。同時,這種觀念的傳遞絕非單一和單向的,它允許人們在經驗過程中形成基于自身的理解,各式各樣的理解又反過來構建了更具多樣性的世界。
4 關鍵詞三:認同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們把目光移到阿爾卑斯山區域。自古以來,各種群體或民族都把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作為靈感和集體認同的來源[10]。作為多民族、多語言國家,瑞士并不完美符合狹義上民族國家的標準,卻是一個不同民族和平共處的防御共同體。雖然阿爾卑斯山地區僅有全國人口總數的11%,但由于瑞士60%左右的國土面積被這片山脈覆蓋,綿延的山脈在建構當地人身份認同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探討的案例也并不只是一條步道及串聯的7座小橋,而是指向了更大范疇中對自我、群體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認識和建構。
4.1 農耕、游牧與壯游:基于阿爾卑斯山的身份認同建構史
早在青銅器時代(約公元前2200—前700年),阿爾卑斯山民就通過農牧業生產進行著土地改造[11],主要活動范圍集中于山谷森林的邊緣地帶,多在一些較為平坦的區域局部。古老的山民以耕作為主要方式,建立了身體與山腳下土地的基本聯系。
中世紀,隨著區域人口的不斷增加,山谷地區的畜牧業開始專門化,并逐漸替代農耕成為主要生產方式——每天與牛羊一同游走于高山之間,成為人們獲得生活所需物資的主要途徑。
17世紀下半葉,壯游(Grand Tour)成為歐洲上層社會青年男子的旅行傳統。起初壯游的目的地是意大利,瑞士只是途中的必經之路。然而一些旅行者在途經阿爾卑斯山時被它的巍峨壯美所震撼,瑞士也就漸漸成了壯游的目的地之一。英國文學家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曾在游歷阿爾卑斯山之后寫道,它“讓人們充滿了一種令人愉快的恐懼”。這段描述恰恰體現了阿爾卑斯山成為新目的地的原因——它滿足了人們對“崇高”(sublime)的審美渴望——一種面對自然界的恢宏、驚奇、甚至可怖的景象時產生的莊重與敬畏的心理感受,《云海上的旅人》(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可以算是這種浪漫主義美學的集中體現。
總體而言,此時人們建立身體與阿爾卑斯山之間關聯的動因已然從生理的(滿足基本生存所需)發展到心理的(滿足對“崇高”的審美)。其后,隨著蒸汽動力交通的普及,壯游拓展至新興中產階級和貴族女性群體中,登山運動(mountaineering)⑥在19世紀中期達到黃金時代。
時至今日,山間徒步還帶有回歸和凈化自身[12]的意思。奧利弗·季默(Oliver Zimmer)認為,在社會文化加速變化的大背景下,厭倦了所謂現代文明喧囂的人們將目光轉向阿爾卑斯山,因為這里是以簡樸、恒心和自由為名的山民棲息地。萊昂哈特·拉加茨(Leonhard Ragaz)在1917年出版的頗具影響力的小冊子《新瑞士》(the New Switzerland)中也這樣寫道:“山脈以其力量和威嚴、寧靜和純潔屬于我們……山脈和農民都代表著純凈。”
4.2 Flem遠足步道與認同建構
從農耕,到游牧,再到壯游、回歸和凈化,阿爾卑斯山民及更大范圍的居住者們在歷史進程的不同階段以不同方式建立著自身與雪山的關聯。這種基于身體勞作與行走的、關于阿爾卑斯山的集體記憶,正如社會學家卡內蒂(Elias Canetti)所認為的,逐漸融入民族認同,最終成為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13]。這個過程也被德國的森林、英國的大海印證著,山、林、海,都在一種“自然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nature)[5]過程中充當著聯系景觀與民族性的有力紐帶。
如今,遠足步道(trail)已然是政府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項重要議題,本文關注的Trutg dil Flem在瑞士全境的徒步路線系統中編號為764,足以證明步道網之龐大。這個綿延于阿爾卑斯山脈的行走的網絡,一方面體現了當地山民自古至今對于建立自身與雪山之間關聯的興趣;另一方面,人們又在日常的遠足活動中,進一步被反向建構著基于阿爾卑斯山的民族自然觀。
7座小橋的區域更像是徒步旅程中一個裝滿與自然之間的奇遇經歷的盒子,它在短時間內提供了體驗山地、叢林、溪流和瀑布的關于視覺、聽覺、觸覺和嗅覺的多重體驗,把身體的經歷濃縮在一段時空之中,建構了一種劇場性的經驗[14]。康策特通過這7座小橋的整體編排,讓步行者以一種身心沉浸的方式完成自我和自然之間的儀式。
5 結語
Flem遠足步道的3個關鍵詞反映了風景園林設計的生命流程。克制,既是觀念,也是方法——它源于設計者的綜合判斷,這里的“綜合”包括了設計者自身的成長與教育經歷、經驗與技術手段、現場的實際情況等,種種因素在設計者腦中碰撞、博弈,最后呈現為恰當的、克制的介入策略;具身,同時是動因和結果——在設計過程中,需要以具身經驗作為思考的目標和準繩,同時,具身也是設計所呈現的空間帶給人的體驗;認同,意味著設計在更長遠的時間中、伴隨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而沉積的文化影響,對于一些設計者和使用者來說,或許這個過程是無意識的,但這種長遠的影響往往發揮著重要作用。
實際上,不論對于Flem遠足步道還是其他風景園林項目來說,一位設計師大抵都需要經歷這3個階段。而如何以具有創造性的姿態介入到自然之中,Flem遠足步道給出了一種參照。
注釋:
① 為了將7座小橋以更直觀的形象呈現給讀者,筆者對它們進行了形象化的翻譯處理,并沒有與德文的橋體名稱形成對照的直譯關系。
② 康策特郵件原文:“The artificial stones in Oberste Brücke were a little bit influenced by sites like the park Buttes Chaumont in Paris.But later on I thought that in Flims we do not need to construct an artificial nature.So I changed to a more geometrical form (the ellipse).This can also be read as an free allusion to the adjacent‘Gletschermühlen’ (carvings in the rocks by stones rotating in water vortices under the glaciers) which show an astonishing geometric precision.By contrast,the handrail is straight,as you move more or less straight.”
③ 拱結構中,拱高相對于跨度的比例(即矢跨比)越大,側推力就相對越小。所以理論上隨著跨度的增加,相應地提高拱頂高度是更穩妥的做法。但如果提高拱頂、增加弧度,則會影響拱與周邊環境的關系。
④ 由法國畫家夏特萊(Claude Louis Chatelet)作畫、雕刻師馬斯奇勒(Louis Joseph Masquelier)雕刻,最初發表于《瑞士風景與科學圖集》(The Scenery and Science of Switzerland illustrated),1780—1786年。
⑤ 康策特郵件原文:“I think in many cases bridge railings are too short,long railings integrate a bridge better into their surroundings.”
⑥ 也稱阿爾卑斯登山運動(Alpinism)。